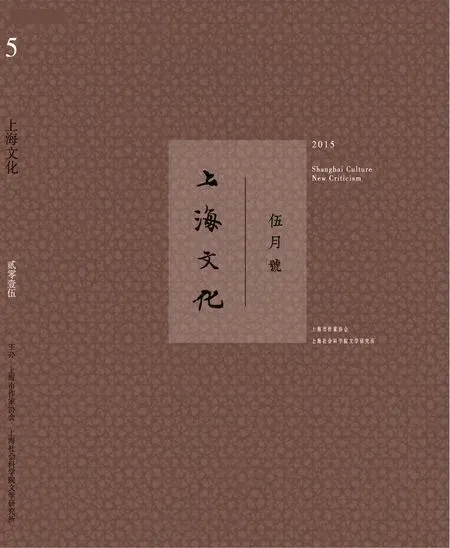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80后”写作与中国梦
黄平
“80后”写作与中国梦
黄平
将自己的批评文集命名为《“80后”写作与中国梦》,很可能迎来嘲笑,以为攀附时议,要借“中国梦”的时髦大卖几本。幸好有几篇小文章可以证明,在发表于2010年夏的一篇谈《蜗居》的文章中,我开始讨论中国梦的危机。那个时候我刚来上海工作,直面锋利的房价,感到压力重重。《蜗居》这部小说文学性很差,但表达出一部分青年的心情。这种心情,流荡在大城市里的青年,大概都会有一点体验吧。作为中国当下问题焦点的房价,并不仅仅是由于昂贵,而是代表着众所周知的结构性的力量,贬低着工作与生活的价值,也贬损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不过这些老话,这几年自己渐渐不讲了,不完全是因为有了房子,而是在这个时代,谈论生存的意义,总会有一种古怪的羞怯。
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研究者,总要应付各种各样生活的问题,谈论起文学来,缺乏耐心去纯粹。在2011年初写的一篇讨论韩寒与郭敬明的文章里,我以为“80后”写作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这个想法在和杨庆祥、金理两位学友的对话中,又重申了一下,这组三人谈曾在《上海文学》当年的第六期、第七期连载。后来读到很多恪守“纯文学”尺度的“80后”作家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棒,在文学造诣上远远超过韩寒与郭敬明。但是影响不大,也是不必讳言的。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有种种问题,但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到甚至于争夺“中国梦”的叙述,这是他们作品的活力所在。我在当时对“中国梦”抱有憧憬,觉得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研究者,哪怕是为自己的境遇说话,也要介入到相关的阐述。故而,通过对于韩寒、郭敬明的讨论,对于相关的青年文学与文化的讨论,比较用心用力。几年下来,留下来或长或短的一些文字,大半结集在这本书里,算是一种纪念。
这个书名当然也是一种掩饰,我恐怕关心的是我与中国梦,借着流行的这些文本,讲着自己的心思
在2010年、2011年大谈“中国梦”的时候,我无法预见到今天这个概念如此火热。这自然是好事,那么多专家学人的高论,远远比自己的看法高明。有些麻烦的,倒是这本文集要出版了,用不用这个名字呢。想来想去,还是坚持。没有什么别的词,能够贯穿这本小书中杂七杂八的论述,一会说到郭敬明,一会谈到《致青春》,一会又扯到春晚,除了“80后”写作与中国梦,别的都不大合适吧。
这个书名当然也是一种掩饰,我恐怕关心的是我与中国梦,借着流行的这些文本,讲着自己的心思。和每一代人相似,在这样的年纪,可能总难逃一点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蛮重要。但不同的是,“80后”这一代,大概没有气魄给出什么终极的答案了。
按照约定的体例,批评文集的后记要写到七千到一万的篇幅,详细讲讲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从故乡小城走到大上海,娶妻,购房,顺利地成为中文系第一个“80后”副教授,这几年的小文章,又荣幸入选了“火凤凰文丛”,这些事情想起来,总会有几分得意吧。然而,现在坐在新房子的书斋里,窗外秋色如洗,自己却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话来说。我还没有愚蠢到要用流行的成功学来比照自己的生活,但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价值观来支撑我的讲述。最近一两年沉迷于关于“反讽”的论述,自己的心境,很接近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的分析,“我称这一类人为‘反讽主义者’……由于始终都意识到他们自我描绘所使用的词语是可以改变的,也始终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词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
我下面还是要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我的“中国梦”之路。毕竟,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故事一样,要真实地讲述什么,就要首先从“我”开始;尽管这种沉溺在“我”的内部的故事,往往走向更大的不真实。
我出生在辽宁东部一座时间仿佛静止般了的小城桓仁,据说是唐朝渤海国所属的桓州,更远古的,还曾经是高句丽的王城,2004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类历史的沿革我到今天也搞不清楚,除了多一个景点招待远方的朋友,和生活也没有什么干系。我出生的岁月,桓仁不过是隶属于以钢铁产量著称的本溪下面一座小小的县城。风景倒是极好的,全境十分之一都是水域,浑江绕城流过,在高句丽王城所在的五女山脚下,围成一片宁静的大湖。每年十月中下旬,这偏僻的小城就进入冬季,直到第二年的三月,大雪弥漫,时常有一尺厚。我记得小时候吃一种冻梨,就是把梨放在水盆里,在外放一夜拿回家,敲下厚厚的冰层取出来,吃那份极冷的甜。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天寒地冻的景象有些骇人,我现在长年客居江南,倒真是有些怀念。
就像被暴风雪所隔断,家乡的一切都太闭塞了。在我成长的年月,没有卫星电视,没有电脑与网络,甚至没有报纸与杂志,在邮局下设的报刊亭唯一能买到的,就是《读者》、《家庭》、《故事会》之类的畅销杂志,或者借当时中国足球职业化浪潮热起来的足球报。我一位初中同学的爷爷走街串巷卖《辽宁广播电视报》,知道我喜欢读报纸,总会给我留一份。电视报副刊上的那类散文,我还煞有介事地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后来小城也有书店了,90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慢慢放开,农林牧渔之外,也可以买到名著之类。我的一个爱好就是下午放学后骑着自行车跑几家小书店,看看有什么值得买的新书。现在的孩子想象不到,书在90年代也可以是匮乏的。
小城苍白的文化环境与贫乏的基础教育,无法满足我莫可名状的求知欲。我尊重我的教师们,但坦率地说,这种小城的教育,真是太差了。当时浑浑噩噩,也不觉得,现在醒悟过来了,难免会不甘心,尽管这份不甘心里,带有一份残忍的自私。对于一个努力向上走的青年——尽管这可能不过是“现代”的幻觉——人与其环境是脱离的,这大概是一个永恒的“高加林命题”。当时未必察觉,但是在潜意识层面很清楚了,我所身处的环境,是一种有待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思维框架里,原子化的个人也悄然诞生了。
算是转折点,初三中考结束的暑假,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图书馆。那应该是1996年的夏天。由于国企改制,东北整体的颓势很明显,县图书馆读者寥寥,新书也没有几本。但是馆藏的“经典名著”之类,对于一个中学生足够了。我借的第一本中国名著是《呐喊》,借的第一本西方名著是《基督山伯爵》。后来那个暑假从高中同学那里借到了《简爱》,这大概是后知后觉的我严肃阅读的开始。在高中之前,我主要阅读的都是金庸、古龙、梁羽生之类武侠小说,只余一人转身的租书店里也只有这些。
作为一个县城长大的文学青年,我向一套文学丛书致敬: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名著普及本(全译本)”。小三十二开,小号字,简单的装帧,便宜的价格。这套丛书从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大致以19世纪欧美俄苏的经典为主,封底的目录成为我当时的购书指南,一本本的凑齐。由此开始,家里书架上的名著渐渐多起来,《雾都孤儿》、《双城记》、《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前夜/父与子》、《茶花女》、《嘉莉妹妹》、《悲惨世界》、《在人间》……此外,借助图书馆,我开始一本本地借阅《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复活》、《大卫·科波菲尔》、《高老头》、《俊友》、《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作品,以及契诃夫、欧·亨利、马克·吐温、屠格涅夫等世界经典中短篇小说选本。慢慢地,像发生在所有文学青年生命中的故事一样,我遭遇了自己最投缘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从《远大前程》开始,我几乎读完了所有能找到的狄更斯作品。另一位热爱的作家是鲁迅,我在中学阶段差不多读完了鲁迅和狄更斯的全集。对于鲁迅先生,我尤爱杂文与《故事新编》。现在自己醉心于反讽,其种子,中学的时候就萌发了。
这种自我教育比听课记笔记的效果好得多。大学就是围绕经典的研习,而不是现在普遍的高中的延续
县城的时间,总是慢半拍的,我的书单里,几乎没有20世纪的经典,比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等等,唯一读过的是卡夫卡《变形记》,但没什么感觉。这还是19世纪的眼光,到今天也没有补上这一课。读中国的作品也很保守,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等;当代则是“茅盾文学奖”系列中最流行的,比如《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这份书单自然大有问题,其局限也不言自明。不过,如果重新选择一遍,我还是愿意在十六七岁这个年龄,和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普希金相遇,和伟大的19世纪文学相遇。我喜欢那种开阔的历史场景与醇厚的人性气质,一直不大喜欢20世纪的破碎与阴郁。
我可以奢侈地大把时间阅读,也是依赖自己成绩很好。在县城的水平线上,我是很优秀的学生,从高一开始我就一直是年级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很大,大概超出三十分以上,不存在竞争的压力。1999年,和预想中一样,我以文科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但反讽的是,哪怕是第一名,由于整体教育水准很差,我也考不到北大清华之类。考上了东北最好的大学,但是还不够中文系的录取成绩。糟糕的是,当年我只报考了中文系,志愿单子上,我填写的是“不服从分配”。本来有落榜的危险,但吉大招生办一位不知道姓名的老师,觉得我成绩尚可,主动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调剂到该校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我只有愿意,现在回忆起来,在社会学的四年,是极美好的一段经历,但在当年满心灰暗。高考后的暑假,去图书馆借的不再是《荒凉山庄》之类了,我借到了一本《社会学是什么》,美国一个学者写的,当时完全不知所云。
来到吉大社会学专业后,大学四年,我几乎没上过什么课。当时有一句事后成真的戏言:硕士换专业,博士换学校。曾经有学界的朋友和我交流过,说我的研究受本科社会学训练的痕迹很重,我只能啼笑皆非。这位朋友的看法不能说错,但直到我读到博士了,才受导师程光炜教授的指导,阅读很多文学社会学的东西。本科那几年,我基本上逃掉了所有的课,或者泡在图书馆里继续读读文学,或者去操场上踢踢球,去自己当社长的“智搏辩论社”搞搞活动。母校的气氛,半是自由,半是东北式的随随便便。每年新学期伊始,我从各科系所在的行政楼一楼溜达到顶楼,自己抄一份课表,完全凭兴趣读书。我自己未必是好例子,但我到现在也觉得,这种自我教育比听课记笔记的效果好得多。大学就是围绕经典的研习,而不是现在普遍的高中的延续。
大学之后,阅读更为开阔,也有很多美好的阅读体验,比如一口气读完《1984》的震撼,比如一本又一本、一遍又一遍读王小波的美妙。但再也找不回高中岁月的感觉了。这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我不想把原因完全推给“体制”,我觉得还是自己定力不够,心思不像中学时候那么干净,读书渐渐混杂进求名求利的念头了。哪本名著“有用”,哪本名著“暂时无用”,只要这样的念头一发生,那种纯粹的阅读之乐就去而难返了。
本科四年,盲人瞎马,没有专业的指点,读书基本不得法,靠一点可怜的天赋连猜带蒙。而且,那几年(1999-2003)网络开始普及,占用大把时间的电脑游戏之外,BBS之类网络论坛大量开花,就像今天的微博,上面都是分泌过于旺盛的正义豪情。那几年深受其影响,偶尔也装模做样地说些傻话,顾盼自雄,俨然以笔为刀的文豪。现在醒悟了,那种文体文风,仅供满足自己的意淫,为无聊的生活增添一点虚幻的光彩。
在专业的意义上渐渐入门,还得在2003年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我在当年考入了本校的中文系,自己定的目标,到此实现一半。开始读研究生时,很不巧,当时的老师调到别的学校,我基本上是自由自在地读了三年。说起来让人难堪,我在硕士第二年,才开始接触到“细读”,慢慢开始写一些文学批评的文章了。之前习惯的都是动辄百年的长篇大论,洋洋洒洒,空洞浮泛,其实不知文学研究为何物。
稍稍入门一点,就以自己最热爱的作家王小波为例,以“超越二元对立”为主题(现在想来其实就是反讽叙事),写一些文本细读类的文章。既是练笔,也构成了后来的硕士论文。当时一边读书写作,一边也开始策划前程。想过继续在本校读博士,但是又觉得在吉大的时间太久了,一方面依恋母校,一方面也已经感到沉闷。作为一个文学硕士,学院之外的出路往往是去媒体,当时联系过新华社吉林分社去实习,已经见过了相关领导;还考虑过到出版社工作,曾经联系过当时很令人瞩目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但就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件充满偶然但又是决定性的大事——
那是2005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去逛学校门口的学人书店,无意中买了一本当年1月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贺桂梅、李宪瑜、姜涛等学者著。随手翻翻,来不及细读,因为要赶去听一个讲座,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的讲座。程老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家,当年来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吉大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往往只有在每年博士答辩的时段,会听到类似名家的演讲。记得当时是借用学校东荣大厦二楼考古系的会议室,乌压压一屋子人,我坐在角落里,托同学留了一个位置。那是第一次见程老师,老师的讲座题目,和他当时的研究方向有关,大致是借助佛克马、蚁布思的理论,讨论1980年代文学经典生成背后各种力量的博弈。讲座结束,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一个环节,请在座的学生提问。我当时随手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128页,这是姜涛撰写的第十章,讨论“经典的颠覆与重置”,其中有一段话:“在谈及中国现代经典问题时,佛克马、蚁布思就指出有关‘经典’问题的讨论,往往与1919、1946、1966、1978这些特殊的年份有关”。我现炒现卖,举手发言,借助这句论述,仿佛自己熟读佛克马的样子,一口气说出这些年份,胡乱问了一个文学经典历史化的问题。程老师当时表情很是惊讶,在回答我问题前,特谓转向讲座主持人刘中树教授表示,听说过吉大的同学素质很高,但没想到对经典熟悉到如此程度。讲座结束,散场时我看到前排的同学在问程老师的电邮,我拍拍那位同学,借本子抄了下来。当时也不带什么功利心,仿佛一定要和名教授结交,吉大见到名人不易,我的本子上留下过很多名家的联系方式,学术追星族的心理吧。
不过,程老师这个电邮我是用到了,回宿舍后大概觉得这位名教授和蔼可亲,没什么北京上海来的架子,我冒失地把新写的王小波批评发了过去,好像有两三万字,又臭又长。没几日程老师居然回信了,表示写得不错等等。我不惮冒昧,又去信和程老师交流。几轮通信下来,大概到2005年的6月了吧,程老师突然问我,将来怎么打算,是否愿意去北京跟他读博士?这封邮件一下子划开了眼前的迷雾,当时我对着电脑久久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大相信这珍贵的邀请是真的——我写这篇后记时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刻意建构什么戏剧性的情节,不过现在回想起这个细节,内心还是有些感慨。这对于后来的我,确实是人生的转折时刻。
通过他一系列精彩的细读与范导,我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以细读文本为基础,建构历史性的形式分析,由此真正开始文学批评
下面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人生的道路变得明晰:我在2005年的9月去了北京,去人大旁听程老师的课(后来我知道那是程老师主持“重返八十年代”的开始),在课堂上认识了当时是程老师硕士的杨庆祥等朋友;同时参加人大一个考博英语辅导班,自己英语不好,担心考试不及格。当时住在清华研究生公寓五舍,本科好友、在清华传播学院读硕士的张晓岩寝室里空出一张床,正好安妥我这个外省青年。从清华到人大,一辆二手自行车,迎着北京秋天的晨雾,周而复返。初到北京,也兴奋地去北大蹭课,旁听戴锦华教授讲电影——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一个女孩子当时在北大学习英语准备留学,也去旁听戴老师的课,我们互相不认识,直到六年后她从悉尼大学回到华东师大读博士时,我们才发现曾经是同学。北京这座城市,带着一种酝酿奇迹的气氛,渐渐向我敞开了。
2006年夏天,我迎来了人生新的阶段,告别母校吉大,在当年的9月7日赴中国人民大学报到。拖着行李从北京站出来,站在天桥上喘一口气,眺望车水马龙的北京,就像陈楚生唱的一样,“那是从来没见过的霓虹”。第一个学期,从以《今天》为对象讨论新时期文学之发生开始,每个学期我都在程老师指导下写作一篇有关1980年代文学的论文,依然借鉴佛克马等学者的方法——如果程老师读到这篇文章,他将是第一次知道其实我对佛克马不熟,当年纯粹是巧合,或者美好的说法是冥冥注定。
沿着程老师这个话头说开去,回顾自己的大学十年,我对三位老师尤其感恩铭念。第一位是吉林大学的杨冬教授,杨老师《西方文学批评史》课程对我的文学理论学习而言是启蒙性的,杨老师用大量原典材料,清晰扼要地分析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等大思想家,安安静静地打开了一个睿智的世界。想起杨老师,总会联想起他十分心仪的韦勒克,博学,醇和,以及优雅的“保守”。文学研究从一部部伟大经典开始,无论今后走向哪个方向,这个起步都很重要。
第二位是伦敦大学的赵毅衡教授,我是在读硕士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赵老师的大作。记得是在2003年的冬天,无意间读到《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感受如受电击,恍然开窍。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后来成为我自己做研究的座右铭:“形式分析是走出形式分析死胡同的唯一道路,在形式到文学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中,有一条直通的路。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通过他一系列精彩的细读与范导,我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以细读文本为基础,建构历史性的形式分析,由此真正开始文学批评。补充一句,因为一直不在这个热那个热的“风潮”之中,赵毅衡教授“形式文化论”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这类学问,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从未真正扎根过,这是巨大的遗憾。
第三位是我的导师程光炜教授。在报考程老师的博士生之前,我正从新批评转向读福柯——原因在于受王小波的影响,硕士论文是王小波小说论,他的作品对于“权力”的描述,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所能够完全涵盖的。这个时候程老师已经开始对于“1980年代文学”的知识考古学分析。考到程门后,在程老师指导下,从《今天》、1980年代的“新批评”、改革文学、“社会主义新人”、《废都》事件这些具体的文本与文学事件入手,从或隐或显的文本中阅读大历史。“重返1980年代”背后涉及到的“元问题”,即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程老师引领的这场学术思潮,我理解它内在地有两个指向:其一,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其二,重新激活“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我还想补充的是,程老师的研究在表面上以学术化、历史化为旨趣,但他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作家论背后,有一种深挚的情感。在学者之外,程老师同样以诗人的身份理解文学,他的文学是和生命历程深融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否也和文学交织在一起,诚实地讲完自己本硕博的十年道路(这种乏味的成长方式恐怕是“80后”文学批评者的普遍道路),我发现和自己熟悉的19世纪故事相似,文学对于我首先是一种“脱嵌”,和故乡的环境、自己的家庭、古老的礼仪风俗与情感结构的脱嵌。通过文学,通过高考、读研、读博,我脱身而去,告别家乡,离开东北,来到北京和上海,开始别样的生活。2009年夏天,我博士毕业后幸运地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在上海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在我写后记的此刻,窗外小区草木深密,秋虫声、邻居的电视、偶尔的狗吠、远方过往的汽车轮胎碾过雨后马路的沙沙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在书房中微微氲开……这就是我此刻的生活,我的所谓历程就讲到这里了。
不知道是火凤凰涅槃,还是本雅明所描述的保罗·科利的“新天使”,自己往昔微茫的通过文学的挣扎,终究是广阔的现代性方案的极小的一部分。自己以为走在一条与众不同的奋斗之路上,其实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剧本。一切都像瓦砾一样从大地上被神秘的力量吸起,重建新的世界。这种脱嵌,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自由”;这种重构,我们这个时代称其为“进步”。迎合着个人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式的文学十分受到欢迎,从路遥重写“人生”的故事开始,到郭敬明营造“小时代”的“幻城”结束,从陕北到上海,从黄土地到外滩,“自我”的文学成为这个时代柔韧的底色。
这本批评文集,我尝试和“我”对话。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批评者,我理解并且尊重父辈的批评观。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刚刚从一个梦魇般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对于现实主义的怀疑,对于语言变革的热切,以及对于纯文学的追逐,都在回应着笼罩着童年的“文革”那浓重的黑影。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这个“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学批评之所以在1980年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
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神话,已然暴露出内在的封闭。然而,对于左翼批评同样要有所反省。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评丧失左翼真正的精神向度,被国家主义叙述所吞噬,蜕变成一套辩护性的说辞。而且,文学批评固然应该向宏大的历史空间敞开,但不能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附庸。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同时,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反思“形式”的历史性,通过叙述形式的分析,进入到社会历史分析。这种批评的使命,是否可以概括为:从形式出发,重返历史性;从个人出发,重建共同体。为共同体,为我们共同分享的历史感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
这样的批评境界,我远远无法达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这几年的初步尝试,是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考察王朔、王小波、韩寒这条隐蔽的文学传统。“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于陈词滥调的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我所关注所追踪的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路可逃。
在无路可逃中,结集在本书中的批评文字,没有终极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在历史现场“缠斗”。这是金理赠予的一个命名,我很认同“缠斗”这个词,并不学术,满身泥污,文章的生命力和所论述的对象一样短暂(谁会再看一遍春晚呢),半是天真半是严肃地逼问生活,仿佛经由文学的追问,可以在燃烧的荆棘中拼出一条“中国梦”的小路来。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