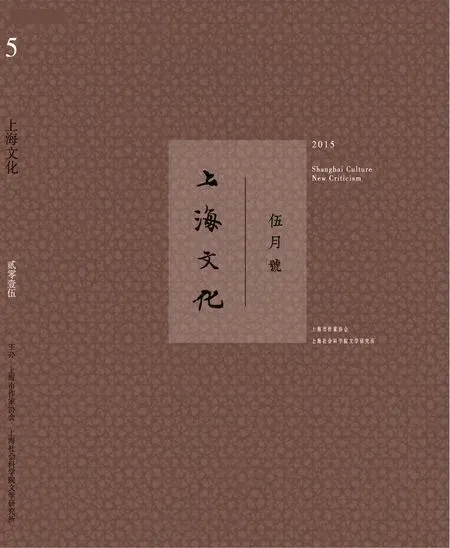为生活于现在评胡桑的诗
王健
为生活于现在评胡桑的诗
王健
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为生活于现在。
——特朗斯特罗姆
如何将“现在”从答案重新转化为问题,如今也变成了困扰着当代诗歌写作的难题
为了让诗歌能更有力的切入“现在”,诗人做着双重驱离的尝试,首先是在作为象征的语言层面;其次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在”层面。这双重的驱离都源于“现在”流传至今后,已变成了一个被用滥的词汇,它因各种话语的塑造而被固化,以至于很多时候都被看做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或被看做是某些物理时间的截点;或被纳入某些以“创新”为名的实验之中(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意义层面),并继而被一些花哨的技巧暗中所替换。“现在”的意义正在变得单一化,它仿佛变成了一种能够被学习的知识而非一个需要被探讨的问题。如何将“现在”从答案重新转化为问题,如今也变成了困扰着当代诗歌写作的难题。从这个角度切入来解读胡桑的诗歌,或许我们能更容易发现他的意图与贡献。
在胡桑的诗歌中,两种驱离的努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先从语言层面寻找解读胡桑的入口,因为作为交流中介,语言总是诗人最先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诗人总是致力将事关自身思考温度的词语擦亮,来承载他所体验到的现在。在对胡桑诗歌的阅读中,黑暗是他呈现给读者的第一个关键词。
胡桑热衷于书写黑暗,这个词汇他的诗歌中时常可见:
小区深处,亮着几盏灯,仿佛一些邀请。
一个灵魂,跨越黑暗,才能取消盲目。
——《空栅栏》,2012
只有卑微的人们接纳了我们的眼泪
最大的勇气是,在别人的羡慕中承认失败。
或者从自己的梦境之中走出来,
和烈日中的黑暗相遇,和危险相遇。
——《与郑小琼聊天》,2012
旅行使我变得漫长,我试图传达黑暗的时刻,
它们却离我而去,如难产的燕子。
言辞的疾苦,毁坏了事物诞生时的快感。
——《命名》,2011
黑暗构成了胡桑的“对手”,以及他的诗歌所要探索的方向。这个词在胡桑诗歌中的意义非常灵动,它似乎是一个难以被容纳的点,游离于灯盏的邀请、梦境的融合和言辞的表达之外,却又需要“光明”(无论是以灯、烈日,还是言辞)的映照才能产生意义。在胡桑的诗歌里,黑暗毋宁说是一种潜在的意义幽灵,它更多被当作“光明”的界限来使用。也正是借助着这个幽灵,胡桑从被一一对应的象征关系所紧束的语言意义中驱离,从而扩大了其诗歌的表述视角:因为他不仅要对暴露在“现在”的光亮之下的东西进行描述,还要将视角投向这些光亮之外,对被它所隐匿的黑暗进行探索与表达。这探索的层面展开会有很多,它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理性与盲目之间界限的探索、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羡慕与失败之间纠葛的理清,也可以是用语言表达生活的过程中诞生与毁坏之间关系的触碰等等,“现在”于是就成了这些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结合体,同时容纳着无数的已知与未知。
在这种“现在”的时间之中,语言是具有着增值功效的。胡桑将自己的语言从象征的神话中驱离,旨在将语言面对未知世界进行的言说功能重新呼唤出来。这世界因其流动性的边界而被软化,诗歌对现实的言说于是就指向了一种对生活的未知层面进行探索的现实行为,因此黑暗就变成了一种有待开发的潜能,从它之中探寻的实则是构筑当下的活动,如阿甘本所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关于当代性之黑暗的主题上,这种黑暗就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惰性的或消极的形式。相反,黑暗表达了一种活动或一种独特的能力。在我们的情形里,这种能力等于对时代之光明的中和;中和是为了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黑暗是可以与光明相分离的。”这种作为活动的黑暗或许也是胡桑所想要的。
黑暗指向构筑当下的活动,而在胡桑的诗歌中,这些活动又具有着高度的复杂性,他所想要的探索是迂回和徘徊着的,而不是一种略带鲁莽的勇往直前。黑暗中蕴含的是一种光明的不完满性,如他诗中表现的“盲目”、“危险”与“疾苦”等,胡桑需要这种不完满性来平复“光明”所带来的傲慢,让行动变得有节制。但这不完满性同时也呼唤着行动的勇气,界限在被设定的同时也会设定着突破界限、抵达光明的欲望,如同阿甘本所阐述的“当代人”那样:“要在现时的黑暗中觉察这种努力驶向我们但又无法抵达我们的光明——这意味着成为当代的人。因此,当代的人是稀少的。出于这个原因,做一个当代的人,首要的就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黑暗中所蕴含的潜能为欲望提供了一个通往无限与圆满的目标,也让这目标变成了一个持续的过程,正是在这来来回回的纠葛中,胡桑的诗抵达了混沌的“现在”入口。
在胡桑这里,黑暗具备了蕴藏潜能、保持谦逊和呼唤勇气的三重意义,它的存在并非为了营造一种诗意的愁思,而是切切实实地指向对被隐匿的秩序和被遗忘的体验的持续探索
在胡桑这里,黑暗具备了蕴藏潜能、保持谦逊和呼唤勇气的三重意义,它的存在并非为了营造一种诗意的愁思,而是切切实实地指向对被隐匿的秩序和被遗忘的体验的持续探索。因此,黑暗并不会蹈向虚无,后者的意义更具形而上的特点。胡桑的诗歌中也有“虚无”一词,只是它出现的相对较少,它仅仅作为一个意义的通道,胡桑需要透过它去触摸词与物的裂隙,以抵达被隐藏的黑暗的部分,从而让自己的语言持续陷入到混沌之中,使其包含更多意义的褶皱,带出生活的废墟。胡桑所要展现的,并不是隐藏在有之下的无,而是隐藏在一之下的多。
如果将如何对黑暗进行探索的问题往下落实,又会涉及到很多的层面,诗歌在这里只是在语言表述层面的一种尝试。与此相应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去表达那些有待书写、有待表达之物,从而让文字变得性感起来?面对这个问题,胡桑的诗歌找到了“沉默”这个契点,但他的沉默并不是放弃言辞,而更像是用文字对待黑暗的一种态度,它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勇气相关,也伴随着语言对黑暗的难以表达。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胡桑有关“沉默”的一些诗歌:
房间里的沉默,已无法应付警醒的白昼,
空气中充满力量。地平线在远处守候。
那永远的休憩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逐渐地,他放松了肌肉,等待命运的注射器。
——《失踪者素描》,2013
那时候,我们需要打开自己进入生活,
命运却超过了我们,禁止赎回那些沉默。
——《那些年》,2012
乌鸦的叫声掘开一个封闭的异乡,
言辞并不多余,不能由沉默代替。
——《空栅栏》,2012
作为一种无声的经验,沉默处于语言表达停止的地方。在胡桑的诗歌中,沉默被各种压力所塑性,诸如“警醒的白昼”、“封闭的异乡”与作为生活的“命运”,它是一种柔性的姿态,包含着无奈与接受。但柔顺不是逆来顺受,因为它同样会以询问与反思的方式召唤着语言的赋形,“言辞并不多余,不能由沉默代替”。沉默之于胡桑,其实是为语言留有余地的一种态度,这也让蕴含着沉默的言说具有了倾听的能力,能够接受他者的进入。胡桑并不想把黑暗容纳到了自己的文字之中来,而是希望借此打开语言的枷锁,让其能够持续地对黑暗持开放态度。与此态度相关的是,胡桑并不轻信于自己的语言,他会在语言的使用中同时安置语言的界限,从而将意义指向语言之外——因为要在语言中找出沉默,并对其为什么会沉默作出思考,这显然超越了语言所能承载的,至少超越了诗歌的语言所能承载的。诗歌能做的只是将意义指向这些沉默,从而让自身变得及物。与此观点相应的是,胡桑并不热衷于在自己的诗中搞各种文字实验,在当代诗坛,他的诗歌在形式和文字层面都不算独特,因为对他而言,语言显然并非诗歌所要重视的唯一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也让他的诗歌能远离了当代诗坛“语言的天花”(欧阳江河语)疾病的传染。
胡桑让诗歌变得及物,从另一侧面也是对诗歌对话功能的恢复。诗歌之于他不再是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字自足体,而是成为了与他者相互关系中的一种题赠与交流的方式。这种交流首先体现在胡桑诗歌的篇名与题记之中,在这里常会出现所赠之人的名字,如《云——给金霁雯》、《叶小鸾——致苏野,兼赠茱萸、叶丹》、《与郑小琼聊天》、《与藏马对饮衡山路至晨》等等,这既可以被理解是他对传统诗歌酬唱传统的嫁接,也可以理解是他力图让诗歌变得及物的努力;其次体现胡桑在诗歌中对“疼痛”一词的使用,他者(包括黑暗)以疼痛的方式被纳入记忆,我们可以看几组他的诗歌:
数个世纪的灰烬,坍塌于岁末的心脏。
一枚无法被时代消化的结石,停留在思想的
胆汁里,无法令空气中的影子宁静下来,
所谓牺牲,就是见证叠加在一起的疼痛。
——《叠影仪》,2011
表达提前到来,甚至不能感知,但它必须
被刺破。没有疼痛,就没有闪现的过去。
——《褶皱书》,2009
疼痛一词在胡桑这里,是一个能够容纳现实感受力的容器。感到疼痛即意味着自身的打开,就书写黑暗的层面而言,如果说沉默是在语言层面的打开,那么疼痛就位于这层打开之后,通过语言指向对现实感受力的恢复。感到疼痛伴随着对边界的触碰,无论是以“无法被时代消化的结石”的方式、还是“闪现的过去”,它的另一端都襟连的是未知的区域,可以是对人,也可以是对事件,对每一个未知他者的触碰都会带来一种新鲜的感受力。沉默是让语言接受异质,而疼痛则是让生活感触到他人。然则胡桑并没有把现实中与他者的关系看做是诗歌表现的终极,而是把它也当做一个维度被纳入到了文字之中。他所要召唤的疼痛是与“思想”、“表达”、“过去”等词语相连接的,这也使疼痛具有了粘合的功能,它可以被看做是在时间、语言与现实等问题之间寻找新的结合点的尝试。此举也进一步打开了胡桑诗歌的疆域,同时让他的特点更加明显:即不囿于语言、不拘于现实,亦不碍于时间,而是将一切思考都推向边界,从边界审视周围各种关系中难以理清的纠葛,如光明与黑暗、可见与不可见、言说与沉默、语言与现实等等。
胡桑致力于用诗歌将其中的各个层面的边界磨得更加纤细与锋利,因为只有当边界更加纤细之后,位于它身边更多的侧面才能被展现出来,其视野也会变得更宽,能够欣赏到菱形各个层面折射出的美丽。他致力于摆脱每一个单面意义的囚禁,从而与其他被隐匿在黑暗之中的可能性相遇,这种写作的方式是包容性的,它总是朝向未知,并不把自己所开掘出的任何一面看做是意义的唯一基础。因此,胡桑的诗歌总是向外张望着的,他的命名并不赋予意义,而总是指向隐藏在命名底下的意义纠葛,指向他自己为这些意义进行命名的惶然的态度与过程。然而这种向外张望也是辩证的,它在给了胡桑惶然的同时也给了他能够分辨的视角与能够书写的勇气,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表达的那般:
已经习惯于被囚的处境了,但仍要
向内张望,索引不可见的事物,离开此地,
就是永远栖居于此地,穷尽它的可能性,
在瞬间抵达永恒,用清晰的绳子绑住混乱。
——《反讽街》,2011
胡桑借助于对黑暗的探索切入混沌的“现在”时间之中,但这种混沌的“现在”时间毕竟还是过于抽象,它需要被外化于一系列我们现代人所接触到的生活意象来表达出来。而当代诗,无论中西,都塑造出了一大批的当代意象出来,而这些意象也成为了当代诗之所以能称为“当代”的例证所在。在胡桑的诗歌里,这些当代意象亦是比比皆是,但不同的是,他会捻取很多当代诗人极少使用的意象入诗,比如抽水马桶、(公园中的)菖蒲、自行车、超市、菜市场、街区等等。意象截取的不同也能看出诗人对“现在”不同的探索方向,许多现代诗人会在工厂、商业街、麦当劳等意象上着力良多,因为相比于其他,这些意象更能代表我们所处的“现在”环境。这种截取蕴带着一种典型化的努力,而胡桑似乎并不想去追求这种典型化的东西,他所截取的意象更加生活化,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的东西。这种截取方式在当代诗歌中算不上是非常罕见,却算得上是非常冒险,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变成索然无味的口水诗。
但胡桑的写作毕竟与口水诗有着参商之隔,他并不像后者那般对一切宏大的东西深恶痛绝,在胡桑的诗歌里一些宏大词汇也时常可见,诸如命运、世界等等。胡桑似乎并不想如口水诗人那般陶醉于某些破碎的现代意象之中,在宏大词汇的碎片之中宣泄着狂欢的情绪。如上所述,在胡桑这里,诗歌的角色并非是个书记官(无论它所面对的名曰“内在”还是“外在”),而是去探摸边界的一双手,而界限所意味的并非只是驱离,更是另一种方式的连接。胡桑致力于在散碎的意象和宏大的词汇之间搭桥,用文字去承载这小与大之间的震荡。因此,他的诗歌带有着鲜明的哲学意味,从而区别开了口水诗对生活的滥用。我们可以先看胡桑的一首诗:
研究老人,比如性欲与自杀,礼物和
秩序。也许,我们并不相信
真的有傲慢。你看,时间只教会了顺从。
不过,这到底是平和,还是无奈的妥协?
命运如同癌症迫使一个人努力变老,
是啊,窘迫的生存让一切变得多余。
不需要怜悯,我们无须变成自足的哀悼者,
只有彻底陷入生活,才触摸它残忍的裂隙。
请向自己问更多的问题,让生活超越我们。
此时,每一条微信都在怀疑自己,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失踪在希望的门口。
我愿意做一个熟睡的人,等待被阳光唤醒。
——《闲谈》,2012
或许在一些口水诗人看来,这首诗的立意本身就过于宏大,但这恰恰是胡桑诗歌写作风格的一个体现。这首诗的切口其实非常微小,就是在日常的聊天中,诗人和朋友谈及对老人的看法,然后在这细微的事件中与宏大相遇,即命运、生活与希望。在这里,命运是作为生活中窘迫一面的载体出现的,它包含着不得不如此的“无奈的妥协”,对此,胡桑期待的是一种“理解之同情”(王国维语),目的是要“陷入生活”并使“让生活超越我们”,以便让生活去穿越不得不如此的窘迫而去叩敲希望之门——这就为普通而细微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质感,这是一片坚硬却并非不可改变、希望深驻却又不易开掘的区域,因此,命运不再因僵硬而变得让人厌恶,希望也不再因空虚而变得廉价。命运将生存者抛入生活之内,而希望又使他对生活有所游离,而“生活”就处于二者的张力之间,也让此二者变成了一对相互生成的镜像。也正是因为对“命运”的重视,“生活”与“希望”在胡桑的诗歌中脱离了宏大词汇所带来的说教感,而是以问题的出现,并在这些询问中探访新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和词语意义的宏大之间,胡桑用不间断的探访与徘徊的方式完成了对二者的连接,这也让他的诗歌充满了内在的警觉。
这也是一种通过“陷入生活”为“现在”提供质感的尝试,胡桑并非仅仅是要为读者还原出一片所谓“真实”的生活样态,而是想将他们邀请进混沌的世界之中去,并尝试为生活中那片未知的区域赋形。宏大词汇也正是来源于这赋形的过程之中,它是借词语为混沌的生活摆上希望的路标。混沌的“现在”需要这希望赋予意义,以便为我们被命运所纠缠的日常生活复魅。也因此,诗歌便与赋形的行为变得相关,而不仅仅只是个语言事件。从胡桑诗歌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书写重心转移的过程,即从“触摸语言的质感”到“传达黑暗的时刻”,这个转变也蕴含着他所要发出的一个信息,即:“来,让我们讨论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
对于“诗歌如何书写现在”的问题,胡桑的诗歌并未提供答案,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诗歌中所呈现的黑暗、沉默与生活等诸多样态,都只是构成“现在”的一些不同的侧面,而“现在”本身却是混沌未知的。而正是因为“现在”本身的混沌未知,需要对这些未知区域进行拓展,才会让“诗歌如何书写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在现实中如何生活”的问题。诗歌并不负责为生活提供答案,它只是将存在感变得更重。因此可以说,面对“诗歌如何书写现在”的问题,胡桑的贡献并不在于为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答案,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指向,从而让这个询问变得更加深入。
❶Giorgio Agamben:NUD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3-14.
❷Giorgio Agamben:NUD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4-15.
编辑/张定浩
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和词语意义的宏大之间,胡桑用不间断的探访与徘徊的方式完成了对二者的连接,这也让他的诗歌充满了内在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