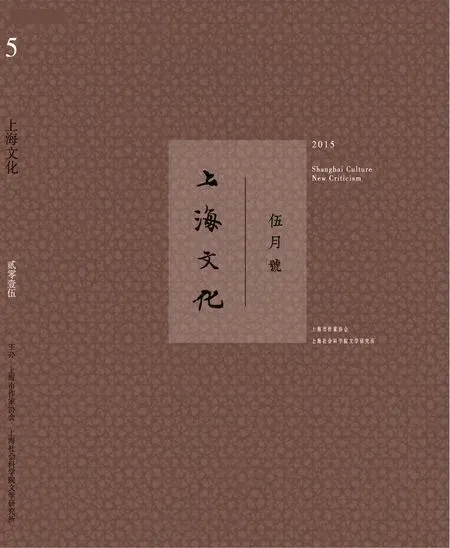乞食的正名①
木朵
乞食的正名
木朵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陶渊明《乞食》
写作的重心就留在自我作为唯一当事人的位置上晃荡,寻求一个使之安静的力
既非利益驱使,也不是求教于人的迫切需要,此次访友的动机来源于诗之开端所需要的那个表面上最易成立的缘由:去蹭一顿饭。一种生理需求,一种解闷的、出去溜达一下的方法,肚子决定脑子,饥饿感首当其冲地表态,把羞耻感作为反观现况的镜子藏匿起来,但同时又从所叩之门的镜面观察自我舍弃面子照顾肚子的决心算不算一次人格的刷新。这个即将要去的地方、要去访问的人均处于匿名状态,似乎只有这样做,叙述的节奏才不受干扰,写作的重心就留在自我作为唯一当事人的位置上晃荡,寻求一个使之安静的力。
这可以是类我处境或如我之人的综合辨认,也即,他要为自己的某种现实生活预先安排好一个如此这般的舞台。但读者更乐于相信的是,这首诗说的正是他的切身体会。他一定体验过那种狼狈的流程,并且必然有一位不拒之门外的友人或熟人赠给他一个例外情况。这当然也是出发前的一次预判:乞求有可能因对方的接纳而变得合乎正义。这里并不是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觅食,不涉及家国的颓废,反倒像在没有知音的地盘上争取一位知情人,赏个脸配合一下饥饿感抓出一把语言的秸秆。
饥饿感是确实有过的,对饥饿感带来的困境的设想也已发生,现在,他捏在手里的花名册因知音的匮乏而必须选中一人来试验人间的真情指数。饥饿感如此真实,哪怕它仅仅是一次设想,也有真实的气息,他琢磨着发生了这种事那该怎么办。如何为自己的末路争取到一个转机?如何在自画像上假设一个顾盼生怜的看客?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不打算直陈人间的冷漠无情,或者乞讨形势的每况愈下,饥饿感仅仅是一个切身感受的唤起,是求证于读者的感同身受的预热,它为迈出人生艰难的、没有脸面的关键一步提供了一个诱因,既合乎理性,又预示着前途不测所附带的悬念。这仿佛是一次绝收之后的坏年景里的出门,而不应是一个常态,也不是屡试屡败的市场调查中的偶有中的,而是一测即准的人间温情的摸底。
这是道德感的试纸,但双方都不去捅破。叩门以及开门之后的寂静,正是双方道德水准的平衡、汇合
受访之人并不明确,可以是左右权衡之后做出的安排。就这个人了,好歹去试一试。那人不是最佳人选,既不是最灵敏的耳朵,也不可能会口吐莲花,但没有所谓的最佳人选,饥饿感不仅是肚子咕咕叫,还包括诗艺高悬时的孤掌难鸣。就近找一个懂得一点诗艺的人,就好像乞求一位合住老农再听他的满腹经纶。这的确是一个塑造自我形象的机会,显示出自己主动出击,物色“猎物”,但又合乎常人的判断,认为其中多少还有一点冒险的成分,很可能丢了少许尊严,然而,这种可能性被控制到最低,他对花名册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确定了这个目标人物。这个人至少符合两个特征:其一,他避开了灾年或绝收的窘境,至少此人在物质上要明显地优裕;其二,此人懂得些许风雅,知道饮酒作乐的妙用。当然,这个人还得刚好在家。
看起来这并非一路行乞的最后一站,而是早在预料之中的开门见山。在那人开门之际,不致面面相觑,而是都多少带有一丝幸存者角色的戏份,主宾配合默契,乙方猜中了甲方的诉求,无需口若悬河或反复解释,就达成了人的需求层次论方面的共识。主人的接纳之快、配合之默契,削弱了蹭饭者一方的尴尬,也为按下尊严之葫芦浮起文雅(礼乐)之瓢提供了合力。仿佛行道迟迟终于得到了一次犒劳,又似民意测验得到了一个爽快的高分,但主人总体上是沉默的,陷入了无名性的沉寂之中,连他家属的眼色也不能使上。主人没有其他方面的搪塞,只有顺水人情的展示,为诗的步步迈进减少了起负面作用的噪音。主人接受了这一授受关系的当然性,没有别的想法,甚至停下自己的时间表,融入客人的连续剧中。
这不是嗟来之食,也不牵涉到施主的人品或社会地位可能带来的压抑性影响(施舍程序的不义),这是一种济世救人的备用措施,也包含着对一个非常时期的底线观察。觅食的一方在叩门之际准备的说辞不是给知音听的,也不算周密的台词,但究竟怎么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如另一个问题重要:如何在乞求与施舍之间制造一个隔层?乞求者带着那个时代的伤痕由外而里,叩击着施主的门扉:这是一条界线,预示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时恰好是一条拯救措施。这也勾勒出一个自我形象:门——隔层、隔膜——吸引他、催促他去叩打。他预先有过对门后响应情况的几种揣测。这扇门把他从他的家里——饥饿的空间、实在的危机——吸引出来,也在一个饥饿的同时存在的无边世界中清理出一块飞地:在那里,饥饿感将消散,尽管是一次性的、临时的,而不是根本上的。
叩打门扉的声音是适中的,不重也不轻,陷入一个中庸的经验值,它极有可能导致应答——无论是敲门人,还是开门人——的喑哑。这是道德感的试纸,但双方都不去捅破。叩门以及开门之后的寂静,正是双方道德水准的平衡、汇合。此时无声胜有声。即便是开门人属于第一次打开这样的一扇门,第一回看到对自身所具备的余裕足以补偿他人的亏缺而形成的一些能力,也应听懂了那指关节的申明。而实际情况在于,这个来到跟前的敲门人是带有某种不凡性的,他携带而来的不只是对吃的诉求,还有他的名声,虽算不上有交往,但是对于这样的人士——甚至不难判断,缺衣少粮对于他来说并不应谴责其懒惰或对稼穑的无知——抠门是有损本方的尊严的。对方既然理直气壮地敲开了这陌生的大门,这个行为本身就蕴含了对开门人人品的积极评价。此刻,还远没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
应尊重他求生的本能,也要积极回馈这次神秘的来访。门的洞开连通了两个不平等的世界,似有面黄肌瘦的人进入了一个他所陌生的饱满空间。这个空间的异己属性提供了一个缓解危机的方案。在这里确实可以蹭一顿饭,但仅此而已,并不许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空间的主人无需磨刀霍霍向猪羊,也不必营造“新炊间黄粱”的惬意景象,只要供给最低限度的吃食就够了,这样做也是对当事双方经济状况不等的真相的相互认可。不宜以某种炫耀乐善好施品德的过度热情强化了不平等的现实,徒生烦恼。这里确实没有阶级差异的批判,也未进行歉收无粮的原因分析。反倒像一个偶感酒瘾的隐士冒险越过边界向市井世界宣告了自我的存在,他即兴般地敲开了任意的一扇门,赌中了自己的命运与衷肠。
但这里还有乞食的艺术:他并未被三言两语打发,也不是被下人递给的几个冷馍婉拒他登堂入室。他竟然有机会走进这个陌生空间。也可说,这首诗——即便是事后回忆,或者凭空臆造——线性叙述的转轴没有停下,它继续发展出叙述的基调与心弦。也就是说,门所具备的表演性还无力承载一首诗全部的负担,还必须搜寻别的什么东西,必须向那个并不熟知的空间深入。当然,塑造一个好心肠的施主形象是妥帖的办法,但是不凝滞地完成这首诗的流程,以凸显出某种关于生存现实的时间意识,才是诗的迫切使命。肚子走过的九曲回肠,诗也需经历这番曲折,作为一个乞食者形象的生发者,他有必要力保这一次乞食的经历是可信的,同时还经得起文学意义的复核。在描摹一个新鲜的自我形象时,还要将另一个人的形貌卷进来,却又避免发展出某种甜蜜的友谊,就像完备的解围机制被发现。读者当然想了解门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想进一步了解乞食的波折、乞食者得到救赎的抛物线。
这个被打开的异己世界几乎是桃花源的微缩版本。这里讲述了一个奇缘,但又不宜夸耀这份闯入他人世界的运气。他突破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忠告,敢于探索自救的措施。也不妨说,他挖了友谊的墙角,测试了如何在知音匮乏的年景里逢场作戏。演好自己的角色,并物色一个配角,这人生的戏剧为诗的周转奉献了动力。诗所寻找到的这张人生切片,一个决定从自己所辖空间中溜出去的乞食者形象,终于变成了诗的素材,转化为诗的损益。凭借诗的终极安慰,乞食与乞食者形象就成为了语言的一个幌子、一个语言事件,发生在现实的嗷嗷待哺般的急迫感中,拓展了生活的边界,最终,嘴中的微妙感觉,那牙齿与食物啮合的瞬间,都将换算为退回去的那个空间的诗意。发明一个生活中的乞食者形象,其实同步在发布两则寻人启事:一则探问知音的化身何在,一则寻求自我的变体划不划算。对残酷的饿肚皮的生活窘境来说,乞食是严肃而不得已的,是对面子和面具的清算,但是就诗艺所对应的那个得体世界来说,这幕戏剧又包含了对人生尊严到底为何物、做人的底线以及诗意还可以从匮乏的生活现实中如何觅取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
谈话中止了乞食者作为“一个乞食者”的冠名的尴尬。他从匿名的乞食者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对话者
乞食者并不需要发明一个上帝般的他者形象,以求心灵的救赎,他只需叩击那扇得救之门即可,即便门后世界泼来一盆冷水,也算是自我救赎的代价,值得去试一试。只要叩响了那门,本方的义务就已履行,自己的戏份已经完成,等待的就是对方的演出,演砸了,并不能怪自己的冒失,而应从理性的逻辑上归咎于人心之恶。但这首诗最后的表演证明了双方的得救,并未以恶之花残酷的、赤裸裸的剖析这一险境来证明这里有一幕双重的加害事故。对方匿名于扮演着一个知情人,他顿然理解乞食者开门见山的意愿。这种理解包含着乞食者这一方面双重的理解在内:一是乞食者事先假设了一个被理解的可能性,得偿所愿的可能性,二是乞食者摇身一变为事后的记述人时认为人生的秘密应在邂逅中被理解,就好比人生的礼物来自于对自我底线的一次次测试之中。
来者空空如也,也有针对施舍一方的陌生性、匿名性,门本来隔离了双方,成为一个邂逅的屏障,而现在,来者出手了,他的空无指明了他的某种弱势权利。不能让他白来——这是另一条人生底线,这也是开门刹那间应该形成的一个关于来者不善的意识:与其说是对方索取某物——而且他早已预估了自己的索取行为的后果——不如说他是来取回他应得之物,施主只是暂时保管了一杯他人之羹而已。但这些思想的微澜都没有拿到桌面上来谈,双方谈论的应是可以谈的一切。也就是说,双方就某些义务的履行不是转眼之际的交接了事,而是必须把吃食之外的谈话这一内容也列入馈赠的仪式之中。唯有加入了一份谈资,双方的义务全都释然。那么,他们——不只是两个陌生的个体,还分别代表着乞食者(饿汉)与施主(饱汉)——会谈些什么呢?
谈话的内容没有在诗中倒映,但谈话所维持的时间长度以及宜人效果得到了交待。双方都明白谈话作为贻赠项目的必要性、仪式感,就好像这是一笔祖先的共同遗产,现在,在一个坏年景(不管是普遍的坏,还是对乞食一方来说绝对的困境)里,双方一起接受这份遗赠。乞食者的身份象征其实在门打开的一刹那就完成了勾勒,他入得门去,就不再是一个乞食者可怜兮兮的样子,而是一个对话者,一个平等的人,他因见证了道义永存并还将见证更多的细节而与富裕的施主平等。他的平等性还将体现在双方促膝交谈所花费的时间上。谈话的时间越长,双方的平等就越充分地被感知。谈话中止了乞食者作为“一个乞食者”的冠名的尴尬。他从匿名的乞食者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对话者。时间停顿了,因为接下来他们边吃边谈,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话题上都得到了保证;乞食者因得偿所愿而不再是一个乞食者。
匿名性得到了稀释,很明显,这的确是一个善者不来的正例:这个人肚子里很有货色。甚至因为接待这一个越发显得独特的乞食者而罔顾其他乞食者的叩门声。馈赠仪式延长到精神层面的丰歉互补上来。但诗中并不透露此消彼长:乞食者在心理上更具优势,是一个占据主动的讲话人,而吃食方面的施主反倒成为精神层面的受主了。这里只有一个关于两情相悦的场面的概述,而我们的文学传统尤其需要这样的场面。对话内容——无论是达成共识的条件,还是产生争议的原因——都没有构成诗的主题,诗似乎一贯忽略这里面也有一扇门通往诗的腹地。虽然时间停顿乃至于无,但是这首诗的线性叙述依然秉承先后关系,不忘探索下一步骤适合出现什么场景。
尽管对话的具体内容被诗搁置了,但是,有一个信息是明确无遗的,二人在言谈中接触到了“诗”,简言之,乞食者兴味浓烈之时已然暴露自己是一位诗人。从一个既定形象滑向一个需经谈话才能摸清的另一个人生形象。考虑到乞食作为一种陌生的、第一次打交道的方式,这首诗描写的不应是回头客的奇遇。施主不应事先了解乞食者是一个读书人,只当那人是此后可算有一面之缘的老者。但仪式感的必要性正好体现在这一个乞食者恰恰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一情况最终被发现所需要的合适时长上。我们确实必须接受老祖宗的忠告,要在吃食的授受之后,再花点时间寒暄,这个弹性的、必须的时间长度会赋予贻赠仪式更多的蕴藉。
这首诗除了乞食者为何选中这一扇门叩击所附带的含混性之外,乞食者与施主的对话内容也是含混不清的,也可说,这两方面的交待在诗的层面上属于次要的考虑,是一种风格的弱项,可以舍弃却无损风格的积累,甚至可以说这恰恰是风格形成的前提。开开玩笑、套套近乎,把酒话桑麻,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乃至这些话语太琐碎而不能成为诗眼。就好像无聊的秋日下午几个半生不熟的人聚在一块打麻将度日至黄昏。但总的说来,双方还是愉快的,算得上新知——这已是不可多得的交往中评价等级最为高端的感情形式。有那么一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却又恪守施主匿名的基调不放,并无从中发展出一条长期有效的补给线的打算。这仅仅是一次奇缘,连施主也似乎明白这是第一次相逢——有求于他——也应是最后一次,乞食者不可能再次以“乞食者”形象出现在门外。那人入得内室、相谈许久,这一情况其实已经产生了某种对再来一次的央求的拒绝。诗也意识到这是对某个唯一性遭遇的刻画,它不可能重现,就好比绝境仅仅是得到半天的缓解却并没有明显的改善,明天还得继续饿肚子,但乞食的进程已经除却了最高一级的感受。我们丝毫不觉得在困境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之前,乞食者为何不向对方乞求一条避险之道,而是手持一株忘忧草似的朗诵起诗歌来会有何不当。这才是乞食者心路的一波三折:从扮演乞食者角色起,到入门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变成了诗人(读书人),再因事后可想而知的“诗的无用性”重又回归乞食者的绝对困境——诗,在诗中浮起,恰好是对乞食生涯最激烈却又最隐晦的描述。
诗成为了谈资,尤其是成为宾主惺惺相惜的基础,但这正好也符合“饱暖思淫欲”的古训,诗必须在喂饱了肚子之后才成为人生另一真相的证据。感情浓烈到了最为关键的一刻,诗就露出了破绽,从胳膊肘遗落下来似的。诗就像一笔交易,是物质匮乏者一方的保底资本,现在,到了拿出手的时候,一是作为回赠,二是作为类似怀才不遇的证明。然而,吃食之余的即兴诗又是匿名的,相对于这首名曰“乞食”的诗来说,现场所赋之诗是一个含混的代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诗既有用但又无用的声明。即兴诗即便存在,也只是作为一个强调的符号存在,表明初次结交的两个陌生人(新知)感情浓烈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也只能如此了,诗就是这个结果。从字面上看,即兴诗还是“言咏”的后续步骤,是对谈话的最终升华,也是言不及意时的最好选择。
但很明显,“诗”要作为一个有分量的礼物回赠给施主,或者说出演诗人角色堪当于谋求到一个与施主平起平坐——同时也赋予这顿饭合情合理的正当性——的机会,还不够意思。这种沐浴着对话光泽——宾主二人都出窍了的短暂氛围——的平等状况很快因诗无力承担起所有的结果或人情评价重任而丧失。诗不是一个像样的礼物,而是对一个得体礼物的戏仿。乞食者介入到施主的内室,施巫般地以半途出现的诗使得施主陷入了临时的迷离状态中,就好像以一个下人的切肤之痛来模拟生活的艰难,而要体验这种艰难——从而体验自己可以充当一个施救者角色——就必须入迷于一件生活的赝品。诗正是现实世界的一件赝品或一个仿像,几乎篡夺了他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处的一颗明珠。
很可能,施主并未心旌摇摆,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救主的身份,似笑非笑、似答非答地应酬着乞食者朗诵的即兴诗。他并非一位诗人,因为诗按理说早就应发现方圆数里之中的另一首诗,也不见得喜闻乐见于这个来客从乞食者摇身一变为诗人的努力。生活不会因他款待了一位诗人而给他加分。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诗人。即兴诗于是成为还假意的一个道具。或可说,诗在这里并未扭转一个情势:它没能把宾主之间类似“一举累十觞”的场景转化为一种坚贞的友谊见证。诗没能胜任感化在场他者的角色。于是,诗必须找一个台阶下:但我们在读到这首乞食之诗时,已很难判断韩信这个典故的联想是在当场散席时的萌芽,还是在对即兴诗进行补救的这首乞食之诗里的促发。出于对即兴诗的忠诚(进而是对诗的普遍的忠诚)的考虑,乞食者在吟诗之后起身辞别时,应不该说到来世报答之类的誓言。那样的话,诗就成为了伪君子的伎俩,誓言之言重又毁坏了诗的结晶努力。应是平淡的告别。但受人滴水之恩所激发的汹涌情感不是即兴诗所能遏制住的,他还想说点什么、承诺一个什么未来,但终于没肯当面说出来。即兴诗没能说出来,誓言又怎么能担此大任呢?
乞食者经由中途出现的诗人形象回归到乞食者本相,要比止步于诗人形象(对诗的价值的乐观估计,或者诗有能力偿付一切的恩惠)更适合作为一首诗的尾声。打回原形除了再度证明生活的残酷现实不因一顿饭的功夫而改变,还预示着乞食者要觅寻一个不同于诗的礼物来了结偿还施主恩情的决心。乞食作为一个必然的寻找生活出口的举措,现在,又变成一个经得起书面认可的对人间真情的响应进度。乞食并不因自身的浪漫性、曲折性、不确定性而成就诗,而是从所经历的乞食过程的一幕幕情节中找出乞食真相之外的语言的可塑性才有可能重塑诗。乞食进度中涉足的诗仅仅是写一首关于乞食的诗的其中一个步骤。后者才是诗人真正面对的重大问题。乞食之中遇见的诗来得不如对乞食之诗(以及对它的反思之诗)那么更有阵痛感,更具化解生活苦难的禀赋。这首诗是诗歌类型的一个崭新代表,也出色地描述了一个经遇苦难的诗人如何从容求生。它本可以停止于宾主相谈甚欢之际出现的即兴诗的理想境地,这也算是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经典愿景,而且不缺友情的点缀(如果诗着重于此,就不难塑造出一份沉甸甸的友情),但是,一个太过知名的准乞食典故改变了诗的尾声,就好像用典会有一种魔力让诗的后院变得更为整洁卫生。
也正是因为这个典故中授受关系的一强(韩信)一弱(“漂母”),以及好人有好报的美好结局,产生了一个诱惑,硬生生地把这首诗作为友情之诗——比如凸显一个患难见真情的主题——的可能性剥夺了,转而变成了一个乞食者必须去面对的终极问题:我将来凭什么来报答他?本来友情就是一种折中的报答方式,朋友来了,接风洗尘,哪求什么投桃报李的及时兑现或承诺,加深了的友情本身就是一个珍贵的礼物,它可以避开另一个实在礼物到底是什么的追问。然而,在这里,话锋一偏的结果是,施主等同于“漂母”了、类型化了,彻底地匿名化了,乃至于变成了一个历史悬念的参与人。友情不存了,即兴诗本已达成的情投意合,因乞食之诗自寻出路的顾虑而隐没了,施主变成了无数个匿名的好人之一,而非一对一的友谊天长地久的见证人。
“漂母”形象的引用,从作为诗的尾声这一点来看,其效果确实值得评估。这也相当于为施主管一顿饭的行为定性了:这是“漂母”般的恩惠。恩惠的性质历史化了的同时,苦难也随之逾越出个人的生活边界,成为一个关于乞食者最终命运的回答。确立这种恩人(施主)属性之后,从诗的层面上看这是一个带有噪音干扰的尾声,而从换位思考之后的恩人立场看,把施惠人的形象历史化地归入“漂母”行列,实际上就赢取了一个历史地位,也即诗不能满足施惠人的虚荣心而历史却能。只恨赠人以食的旧例不多,匿名的施惠人好歹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名称——“漂母”——那就索性往那边依凭一下,这样做还有别的好处,尽管不一定要与施主分享,就好像感激之诗是现场所赋之诗以外的呢喃。这里所说的别的好处是指诗人可以明辨是非,从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察觉到自身处境之非:我不是年轻的、潜力尚未开发的韩信。暮年之人何谈报答?这个典故中的“是/非”对仗关系实际上引发了一次对乞食者有限光阴的感喟,点明了某种未卜先知的末日色彩。乞食者已不可能完成一次报答,涌泉相报也只有在命丧黄泉之后。但是,作为一位诗人还有可能予以答谢:诗的好处正在于只要说明自己年迈无以回报,凸显出某种绝望、深深的愧疚,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回馈。有一颗感恩之心,以及在感激之际稳扎稳打的对仗上的解答,这顿饭就没有白吃,好似一顿圣餐,从中悟出了人生真谛才算是真正的馈赠,这时,不妨说,无名施主的施舍不是为了博得个人的名声,而是代菩萨或上帝履行对乞食者人格的提炼手续。
一个太过知名的准乞食典故改变了诗的尾声,就好像用典会有一种魔力让诗的后院变得更为整洁卫生
对厚报之可能性的绝望,并非对来年歉收的再度预计,而是两种意识的瞬间混合:一是乞食者自忖老不中用,又不能嘱托儿孙承接这笔人情债,事实上,可当作认识人到晚景这一情况的契机;二是平心而论施主并不缺衣少食,大致已猜到了乞食者无力回报的现实,既如此,他应理解到诗作为一个最好礼物的前因后果,也应谅解诗人重提“漂母”典故时对所受恩惠的称量。但这首诗的读者应注意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其一,极有可能酒足饭饱之后,乞食者辞别时并不会提到来世报答的誓言,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冥报”计划是现实以外的诗的修辞安排,为施惠人所不能看到的;其二,引入典故之后,这首诗一以贯之的线性叙述流程中断了,席间赋诗之后的时间消失了,由一块历史剪影来填补,既没有交待辞别的场景,也没用关于随后投宿何地的说明,更没有触及揽月感怀或黄粱美梦一场。
我们也许都有对“乞食”设身处地的想象,也都会假设(也倾向于)碰到如此场面,但是与陶渊明作法不同的是,我们都缺乏一次文本的训练、运作和反思
一次乞食的经历已凝练为任何一次乞食的美好预期,得偿所愿的除了空肚子,还有诗人额外挣得了一个乞食者形象。这首诗并没有提升乞讨的技巧,也没用乞食过程中的其他花絮来贴补诗环环相扣所需的陪衬,它描写了一个普遍有效、可想而知的施主形象或一个施舍行为发生得毫不难堪的场面。如果说乞食在现实生活中是被逼无奈的近乎猥琐的举动,那么在诗中——成为诗的主题——不光是勇气,还有一点侥幸与运气。这首诗保住了乞食者的颜面,也为乞食作为一个行动正名:每一步既合乎预期,又来之不易。那叩击门扉的一个简单动作放到生活中就尤显艰难,但在词句的规整安排下,却不露声色。这首诗开启于一次“去”(计划、决心、第一步),结束于一次关于死亡(来世、阴间、有去无回)的思忖之中,都合乎章法;后人钦佩这首诗并非这种章法的严谨、可靠,更多的是它为读书人反思类似“嗟来之食”的精神内涵提供了可信的样本。乞食的无计划性、盲目性确实会带来某种字面上的浪漫性,就好像遍寻各地,碰运气似的得到一枚知音的脚印,但如今不易察觉的困难在于乞食之事入诗——入情入理——的每个步骤如何开展。读者不会断言这是一次臆想,而是肯定这首诗的作者确然有过乞食的实践,这样一来,乞食作为一个文本范例、一个理论,不证自明地说出乞食之诗就该怎么写的原则。
这是首次到这一个施主家里乞食的经历,但很可能不是唯一一次乞食的体会,后世读者不免设想这首诗的作者过着一种“乞食生涯”。但家境困难不致如此。即便是乞讨,也轮不到他出马。不妨说,他放手一搏,为极有可能陷入如此不堪处境的文人隐士虚构了一桩奇遇之事,如前所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小一号桃花源的探究呢。在这首诗中出现多次的一个字是“知”:开篇所提的“不知”,席间欢畅之余的新“知”,以及“知何谢”中的“知”。这是一连串暗示。他通过这首诗确认了他所知道的乞食行为将要面临的一种情景、一个后果。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反常之例,而是人心所向的交融景象。我们也许都有对“乞食”设身处地的想象,也都会假设(也倾向于)碰到如此场面,但是与陶渊明作法不同的是,我们都缺乏一次文本的训练、运作和反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以为不曾切身经验的不能写,这是所谓的符合真实生活的写作戒律,另一方面我们过早地被陶渊明作品的经典化所麻痹,私下里不免揣度自己不能超越他的这首诗了——试想:我们处理同样的素材时,诗的末尾除了用典还可以怎么办?
这是双重的体验、闯入。一方面他作为当事人有过至少一次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乞食经历,另一方面他作为作者体验了我们民族心理的一波三折:我们的传统心理在乞食这样一件意义非同小可的事件上到底会怎么触动?韩信以另外一种方式——传记的方式、间接的方式、有后续报道的方式——阐释了我们民族面对乞食一类的事件的心理反应。这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反应。眼下,作为诗人、作为当事人、作为直接记录人的陶渊明延续了乞食的近似浪漫化的叙述流程,只不过在策略上给出了一个不同于韩信事件的答复,但是,民族心理的共同点在于感恩是必须的,也正是由于有普遍的对感恩/回报(无论是物质上的数倍报答,还是名誉上的额外收益)的预计,施惠一方才在他人危难之际、时局不稳之时慷慨解囊,因为我们的民族心理认为救人之急是正当的、好人有好报。陶渊明无非是揽下了这个看起来非他莫属的差使,中规中矩地描述了乞食场景中宾主双方应有的心理负担及其担当。
由于乞食者意识到自己作为纯粹的受益者(而不能及时地给予某种补偿、报答),这首诗就不太可能发展出一种对人间真情(友谊)的讴歌,它看上去就像是严格按照乞食与行善两方面应有的程序走下去,只不过其间还有双方的互动作为一个感情基础的铺垫,尽管我们对这次乞食经历一开始悬着的心放置下来了,但是对于发明一个崭新的有别于“漂母”形象的施惠人这一要求,诗人并未满足我们。这里的施主自始至终都是匿名的,连他的职业、社会地位、住宅的坐落位置统统都是匿名的,他在这首诗中最终并未得到对半分的待遇;诗,更为侧重于乞食者一方心路历程的刻画。或许可以说,这个样子最好,符合我们对施惠人的普遍设想,他位于这样一个历史暗角似乎更利于我们对乞食行为——这件事还可能在其他诗人的命运中重演,只不过我们已很难在诗中发现巨人的影子了——的叙述与评估,我们可以在施惠人处于喑哑状况中发挥我们对乞食这件事的想象力。
一个临时救济的空间即将消遁,一个历史性契机也将逝去,唯有在字面意义上予以记述,才可延缓那离去的速度;现在,这首诗分步骤地提示我们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引导我们去评估诗人出任乞食者这一使节在名誉上有无损失。至少我们难以察觉到其中的不妥之处,认为其中的细节足以取信,换言之,我们已经丧失了对那个空间、那个时代乞食真相的其他想象,接受着这一诗文本圈定的妥帖景象。由于它合乎普遍的预期,也以最希望看到的样子为描写对象,“乞食”作为一种题材,已经被掏空了:一个关于如何写的标准内藏在这首诗中,凡是低于这个水平的创作——另一些关系到当事人切肤之痛的诗——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乞食者。在陶渊明这首诗面前——这首诗通过千年历史光阴锤炼已成为一个内在的施惠人,何尝不是对那诗中施主的长久报答——类似的诗扮演着乞食者角色来到跟前,来到这首诗曾经拓展的精神空间、记忆空间、情感空间,除非其中的幸运儿超脱而出,再度为乞食正名,才有可能把陶渊明这首诗、这个文本施主的影响力削弱,并使之匿名化,以迎来自身作为一首气势得当的乞食之诗所应有的另一个足以千年流传的历史使命。
❶陶渊明通过《乞食》一诗确立了一个“乞食者”形象,我们不禁担心他生活窘迫、斯文扫地;通常,我们认为早期诗歌作品已没有深度阐释的必要性,它们的含义已经明摆在那里,但作为一位当代诗人、一个同行,应有兴趣也要有雄心采用今人的思维重新理解这些作品,这些作品也只有在一种新条件下被再度阐释,才真切地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
编辑/黄德海
这些作品也只有在一种新条件下被再度阐释,才真切地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