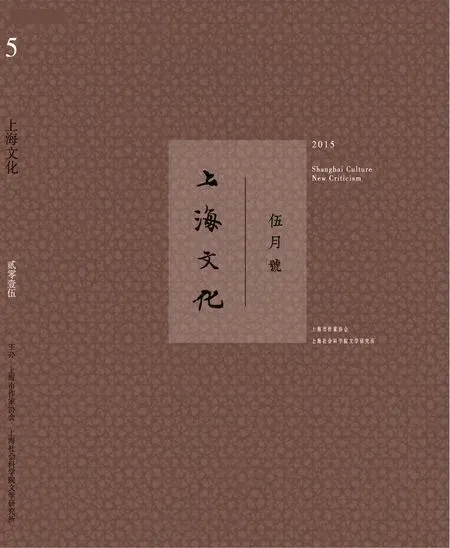成心与初心黄丽群《海边的房间》
张定浩
成心与初心黄丽群《海边的房间》
张定浩
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没有光线。官能既无所不在也全面引退,空气里有各种理所当然、不需符号背书的诡异自明性,天经地义,像他抚养她那样天经地义。像她屈膝腿弯、他侧身轮廓那样天经地义。他轨迹确定的热手不断顺流着她披在枕边的冷发,掠过她耳后脖根。
没有抗拒,没有颤喘,没有狎弄。她古怪地直觉这不过会像一场外科手术,有肉体被打开,有内在被治疗,有夙愿被超渡,然后江湖两忘。他双手扶住她腰与乳之间紧致侧身,将她脸面朝下翻趴过来,揭开她运动T-Shirt的下摆(自六年级班导庄老师带她买少女内衣穿的那日开始,她的睡眠一定规矩无惑地由各式运动长裤与长短袖T恤包裹)。她双臂往前越过耳际伸展,帮助衣物卸离,处女的雪背在夜里豁然开朗。
——黄丽群《海边的房间》
身为中医的继父要留住自小相依为命的养女,不让她随男友远走高飞,他半夜来到养女床前,用祖传针术使之瘫痪。在黄丽群最具声名的短篇小说《海边的房间》里,最具原创性的,并非某种社会新闻和影视剧里见惯不惊的暴力、情欲乃至伦理戏,而是某种作者企图捕捉的“诡异自明性”,如此,我们不绝于口的所谓现实的荒诞离奇遂在小说家这里转化成人世的“天经地义”。
在这个资讯发达信息爆棚的网路时代,无数平庸的书写者都在抱怨小说何为虚构何为。因为,就对现实事件了解的快捷和深广程度,他们和媒体用户相比毫无优势可言,而他们可怜的想象力,甚至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罪犯。人类心灵对于事件的感受力,有点类似眼睛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力,天然受制于距离的远近。那些一边刷着微博一边哀叹社会变化剧烈、时代面目全非的成年人,其实就好像一个刚刚拿到望远镜的孩子,他们能够发现的并不是一个新大陆,而只是自己过去的局限。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会把对历史的无知等同于历史,把自己的耳闻目睹等同于现实,把一切不适归咎于时代和社会,把自己的意见视为确凿无误的知识。普通人这么做,是值得怜悯的;小说书写者若也这么做,则是匪夷所思的。
《海边的房间》将父女亲情翻手成不伦,又将这种不伦再覆手为不可告人的亲情,第一层翻覆是社会新闻,第二层翻覆才抵达小说
以此为背景,可以看出黄丽群作为一位小说书写者的努力。《海边的房间》将父女亲情翻手成不伦,又将这种不伦再覆手为不可告人的亲情,第一层翻覆是社会新闻,第二层翻覆才抵达小说。“有肉体被打开,有内在被治疗,有夙愿被超渡。”因为有些隐秘难与人言,有些情感无从表述,有些事实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一说就错,一传就失真,于是才需要现代小说的存在,借助虚构面纱之伟力,帮助人们将肉体打开,将内在治疗,将夙愿超渡。
只不过,在黄丽群的小说里,这种帮助似乎过于依赖那位如旁观者般的隐形作者的叙述了,换而言之,在她的大部分小说里,人物都有如那位被施以针术的瘫痪女孩,不能自主行动,却可以维持某种骇人的优美与悲戚,而作者就是那位身怀绝技的医师,掌控一切的幸与不幸。纪大伟曾敏锐地指出黄丽群小说中人物对于“算”的执迷和偏执,但在“算”的问题上更为执迷和偏执的毋宁说是作者本人。《海边的房间》的作者尝试理解一切善与恶,测算各种人心的起伏明暗,并提炼出典雅细密有质感的汉语,像制作配方精准的西式点心,连苦涩的比重也先行设置。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是完美无瑕的短篇小说,堪称文学奖作品的典范,却也因此,很奇怪地,缺失了一些动人。
这种缺失,也许在作者另一些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入梦者》,讲一个平庸到极致不受任何异性喜爱的男人,因为一份交友来信而焕然一新,最后偶然发现这位女网友只是自己午夜梦游的分身;比如《猫病》,借猫咪的发情写一位独身年长女子的晦暗又汹涌的情欲;又比如《有信》,写一位中年男教师出门上班时忽然从信箱里发现一封貌似情书的信件,一路思前想后,意乱情迷,最后拆开,却是初恋女友来信,央他帮忙解决孩子入学问题;又比如《贞女如玉》,一个相貌平庸身材粗短的房产女中介养成按摩的习惯,“付钱买各种不一样的男人在她身上光明正大摸一个小时”,一次在按摩时忽然恼怒于自己情欲的奔涌,转而诬赖安静清纯的按摩小哥猥亵,却被店家告知这位按摩师傅也是女生。如是,洞若观火的第三人称叙事,情欲压抑的畸零者的人设、紧凑有序的对手戏而非芜杂纷扰的群戏,意识流的时序闪回以及略带反转的精巧结构,似乎已经成为作者操练纯熟的套路,也帮助作者成为台湾三大文学奖的囊括者。
在一篇评论王聪威小说的短文中,丁允恭曾设身处地坦陈文学奖的存在对台湾文学的巨大影响,“我们以上以及以降的数个世代纯文学写作人,几乎都要靠文学奖取得入场券,或甚至把它当成比出版还要重要的杀人执照,而这个趋势与权威性,随着写作取得有效认证管道的日益局限,更有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也因此,透过文学奖所选拔的纯文学菁英,也习于用‘文学奖体’来写作”(《王聪威:自由穿行小说‘这边’与‘那边’》)。所谓台湾的“文学奖体”,在我想来,有点类似于内地的“选刊体”,同样是一战成名式的遴选,同样受制于有限几位评委或编辑的趣味,每每要在艺术性和可读性之间努力找寻平衡,却往往容易陷入写作视野的牢笼。
“文学奖体”和“选刊体”,其更为古老的先驱或许是《古文观止》之类的选本。鲁迅曾谈过所谓“选本的势力”,“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大多倾向于讲究作品的成熟度或者说是完成度,但文学的悖谬之处在于,它的所谓成熟和完成一转瞬就意味着衰朽和陈腐。与其他技艺不同,文学是“日日新,又日新”之物,或者,用吉尔·德勒兹的术语,是一种“生成”,西西弗斯式地不断重新开始。每位小说书写者都需要文学奖和选刊的肯定,这是必要的激励,但有时也会转化成一种隐性的束缚,令小说书写者无意中遁入对现有成功模式的重复,而不是一再奋力回到写作的初心。
《跌倒的绿小人》写于2000年,彼时作者刚满二十岁,以九九之名初涉小说。时隔十余年,这篇以作者后来很少采用的第一人称写就、通篇对话体的早期小说,却是黄丽群小说中我相对最喜欢的一篇。
绿小人是台北新款红绿灯里的小人,每逢绿灯时会显示一个走路的绿小人,随着倒数秒数的减少,小人会越走越快,乃至奔跑起来。“我”和高中死党老B听说,那个绿小人,偶尔,在倒数两秒快跑的时刻,会跌倒。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于是,某个夏日,他们一个刚辞职一个已失业,约定在十字路口守着红绿灯,买来面包、口香糖、水还有烟,像是看午夜球赛的架势,他们要看跌倒的绿小人。
这样的场景,即便这么简单复述一下都是足够动人的,它让我想起北野武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夏日的不朽光芒,少年人尚存的纯真,以及初涉社会的落魄无聊,它们裹挟在一起,藏匿在两人之间仿佛无休无止的讥诮拌嘴中,仿佛时间停止,每一件无聊的事都可以拿出来晾晒,就像童年。
“不是说每二十次就有一次吗?该不会真的是随机的吧?现在几次了?”
“嗯,二十八次。”
“二十八次?”我怪道,“不是二十六次吗?”
“二十八次啦。”
“不对啊,我明明算了二十六次。”
“可是我算二十八次啊,”老B说,“你数学太烂了。”
“你数学又有多好?我们一样烂!以前你每年都跟我一起补考。”
“屁啦,我只有升高三那年补考过数学好不好。”
“你放什么美国屁?你明明三年都补考。”
“就算三年都补考又怎样?我算得很清楚!二十八次!”
“二十六次!”
——《跌倒的绿小人》
两个人后来终于看到了一次绿小人的跌倒。作者很准确地写出了那种情感耗尽之后的淡然而非狂喜。这时候,老B忽然提议还要再看一次绿小人跌倒,
“可是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下雨?等到被某个酒驾的白痴撞死?”
“我被太多可爱的谎言唬弄过,”老B没有抬头看我,只是说不上来多么神往地注目着红绿灯。“你知道我为了那些谎言,等过太多等不到的电话、神话、屁话、废话。对统一发票很可能对上八百万张还中不了一张。但这个,”他指了指对面,“这个绿小人不会唬弄我。”
——《跌倒的绿小人》
这里有显而易见的作者意图,和简单直接的人生哲理,更加成熟更具掌控力的小说书写者或许会嫌之粗糙,但读惯了太多圆熟作品的小说读者如我,却会被它的青涩与诚挚打动。我想,这里面未必是一种吃腻大鱼大肉后贪吃蔬菜的口味调适,它也许更关乎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存在依据。我以为的好小说,不仅是橱窗里的技艺展现,更是一种有力的邀请,邀请读者共同进入一种可能的、需要探索的未知生活,一起重新经历世界的长成和历史的流转,用最准确的方式抵达生命本身的模糊,并找回他们自己。张新颖曾经拿沈从文和当代作家比较,“沈从文写得比较粗糙的小说,打个比方,每个作品就像一块矿石,这块矿石的背后有它所属于的矿,或者说一块块矿石加起来就指向一个矿,这个矿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的作品,也许非常精致,不像矿石那样粗糙,是一个打磨得很漂亮的成品,你把成品和矿石放在一起比较,当然是成品看上去悦目,但是你从这个成品中找不到它的矿”。以此为喻,《跌倒的绿小人》就仿佛一块粗糙的矿石,《海边的房间》则是精致的成品,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其中尚待发掘的生活容量的大小。
进而,作为正式以本名行世的第一部小说集,“海边的房间”这个书名也可以视为作者在有意无意间的自喻——面对人世的海洋,作者专意营构自己小小的房间,收留一些边缘人定居于此。我又想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海浪》,同为女作家,同与海有关,同样精练如诗甚至令人神魂颠倒的语言,甚至也都秉持意识流的写法,但《海浪》显然更为浩瀚,它不仅是要试图打开某一个人的封闭世界,而是要让众声喧哗奔腾流动的世界在相互碰撞冲击中自行打开。在《海边的房间》后记里,黄丽群自言是长久地“在潮间带上发呆”,如此,不归大地不属海洋,虽然时常也有浪花扑鼻,终究还是近于讨巧的企图两全。因为少了一点点的奋不顾身,那大海也就仅仅成为从房间里窥望的风景,甚至连房间本身也只是静止的风景,它不会令我们有纵身其中的愿望,也不会催生我们任何的变化。
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