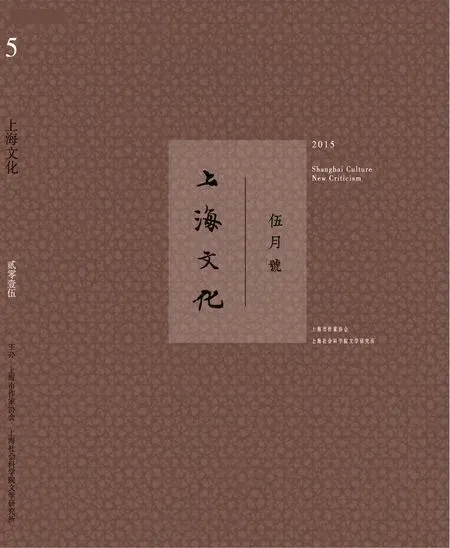谁为你作证诗人马雁
唐甜
谁为你作证诗人马雁
唐甜
1
但我主要还是喜欢看她的面容,然后试着对她微笑
就连看马雁的照片,都是一件让我流连忘返的事情。当然我曾经是搜集过马雁的照片的,她的长相,就是让人喜欢看。面孔是可以流露内心的,更何况还有肢体语言,可以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我主要还是喜欢看她的面容,然后试着对她微笑。因为基本上,她的笑容总是更加灿烂,所以不能不微笑呵。但是她的文集封面展示的形象,大概也很深入我心,严峻而略带哀愁的眼睛——我常常在看不懂的时候就翻到封面看她,疏远而迷人的样子。左边嘴角有一颗痣,爱调笑;目光清澈,透出一点隐忍,好像已经能想象出她说话时那种爽朗的语气,斩钉截铁的,飞珠溅玉一般……
这两种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诗集的第一辑“迷人之食”里刻意交织在一起的两部分内容。“我缓慢吞食这蜜样的/嫣红尸体”(《樱桃》2004春,“迷人之食”一语之出处),也即生活的真相,一部分是甜蜜喜悦,另一部分则是痛苦失望,两者在樱桃身上含混地存在为一体,当我们吞咽下生活时,也必然地同时接受这二者。“迷人之食”中的诗并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往往是语调轻松的诗后面便接着表达惘然无奈的文字,随后却又是腻甜的幸福的基调,继之以猛然的反转,如此刻意地一路跌宕反复下来,(情绪的强烈程度亦在加深)以模仿某种生活的真实与秩序。
我试图偏狭地概括马雁走过的世界,它总体上是什么样子;我也无数次不得不凝视,她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她自己所做的具体的改造工作——它们无一不是精致的、可爱的、艰难的、奇诡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兴味盎然的。其实马雁本人,对于生活本身,始终采取的是那样平等的邀请的态度。或者说,是毫不防护的。
我注意到,我会忍不住随时在“生活”与“世界”之间切换,生活与世界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世界往往是对“生活”一词的抽象。
我所能讲述的是文本的马雁,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个区分,它不会距离真实太远的,否则要文本何用。但是还是很遗憾,马雁主要的两本作品集《马雁散文集》和《马雁诗集》里几乎都找不到马雁大学时代的作品了。简直让人心痒痒!她的青春的妩媚的那些时光我也没有捞得见着,见着的人都是侥幸啊,何其侥幸。
2
马雁也写散文,达数十万字。马雁的散文分两种,有显然的即兴之作,也不乏深思熟虑之后下笔的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人文字的特别之处。在即兴之作中,尤其突出的特点是酣畅淋漓的快,单句、短句在其中无所顾忌地密集出现。在我的阅读史上,这几乎可被称为一个别具一格的发明。在一则诗歌笔记里,她写道“我喜欢直接,一针见血。”“直接”和“一针见血”这两个词很有个性,也完全道出她独特的散文风格的奥秘。直接,是直接地给出思考过程,你看见她如何清晰地思考,迅疾地反应,“我就跟她学着一路水往低处流了事”也委实是很畅快的。而紧接着,她还写道“当然也可能并没有什么血可见,那么给出这个空无也是对的,给出毫无惊奇的现实”。
我甚至一度有种阅读马雁的散文能开发智力的感觉……
而快有时会快到不假思索的程度,下笔任性,也颇为一观,因为她说了,“我讨厌解释,我有高级的厌烦情绪”。我有时在她留下的那些不许人跟随的天女散花一般的文字(简称散文)里看来看去,既觉得摸不着头脑,又觉得相隔好近,心里一紧,虽是对着断垣一块,也高兴一回。反正雁过留声,但是那雁是谁也抓不着的。有些羚羊挂角的意味,总之是个武林高手,不留招式痕迹。
马雁的语言也极有辨识度,尤其是由于她对活泼的生活化语言的运用,有时常常达成一种幽默的效果,不由得让人佩服那些有着语言敏感的人点铁成金的能力。在语言和修辞方面,可体味的太多了,我想它可以成为读者私人的乐趣,且是“悠然见南山”那样不期许的喜悦,所以不加赘述。在《马雁散文集》的编后记中秦晓宇也有较详尽的赏析,或可成为一个引导的方向,但其中也有些似乎是过度诠释了,不尽可取。
马雁独特的散文世界,构成的意义在于对日常生活的纪念,如同《爱劳动的人有爱情》、《必须保护黑社会》,直接地将我们与那些数千年前的烦恼和喜悦对接,去观看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现在每天就像写日记一样写一首古诗,因为好像诗歌中有生命,又因为我的生活中有诗歌”,是这样一种态度。在她之前,以这样一种方式读诗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直面生活的粗糙与质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领会诗歌的生命力所在——更好的说法是,让它们回到本来的面目。而又不仅是读诗,读小说、读史、读文献……均有一种清洁而平易的态度,不特为深入浅出,而是直击要害,并且伴随着品质的要求。
3
“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古典学术与西方哲学,历史与宗教,音乐、绘画、建筑、电影等各门类艺术,围棋,帮会和秘密语,神秘学,敦煌学,文字学,革命学,法学,医学,飞碟和外星人,女权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张春桥,田园城市理论与世界国家生成理论……她无不格致,充满了严肃的热情”(《何谓“读书与跌宕自喜”》秦晓宇)。如此驳杂的兴趣门类均整理自马雁的散文,她广泛的热情让人惊奇,却也不足为怪,一个热爱生活、认真生活的人,似乎都天然地匹配有一颗愿意认识一切、理解一切的好奇心。它不断地采撷世间万事万物的光辉,研究它们各自的道理,而增益和完满的却是对自己的认识。“在我看来,投入的阅读行为应当如此:积极的读者可以使一本书不只是它自身,而是整个生命,整个宇宙。”整个生命,是阅读者的生命,整个宇宙,是你正在其中探索的宇宙。
而对应地在诗歌写作中,她有类似的表达,“其实我们不需要写出什么样精美的作品,我们只是通过诗歌,一步一步澄清自己,一步一步了解黑暗……”(《谈片》2002)
马雁的散文与诗歌的风格并不相同,其中或许有刻意为之的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片风貌不同的森林,有着相似的照亮它们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个人,也是每一个人。马雁的文字所记录的是诗人对生活和生命直击式的感悟,对自己的珍重,而如果我们愿意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世界的秩序,这个态度可描述为是对每一种平凡姿态的关注与珍重。马雁每一个时期的诗歌中,都不乏这样主题的创作,《乡村女教师》则属于早期的作品。
又不仅是读诗,读小说、读史、读文献……均有一种清洁而平易的态度,不特为深入浅出,而是直击要害,并且伴随着品质的要求
乡村女教师
短暂秋天的纪念
他们裂开嘴巴,笑。他们在教室里奔跑,
我呵斥,禁止乃至沉默。是的,后来我就
沉没在他们中间。逐渐找到仍旧陌生的东西。
那一年,我们在山脚下的小楼里,谈论到午夜。
在空旷的水泥广场上,看陌生的星星。可是,
当我们爬上朽塌的山崖时,毕竟是在晚风中唱吟。
我们将花光最后一分钱。桌子上的花,很快
就要枯萎,洒落……乡村女教师的生活。
她经常在课堂上走神,经常造一些离奇的句子。
有时候,她在教室间走动,像个丢东西的人。
2002年秋
这首诗根基于经验,但是根据时空的不同,又可以做出“虚”、“实”之分,从“那一年”引起的一段带有浪漫气质回忆,显然是作为现实的一种对照。而被这些回忆所分隔成的两部分现实经验,又前后呼应着,显示出某种变化来:她“逐渐找到仍旧陌生的东西”,但也像个丢了东西的人,在教室间走动;有的东西在渐渐增多,有的东西在渐渐减少。但无力感是两个时期共有的特征:在此刻“我呵斥,禁止乃至沉默”,“沉没”;而那段唱吟的美好时光,终因为“我们将花光最后一分钱”,随着桌子上的花的枯萎而自然地结束……
马雁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是一首平淡的抒情诗,记录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生活,有一些平淡的难以捕捉的痛苦,在不受控制的世界里感到无奈的人。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变化,女主人公自己也在慢慢地变化着。平淡的痛苦里,有着同样平淡的幸福感。这是诗人感受和理解中世界的某种真相,所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得以克服和超越……(《无力的成就》2010.9.23)
一部个人的写作史,是对克服和超越的记录,也同样是和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怀疑做抗争的历史。如同她在《未免有情,我私人的鲁迅记忆》中为鲁迅所说,“鲁迅也常说,他灵魂里太多黑暗是不能拿来与年青人分享的。可是又是什么样的黑暗呢?他有什么罪?他一直想要尝试的是过一种更正确的生活,却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在错误中彷徨。而这只是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正确,这就是原因”。
马雁诚如她自己所言:偏执。因此即使是困顿的样子,阐释的其实是刚强。“她也有一些挚友,跟她一起在这个璀璨都市灯光里飞驰,谁都没有她那么固执的要冲往那片亮光。她一言不发,但是她说,那是毁灭。那是欢乐。那是极致。那是一切。”冲往那片亮光,直到无处可走,成为文字的虚空里一个坚毅的殉道人。
4
在我看来,马雁的诗艺已达臻相对成熟的阶段,但是以我的能力来说要完全解读它们是困难的。因此,我挑选了一首更加平易的早期诗作,以展现她创作风貌的一角。
看荷花的记事
我们在清晨五点醒来,听见外面的雨。
头一天,你在花坛等我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些雨。现在,它们变大了,有动人的声音。而我们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两个人。亲密
让我们显得更年轻,更像一对恋人。所以,你不羞于亲吻我的脸颊。此刻,我想起一句曾让我深受感动的话,“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生中最幸福的,又再降临
在我身上。她仿佛从来没有中断过,仿佛一直
埋伏在那些没有痕迹的日期中间。我们穿过雨,
穿过了绿和透明。整个秋天,你的被打湿的头发
都在滴水。没有很多人看见了我们,那是一个清晨。
五点,我们穿过校园,经过我看了好几个春天的桃树,
到起着涟漪的勺海。一勺水也做了海,我们看荷花。
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因为它是一首关于幸福的诗,幸福而且颇有惺惺相惜的意味,是如此的幸福,以至于没有一丝杂质。因此它也可以成为“完美”的代表之一。乐极生悲就不行,不够完美,大概是突如其来的喜悦,让人没有安全感。就像在博物馆里面对一件巧夺天工的玉器,就像范蠡在溪边初见着西施……为了表达完美,为了“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最,则必须掐头去尾,截取一个片段。
“我们在清晨五点醒来,听见外面的雨。”所以这个片段,是在雨声里开始的。我最喜欢下雨天,原因有很多,譬如说,是人生如梦一场的异样证明,至少这雨并不是在我的期许中降临,也不会因我而更久地流连或更快速地结束;但是它又很像是,多愁善感的灵魂的喊声,隔着时空,在寥廓的人生中不分彼此地呼应着。多少对雨天心存厌烦的人,就不能领会其中的美感了。但是如下几行佩索阿的诗句或许更有说服力。
在下雨
在下雨。一片寂静,因为雨除了
安宁的声音再造不出别的声音。
在下雨。天已睡去。这时灵魂已被
无知而多情的摸索夺去。
在下雨。我的本质(我所是的那个人)已被我取消。
雨是如此宁静,仿佛融进了
(那并非用云朵制造的)大气,
仿佛不是雨,只是一阵低语,
在低语中变得模糊。
在下雨。一切都不发光。
没有风在翱翔。也感觉不到
有天空。天在下雨,遥远,不确定,
就像确定的事物没准是个谎言,
就像某种被渴望的伟大事物在对我们撒谎。
在下雨。什么都不能让我激动。
“头一天,你在花坛等我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些雨。现在,它们变大了,有动人的声音。”雨在诗中,是幸福的象征,是“动人”的幸福,同时也成为被截取的这段时光予人的整体印象。诗人的控制能力极佳,体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机,在今天这最美好的时光之前,向前铺垫一点点,向后,也渲染一点点。所以其实“雨”是在昨天开始的,只是在今天,它们才变大了,而我们也更加亲密了。并且,更要命的是,这样甜蜜还不算完,夏季的幸福一直漫漶至秋季,“整个秋天,你的被打湿的头发/都在滴水。”所以,在前后的稳稳的陪衬下,今日这一日,才显得这样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幸福。
“亲密/让我们显得更年轻,更像一对恋人。所以,/你不羞于亲吻我的脸颊。”此处的“亲密”,似乎来得突然,让人猜想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般不尽的言外之意;而另一种解释则是,为了躲雨,恋人相互依偎,因此是亲密的。
“一生中最幸福的,又再降临/在我身上。”幸福到极点是什么样呢,就是谁此刻幸福,就永远幸福。永远还不够,“她仿佛从来没有中断过,仿佛一直/埋伏在那些没有痕迹的日期中间。”连过去的日子也一起被这幸福照亮,整个人生都是幸福的。
桃花马雁也曾在日记里提到过,是图书馆拐角处的桃花,她也许是一个人寂寞地看了几个春天。如今,是“我们经过”,经过“我”独自的岁月,只是经过,遂成为一个背景,一切都在幸福的雨里消散去,无限地后退,让步于现实的涟漪。涟漪,是心潮起伏,是幸福带来的颤动,微小的,安宁的,而自有一种矜持,一种尺度。也是清洁的,没有很多人看见“我们”,而我们却看见了荷花。
全诗节奏优美明快,形式上回环复沓,穿过雨,穿过绿色和透明,穿过了校园,而韵味不绝,真是营造气氛的高手。诗的内容紧凑,还归因于过程的省略,仅仅以“我们穿过雨,/穿过了绿和透明。”便概括了“我们”穿过校园的行动,值得回味的是“我们在清晨五点醒来”,同样“五点,我们穿过校园”,到达了勺海,这或许是一个提醒,这根本是一场想象中的观看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样艺术化的处理都是成功的。
这是一个无所不美,充溢着积极明亮的色调的时刻,一勺水也做了海,一点雨也滋润着整个秋天,清晨五点钟也足以成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看清洁而妖娆的荷花,象征希望的花。披淋着大雨,一件看荷花的记事,荷花也才将将出现,也就将将退场——是退场,也是永远不退场。
在马雁的诗集里,这首诗只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幸福不应该被过分地强调,这样它是平凡的,简单的,是真的,也是假的。是拥有的,也是失去的,是多少人的,最美好的时光。
幸福不应该被过分地强调,这样它是平凡的,简单的,是真的,也是假的
5
在马雁的诗论中,则很少直接地谈及自己写诗的主题,而更多地表达对一些更加普适性的问题的关注。这些评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高度上,事实上也对诗人自己的写作是具有指导意义。在马雁的诗论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她对于语言问题的严肃而深入的探讨,但是并不难理解,语言问题牵涉之广,使它既是成为一门科学,也几乎关于整个世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的能够反应世界秩序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诗人们倾向于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诗歌的写作和传播在今天的艰难):选择一些特殊的语素群,偏爱易于被影射、被误读的经验,这使诗歌呈现出相似的面貌。……如果不同的语素不能获得平等的被书写权,则相应地,会有某一些经验不被书写。只要存在着‘不被’,那么所有的‘被’也会空洞无效。这将使诗歌艺术失去尊严。因此,我和朋友们致力于寻找、质疑和运用最基本的诗歌手段,不满足于现有的语法框架内的语素搬运,我们希望使不同语素获得平等的被书写权”(《自从我写诗》2009)。
哪些经验不被书写呢?我想在这里只需要做一个大略的区分,它们在“易于被影射、被误读的经验”之外,而这应该不难想象。语素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的术语,它的定义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构成词语的材料。海德格尔提出,词语即存在,与此相似的,“语素获得平等的被书写权”的意味也不言自明。而马雁对于诗歌所应实现的这个功能,是相当笃定的,“但诗歌并非如此(和塑料桶一样有用),否则不会有那么多诗人在振振有辞,他们拚命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那不存在的权利”;“我还想,诗歌并不是比日常生活更高的东西。每个人都在进行着创造,我们都为实现一个完美的世界而使用语言”(《塑料桶》2010)。
高贵和骄傲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同时也有显而易见的区别,譬如说,一个是完成时,而另一个则永远属于未完成时。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马雁是一个保持骄傲的人,但是我同样不吝惜于使用高贵这个词,在驰往高贵(它是迢迢万里之外的远)的道路之上,那个奋力的身影即使失败于渺渺起点,在她迈出坚定的脚步之时,她分明已经被高贵所照亮了。并且终其旅途,她都应该只被这种光芒所笼罩着,即使是在身涉龃龉之时。
我无法看见她全部的痛苦,但是我把自己有过的痛苦也视作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值域的问题。但是我宁愿看到她是在路上的人,在路上吃苦的人,并且也依然努力去克服和超越——“这个世界过于整饬,以至于多数人都为此感到厌倦和劳累,每天在同样的世界里行走的是可怜的囚徒。诗歌应该有这样的野心使他们获得解脱”(《塑料桶》2010)。
我还在想,文人总难落得一个好的身世,这并不让人意外,大凡能让我们记住的文人,尤其如此——我们记住他们,大概也无非为了寻一寻身世之感。或者是为了刺激其他的某些既有敏感神经。于是又想起了马雁对于诗歌的抱负,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个死循环,如果阅读者的趣味、认知不做改变,更好的诗歌一样会面临传播的问题,正如同她的高贵,如今谁来为她作证?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