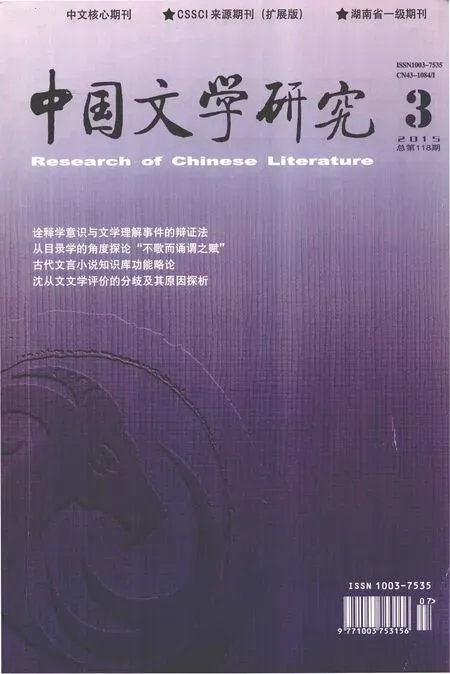从目录学的角度探论“不歌而诵谓之赋”——马积高先生《赋史》关于赋体论述的启示
何新文 张家国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古今学人较为普遍的解释是指赋在形式上具有“不歌而诵”的特点。现当代学者,如朱光潜认为“赋可诵不可歌”,骆玉明谓“赋之命名,取义于诵”,费振刚说“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马积高先生既在《赋史》中力主“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指出此说“为探本之论”,后来又在所著《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进一步论述了汉代“以赋的不歌而诵与诗相区别”的观点。
但是,由于刘、班叙论颇欠周详,《七略》、《汉志》义例缺焉无闻。故对于这一提法的解释,也存在着疑惑和分歧。如明人陈山毓《赋略序》曰:
古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夫词非己作,春秋列国大夫之赋也;体由自制,郑庄、晋蒍之赋也。皆“不歌而诵”之义也。
在这里,陈山毓明言“不歌而诵”是指春秋列国大夫“赋诗”时的诵读《诗》篇,和鲁隐公元年郑庄公赋“大隧”、僖公五年晋大夫士蒍赋“狐裘”之类的自作韵句,而不一定是指楚汉赋体。当代学者,也有人“不同意赋为不歌而诵的说法”,或以为这一说法只是就“赋诗”问题而言,而“不涉及赋体定义”。
本文以为,《汉志》的这一说法不仅源远流长、影响深广,而且关系到对于赋体命名、赋体特征诸多问题的认识,故有必要讨论清楚。而回到目录学著作本身,即从《七略》与《汉志》对于诗赋著录及其序论撰写体例的角度切入的分析探讨,或许更有可能得到接近客观的看法。
一、从《诗赋略》的著录而言:“歌诗”可诵可歌,“赋”则不歌而诵
《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故其所载及论述,主要是刘向、刘歆的主张,不是班固个人的意见。而作为文学目录,《诗赋略》著录两类文体,一类是歌诗,一类是赋。这是我们理解“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的基本事实和基本前提。
《诗赋略》首先著录的是“赋”。依次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等四种,共78 家、1004 篇,多是可诵不可歌的作品。
汉赋作品大半描写事物,又“篇幅较长,辞藻较富丽,字句段落较参差不齐,所以宜于诵不宜于歌”,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有学者对于《诗赋略》所著录的“屈原赋”是否也“不歌而诵”则有怀疑。其理由,一是屈原的《九歌》本是根据民间祭神乐歌写成的,二是楚辞作品的末尾往往系之以歌,如“乱曰”之类。关于屈原《九歌》,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原本是可以歌唱的,但至汉人视“楚辞”为“赋”之时就应该是不歌而诵的了,《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而不是“歌唱”,便是一个证明。至于所谓“乱曰”,则除其为音乐术语之外,尚有其它意义,如《离骚》末尾有“乱曰”五句总结全诗,王逸《楚辞章句》即注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以明所趣之意也”;洪兴祖《补注》亦谓“乱者,总理一赋之终”。可见王逸、洪兴祖都认为楚辞之“乱”是总撮全诗旨意之辞,而与音乐没有关系。又如马积高先生所言:“屈、宋之作称为‘辞’,盖取其‘不歌而诵’之意,以与和乐的歌诗相别”,“辞、赋既均为‘不歌而诵’之体,故汉人辞、赋每连称或混称”。
其次著录的是“诗”,分为“歌诗”一种,计28 家、314篇。
《诗赋略》名义为“诗”与“赋”,为何在实际著录诗和分类时却不称“诗”而称作“歌诗”呢?这一方面,当是与《六艺略》著录《诗经》而《六艺略序》及《诗》类小序均称为“诗”相区别;另一方面,当是与《诗赋略》所著录的“诗”原本就称为“歌诗”有关。且看《诗赋略》所著录:
《高祖歌诗》二篇。《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
以上所著录的28 家作品的标题,无一例外都标明有“歌诗”二字,表明这些作品原本就可以歌唱。那么,这些作品为什么均题为“歌诗”呢?刘、班义例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汉书·礼乐志》对《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的记载中,却可得到启发。如《礼乐志》载: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诗曰: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郊祀歌》十九章,其诗曰:练时日,侯有望,焫膋萧,延四方。九重开,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
这两篇作品,标题均作“歌”,其歌词则称作“诗”。由此可知这些在汉代称为“诗”或“歌诗”的作品,多是“歌”与“诗”一身二任,乃至“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诗赋略》及《礼乐志》之所以如此记载,其意在突出“歌诗”有声有义、既可歌又可诵的两栖性特点。故如《六艺略》“诗”类小序所谓:“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这正是作为目录学家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对于“诗”或“歌诗”重要特征的共同认识与界说。
而且,《诗赋略》所著录“歌诗”作品的可歌性,也有可考之处。如列入其首的“《高祖歌诗》二篇”,宋王应麟《汉志考证》以为即是汉高祖所作《大风歌》与《鸿鹄歌》。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高祖“《风起》之诗”,是他既定天下之后过家乡沛县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时所作,当时就“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其他作品,如《吴、楚、汝南歌诗》,《邯郸、河间歌诗》,《齐、郑歌诗》,《淮南歌诗》,《京兆尹、秦歌诗》,《河东、蒲反歌诗》,《洛阳歌诗》,《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南郡歌诗》等等,“盖皆出于民间”,都是可以“被诸管弦而播之廊庙”的。还有,其中所谓“声曲折”,据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等考辨,即是“歌声之谱”。
如此看来,《诗赋略》因“赋”与“歌诗”而设立此一文学目录,而所著录的“赋”不歌而诵,“歌诗”则可歌可诵,这正是诗与赋在形式体类上的区别。
二、从《诗赋略序》及《七略》叙论撰写体例看:“不歌而诵”是界定赋体
1.《诗赋略序》总言“诗、赋”,再分述“赋”与“诗”的不同特点
如《序》云:
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不歌而诵谓之赋。《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序诗、赋为五种。
上引《诗赋略·序》,相当于《诗赋略》的说明或类例。它与《七略》各略之序一样,先发凡起例,以“凡诗、赋”若干家若干篇一语承前启后,然后再分两大段分别叙论“诗、赋”二体:
第一段先言“赋”。如果依程千帆先生的标点,即是先有“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界定赋体,接着才引“《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再转到春秋之时,诸侯卿大夫盟会及宴享场合不歌而诵读《诗》的方式也叫做“赋”。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起,屈原、荀况皆“作赋以讽”,其后宋玉及汉人赋远离古《诗》“风谕之义”,因而扬雄评之为“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段文字,虽然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春秋卿大夫“称《诗》谕志”的史事,但却主要是就赋体产生的历史条件而言及的。序文开头以“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断语领起,并且以主要的篇幅叙论“赋”(并非是“诗”)的历史发展和评骘“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不同价值,其逻辑顺序仍然清晰可寻,且一气贯下。
第二段再谈“诗”。作者概括自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之后,及至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的各种“歌诗”。肯定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认识价值。很显然,这些乐府“歌谣”和土“风”民“讴”,与“不歌而诵”之赋不同,它们是可歌可诵的。
若如上述,则《诗赋略》一方面著录各地土风歌谣与可以被诸管弦的“歌诗”,一方面著录“不歌而诵”的楚汉辞赋;《诗赋略序》首引“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语,与后文“立乐府而采歌谣”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对而言,既是说明其著录“诗”、“赋”的例类,也是在区分“赋”与“诗”不同的形式特点。
对此,刘师培曾说明刘氏父子及《汉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不歌而诵谓之赋,则诗歌皆可诵者也)”;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亦谓“《七略》序赋为四种,其歌诗与之别”,“要之,《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马积高先生论述“赋的基本文体特征及其演变”时,也引述了章太炎这段话,且肯定“在当时条件下,汉人的这种界定是有据的,也是大体合理的”。
2.《六艺略序》的撰写体例与《诗赋略序》一致,可资佐证
上述《诗赋略序》先总提“诗、赋”,然后再界定诗、赋各体特点的撰写体例,在《六艺略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六艺略序》曰: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序六艺为九种。
可见《六艺略序》也是先以“凡六艺”若干家、若干篇一语承前启后,再分别定义《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的。明白这一点,可以佐证《诗赋略序》开宗明义“不歌而诵谓之赋”的目的,是在界定赋体特点,而不是去解释什么叫做“赋诗”。
3.《汉志》及《别录》“谓之”一词所指称的对象皆是名词或专有名称
我们推论“不歌而诵谓之赋”是在说明赋体特点,而不是去解释所谓“赋诗”,还可以从“谓之”一词的用法得到证明。考《汉书·艺文志》(亦即二刘《七略》)及刘向《别录》所用“谓之”一词的共有如下4 处7 例:
(1)《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六艺略》“诗”类序)
(2)《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六艺略》“论语”类序)
(3)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诗赋略序》)
(4)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传谓之《古论》。(《全汉文》卷38 刘向《别录》佚文)
在古汉语里,“谓”可训“为”;“谓之”,尤“为之”也,可释为“叫”、“叫做”等,引申有“指称、意指”之意。上引《汉志》4 例、《别录》3 例运用“谓之”的句子,都是就某一概念、文体、词语所下的断语,“谓之”后面所指称的对象皆是文体名或专有名称,如“诗”、“歌”、“论语”、“赋”、“鲁论”、“齐论”、“古论”。若诚如是,则“不歌而诵谓之赋”句的“赋”,就应该是与《六艺略》“诗”类序所称的“诗”、“歌”一样,都是文体名称。而且,若将《六艺略》“诗序”中的两个“谓之”句,与《诗赋略序》中的这个“谓之”句连起来,即成为一个关于“诗”、“歌”、“赋”三体的完整判断句:
诵其言谓之诗,
咏其声谓之歌,
不歌而诵谓之赋。
我们在惊讶之时,还必须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目录学家对于自先秦楚汉以来“诗”、“歌”、“赋”三种文艺形式发展演变之迹及其关系、特点的精准把握,在《七略》的《六艺略》“诗类序”与《诗赋略序》的相关表述中还做到了相互呼应和关照。或许正因为如此,清代批评家刘熙载才在其《艺概》中说:
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诗概》)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大抵歌凭心,诵凭目。方凭目之际,欲歌焉,庸有暇乎?(《赋概》)刘熙载相当完整地理解了汉代目录学家关于“诗”、“歌”、“赋”三者关系及各自特点的意见,而且还分析了赋“凭目”而“诵”而非“凭心”而“歌”的原因。
反之,若将“不歌而诵谓之赋”句之“赋”解释为“赋《诗》”之“赋”或“赋《诗》”本身,就不仅与《诗赋略》界说并著录“诗、赋”二体的主旨相疏离或节外生枝,而且也文理不通。因为,汉人言“赋诗”之“赋”有“或造篇、或诵古”之“二义”,也说写诗为“赋诗”或“作诗”、“自为诗”、“自为歌诗”等,但却不称“造篇”为“诵诗”的;还有,以“不歌而诵”定义所谓“赋《诗》”,则与“赋《诗》”之《诗》原本就兼有“可歌可诵”的品质相矛盾。
因此,只有将“不歌而诵谓之赋”句之“赋”解释为文体名之“赋”,则不存在上述矛盾,而自然通顺。
三、从汉赋及“诵读”辞赋风尚看:“不歌而诵谓之赋”观念形成有现实依据
“赋”本有不歌而诵之义。《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这里的“赋”与“诵”,都是指诵读。又《晋语》三载“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韦昭《国语解》亦注曰“不歌曰诵”。《左传》多载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之例,其所谓“赋诗”是相对于“歌诗”④而言的,指不用与歌曲配合的诵读古《诗》或诵读自作诗篇。例如隐公三年载“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唐孔颖达《正义》曰:“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然则,‘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又《楚辞·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王逸注曰:“赋,诵也”。
由春秋时卿士大夫不歌而诵读“诗”篇被称为“赋诗言志”,再到“不歌而诵”的楚辞汉赋作品,进而还有了汉代朝野诵读辞赋的风气。这一现象,在《史记》、《汉书》中也颇有记载。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及《汉书·司马相如传》均载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又载“太子喜(王)褒所为《甘泉》及《洞箫》(赋)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如上所述,“赋”原本有不歌而诵之义,宜诵不宜歌的辞赋作品与此前重章叠韵、可歌可诵的《诗》不同,再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的诵读辞赋之风,这些既说明赋在汉代已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学文本,也说明《诗赋略序》“不歌而诵谓之赋”观念的产生已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四、汉以后学者的解读使“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本义由晦而显
在《诗赋略》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的说法以后,历代学者较为普遍的解释都是指赋在形式上具有“不歌而诵”的特点。
西晋人皇甫谧可能是现知最早作出这一解释的,其《三都赋序》云: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皇甫谧从《诗赋略序》“《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等一大段与春秋“赋《诗》谕志”牵连的文字中,引出“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冠以“古人”这一称说主体,再申述自己对于赋体的论说,从而表明了视“不歌而诵谓之赋”为“古人”赋体定义的认识。
再就是梁代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诠赋》篇更试图定义赋体。刘勰先引《毛诗序》“《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之语,以论证自已关于“赋者铺也”的定义,原本就与《诗序》所谓“六义”其二的“赋”相同;而《毛传》所云“登高能赋”的“赋”是指“诗”,则与赋体相异。所以,下文才说:“《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而“刘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两句,明显是对刘向“不歌而诵谓之赋”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句的缩减,若读者再对照地读着刘、班原句,就自然会得出“不歌而诵谓之赋”与“赋者古诗之流也”是刘、班二人各自定义赋体的看法。
唐徐坚《初学记》卷21 文部“文章第五”叙事曰:
文章者,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盖诗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诵谓之赋。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矣。三代之后,篇什稍多。
《初学记》在“文部”的“文章”类“叙事”中,于“诗言志、歌永言”之后列出“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显然是将“赋”与“诗”、“歌”并列为“文章”三体,认为“不歌而诵”是赋的文体特点之一。
降及明清,诸如谢榛、章学诚、刘熙载所云:
《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若《子虚》《上林》,可诵不可歌也(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至于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
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
也很明显,都认为“不歌而诵”是指赋体特征,而不是指所谓“赋诗”的。
直至当代,朱光潜《诗论》指出:
什么叫做赋呢?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的“赋者古诗之流”和在《艺文志》里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是赋的最古的定义;
归纳起来,它有三个特点:就体裁说,赋出于诗,所以不应该离开诗来讲。就作用说,赋是状物诗,宜于写杂沓多端的情态,贵铺张华丽。就性质说,赋可诵不可歌。
朱光潜上述文字,既总结了包括“不歌而诵谓之赋”在内的两条“最古”的赋“定义”,又归纳融入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的结论,仍然同样是:“赋可诵不可歌”。
诚如上述,当我们回到目录学的本身,即从《七略》、《汉志》著录诗赋及其序论撰写体例的角度切入之时,就会发现:《诗赋略》著录诗赋作品的形式区分,《诗赋略序》与《六艺略序》及“诗类”序的撰写,《七略》“谓之”句指称的名称,还有魏晋以来自皇甫谧、刘勰以至刘熙载、朱光潜、马积高等的解释,“不歌而诵谓之赋”一语中“赋”字的意义都是指向“赋体”,《汉志》所谓“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不歌而诵谓之赋”三个单句相连,就构成为一个关于“诗”、“歌”、“赋”三体特征的完整判断句。而这些论述及结论,又并非凭空推论,而是有汉赋作品及当时诵读辞赋之风的现实根据。因此,“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本意是指赋体的特点,而不是所谓“赋诗”,这一结论应该是可信的。马积高先生以此为“比较有权威的说法”,乃至“可谓是探本之论”的判断,亦属言之有据。
〔注释〕
①《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徳音,可以为大夫。”此处“《传》曰”当是引此《毛传》语,但因“不歌而诵”句不见其中,故历来颇有歧见。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则以为“《传》曰”当置于“不歌而诵谓之赋”句之后(齐鲁书社1988 年版,第51 页),极是。故此一句,当是刘向之言,用在此处开头作为对“赋”体下的断语。
②《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自为诗曰”,《高祖本纪》载高祖“自为歌诗曰”;《汉书·礼乐志》载“作‘风起’之诗”、“作十九章之歌”,《王褒传》载“上颇作歌诗”;《后汉书·文苑传》下载“议郎蔡邕等皆赋诗”。
③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释“瞍赋”说:“赋,不歌而诵;疑即今所谓‘朗诵’”(中华书局1962 年新版,第261 页),可谓得之。
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卫献公“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公使歌之,遂诵之”;又,襄公十六年载晋侯“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这两例说明“诗”是可“歌”可“诵”的。
⑤刘勰所谓“赋者铺也”的定义,是继承汉人郑玄注《周礼》“六诗”所言“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而《周礼》“六诗”正是《诗序》“六义”的来源,故后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又直接引郑玄“赋之言铺”此语解释《诗序》六义“其二曰赋”之“赋”。
〔1〕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J〕.文学遗产,1982(2).
〔3〕费振刚.辞与赋〔J〕.文史知识,1984(12).
〔4〕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3〕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5〕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徐坚.初学记(下卷)〔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19〕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