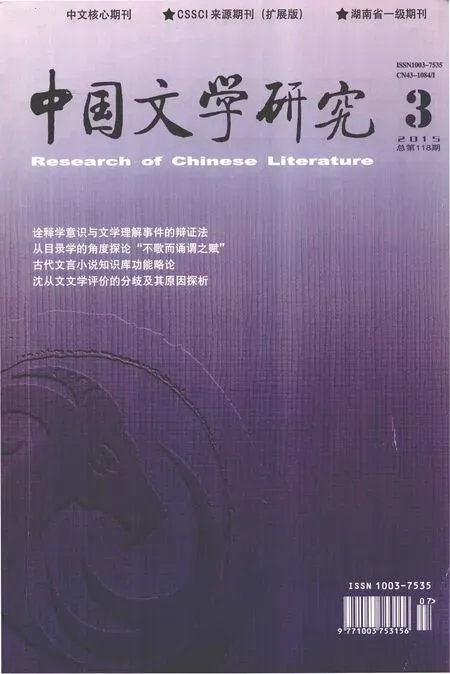浅论消费文化中身体话语的分野
胡 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 湖南 娄底 417000)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斗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之后存在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由于匮乏的逐渐消减,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商品的极大丰富。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消费选择。我国的经济结构重心正逐步由生产转向消费,开始走向让·波德里亚所描述的消费社会。这种以大规模的物(商品)的消费为特征的情形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态度。
在消费社会里,一切以交换为目的。所有物质的、非物质形态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近年来,消费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逐渐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移,符号系统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现代广告和传媒形象在当代文化实践中成为一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基于这种变化,一种最美丽、最珍贵、最眩目的物品脱颖而出——这就是身体。“消费者文化不但使欲望、需求和快感带上了性的色彩,并将身体转化为其主要载体”。在消费文化的催生下,身体在作为罪恶和耻辱的代表黯然沉寂了几千年之后,承担着性解放符号和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获得了全面解放。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环绕着它的是青春、美貌、活力、阳光或阴柔,人们对它趋之若骛。文学作为时代之子,市场对身体的消费必然会体现在文学中。
将身体当做商品,在文学中尽情消费身体成为年轻的“晚生代”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晚生代”作家被多数评论家界定为“断裂的一代”,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他们的成长面临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发生了一个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象征的过程”。没有上山下乡的沉重经历,没有文革的梦魇,他们目睹并经历着一个欲望解禁全民致富、消解经典亵渎神圣的时代,宏大叙事的律令成为空洞的所指,他们的生活无比顺利却又缺乏激情,在这个平凡而忙碌的时代里,理想的消解、生活的平面化、精神的自由轻松使他们狂热躁动的青春找不到可以发泄和释放的渠道。他们再也找不到可以令他们振奋、充满激情的理由。他们不再为任何理念而活,他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一切神圣、意义、价值等宏大词汇消亡的消费社会里,身体成为“晚生代”作家宣告自己存在,释放欲望的最佳表现对象。他们因此放弃了种种形而上的追求,沉浸于当下,茫然仓促中,他们找住自己的身体,将它作为唯一的救赎,认可平凡琐碎的生活,并竭力在其中尽可能地挖掘身体的感受,以此来确证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尽管裹挟着重重欲望的身体是“晚生代”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但在具体的创作中,由于性别的差异,晚生代作家在关于身体的写作中,又呈现出相异的文学景观:一方面是取消女性主体地位,将女性作为欲望对象的男性创作,另一方面则是将身体作为可供观赏交换的“美丽商品”的女性写作。
一、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欲望写作
在晚生代的笔下,身体呈现出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面貌。这一突破与崭新性,并非来自对身体象征意义的重新书写,而是恰恰相反,它完全抖落历史赋予身体的所有象征意义,而且与初期王安忆们对身体的认可、单纯地表现身体截然不同。王安忆们将身体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认可它的本能冲动性,看似对身体的彻底还原,实则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蕴涵着巨大的文化革命意味。而在晚生代这里,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还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真正的还原,它让身体只是身体,甚至可以说是肉体,而不是其他,它与任何文化意义和价值无关,它只不过是个人生存的载体。它不再受到任何观念的支配,也拒绝被任何统治性的话语收编。晚生代作家对身体的还原主要体现在对待身体的本质即欲望的认识上。他们认可的欲望是一种纯粹与原始的欲望,不夹杂任何文化的色彩,也不带有任何文化的面具。它只与器官、原始冲动、本能需求有关,并且只指向个体,是一种凌驾于道德评判之上的自由欲望。试图从这些欲望表达中寻找潜在的价值尺度,几乎是一种可笑的妄想。晚生代男作家的身体写作主要体现在:在以女性客体化为代价的前提下,彻底体认身体的本质——性,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
对身体本质的还原突出地表现在朱文的《我爱美元》中。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朱文毫不掩饰地敞开了对物欲的渴求,极力赞美以美元为象征符号的金钱和物欲。他撕毁旧有的种种虚伪的价值面纱,将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袒露出来,置于阳光下。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获利的欲望,对赢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朱文不无热情地认可金钱所代表的价值:“美元就是美丽的元,美好的元”,“那种叫美元的东西有着一张多么可爱的脸,满让人神往的异国情调”。同时,他诚恳地建议:“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朱文平静地向我们揭开了我们长期羞于开口的事实:作为现实生存者,我们渴望金钱,向往财富。然而,撕毁人类贪欲的诗意面具,并不是朱文的最终指向目标。“‘美元’在此只不过是暗示了一条通向更高欲望的楼梯,成为一张门票而已。穿过欲望这条五彩缤纷的禁忌小径,尽头指向的是欲望的最终本体:身体。它成为所有欲望的综合表达,并且百川归海般也成为所有欲望的终极表达,因此,‘我爱美元’其实只不过是对这一身体欲望——‘性’——的换形表述而已”。对金钱欲望的解禁仅仅只是作为对身体欲望全面解放的前奏曲。在美元的中和下,性和其他物质一样,成为一件普普通通的商品。弗罗姆曾经指出:“‘性解放’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依德,但我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消费社会里,性不自觉地成为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消费品。消解了金钱的神圣性后,朱文进一步袒露占有金钱背后的心理动机:“我们知道,性不是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我们需要它,这是事实,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正好商场里有买,为什么不呢?从商场买来的也是货真价实的,它放在我们的菜蓝里,同其他菜一样,我们不要对它有更多的想法。就像吃肉那样,你张开嘴把性吃下去吧,只要别噎着”。朱文将性作为生活的原材料引入叙述,启动了自己创作。他剔除了附加在“性”上的心理和社会意义,将其作为人的本能或机械性的日常行为,最大程度地抛弃了它的文化意义及神秘色彩。在商品社会里,性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本体,它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甚至可以被交换和买卖。它成了个体的一种自由需要,随身体的需要而随意出现,人们毋须克制自己的欲望。
朱文们并不着意于裸露的性场面的展示和描写,他们如同吃饭吸烟般自然平常地记录性,无非是想撕裂这东西,向性禁忌发出尖锐的挑战,向现行的伦理道德挑战。正如陈晓明指出的:“性对于朱文是一个支点,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他只需要这个支点,就能把我们的世界颠覆,这本身说明了我们的文明确实有孱弱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在朱文们力图颠覆传统,将身体的本能合法化、合理化的同时,却是以女性客体化为代价的。在朱文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女性似乎都是一个没有主体知觉的生物性存在,她没有面貌,没有思想,甚至千人一面。在男性主体的眼中,她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漂亮与否,性感与否。正因为将女性作为无主体的物,《我爱美元》中,“我”才诚挚地请求女友陪自己的父亲睡觉,对妹妹是否成为“鸡”并不在意,甚至考虑将朋友们都介绍过去,让妹妹生意兴隆,同时亦希望她“会唆使她的同行姐妹们业余时间来看看她的哥哥,七折或者八折”。
韩东的《障碍》在欲望化的自白中,同样流露出浓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况味。在这篇小说中,所有的男性都是作为欲望主体,而女性则是实现他们欲望的客体。石林终于突破了“朋友妻不可欺”的障碍,在好朋友的女友身上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冲动,同时又忐忑不安地担心“有关内容将成为我和朱浩今后交往中的真正障碍”。多年后与朱浩的一次谈话,彻底解除了石林的担忧。原来是朱浩怜悯朋友当时拮据的单身生活,将王玉友情输送到石林身边:“我让她去许城找你就是那个意思”。女性的物化于此流露无遗。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只是他们深厚友情的见证,是他们传递情意的礼物。对于文中的另一男性东海而言,王玉是他迫切渴望缓解性压抑的对象,至于和王玉是否有感情,王玉本人对此有何看法,一概不在他的考虑之列。而在邱华栋的笔下,金钱与女人,是奋斗在城市中的“拉斯蒂涅”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和最大动力,也是他们衡量自己“成功”的外在尺度。他作品中的“我”无一例外的都是男性,而女性则始终处于被男性的观照和审视中。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始终处于叙事的两极:或者是物质化身的“妖女,或者是慰藉心灵的“天使”。无论哪种视角,女性都围绕男性而存在,她们的身体始终处于男性的视野中,对于男性而言,“她们全都是物质的化身,欲望的容器以及简单快乐的催发器”,正如他在《新美人》中所表达的“归根到底这世界其实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仿佛有一架我们看不见的摄影机,这架摄影机就是一双男人的眼睛,它规定好了视角,让一切都具有了它预先设计的特征”。而在何顿的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中,世界是男人的,女人只是玩偶,作为男人的性对象而存在。在《黑道》中,何顿写道:“世界上只有三样东西吸引男人:金钱、女人和权势。”对男人而言,女人的“好”无非“也只是漂亮、丰满、性感,顶多加上对爱情专一、不滥交的名号。”作品中的女性则往往将自己的生活攀附于男性身上,作为男性世界的寄生者而存在。
男性中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写作,使他们在对传统文化禁忌与意识形态的解构、冲击、亵渎的同时,并没有获得身体的真正解放,“在消费社会的指引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无济于事”。身体贴近了,灵魂却远离了。他们坠入了虚无的深渊。突破了道德的禁忌,欲望平息后的石林却感觉:“然而此刻,某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属于我”。欲望冲动释放的背后,虚无出现了。邱华栋的叙事集中体现了这种欲望满足后透彻骨髓的无聊、倦怠与虚妄。主人公怀着熊熊野心来到都市,欲图征服城市。经过一番浴血奋战,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爱情、身体、理想为筹码获取了都市法则的通行证,最终赢得了金钱和女人,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但是在功成名就后却深感空虚无聊,生活失去意义。作品中叙述者“我”成功后常常感到迷惘和困惑,痛感生活的无聊。《哭泣游戏》的“我”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将黄红梅作为自己的行为艺术作品,在变态的自我欣赏中爱上自己的“作品”。《午夜狂欢》中,于磊的幻象游历、秦杰的神经麻木症、何晓的“飞行死亡”所表现的欲望满足后的虚妄则达到了颠峰和极致。虚无的出现暗示着:肉身的彻底解放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幸福安定,相反,它使人陷入了虚无的焦虑中。
二、观赏交换的女性写作
与朱文、韩东们并驾齐驱行驶在消费时代的是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女作家们。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意识形态的禁忌相继被打破,给卫慧们提供了更为自由、开放和无所顾忌的写作环境和创作心态。这使她们的身体写作更为放肆和裸露,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表现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她们的写作具有了时代特点,不仅作为观赏和交换对象的身体成为她们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也使她们的创作汇入时代汹涌澎湃的消费浪潮中,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满足人们观赏和窥视欲的精神消费品。卫慧们的写作以一种肆无忌惮的身体/性表述,传达了整个精神领域的空虚与绝望以及在这种空虚与绝望中,我们依赖的只有我们的身体和无穷的欲望。她们的出现,昭示着“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理念在当代消费大众的享乐主义的胁迫下已经寿终正寝。卫慧、棉棉们通过身体的“祛魅”及世俗化实施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观念的象征性颠覆,生产了她们媚俗不媚上的身体叙事文本。她们的写作记叙了价值体系崩溃时代,青年一代苍白乏味的成长经历、叛逆不羁的青春岁月、无所适从的人生道路、半真半假的情感游戏、迷惘徘徊的道德选择,给文学史增添了一群挟裹着鲜明时代特征的青年群像,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
客观地说,卫慧、棉棉们在创作之始,并未有意将身体作为一种商业炒作的密码,或许确实如棉棉所言,身体写作并非一种愚蠢的冲动,而是用身体领会宇宙万物,这个过程是纯洁的,透明的。然而,随着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个“纯洁的、透明的”身体变得复杂而暧昧起来了。它敏锐地嗅到了巨大的商机。消费社会里,大众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本能从压抑它的理性的暴虐下解放出来以后,“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她们的创作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给享乐的身体提供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满足了大众的窥视欲及其对一息尚存的传统伦理道德的驱逐。她们笔下的身体逐渐脱离了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而成为“资本意义的身体,为了与资本进行一本万利的交换而精心打造的身体”,它与“生命欲望无关,这是色情的堕落。肉体不在欲望之中,而是在交换之中,意义不在表达中,而在传播中;快感不在生命之中,而是在利润之中。肉体和新奇,成了文化消费商品博览会上必不可少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身体便成了交换和观赏的身体,以满足大众的需求来获取商业上的成功。这从她们作品无处不在的性事叙述中可见一斑。以卫慧为例,她的四篇小说集《蝴蝶的尖叫》、《像卫慧一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男女之间的性事。《艾夏》是女主人公由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的性行为的编年史册;《愈夜愈美丽》中的“她”具有见了男人就上床的献身精神,让读者叹而感之;《陌生人说话》中的“他”与“她”在欲望的指使下完成了从邂逅到上床的仪式化过程;《上海宝贝》其实不过是倪可在情与欲中挣扎的一场矫情表演;《欲望手枪》写的是主人公米妮和四个男人之间具有虐恋倾向的性活动,“欲望手枪”成为女人的性爱自助餐和满足自虐冲动的象征物。在她们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上演了一幕幕如火如荼的现代性爱肥皂剧。在男女主人公们乐此不疲如火如荼的性邂逅中,欲望的身体沉沦在色情的身体中。波德里亚曾指出:“应该将作为欲望交换符号的载体的色情身体与作为幻觉及欲望栖息处的身体区分开来,在身体/冲动,身体/幻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欲望的个体结构,而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的社会功能。在此意义中,色情的命令,和礼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礼仪一样,受到符号工具化编码规则的约束,只不过是功用性命令的一种变体或隐喻”。
身体的价值曾作为意识形态最尖锐矛盾的发源地,具有颠覆性价值。但是这种颠覆性是以历史语境中所真实存在的身体压抑为前提的。然而在“身体被出售着,美丽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的消费社会,它的颠覆性价值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沦为与现实同构的存在。“身体由于永远处于被压抑状态而被赋予了破坏特权,现在,在解放身体的过程中,这个特权已经到达了终点”。因此,在卫慧们看似获得全面解放的身体,只是简单地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有关灵魂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更具功用性的当代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一意识形态主要保护的是个人主义体系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它甚至还强化了它们,给予它们一种几乎是决定性的根据,因为它用身体的自发表现取代了完全内在的灵魂超验性,然而,这种表现是虚假的。当代神话建构的身体并不比灵魂更加物质,它和后者一样,是一种观念,或者应该这么说,因为观念一词尚不足以表达,一种部分客体化了的物品,一种享有优先权并因此得到投入的双重体。它就像灵魂在其自己的时代中那样,变成了客观化的特权体支柱——消费伦理的指导性神话”。
卫慧、棉棉们的写作,本想通过身体来寻找无根无父时代的个体生存依据,通过个人叙事来对抗宏大叙事,却使身体被重新“圣化”——只不过是消费话语中的神话而已。原因在于她们在面对业已沦为消费社会“最美的商品”的身体时,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思考,放弃了任何疑虑与挣扎,以一种投怀送抱的姿态纵身跃入肉欲狂欢的时代。以卫慧的代表作《上海宝贝》为例,尽管作品也略微提及主人公倪可承受着性与爱割裂的痛苦,但在叙事中,却分明传递出性并不必然与爱冲突,性的快乐是可以与爱分离的,它不必然也勿须导向真正的爱情,它是可以与爱情相异而并存的事实,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性爱必须统一的道学。在她具体的表述中,她“让我们感到她在写作中常常有一种快感要呻吟出来”,让人们感到她并不反对这种结合,而是抱着一种欣赏认同的姿态。这样,她的写作就无法穿越身体,仅仅停留在欲望的层面,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并没有太多建设性的作用,而只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一次暗送秋波、眉目传情的色情消费。劳伦斯曾愤怒地谴责:“色情就是企图侮辱性,玷污性,这是不可原谅的……那完全是对人体的亵渎,对至关重要的人类关系的亵渎”!
一个时代给出一个时代的身体模型。尽管卫慧们狂乱放纵的写作给文坛增添了“异类”的空间和道德破禁的震撼,但频频出现在酒吧、时刻愤世嫉俗的情绪、颓废放荡的青春,使她们的面孔趋同,仿佛使用的是同一具身体。在消费文化的催化和作用下,她们的写作不幸落入消费主义的槽模中,关于身体和性爱隐私的叙事成为商品化时代最具市场价值的促销代码。
小 结
晚生代作家将身体打造成消费社会中最炫目的商品,使身体摆脱重重规划,搔首弄姿地摇曳在当代文坛。就文学本身而言,晚生代创作的意义既未传递深刻的思想内容,亦未带来任何形式上的创新,但他们的创作却使个体通过身体欲望的释放,逐渐摆脱了外在的权威而独立,建立了基于个体自由伦理的叙事,以绝对个体化的写作消解了传统道德,通过“我消费我存在”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首先,晚生代的创作以身体为基点,关注身体的本能与感官享受,剥离了历史、文化、伦理等一切宏大叙事附加于身体的种种规划,在某种意义上,也最大程度地摧毁了集体理念对基于身体的个体命运的统治,将个体感受从群体体验中解放出来。晚生代作家坚持将有真切生命感受的孤独个体作为叙述主体,以展示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的偶然命运为叙事基点,让个体生命的体验与生活的碎片在身体的舒展中尽情铺展。
其次,晚生代作家将个体统统还原成身体性的存在,确认身体的正当诉求,将身体作为个体反抗诸神的绝对武器。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我思、我欲、我愿的自由神取代道德法官的上帝的位置,自我的内心法庭取代世俗判断的道德审判。晚生代作家否认文学任何的教化功能,反对道德批评家以道德判决的方式高高在上地评判作品,而是希望通过叙事使个体生命还原到本真状态,尽力保留个体的自由与完整,抵御传统道德规范对个体的压制和打击,使脆弱的个体生命从道德归罪中解脱出来,让人物命运的偶然与残缺变得比任何事情都尤为重要。恰如评论家葛红兵所言:“新生代小说不能给我们提供道德戒律和信条,它和善的说教无缘,新生代创作也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因素,它与无主体的‘真’无缘,但是,它给我们的是人对于存在的超越了伦理学教条以及认识论局限的完全建立于个体的自由领受基础之上的原始性体验。这种体验来自于我们身体的深处,与我们存在的本原比任何道德小说、客观小说都要接近”。
某种程度上,晚生代作家的确完成了摧毁旧道德的任务。但摧毁并非文学追求的最终目的,摧毁是为了重建。重建自然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的道德。晚生代显然未曾在崩塌的废墟上建立起新质。在强调个人化、身体化的同时,他们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社会生活,忽略了群体情感。事实上,文学终究不是个人的呢喃叙事,个人化、身体化也并不意味着从时代中抽身而退,不是逃避对时代的责任和对传统的绝对反叛,而是显现为人与世界的必然相遇,显现为个人对以往人类精神的主动承续,以及凭借一己的存在来承担起人类命运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卡夫卡的创作无疑是绝对个体性的创作,但他的写作却以一己之感受穿越了人类生存的困境,照耀了人类精神的天空。在这个意义日渐匮乏的时代,小说应重聚反抗生存危机的力量,对当下的精神困境担当责任,而不应为当下的精神沦落推波助澜。当然,小说从来也无力承当世界终极阐释者的角色,小说对世界的解释和意义的呈现从来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个人化的,小说只是人类“乌托邦情结”的理想寓所之一。然而,在人类的精神圣火点燃的地方,终必看到诗意栖居的曙光。
〔1〕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3.
〔3〕陈思和.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为例〔J〕.小说界,2000(3).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朱文.我爱美元〔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6〕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弗洛姆.生命之爱〔M〕.罗原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陈晓明.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J〕.大家,1999(5).
〔9〕韩东.障碍〔J〕.花城,1995(4).
〔10〕何顿.黑道〔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1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2〕张柠.肉身符号的文化分析〔J〕.花城,2003(1).
〔13〕吴炫.穿越经典——“晚生代”文学及若干热点作品局限评述〔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12).
〔14〕葛红兵.晚生代的意义——晚生代作家论写作札记〔J〕.山花,19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