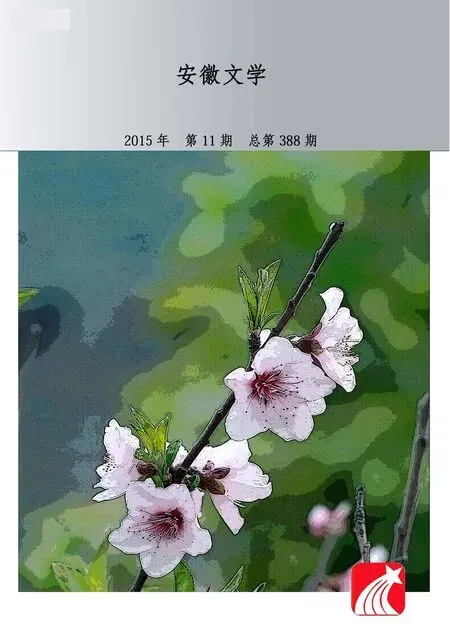从《喜福会》的东方面孔说开去
黄春燕
北京物资学院外语学院
从《喜福会》的东方面孔说开去
黄春燕
北京物资学院外语学院
中国观众对《喜福会》这部作品相对熟悉,要归功于1997年把它搬上好莱坞银幕的导演王颖。不过这部作品1989年在美国问世之初,就已颇受瞩目,并被公认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因此而跻身美国文学经典排行榜。作为一部具有“东方面孔”的作品,《喜福会》在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立足的艰辛历程中写下了功不可没的一笔。
喜福会 东方面孔 文学
纵观华裔美国文学发展史,早期作品几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比如1961年雷庭招的长篇小说《吃碗茶》出版伊始市场反应冷淡,其后长达十多年无人问津,直到1979年才被重新“发现”,后来被改编成舞台剧,1989年被拍成了电影。1975年,距《吃碗茶》首次出版14年之后,汤亭亭凭借《女勇士》一书成功打入美国主流文学市场,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一。尽管汤亭亭强调自己是美国人,追求文化融合与认同,她的东方面孔已然成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代表,她的成功也代表着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圈内地位的标志性上升。在她之后,1989年面世的《喜福会》也大获成功。1991年,第二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任碧莲出版了《典型美国人》。
在不少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是其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但不少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更关注的是两种文化的磨合与并存,他们探讨的也是如何融化和打破文化坚冰,例如汤亭亭和任碧莲都在作品中“乐观地提倡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共存”(程爱民,10),因此,这些作品大多围绕着两种面孔甚至多种肤色的面孔共存、互动或和谐共处的情节和主题而展开,华裔美国文学也因此成为美国文学中最需要“看脸”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东方面孔的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的接受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于1997年出版了《亚裔美国女作家》一书,该书的出版本身就证明一些华裔美国作家“尤其是汤亭亭和谭恩美,在美国拥有大批主流读者(主要是女性主义读者)”(Dhingra,183)。布鲁姆在该书的引言指出,有研究者甚至把谭恩美极具个性化的表述和惠特曼相提并论,认为“她在多年之后步惠特曼后尘奏响了一首‘自我之歌’”(Bloom,1-2)。对于评论界如此高的褒扬,哈罗德倒是希望能够让时间来证明,谭恩美的作品究竟是能够牢牢跻身美国经典文学之列,还只是昙花一现。
在谈到谭恩美及其作品的成功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认为由于西方主流社会缺乏对东方社会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因此,他们把谭恩美小说中所描绘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故事等同于现实中的东方世界,把它当做人种志、纪录片甚至文献资料一样来理解和阅读。这种读者反映显然超出了作者本人的预期,她在2007年接受《南都周刊》的采访时指出,自己的作品想要传达的是个性化的体验,小说中不少内容来自母亲的回忆以及给她讲述的故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无需贴上“中国”这个宏大的标签,她本人无意成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虽然由于从小的家庭教育,她的很多观点被打上中国烙印。
显然,忽视作家创作中的个人因素是造成西方读者误读的原因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谭恩美小说只是反映了她自己本人的一些态度和认知,受视角局限,对东方传统文化存在着误读或想象夸大的成分,这也是不少华裔美国作家作品共同的缺陷之一。因此,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谭恩美的作品不属于华裔美国文学,这种将谭恩美彻底逐出华裔美国文学队伍的做法未免有些偏激,但至少提醒读者注意,不要将谭恩美小说中的细节和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细节等同起来,作者受其个体成长经历、环境以及认知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小说中创造的是她个人所理解和想象的中国故事,不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
相比于当西方白人社会对本作品的态度以肯定为主,国内研究者们对其作品的评价毁誉参半,即谭恩美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渲染了西方人眼中的‘他者’中国,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东方与西方存在的差异与隔阂,并表达出了和解共生的主题和愿望。笔者认为,对于谭恩美之类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呈现方式,首先必须承认这些作家视角的双重性,作为曾经的边缘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并因为这种视角的局限性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误读。
其实西方读者也未尝没有判断力,有国外研究者发现,他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对包括《喜福会》在内的某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令人反感的种种‘夸大’、‘扭曲’、‘错误概念’、‘偏见’”(Wilcoxon,316-317)也心知肚明。比如学生们对《喜福会》中割肉救母的情节就深表不解和怀疑。如果说在几十年前,中国在西方社会眼中宛如一个披着面纱的神秘少女,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媒体的发展和信息获得手段的多样化,东方面孔已越来越为西方所熟知,西方的读者也不再把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当做唯一的信息了解渠道。
二、在不同肤色的面孔之间取舍
同很多华裔美国文学一样,《喜福会》里的母女两代人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华人形象。母亲们算得上是第一代移民,她们从东方来到西方,试图在两种面孔中求得平衡;女儿们生存在美国本土文化以及东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夹缝人,是外黄内白的香蕉人。和女儿们相比,母亲们试图坚守自己的文化的传统,坚持自己的判断和选择。龚琳达在讲述自己当年待嫁前的情景时,有这么一大段对自己心理转变的描写:
我独自守在窗前,沉思遐想,不禁扪心自问,什么叫命?比如汾河的水,在夏天是黄浊的,到了冬天,则是蓝绿的,但它还是汾河。可我,能像汾河那样变幻不定,却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我依旧坐在窗边,只见窗帘被风挟持着,狂暴地掀着,鼓荡着。窗外,雨大了,浇得路人嚷嚷着四下逃窜。我笑了。我感到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风的力量。诚然,我无法看见风,但我能看见它带动河水缓缓地朝同一方向淌去,灌溉滋养大地,就像给田野披上一张银光闪闪的大网。它可以令人们任意咒骂,也可以使人欢欣鼓舞。
……
我仰头对镜傲然地一笑,便把那条大红绣花绸巾将自己的脸蒙盖上,同时,也将感刚刚冒出的种种思想蒙盖上。即使蒙在红绸巾下,我依旧十分明白,我究竟是谁。当下,我对自己许诺:我经常会讲双亲的期望记在心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我”。①
龚琳达发现眼前的汾河颜色随季节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她意识到风虽柔软无形,却充满力量。此时的琳达仿佛如梦初醒,她不再对未来充满未知的恐惧。尽管有红绸巾蒙盖,但她觉得自己依然能看清前方,明白自己是谁。红绸巾把真实的自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抗拒。她希望自己像风一样有力,又能像汾河一样,无论外在如何改变,内心始终是原来的自己。琳达的这种心态也正是几位妈妈们的写照,无论脚踏在哪片土地,她们都没有忘记自己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国基因,她们为自己拥有一张东方面孔而感到骄傲。
琳达格外注意人的面容和长相,认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质性格甚至命运。她慨叹自己的女儿除了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内部则全是美国制造的。她明白自己虽然有时能够展露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229)。她意识到,“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230)。即便同为东方面孔,也未必能顺畅沟通,就好比她和自己的女儿“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确实不同的”(238)。对琳达来说,这是个看脸的社会。母亲要求女儿们保持中国面孔,看懂中国面孔,更深层的涵义不言而喻。但事实上,母亲也发现,生活在西方社会,很难保持单纯的东方面孔,她们自己,始终苦于在两种面孔之间求得平衡:“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舍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238)。
更令人尴尬的是,琳达们在美国被归入边缘人群,回到自己的祖国,也被视为外来人群。琳达曾在阔别40年会后回过一次大陆,她发现,即便自己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用人民币,讲当地方言,但仍然能被人一眼看出是海外移民,买东西也要照外国人的标准付高出几倍的价钱。她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去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238)。琳达们被这种无法融入和回归的而感到苦恼和困惑。她们自以为不变的东方面孔在别人眼里却早已变了颜色。
三、结语
有研究者曾作过这样的总结:“海外华裔文学主要就是通过对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通过两代人新旧生活观念的差异的描写来表现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胡勇,80)。换句话说,《喜福会》借助移民家庭中母女的隔阂与冲突充分展现了东方面孔与西方面孔相遇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两种面孔之间如何取舍,怎样平衡,琳达们的苦恼即便是在中国形象更为西方熟悉和了解的今天,依然也难有完美的解决之道。
注释
①小说引文译文均出自程乃珊(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人的译本.(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以下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不另加注,个别译文笔者有所改动。
[1]Bloom,Harold.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9.
[2]Dhingra Shankar,Lavin.Review of The Joy Luck Club[J].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1999(24-4):183-184.
[3]Wilcoxon,Hardy C.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eyond the Horizon Author(s)[J].New Literary History,1999(27-2):313-328.
[4]程爱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3.
[4]胡勇《文化的乡愁: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5]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