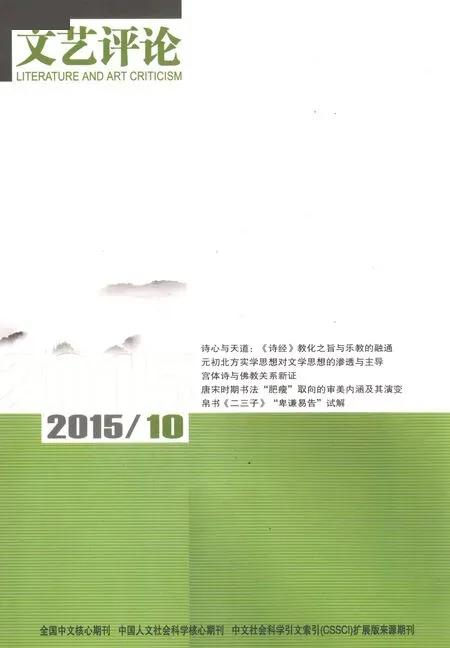刘知几对欧阳修小说观念及小说创作的影响
——兼论文史互渗表象下求其“雅正”的内在理路
吕海龙
刘知几对欧阳修小说观念及小说创作的影响
——兼论文史互渗表象下求其“雅正”的内在理路
吕海龙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史通》”条指出:“刘氏(按:指刘知几)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宋《新唐》,往往采其绪论。”①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云:“唐后诸史中,采《史通》之说者,以欧阳《唐书》为最多,《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兴。”②前贤今人对刘知几及其《史通》极为推重,认为其对欧阳修等在史著修撰体例方面有着影响深远,这是符合事实的。
欧阳修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上也受到了刘知几《史通》的影响。其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持的小说观念,其著述《归田录》等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都深深打上了刘知几《史通》的烙印。而由其检阅完成的《新唐书·列女传》采小说以补《旧唐书》,文史互渗表象下,体现出一种求其“雅正”的内在理路。这亦和刘知几的观点相呼应。详论如下。
一、小说观念方面的影响
“小说”明确作为文类之观念,由来已久,上可溯东汉桓谭、班固等人。当时又被称为“短书”。《文选》卷三十一收录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有《拟李都尉从军》诗云:“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③江淹所言之“短书”是指写给妻子的书信。而李善注“短书”一词时即引桓谭《新论·本造》篇有关“短书”之说法。其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④两者互相参看可知,“短书”是和书信差不多的一种短篇文字。就形式而言,顾名思义,可知篇幅短小。余嘉锡先生认为:“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⑤
桓谭稍后之小说书目尤著者,为班固在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基础上进行整理,“删去浮冗、取其指要”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作品共十五部。其中,除《青史子》外,于《隋书·经籍志》皆不载,具体内容亦不可考,所以只能根据班固、颜师古等人的注文及后人辑佚的断简残章作一些推论。
十五部小说中,大多数在题目或者注语中有“语”“说”或“言”者。其中,题目中明确标明为某“说”者,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此外,《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四家,注语中有“言”“语”字,内容似与语言谈论关系密切。而《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二家,题目中皆有“术”字。《说文解字》曰:“术,邑中道也。”⑦是指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和途径。概为方术之士妄求长生“未央”等言谈。
据班固自注,明确为言“事”之作的小说只有《周考》与《青史子》两部。《青史子》,梁代犹存,见《隋书·经籍志》“燕丹子”条注云:“梁有《青史子》一卷”⑧。原书今佚,现考其辑录内容较全者,有鲁迅从《新书》、《大戴礼记》、《风俗通义》中所得辑本,见《古小说钩沉》第一篇。主要谈及的是周王子胎教及抚育,士大夫贵族出行及祭祀的相关礼仪和规定。
总的看来,就内容而言,班固提到的“小说”应该多为子著“浅薄”杂说,偶有“近史而悠谬者”⑨,所记之内容,也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一些历史资料。
此后,直至《隋书·经籍志》所持“小说”观念,仍然没有大的改变。其子部“小说家”录作品二十五部,分别为:《燕丹子》一卷、《杂语》五卷、《郭子》三卷、《杂对语》三卷、《要用语》四卷、《文对》三卷、《琐语》一卷、《笑林》三卷、《笑苑》四卷、《解颐》二卷、《世说》八卷、《世说》十卷、《小说》十卷、《小说》五卷、《迩说》一卷、《辩林》二十卷、《辩林》二卷、《琼林》七卷、《古今艺术》二十卷、《杂书钞》十三卷、《座右方》八卷、《座右法》一卷、《鲁史欹器图》一卷、《器準图》三卷、《水饰》一卷。⑩其中仍有大量语对辩词类作品,如《杂语》、《杂对语》、《要用语》、《琐语》、《辩林》等。叙事类的作品只有《燕丹子》等寥寥数部。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最早明确提出小说当以“叙事为宗”⑪的观点。刘知几“叙事为宗”的小说观,是建立在殷芸等前代小说家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之上,又受同时代史家李延寿等启发,是对前人创作实践及理论探索的认知、归纳与提高。
南朝梁殷芸《小说》,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用“小说”一词作为书名者。全书于明代已佚。今辑本中收录较全者为上海古籍1984版的周楞伽《殷芸小说》,收录163条。殷芸《小说》大部分内容采自各种杂书,但同时又有自己的选材标准:材料多有较强的叙事色彩。如其第8条为“汉武微行遇刺”事,原注出《幽明录》,清晰交代了事件的起因、经过、高潮及结果。其中亦有刺客数次意欲行刺而未行之细节描写。又如第17条,原出《世说新语》“假谲”篇,记录了曹操与袁绍抢劫别人新婚妻子与曹操所谓梦中杀人事等。有部分出处未明者,概广为流传于民间,或其先已见于他书,后由殷芸整理收录,如第151条,下人被王武子冤杀后,魂魄至天帝处告状,终索王氏性命。故事首尾具完,意在劝诫。总的看来,殷芸《小说》所载内容已经不同于魏晋以前小说的琐屑言论,而对记事较为重视。
刘知几《史通》当为最早提及殷芸《小说》这一作品的撰述内容,也是最早阐发其编撰缘由的理论著作。《梁书》、《南史》之《殷芸传》,皆未提及殷芸著述《小说》一事。《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仅提到:“《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⑫而刘知几于《史通·杂说中》云:“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认为武库失火,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等怪异事件,荒诞不经,所以未入官方正史,而被殷氏编成《小说》一书。
刘氏此说影响颇大,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殷芸《小说》”条目下引刘知几《史通》上段话后,又以小字继续阐发曰:“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事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此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也”⑬。后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序言》、周楞伽《殷芸小说·前言》等皆承其说,遂为定论。
刘知几“叙事为宗”的小说观亦应受初唐史家对小说一体有关看法的影响与启发。刘知几对李延寿评价较高。《六家》篇云:“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刘知几小说叙事观似亦受到李延寿的影响或者启发。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云:“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叠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⑭。这时的小说依然与短书联系在一起,不过在李延寿等史家之观念中,其已经和南北朝时期的“互陈闻见,同异甚多”的叙事类“史牒”作品有类似的功能,甚至略可相提并论。
刘知几在前人及同时代史家的基础之上,鲜明提出“小说”当以“叙事为宗”的观点。至此,对小说本质属性的认识才有了质的变化。《旧唐书·刘子玄传》云,“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时间仓促以及对文学相关认识的自身发展惯性等种种原因,五代后晋年间修撰的《旧唐书》,“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⑮,而其《经籍志》亦基本因袭了《隋书·经籍志》对小说一家的认识。
时至北宋,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艺文志》接受了刘知几的观点,打上了刘氏小说当以“叙事为宗”之观念的烙印。一方面,《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将大量的记言类、科技发明类作品,如《杂对语》、《要用语》、《琐语》、《迩说》、《古今艺术》、《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逐出了小说的队伍。另一方面,大量选入题名为“传”、“记”等的叙事类作品。正如鲁迅指出: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⑯
至宋皇祐中,史籍目录《新唐书·艺文志》中小说队伍急剧扩军,大量“志神怪”、“明因果”的叙事作品开始被欧阳修为代表的史家视为“小说”,而此后,“史部遂无鬼神传”。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和刘知几小说当以“叙事为宗”的观念分不开的。
二、小说创作方面的影响
史著对个体生命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史家的一种共识。刘知几的好友朱敬则深为佩服,叹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⑰所谓制人之“生死”,就是说史著可以使人身后留名得以不朽,即使是圣君贤臣,也要借助史官及史著。
古人对史著非常重视,所以很多小说家亦明确宣布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归为“史补”一类。如晋张华《博物志》卷八标目即“史补”篇。但是,其所记载的内容,却充满了想象色彩。如晋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篇:“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⑱为了帮助燕太子丹逃脱秦国,乌鸦白头,骏马生角,这些内容很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
张华写作《博物志》之事,又被后世小说家以“拾遗”的名目收录自己的作品。如王嘉《拾遗记》卷九“晋时事”云:“(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
对于这些内容,刘知几指出此类小说存在的合理性。《史通·杂述》言:“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但同时也认识到其弊端所在。其于同一篇中接着又说:“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刘知几谈及的是古代小说中“逸事”类作品,重记事,和今天的小说较为接近,比较具有代表性。肯定了“逸事”类小说和历史的关系,认为其为不同于正史的“异说”,同时可以对正史加以补充。但是求其“异”的同时,还要注意辨别“真伪”。这直接影响到了其子刘餗的观点,间接影响到李肇、欧阳修等人。他们对刘知几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为欧阳修的小说创作。
刘餗的《隋唐嘉话序》曰:“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参择吏必于长者,惧其文害。观焉马周上事,与曹参异乎!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非言所也。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⑲这里连用“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等四典,反复说明父亲刘知几对其影响之大,自言“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对于能够证实的内容,即使较为奇幻,也要“书以记异”。但同时又强调辨别真伪的重要性,所载之事,言必有据,不能验证的内容,如“推报应之理”,则“存而不论”。
李肇《国史补》上承刘餗《隋唐嘉话》,并与之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总体而言内容较为客观,少了许多怪异。李肇自序曾云:“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⑳可看出,李肇有着向史著靠拢的意识;所以其在记载人物轶事时,往往爱憎褒贬,表露无遗。即使涉及到最高统治者时,也不讳言。如该书卷中载:“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唯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写出了当时异常复杂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姑息”二字,更是非常直接地写出自己对唐德宗对藩镇的苟安政策的批评。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同时代的官修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内容。
李肇《国史补》其书正如今人周勋初所言,“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线,确立了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㉑。《国史补》较早把奇怪之事排在笔记体之外。承其后而又不尽相同的,又有欧阳修的《归田录》一书。
与李肇相比,欧阳修在创作《归田录》时,则清醒的意识并反复的强调自己作品和史著有着根本的不同。其《自序》云:“《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㉒。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初衷,欧阳修于《后序》又云:“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㉓
欧阳修《归田录》对为恶之事的记载很少,即使有也非常隐晦。如其卷二记载了一次宫廷内的暴动:“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卫士作乱于殿前,杀伤四人。取准备救火长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问:‘寝阁在何处?’宫人不对,杀之。既而宿直都知闻变,领宿卫士入搜索,已复逃窜。后三日,于内城西北角楼中获一人,杀之。时内臣杨怀敏受旨‘获贼勿杀’,而仓卒杀之,由是竟莫究其事。”一个“竟”字,这似乎是这则故事的弦外之意:欧阳修认为罪责要归到杨怀敏身上,但是在字面上却仅以“仓卒”二字轻描淡写。
欧阳修为何要反复强调自己“职非史官”,而作品为“史官之所不记”呢?概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王明清《挥麈三录》曰:“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㉔欧阳修并不想记录下“有未欲广布者”的内容,以免带来祸害。这也是小说家创作的一个出发点,可以起到一种对自己保护的作用。欧阳修注意到了其作与史著的不同处,史著多“惩恶劝善”,而自己的作品则多为“掩恶扬善”。同时,《归田录》里面记录了大量“戏笑不急之事”,发展了刘知几的观点,对小说的消遣娱乐作用采取认可的态度。后世如纪昀等是认同的。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收录于“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并评其书云:“然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㉕
正如谭帆先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所言:“刘知几《史通》于‘史部’中详论‘小说’,‘子’‘史’两部遂为中国小说之渊薮”㉖。在刘知几影响下的一脉小说,如《隋唐嘉话》、《国史补》、《归田录》等,移步换形于子史之间,体现了兼具小说家与史家两种身份的作家,一方面心怀历史,一方面又消遣自适的创作情趣,摇曳动人、独具姿态。
三、文史互渗表象下求其“雅正”的内在理路
古代史官在撰述史著时历来注重对材料的筛选。如司马迁自己就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故而,他在“论次”时,就仅“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㉗。然而,在《史记》的具体写作过程中,司马迁保留了有关于虞舜等三皇五帝的一些原始神话和民间传说,使其成为正史的一部分。如《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㉘
在刘知几看来,《史记》这里提到所谓“舜穿井”的“匿空”之术是指方士凭空遁形的旁门左道。对此记载,刘知几《史通·暗惑》大加问难:“夫杳冥不测,变化无恒,兵革所不能伤,网罗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质为羊,刘根窜形入壁是也。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如《史记》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则其意以舜是左慈、刘根之类,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识事如斯,难以语夫圣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黄帝、尧、舜轶事,时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
司马迁的做法被刘知几批评为不够纯正端严:实为“俗之愚者”,“难以语夫圣道”。而对司马氏的所谓“余择其言尤雅者”,刘知几更是质疑说:“若如向之所述,岂可谓之雅邪?”司马迁撰写史著采录历史人物种种“幻化”的材料,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不是所谓的方士,也不具有奇异的法术。刘知几对其的批评是有其道理的。
相对于对《史记》的严厉指责,刘知几又盛赞了一部小说作品。《史通·杂说下》“别传”云:“杜元凯撰《女记》,博采经籍前史,显录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犹阙而不载。斯岂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长者哉若人也!”。刘知几认为,杜预撰写《列女记》,广泛采集经史资料,引录以往圣哲明言,如有可疑之事,则缺而不载,表现出他坚持“理存雅正”的写作原则而厌恶乖谬不正的写作态度,杜预是一位地道的君子和长者,而《女记》亦是自己心目中的典范之作
杜预《女记》今仅见三则。其一为《太平御览》卷422“人事部”63“义妇”条载:“王氏之母者,汉丞相安国侯王陵之母。汉王击项羽,陵以兵属汉王,项羽得陵母置军中,汉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欲私送使者,为之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母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剑而死,以固勉陵。”㉙赞美的是大义明理,为了不让儿子因为自己受到牵制而伏剑自刎的“王陵之母”。
另外二则,皆见《太平御览》卷441“人事部”82“贞女”条。其一载:“淑丧夫守寡,兄弟将嫁之,誓而不许”㉚赞美的是丈夫死后,为其守节而决不再嫁的“寡妇淑”。其二曰:“大女缑玉者,陈缑氏之女也。夫之从母兄弟杀其父,玉乃为父报仇,其杀已至亲,缚玉付吏狱,竟当行刑。”(31)赞美的是为父报仇的“陈缑氏之女”。
由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对杜预《女记》的赞扬,刘知几从正反两方面,以事例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自己所追求的“雅正”。不是指语言的文雅或者典雅。亦不是指内容的高雅、风雅。而更侧重于所载内容的雅正与实录,可以成为典范,从而起到讽劝的作用。这种对“雅正”的追求,是文史互渗的内在理路。这一点在涉及到描写女性的作品,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主要强调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做母亲的要深明大义、有识见,能对儿子的人生事业起到指路作用,必要时为了不拖累儿子,甚至主动付出自己的生命。其次,丈夫死后,无论什么情况下,做妻子的要为丈夫守节,不再嫁。第三,父亲被人杀害,哪怕是违背法律,以自己的大好青春为筹码,做女儿的也要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父亲复仇。类似的观点,同样可以在《新唐书》“列女传”中看出。欧阳修校阅完成,宋祁具体编撰的《新唐书》“列女传”,相对于《旧唐书》,增补了诸多女子的传记,其中大量借鉴了小说中的内容(32)。
一如“李畲母”,改编自《朝野佥载》卷三“监察御史李畲母”。内容为:“李畲母者,失其氏。有渊识。畲为监察御史,得禀米,量之三斛而赢,问於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问车庸有几,曰:‘御史不偿也。’母怒,敕归馀米,偿其庸,因切责畲。畲劾仓官,自言状,诸御史闻之,有惭色。”(33)写的也是深明大义的母亲。
再如“坚贞节妇李”,改编自《朝野佥载》卷三“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只是隐去了故事的发生地“沧州弓高”四字。其曰:“坚贞节妇李者,年十七,嫁为郑廉妻。未逾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梦男子求为妻,初不许,后数数梦之。李自疑容貌未衰丑所召也,即截发,麻衣,不薰饰,垢面尘肤,自是不复梦。刺史白大威钦其操,号坚贞节妇,表旌门阙,名所居曰节妇里。”(34)写的是一个自污形貌,以示坚决不嫁的决心。不过,又加入了一点离奇的情节,追求的她的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梦中的一个男子。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新唐书》“列女传”之“段居贞妻谢(氏)”传,缩编自著名的唐传奇李公佐之《谢小娥传》。其曰:“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贞本历阳侠少年,重气决,娶岁余,与谢父同贾江湖上,并为盗所杀。小娥赴江流,伤脑折足,人救以免。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曰:‘杀若父者必申兰,若夫必申春,试以是求之。’小娥泣谢。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余,得兰于江州,春于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佣兰家,日以谨信自效,兰浸倚之,虽包苴无不委。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出入二萁,伺其便。它日兰尽集群偷酾酒,兰与春醉,卧庐。小娥闭户,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赃千万,其党数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状。刺史张锡嘉其烈,白观察使,使不为请。还豫章,人争娉之,不许。祝发事浮屠道,垢衣粝饭终身。”(35)说的是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被盗贼所杀,谢小娥通过占卜获知仇人的姓名,然后设计除掉盗贼,为他们报了仇。后来很多人要争相迎娶她,谢小娥却身遁空门,以了余生。《新唐书》的编撰者没有看出,所谓李公佐占梦云云,是地地道道的“小说家”之言。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史学因子互渗互融,相扶相益。这一点,较早的体现于《左传》等历史散文中。在针对介子推逃亡前母子对话、“鉏麑触槐”刺客自杀前的喃喃自语,钱钟书曾谈到文史之间的关联,其曰:
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36)
小说和史著,除了钱先生提到的人物语言“对话独白”与“假之喉舌”的共同点外,我们认为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文史互渗表象下还有一个求其“雅正”的内在理路。这是中国史著编撰和小说创作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刘知几较早论述了这一点。无论小说创作,还是史著的编撰,刘知几都明确言明对雅正的追求。他同时要求史家在采录小说作品材料而入史著时,也要坚持雅正的筛选标准。《新唐书·列女传》所增补《旧唐书》的内容,是和刘知几的提倡彼此呼应的。
《新唐书》刘知几本传云:“(刘氏)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讥评今古。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37)徐坚之语,并非虚誉。作为《新唐书》主要修撰人之一的欧阳修,其在《新唐书》、《归田录》等文史之著的具体创作中,即多以刘知几观点为参照。刘知几《史通》对欧阳修等后世史家,在小说观念、小说创作及采小说以补史求其“雅正”之高标等多方面,都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41);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224002)】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②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6页。
③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4页。
④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⑤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1页。
⑥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2页。
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⑧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1页。
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⑩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2页。
⑪本文所涉《史通》引文全部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通释》。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注明。刘氏小说以“叙事为宗”之观点,详另可参谭帆《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叙事为宗’:子、史的共性与小说学”一节,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7-62页。
⑫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1页。
⑬《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37页。
⑭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45页。
⑮《旧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页。
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⑰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20页。
⑱《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⑲⑳《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58页。
㉑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㉒㉓欧阳修《归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㉔㉕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90、1190页。
㉖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㉗㉘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页。
㉙㉚(31)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49、2031、2031页。
(32)详可另参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第八编“史学篇”,第八章“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1563页。
(33)(34)(35)(37)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21、5822、5828、4521页。
(36)钱钟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1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史通》文论研究”(编号:14BZW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