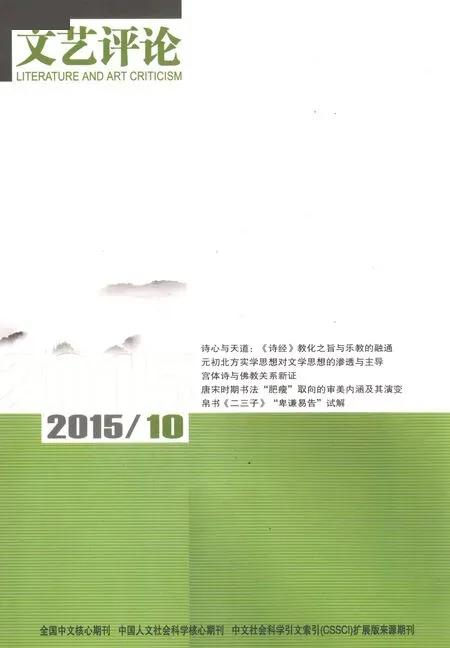北宋理学诗在朝鲜时代流传与接受
——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中心的探讨
袁 辉
北宋理学诗在朝鲜时代流传与接受
——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中心的探讨
袁辉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的著名论断,多年来已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由是可见宋代文化在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演进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其中作为代表性的理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文道关系论则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理学家以为作文害道,大多将诗歌创作视为末技小道不予重视甚至摒弃不为。相比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卓绝贡献,其诗歌实绩则显得黯淡了许多,且常以浓厚的道学气为论诗者所诟病,被称作“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②。我们认为,理学家诗亦多有洋溢生机与理趣者,如程颢《春日偶成》、朱熹《春日》诸篇。这类诗歌的文学价值,近年来已多为学术界所关注。事实上,理学家诗歌还随着思想的传播流传到域外,对域外士人的创作和心态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就是其中典型。
一、《击壤集》在朝鲜时代诗坛的流行
邵雍诗歌在域外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朝鲜时代,受到众多士人青睐,几无贬抑之词。众所周知,中国很早就有与域外进行文化交流的记载,唐宋时期愈趋繁盛,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明代后期。这期间东邻各国与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多以一种单向输受的方式在维持,多呈现出全盘吸纳与仿效创造的情形。高丽后期理学传入东国,由此“理学成为官学,宋代理学家的诗文和他们所编的诗文选本,在朝鲜时代也成为非常流行的书……理学家的诗歌,尤其是朱熹的诗,甚而成了朝鲜时代朝野上下士人修业进德的途径之一”③。与宋朝开始便对理学诗多有非议、将其视作诗坛末流不同,朝鲜士人显示出更多对理学诗的偏好。这固然与其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向往有关,但更得力于文化情感上对程朱之学的认同与皈依。尽管朱子学在朝鲜也不乏异声,但更多士人是将其当作一种生命信仰,毕生浸润其中,皓首穷理,以倡扬道统为己任,视作安身立命的操守,终身行之矢志不移。因此,他们对理学诗也予以格外青睐并颇下了番功夫。“诗可以抒情、叙事,自然也可说理。问题是怎样说理。若一味说理。通篇是说理之韵语,自不免令人生厌;然若能得其理趣,则水流云在,月到风来,同样是好诗”④。取象生动鲜明,言理通透圆活,寄意流畅悠远,机趣盎然,自然不失为上乘之作。这决定了理学诗作为理学附载的存在,同时也具有独立的诗学价值,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邵雍诗歌在异邦的流传最初伴随着文化输入的潮流而兴起,自然不会受到什么阻碍,这大概可视作当时中华文化传播的共态。而在流传过程中,《击壤集》又不断以自身所蕴含的独特诗学风格和鲜明人生体验渐为更多士人所主动接受,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学思想本身影响的范围所及,成为东北亚各国儒生士子修业进德、体道全真的价值寄托。得以文学化的形式深入广泛地参与士人心态的塑造和理想人格的建构,恐怕是邵雍诗歌在域外接受最深层的原因。他们不仅争相阅读吟诵收藏邵雍诗歌,还不断将其付以刊刻,从而使得众多朝鲜本《击壤集》得以保存和流传。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邵雍诗歌尽管在朝鲜时代流传已非常广泛,但不得不承认它还远远算不得主流,影响力更无法与李杜苏黄等久负盛名的大家相比,故论述《击壤集》之接受不能越俎代庖夸大其实。仅就理学诗而言,邵雍的地位也难与朱熹抗衡。但以宋儒存诗数量论,邵雍尤多且独具风采,这便不能不引起朝鲜士人的注意。南孝温曾说:“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使人养浩然,牢笼百态,弥漫乎天地之间……邵子、周子亦未免于好诗……自勖以诗为异端,则亦异端周、邵乎,晦庵乎,占毕斋金先生曰:‘诗陶冶性情’,吾从师说”⑤。南孝温反对郑自勖只通经不为诗的态度,遵奉乃师金宗直之说,以为诗见性情。金宗直本身就是享有盛名的朱子学家,有“山翁康济自家身,须信尧夫语最真”⑥的诗句。这“语”,自然也包括邵子诗语,理学和诗学是相互交融的。严羽《沧浪诗话》单立“康节体”,朝鲜士人也注意到邵诗的自成一家。如金构有《效邵尧夫体》诗,李栽《病暑书怀》副题中亦有“效击壤集体”之语。无论是“康节体”、“邵尧夫体”还是“击壤集体”,在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中,得以独列一体,本就关乎大焉。《击壤集》和《皇极经世书》相互映衬,成为通往康节学术的又一关键,而又蕴含了更为浓厚的生命镜像与人格体验。
随着接受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邵雍诗歌也开始为更多朝鲜士人所喜爱。“暇时闲吟邵子诗”⑦,邵诗逐渐成为众多士人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更有如尹根寿“半世长吟邵子诗”⑧者,径将其视作生命寄托。这就只能以《击壤集》自身诗学魅力进行解释了。如尤庵宋时烈“积置《朱子大全》、《朱子语类》及《击壤集》、《两先生往复书》等文字,沉潜不已,而常以《击壤集》为主。其余则随意看过。在道之时,《击壤集》一卷,常不释手矣”⑨。作为程朱理学在海东的传承代表,宋时烈独醉心于邵诗,自是对其深有会心。又如白时昉“慕邵先生之为人,丌上常置《击壤集》。朝夕吟诵,优游厌饫。神融而意会。则拈取其深契者,集句为章,编成一册。目之曰集邵”⑩。完全集邵句为诗,亦可见其喜爱之深仰慕之切,而这多半缘自对其人道德人格的深刻体认。
二、邵雍诗歌在朝鲜诗坛的接受与价值呈现
整体上看,朝鲜时代对邵雍诗歌的接受深刻而广泛,涉及诸多层面,我们大致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初步探讨:
(1)朝鲜诗坛对邵诗典型意象与题材的撷取。
朝鲜士人大多熟习汉文,热衷汉诗创作,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思维和艺术魅力有着深切感受。如前所述,对《击壤集》的接受伴随着理学思想的传播而进行。有了理论上的支撑,他们不难会心于邵雍理学诗中的一些独特意象,这些意象,大多是诗歌中所习见的,但在邵诗中常别具意蕴。如杜鹃,常以杜鹃啼血形容哀痛之深。在邵诗中,则被赋予新的寓意。这首先源自邵伯温笔下的神奇传说:
治平间,(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⑪
“南士为相”指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一事,“自此多事”指由此所致的朝野动荡、党派纷争。邵雍于治平间便从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推测朝廷巨变,可谓得风气之先。这固然只是传说,却一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并凝定为一个崭新意象,流传于民间。杜鹃寓意也由啼哀发展出小人当事,国之将变的先兆,此亦为朝鲜士人所领会。如沈彦光《闻杜鹃》有“天津忆邵雍,再拜思杜甫”⑫,成俔《夜闻子规》有“初似天津康节叹,还如锦水草堂吟”⑬,柳袗《夜闻杜鹃》亦有“几入尧夫叹,偏伤杜子诚”⑭句,都以杜鹃为媒将邵雍和杜甫两位诗人并列而言,更突出了该意象的典型性。在深层上,他们常借此表达对于历史的感思与嗟叹:
天津桥上杜鹃声,执拗金陵误当局。先王宪章翻手改,满朝群贤相继逐。(南龙翼《读史诗长篇》)⑮
南来闻杜鹃,夜啼咽幽泉。昔闻天津感,有激尧夫言。(李晚秀《闻杜鹃有感》)⑯
其中虽有对邵雍利用禽鸟得气之先推演天地人事之洞察幽微的惊服,更使杜鹃带上了深沉的历史感。邵伯温记载不免虚构,但宋王朝变故则由来有征。实际上是邵雍地处西京,已敏锐地感受到朝廷内部难为人察的派别纷争,升平表面下已然有了动荡的潜流。
又如“小车”和“安乐窝”。这是邵雍诗中时常提及的两个物象。前者是代步工具,后者则为其居所。两件再平凡不过的物事因邵诗的反复吟咏而定格为两个具有浓厚尧夫色彩的意象:
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小车吟》)⑰
安乐窝中春不亏,山翁出入小车儿。(《安乐窝中吟》)⑱
小车随意出,所到即成欢。(《小车吟》)⑲
此类吟咏在《击壤集》中几乎触目可见。邵雍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乘车外出,赏花观景,所到之处无不欢欣,俨然洛阳城一道独特风景。每当寒暑风雨所谓“四不出”之时,他则居于安乐窝中,弄丸悟道,呈现出一派宁静清和的气象。此二者伴随邵雍最久,深刻贯注着他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内核,因此在朝鲜诗坛上得到反复咏叹。“爱玩濂溪草,慕驾康节车”⑳、“济胜玄晖屐,乘闲邵子车”㉑,邵雍小车和“濂溪草”、“谢公屐”一样,已化为古典进入汉诗创作,凝聚了对于先生之风的认可与钦仰:
坛上暂希曾点瑟,洛中方待邵雍车。(李纯仁《闲中即事》)㉒
欲挽小车随意出,尧夫趣味此时长。(南鹤鸣《春日偶吟》)㉓
坚贞自守、安贫乐道是传统儒家士人恪守的基本准则。邵雍小车所包含的意蕴与“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㉔的曾点气象一脉相承。
又如:
直到浩然归顺日,数间安乐是吾窝。(申光汉《咏史·邵子》)㉕
康节安窝室,拾遗吟草堂。(朴英《杂诗》其四)㉖
安乐吾窝为众多朝鲜儒士所想慕,不仅因其避风遮雨,更能藉以自乐,静居其中读易弄丸,修性养心悠然自适,博得精神的自足,成为他们心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修道佳境,直与杜甫草堂并驾齐驱。其实安乐窝也好,草堂也罢,都只不过是普通宅居之所,正因有了邵雍、杜甫诸贤的经营与揄扬,成为了域外士人体认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
此类意象不胜枚举。如邵诗中有《太和汤吟》一首,朝鲜学者金昌翕则谓“近得尧夫安乐法,太和汤以小杯尝”㉗。太和汤者,不在酒名,尤在饮酒方式与节度。“唯喜饮之和”乃邵雍饮酒之方。饮和者,醺酣之谓。饮至酩酊便身心两害了。这也是朱熹所言“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㉘的具体体现,符合邵雍一贯的行事作风。
此外,还有花草等意象都因邵诗而赋予了崭新的阐释,朝鲜士人多将其移入诗中表达一己的修身体验,丰富了其理学表达,在朝鲜理学界乃至诗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通过比附观照,对邵雍创作实绩进行自觉的诗学化确认。
朝鲜中期的诗人林亿龄在《醉吟雪月寄示诸公》中有“唐有李太白,宋之邵康节。诗卷在人间,冰雪生口舌”㉙句,黄俊良《次李子发》中亦有“谪仙佳句烂星文,邵子天真任半醺”㉚之句,皆以《击壤集》与太白诗相提并论而毫无愧色,显已超越理学话语的苑囿。金兴洛谈及柳景绪的创作时说其“于诗泛览诸家,能解正变。尤好少陵诗击壤集,往往成诵。有时发之哦咏,率豪爽可讽”(《柳景绪墓志铭并序》)(31)。能与杜甫诗同博得“泛滥诸家、能解正变”之诗家的喜好与青睐,也足以说明邵诗自身强大的诗学吸引力。这在宋以后诗坛是不多见的。假如说与李杜相比是对邵诗地位的揄扬的话,那么与陶渊明的并举则是因其诗歌底质之间有着切实明显的诗学关联。
由于自宋代开始便对理学诗派多持贬斥态度,加之陶渊明地位的崛起以至炙手可热,很长一段时期内诗坛并未将二者放在对等的坐标中进行历时评价,多是将邵雍与司马光、富弼等作共时比较,尽管《击壤集》中多处提及对陶渊明的仰慕。朝鲜诗坛则不然,陶、邵二人在高丽末期到朝鲜时代的诗文创作中经常对举而言,如“长吟彭泽归田赋,拟续尧夫击壤歌”(32),这种对比更多基于“归田赋”与“击壤歌”共通的诗学旨趣。他们甚至还独出机杼地打破二人异代之隔,以友朋相期。高丽末期著名朱子学者李穑曾戏谑写道“公真陶渊明,我即邵康节,相从固为圆,相失亦何缺”(33),将好友韩柳巷比作陶渊明,以邵康节自比,二人心意相侔,乃为此言。或许是社会风气使然,大家乐于将陶、邵放在一起比较,到了朝鲜时代这种风气愈发明显。“曾学归来陶靖节,正如安乐邵尧夫”(34),清晰昭示了二人相同的隐士身份和相近的诗歌风格所体现出的彼此之间的承继关系。“后靖节而兴起者,亦有邵子,其诗曰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此亦适其适而世无能知其乐者”(35),由于陶、邵这种内在精神上的传接,使得其个人喜好和隐逸志趣也成为东国士人冀以师法的共同对象。如“水竹花前谋阔计,琴书酒里作生涯。虽居人世出人世,元亮尧夫是我师”(36),“看戏尧夫惟倚枕,息交元亮只关门。嚣嚣却有闲中趣,浮世喧豗欲忘言”(37)。桃花源和安乐窝本是两个象征隐逸的意象。虽然桃花源穷于僻壤,安乐窝居于闹市。陶渊明高蹈遗世,而邵康节闹中求静,但二者作为士人可以退守的两个理想世界共同为朝鲜时代的儒士所向往与尊尚。“渊明宅畔柳初绿,康节窝边花复栽”(38),朝鲜士人也不惮将一己居所幻化成渊明宅、安乐窝,因此初绿之柳、复栽之花便也成了心意的寄托。陶氏诗歌恬淡自然,邵氏诗歌清和质朴。但陶渊明对邵雍的影响主要是心意的接续与传承,而并非生活方式的蹈袭。以此而言,二者可供对举的包容性就更为广远,如“清风梦稳渊明枕,芳草行宜邵子茵”(39),“有月尧夫院,无弦元亮琴”(40)。加之二人皆钟情诗酒,所以类似“靖节只应耽饮酒,尧夫似是爱吟诗”(41)、“邵子吟怀今既得,陶生醉兴又从高”(42)之类诗句就更层出不穷了。
(3)在朝鲜时代汉诗文集中,追摹邵诗的形式多样,较为集中的有拟诗、和诗、集句诗等。
鱼有凤《杞园集》中有《拟康节历代吟》诗,从邵雍《观三王吟》到《观盛化吟》的十三首咏史诗中选取七个朝代,同样以《观嬴秦》到《观宋》为题进行吟咏,以东国人的视角表达对于中华历史变迁的兴亡之感,用韵除《观嬴秦》外均一致。此外还有像《效邵尧夫体》等诗也都属这一类。
朝鲜士人和邵雍诗在数量上颇为可观,这种异时异域的追和,形式亦较多样,如《次邵子闲吟》、《次康节诗》、《咏白菊,用康节先生韵》、《和邵子感事吟》等等。还有和邵雍组诗者,如宋征殷的《次康节〈安乐窝中吟〉十三首效体》、申光汉的《次邵尧夫〈年老逢春〉韵十三首》、元天锡的《次康节邵先生〈春郊十咏〉诗》等,皆由《击壤集》的心意感发而诉诸笔端,大多颇堪玩味而又风韵独具。最值得注意者当属邵雍一百三十五首《首尾吟》的和诗。“首尾吟”体由邵雍开其先河,每首均七言八句,由“尧夫非是爱吟诗”一句领起,又以此句收束全篇,有首尾呼应参差错落之感。邵雍诗歌传到域外之后,这种形式特别而殊有韵致的诗体便引起极大兴趣。李德懋在《〈次丘琼山首尾吟〉并序》中说:“古无是格,邵先生以理胜醇粹之语,为首尾吟鼻祖。语厖气广,非汉魏六朝唐宋语,宛然独是邵先生语,其后作者往往仿焉”(43)。此种风貌的语体,朝鲜士人不仅乐读,且纷纷捉笔仿效。但邵雍《首尾吟》组诗凡一百三十五首,倘完全拟和着实极费心力,所以诗人大多根据兴趣自由控制篇幅,或一两首,如赵昱《效康节先生〈首尾吟〉》(景阳非是爱吟诗)一首;或上百首,如金正默《次〈首尾吟〉》(过翁非是爱吟诗)则一百一十九首。且并不囿于“吟诗”模式,扩展到诸如“闲居”等生活方式上面,灵动活泼,像权好文便以“松岩精舍独闲居”为首尾句。其实这种随意洒落的态度反而更符合邵雍诗学精神。在和《首尾吟》的诸多佳作中,篇幅最大、水平最高而尤见性情者当属宋时烈《次康节〈首尾吟〉韵》。尤庵宋时烈是继花潭徐敬德、退溪李滉之后又一位声名卓著的朝鲜大儒,曾发愿“平生只看朱子书”的他,认为邵子诗“虽诙谐纵谑,若无意于人世,而其辨析义理,分别善恶处,有毫厘不差者,所以眼目高明,胸襟洒落,腾腾自在,以送平生,真可谓千古之豪杰也,然规模气象与晦翁不同”(《与申圣时》)(44)。他的《观〈击壤集〉偶吟》、《观〈击壤集〉》等诗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感受。《次康节〈首尾吟〉韵》共有一百三十四首,在整个朝鲜时代各类次韵诗中也数荦荦大者,以诗歌形式全面而又深入地表达了尤庵之学所涉及的诸多方面,既有人事的慨叹,也有理学的感悟,亦不乏历史的沉思。试看其中一首:
尤翁非是爱吟诗,寤寐尧夫安乐时。帝伯皇王些子事,风花雪月化工为。
如无太极先天学,谁识文王易系辞。最是伏羲亲见后,尤翁非是爱吟诗。(其七十一)(45)
该诗是对邵雍一生功绩的总结,有先天之功,也有风月情怀。既有达于一身的安乐,又是伏羲画卦的传人。将理学话语化为诗式表达,纳入“首尾吟”的框架中,比直接说理要有意味得多。
集句诗也是产生于中国的一种诗歌创作的独特形式。“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集句诗创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创作者“博学多识,融会贯通,如出一手,然后为工”(46)。只有通过大量阅读,在悉心揣摩诗歌艺术的基础上建立起艺术化的直观审美力和感受力,于一家或诸家诗有所会通才能锤炼出高超的集句诗艺。否则易陷入文字游戏的俗套。集句佳作则浑然天成,与纯粹的文学创作无异,如文天祥的《集杜诗》。这种诗歌形态,在朝鲜时代也流传到了东国,诸多诗人大力创作集句诗,在域外也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珍贵的集句史料。邵雍诗歌就常被用作集句来源。如前所述白時昉《集邵》,便是“拈取其深契者,集句为章,编成一册”(47)的,但遗憾的是,是书仅见于记述,没能保存下来,难窥其目。现在所见大多为多家集句中选取邵诗。如金时习《山居集句》一百首,全都是七绝,用来表现其隐逸之趣,故于邵诗亦多所摘引。如其十四“随意乐处省营为”、九十五“幸自无风又起波”等均出自康节之诗。又如金是榅《溪居集句》(48)一诗,第二句作“都将无事乐,得作自由身”,前句出自邵雍的《静乐吟》,后句则取自白居易,表现了作者的隐居自得之乐。另外,李光胤《瀼西先生文集》卷四所选皆为集句诗(49),对邵雍诗句多有采集,如《春兴》(其一)“一壶芳醑别涵春”,《幽居杂咏》(其二)“一毫荣辱不须惊”,《早春对酒》“造化从来不负人”,《早春独步》“独步独行仍独坐”,《中酒》“焉有闲愁入两眉”,《闲懒吟》“林下居常睡起迟”等。金应祖为其所撰墓志铭谓其“留连觞咏,放怀风月,其高风雅韵,为远近所想慕”(50),也是和邵雍风范很接近的。整卷集句诗多集唐宋人诗,表达的多是一种居于林下、悠游从容的高风雅韵。朝鲜时代诗人创作集句诗,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为作而作,通常是藉古人诗句抒发一己之情怀,选入其中的邵诗多取材于闲适一类,绝少理学诗语。这种待遇,是倡言作文害道的理学家难以比拟的。
三、邵雍诗歌对朝鲜士人的精神塑造
朝鲜士人阅读《击壤集》,远未停留在追索诗据、模拟效仿的表层,而是由观物思想入手,探究邵诗深层本质,努力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与心意的调适。
朝鲜后期的学者金平默曾有“病枕不胜千古感,尧夫岂是爱吟诗”(《病枕偶吟》)(51)之句,病中直有以尧夫自任,吟诗遣怀之意。这种感怀甚至扩展到对于生死的认知:
君素有嬴疾。至甲午二月初四日。竟不起。年仅二十六。君于死生之际,甚从容。顾语在傍者曰:“康节云生太平死太平,我亦何恨焉。(52)
邵雍《病亟吟》有“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53)之语。该诗作于邵雍六十七岁去世之前,尽管颇有大限将到之慨,但言语之间透露着恬淡从容的气象,而无丝毫恐慌焦灼之态,这种不无老庄馀意的生死观,竟使得二十六岁的金利见淡然超脱生死大限,着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虽朝暮死,临化晏如,当如尧夫矣”(54),邵雍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深化了朝鲜士人对自我存在的认知与感受,这大概可视作一种浸润着浓郁生命色彩的终极诗学关怀。
“诗者,性情之发。而吟咏之间,又足以颐神畅志。此尧夫之吟所以发于月梧风柳得意之时者也。若专事吟咏者,只是玩物”(55)。心意的颐神畅志或许是邵雍诗歌对朝鲜士人更深层的感召,其早已突破专事吟咏的玩物阶段,更注重诗中传递的意而非诗歌外在的言语形式。以此点论,有深厚理学修养的朝鲜士人尤能会得邵诗三昧。“幽花幽草皆真性,闲鸟闲云亦本心。生死太平真乐在,尧夫先我有诗吟”(徐居正《次韵李次公见寄》其四)(56),邵雍诗歌中的乐也好,闲也罢,都是参透天人世事演化基础上自然之气的周行所使,皆出自先天真性本心,所以才能够乐而不淫,闲而不浮,是为真乐真闲之所在。个体生命一旦有了如许保障,便能够悠游从容,不为俗世所牵绊。邵诗对于心意的调适,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士人对《击壤集》的由衷热爱,激发创作的灵感和动力。诗人有“朗吟康节句,诗思十分添”(赵任道《茅檐夜咏》)(57)之感,多半得力于此。
邵雍诸多诗句也常被朝鲜士人作为立身行事的格言奉如圭臬书诸座右,如“施为欲似千钧弩,磨砺当如百炼金”(《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58)一句,李洪男便作“欲作千斤弩,当如百炼钢,邵子岂余欺,服膺愿毋忘”(《送义州牧使》)(59),既藉以自励,又是对友人的劝诫。又如尹东洙《拟上伯舅》云“邵子之言曰:‘快心事过易为殃’,此诚今日所当深慎者也”(60),同样强调凡事当有限度,否则必致灾殃。邵雍观物体验中有“频频到口微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之语,影响了朝鲜文人在饮酒方式上最大限度地体验身心两益的微醺之乐。所以朴长远有言:“人能于醉时不忘邵尧夫‘频频到口微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之句,则必不至于乱矣”(《劄录下》)(61),他甚至还将此言“书贴于壁以自喻,以为如此则庶免为酒所使。而惟有邵子许大胸次然后能之矣,余奚遽望乎藩篱哉”(62),他深服此言,但又认为无邵子胸次很难达此境界,颇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慨。还有“西湖李先生素好酒,取此诗扁其所居”,朴允默题诗曰“千秋佳句心相契,二字华题手自书”,爱酒之人也深会尧夫之意,并且还名其室为“醉春堂”(《题醉春堂并小序》)(63),更是深得邵雍饮酒之方。
类似取邵雍诗意名其室堂以至自号者还有很多,如:
延安李公,名其斋曰四不。盖取邵尧夫风雨寒暑不出之义也。(丁范祖《四不斋记》)(64)
康节先生有四事诗,看花一、观柳二、吟诗三、饮酒四。吾(指李善长)取而名吾堂。守此四以终吾馀年。(俞汉隽《四事堂记》)(65)
邵子诗有月到天心处之语,请名之曰天心亭。(曹兢燮《天心亭记》)(66)
惟以诗酒自适,自号收春子。盖取诸邵子所谓收天下春,归之肝肺之义也。(崔是翁《仲兄内翰公行状》)(67)
一般而言,士人斋室字号的选取通常有所寄托,或表达宗尚,或抒发情志。朝鲜时代诸多雅士都乐于撷取邵雍诗歌中既凝炼又含蕴丰富的只言片语或取以名斋或选作字号,显示了《击壤集》中体现出来的道德人格和隐逸气象在东国已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并引起他们的共鸣,成为诸家争相效仿的范式。
此外,朝鲜时代上梁文也常以邵诗为题材。“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68),是古人建造房屋上梁时表示颂祝的应用型骈文,也是由中土传至朝鲜,随之广泛应用于民间。邵雍其人其诗得以频频现身其中,如“慕尧夫之真乐,何忧抬头不起”(李海朝《水村新屋上梁文》)(69),说明其形象在民间也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些都是邵雍诗歌在朝鲜时代广泛传播的力证。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与唐宋时期许多大诗人在朝鲜时代流传的情形一样,邵雍诗歌在东国诗坛所受也并非全然赞美之声。像崔奎瑞就认为“《击壤集》诗,似为气所使。不如程朱之诗自然”(70),权尚夏则说:“以尧夫盖世之豪,一生经纶,只在于风花雪月之间,岂非千古之恨也”(71)。抛开这些批评的是非不说,平心而论,他们的态度是中肯的。正因为他们喜爱邵诗,所以才未流于一般化的浮泛夸赞,况且一些阐释还切中肯綮。如此,才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朝鲜时代域外视野下一个更丰富的邵尧夫,这于《击壤集》的流传是百利而无一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46)】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②刘克庄《恕斋诗存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一十,《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
③④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2、112页。
⑤《秋江先生文集》卷七,影印标点本《韩国文集丛刊》第16册,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137页。
⑥《占毕斋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2册,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255页。
⑦《讷隐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87册,1997年版,第151页。
⑧《月汀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47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94页。
⑨《宋子大全》附录卷十六语录,《韩国文集丛刊》第115册,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537页。
⑩(47)(51)《重庵集》,《韩国文集丛刊》,景仁文化社2003年版,第320册,卷五十一,第375、375、319、74页。
⑪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页。
⑫《渔村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4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12页。
⑬《虚白堂诗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4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02页。
⑭《修岩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9册,景仁文化社2006年版,第460页。
⑮《壶谷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131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⑯《屐园遗稿》卷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68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91页。
⑰⑱⑲(53)(58)邵雍撰郭彧整理《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5、340、461、514、243页。
⑳金榦《次申明允所寄述怀韵》,《厚斋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55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0页。
㉑崔锡鼎《又用前韵》,《明谷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53页。
㉒《孤潭逸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53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54页。
㉓《晦隐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1册,景仁文化社2008年版,第300页。
㉔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页。
㉕《企斋别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2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04页。
㉖《松堂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83页。
㉗《三渊集》卷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65册,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293页。
㉘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4页。
㉙《石川诗》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7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38页。
㉚《锦溪集·外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37册,1996年版,页137。
(31)《西山先生文集》卷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321册,景仁文化社2004年版,第330页。
(32)宋奎濂《闲居即事》,《霁月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37册,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348页。
(33)《牧隐稿·诗稿》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4册,1996年,第244页。
(34)申光汉《和邵子感事吟》,《企斋别集》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2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37页。
(35)金大贤《悠然堂记》,《悠然堂先生文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续)第7册,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第517-518页。
(36)林亿龄《秋城春怀》,《石川诗》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27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41页。
(37)尹东洙《幽居漫吟》,《敬庵遗稿》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88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84页。
(38)李桢《病后》,《龟岩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33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25页。
(39)朴守俭《次李友韵》其三,《林湖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9册,景仁文化社2007年版,第251页。
(40)尹拯《次崔来叔韵》,《明斋遗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35册,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109页。
(41)李稷《秋日遣兴》,《亨斋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547页。
(42)郑硕达《春兴》,《涵溪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3册,景仁文化社2008年版,第216页。
(43)《青庄馆全书》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0页。
(44)(45)《宋子大全》,《韩国文集丛刊》,1993年版,第111册,页34;第108册,第173页。
(46)(68)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69页。
(48)《瓢隐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7册,景仁文化社2006年版,第459页。
(49)(50)《瀼西先生文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3册,景仁文化社2006年版,所引诸句出自卷四第259-264页;卷六第295页。
(52)沈錥《西庵金利见墓碣铭》,《樗村遺稿》卷四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08册,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315页。
(54)金柱臣《随事劄录》,《寿谷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176册,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271页。
(55)张显光《趋庭录》,《旅轩先生续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60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64页。
(56)《四佳诗集》卷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95页。
(57)《涧松先生续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89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81页。
(59)《汲古遗稿》卷中,《韩国文集丛刊》(续)第2册,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第444页。
(60)《敬庵遗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88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31页。
(61)(62)《久堂先生集》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121册,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405、412页。
(63)《存斋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92册,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第169页。
(64)《海左集·文集》卷二十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39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449页。
(65)《自著续集》册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49册,景仁文化社2000年版,第622页。
(66)《岩栖集》卷二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50册,景仁文化社2005年版,第353页。
(67)《东冈遗稿》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续)第46册,景仁文化社2007年版,第555页。
(69)《鸣岩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175册,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566页。
(70)《艮斋集》卷十五,《韩国文集丛刊》第161册,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289页。
(71)《土亭遗稿跋》,《韩国文集丛刊》第36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