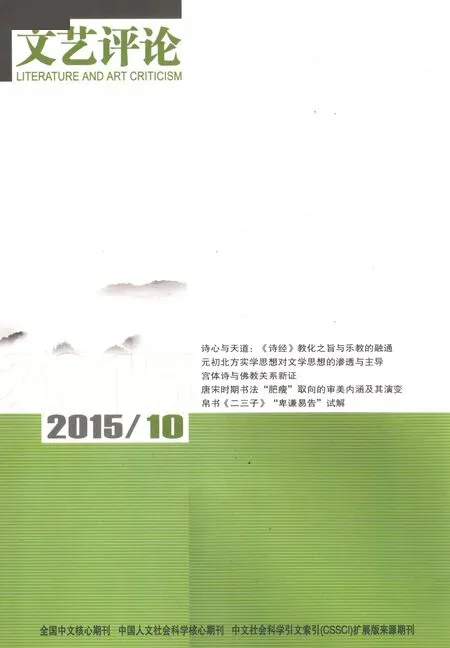生命忧惧中的自我救赎
——西晋文学的生命主题
段春杨
生命忧惧中的自我救赎
——西晋文学的生命主题
段春杨
西晋时期文人在面临现实的生死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时,试图寻找新的安身立命的途径,在此过程从表现出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对生命的反思,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念,钩沉出他们对生命主题的特有理解。钟嵘《诗品序》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①实际上活跃于西晋文坛的的重要作家还应包括稍早的傅玄、张华等人,他们以其创作实际践行了对于生命主题的思考与体悟。
一、新型人生观与信仰的缺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黑暗、恐怖、混乱的时代,前有三国鼎立、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之争,后又形成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之乱”、“侯景之乱”等一系列混乱的局面。“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②的恐怖政治环境,使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忧惧心理,一种世事难料的孤寂感和幻灭感萦绕于心,人们需要用日益衰微的经学以外的理论来解答对生命的追问、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等诸多问题,这便推动了思想的解放、人的觉醒,李泽厚先生曾说:“魏晋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著。”③魏晋士人所怀疑的是原来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术迷信、道德伦理等规范和标准,他们开始执著于现实的人生,慨叹自身的生死存亡,在自由开放的思想领域,内向型的文化意识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内心的新型人生观,他们试从全新的视角关注死亡、思考人生。
西晋是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个大一统政权,出现了短暂和平的局面,西晋的统治者以儒家礼教为立国之本,大力鼓吹儒教:“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④,“泰始三年十二月,徙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⑤朝廷的崇儒政策及整个社会的儒学教育环境培养了一大批业儒攻文的士子学人,代表“太康中兴”的作家“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晋的统治者虽以儒家思想治国,但这时整体的思想文化环境仍是比较宽松的,儒家思想之外的先秦各家思想均得到了发展的空间,汉末以来思想的解放在崇尚儒礼的西晋士人这里并未泯灭,其中以玄风的盛行为主要特征,西晋的文人士将儒学作为一种求取功名、实现自身建功立业愿望的手段,而在思想上他们并未仅仅以儒家提倡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常常是以儒道兼宗的态度来处理各种问题,他们遵循群体纲纪又尊重个体自由,既努力适应门第社会的实际需要,又追求自我的逍遥,因此他们徘徊在儒道之间,运用特殊的生存策略,谋求发展。西晋时期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使建安以来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新型人生观得到了继承,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仍是西晋文人士子所关注的问题。
但是,西晋士人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却伴随着群体性的信仰缺失。汉末以来思想领域的自由开放并没有减轻西晋文人士子的生存压力,前朝血腥恐怖的权力之争、频繁的战乱给他们带来的心灵震撼持久而深刻,建安、正始士人生存的危机感和畏惧感在西晋士人这里未减分毫。司马氏集团在立国之初对文人采取打击和拉拢的双面政策,嵇康被杀和向秀入洛是司马氏所采取的文人政策最典型的例子,它给后来的文人士子以警示,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士人的心态和行为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被动性和受迫性,渐渐演变成适应环境的理性自觉,这使得本来充满着生存畏惧感的士人们斗志进一步的退化,人格偏于依附和驯化,因此西晋士人的人生观较建安、正始的士人多了一个前提,这便是求全自保,他们的功名心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带有明显的个人功利目的,社会责任感被淡化。有着“摇笔而散珠”之才的张华,名望地位皆高,他“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⑥受到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熏陶,他济世用世、忠于朝廷,但他对于玄学清谈的态度也非常宽容,并参与其中,有着亦儒亦道的两面人格。“太康之英”陆机,恪守儒家之忠义观,闭门勤学,却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⑦为理由固辞高官,可见其人格的复杂性。潘岳流传千古的名作《秋兴赋》、《闲居赋》,明确表达出对仕途的厌倦和远离政治的向往,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始终未改“志深轩冕”的初衷,又“干没不已”,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左思同样是个思想行为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可以为了显身扬名而攀附势要,成为名噪一时的“二十四友”的成员,也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胸中不平,抨击社会黑暗,而对功名利禄表现出清高淡漠的态度,左思本人的真实情况与其诗文中塑造的自我形象间的疏离,正是儒道两种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另有少数冷静明智者如张载、张协、张翰等,他们最终选择远离政治,也是经历了先出仕后隐退的过程。西晋文人士子的人生选择都是以自身生命的保全为前提,但多数人不幸的结局,又使得这个前提是那么的具有讽刺意味,他们内心始终充满着无法排解的纠结与痛苦,他们的所为也包含着许多的不得已,却无法掩盖其人格缺乏独立性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带有极强功利性的求全自保心理导致了他们信仰上的缺失,也导演了他们个体的人生悲剧。
西晋时期的文人士子在新型人生观与信仰缺失的现实碰撞中执著于人生,努力在求全自保的前提下实现自身价值,呈现出一种实用性的生存观念,表现出对生命的忧惧心理,又试图探求生命本体意义,抒发关于天地人生的宏观感慨,他们对生命主题的解析是偏重于世俗化、功利化的生命体认,其中既包含了感性的生命体验又有理性精神的折光。
二、生命的感性体验:偏重世俗化的惧死恋生
西晋士人的心态中包含着忧惧的基质,这是汉末以来社会给士人带来的人生无常的忧惧心理的延续,同时也与儒道调和的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亦儒亦道的双面人格密切相关,他们如汉魏之际的士人一样,重视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却失去了自主独立的人格个性,他们以追求功名为人生目标,以名教的规范来塑造自己,又在玄学那里学会了以小谋大、求全自保的生存智慧,在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饱受心灵上的折磨,他们以惧死恋生的真切体验不断寻找着自我救赎的途径,他们对死亡的忧惧表现为更加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张华的《鹪鹩赋》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何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⑧表达的是求全自保、伺机而动的生存策略。潘尼《安身论》曰:“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惧乱所以保治,戒亡所以获存也。”表达了一种以退为进、全生保身的人生经验。这些都是西晋时期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求全自保、忧生惧祸的心态下面对死亡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晋士人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心理,他们时而表达祸福难料、人生无常的悲伤:“人生不能行乐,死何以虚谥为?”(潘岳《笙赋》)“人鲜知命,命未易观。”(陆机《秋胡行》)时而正视现实人生、反省生命价值:“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潘岳《河阳县作二首》其二)“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门有车马客兴》)在关注死亡的伤悼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士人们对死的恐惧、生的贪恋,如张华《永怀赋》、陆机《晋刘处士参妻王氏诔》、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等,侧重表达个体伤悼的现实的悲情,将个体对死亡的忧惧融入对死者的悼念之中,表现出西晋文人对生命主题独特诠释。
当文学家们意识到宇宙天地的永恒与人生短暂无常是一对无法得到解决的矛盾时,感情的脆弱和敏感就表现为挥之不去的迁世之悲。陆机《文赋》中“遵四时以叹世,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感慨,将自然界的倏忽变化与情感体验联系在一起,《叹逝赋》进一步于年光流逝中慨叹人生的短促:“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西晋士人延续了汉末以来抒发人生短暂的主题而表现为更加明显的对生的贪恋,张华“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的感慨,潘岳“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的哀伤,在悲叹生命价值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同时,表达对现世人生的无限眷恋,情感的个体化倾向十分鲜明。
西晋文学中对生命感性体验最为典型的要数潘岳的诗文创作,他在诗、赋、哀、诔等多种文体中表达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对现实人生的强烈欲求。潘岳常常在时空的转换中思索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冲突,反映士人探索生命意义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如《寡妇赋》:“终归骨兮山足,存凭托兮余华,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直面死亡,与阴阳两隔的现实相抗争,对生命的忧惧转化为震撼的力量。《怀旧赋》:“宵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时间的流逝没有成为抚平忧伤的良药,反而带来知音难再觅的感伤,再如《哀诗》:
漼如叶落树,邈若雨绝天。雨绝有归云,叶落何时连。山气冒冈领,长风鼓松柏。堂虚闻鸟声,室暗如日夕。昼愁奄逮昏,夜思忽终昔。展转独悲穷,泣下沾枕席。人居天地间,飘若远行客。先后讵能几,谁能弊金石。
空间上由室外到室内,时间上由白天到晚上,表达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悲伤痛苦,后四句看似对人生失望,充满着颓废与消极,其实是从反面表现对人生的执著。
用时空转换表达对生命的思索,已成为潘岳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惶恐与忧惧,而是在努力寻求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矛盾的方法。潘岳对人生的执著、对现实的挣扎与抗争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有的作品在不幸中拷问天地造化:
《金鹿哀辞》:“呜呼上天,胡忍我门。良嫔短世,令子夭昏。”
《伤弱子辞》:“叶落永离,覆水不收;赤字何辜,罪我之由。”
《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茫茫造化,援启英淑;猗猗泽兰,应灵诞育……彼苍者天,哀此矜人;胡宁不惠,忍予眇身。”
为什么不幸会接连而至?为什么生活的美好不能长存?为什么现实如此的残酷?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原来的天人观念所无法解答的,反映的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⑨有的作品在感叹中抒迁世之悲:
《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在怀县作》其二:“春秋代迁逝,四运纷可喜。”
《悼亡诗三首》其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悼亡诗三首》其二:“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悼亡诗三首》其三:“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
四节的倏忽变化使人联想到转瞬即逝的人生,带来无限的悲凉,《悼亡诗》以组诗的形式抒写迁世之悲,人生如同四季变化一样短暂,生命却不能像四季一样轮回,亲人的逝去永别,叫生者情何以堪。也有的作品在悲伤中抒发不朽名声之追求:
《许由颂》:“死而不朽,公有其荣。”
《司空郑袤碑》:“清风显烈,没而不朽。”
潘岳同西晋时期多数寒庶子弟一样,在门阀士族联合统治的夹缝中寻求士进之阶,他延续了建安文人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是功业的实现更加世俗化了,他艳羡许由的清名留世,钦佩郑袤勋名位望的取得,一想到自己事业的不顺便悲从中来,“非为子恸,吾恸为谁”(《夏侯常侍诔》),物伤其类,是悼友人亦是伤自己。
西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虽未达到超脱于社会与客观外物而达到内心与外物和谐平衡的充分自觉状态,但是他们在人与自然、社会冲突中的探索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萌动与个体意识的蓬勃发展却是实实在在的,尽管表现出来的是世俗化的惧死恋生,但这是生命意识达到充分自觉前的必经阶段。
三、生命的理性审视:偏重功利化的人生体悟
西晋文学所表达的具体感性的人生感受,是延续正始以来表现生命主题的方式,而由于对现世生命的强烈欲求而失去了自主的人格个性,显得更加的世俗化,在此基础上,西晋时期又出现了用理性思辨探索人生的新趋向,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对天地人生的宏观把握,是他们在用理性的方式努力探索自我救赎的途径。西晋士人因天道以论人事,努力去理解天道、顺应自然,表达对天命的敬畏,这种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对生命的追问,实际上是想通过天地自然的盛衰之变来探寻人事变幻的规律,为在政治形势多变、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生存环境下挣扎的自己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通过这样的理性审视来寻求自我救赎的方法,也可以避免直接正视现实、抒发个人遭遇,这样试图用天地大道探索人生的理性,具有庸俗功利性的一面。
西晋士人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天道的认知、对宇宙人生的感悟,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决定了他们对于天地人生的理解必然形成于文学作品而不是抽象客观的说理。张华《归田赋》以顺应天性、遵循自然规律作为开篇:“随阴阳之开阖,从时宜以卷舒,冬奥处于城邑,春游放于外庐。”充满哲理意味。潘岳《西征赋》同样以天地人生的大道作为开篇:“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廖廓忽恍,化一气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与位,谓之大宝。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圣智弗能豫。”这段化用经典的文字是《西征赋》的指导思想,带有朴素唯物思想的对天地人生的感悟,使整篇赋作大气磅礴,超越了以往纪行赋只谈经历和思考,而带有深刻的哲理性反思。“天”、“地”与“人生”构成了一个时空交错的轮廓,与魏晋时期人们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发现、思索、追求的时代思潮相契合。
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赫赫大晋,奄有万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潘岳《关中诗》十六章(其一):“三祖在天,圣皇绍祚。德博化光,刑简枉错。”《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肇自初创,二仪絪缊。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结绳阐化,八象成文。”何劭《赠张华诗》:“四时更代谢,悬象迭卷舒。暮春忽复来,和风与节俱。”因天道自然起兴再论人事,在陆机的应诏赠答诗中更是比比皆是,他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答贾谧诗》、《与弟清河云诗》、《赠潘尼诗》等都以天地造化万物灵气开端而转入酬唱赠答,这些诗歌看似毫无真情实感,其实也是处于风云变幻时代的士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试图在天道规律寻找主宰人事的某种规律,这种探索规律的“理性”支配着文学作品中因天道论人事的模式,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程式化的诗风来概括西晋诗歌中的这个特点。西晋文学家们在赞美人物时也常常从天地之灵气说起,如陆机《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曰:“冉冉晞阳,不遂其茂。晔晔芳华,凋芳落秀。”陆云《赠顾尚书诗》:“五狱降神,四渎炳灵。两仪钧陶,参和大成。兆光人伦,诞育至英。”都是以天地自然喻人,在显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的同时,也折射出自然的规律的不可抗拒,流露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晋文学家善于从自然中探索天道意志与人事关系的理论兴趣,努力于自然规律中探索人事更替变迁的因由,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西晋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探索天地人生、自然规律的兴趣,是在为其功名之心寻找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他们逃避现实政治、不敢揭示甚至不敢正视现实积弊的写照,暴露了西晋士人依附性的人格弱点,也折射出西晋士人所谓的生存智慧其实是以其庸俗性、功利性完成他们在生命忧惧中的自我救赎。
四、结语
西晋士人对生命的体认带有明显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他们所要表现的是现实的生活境遇,他们的生命价值观相较于建安文士对不朽共鸣的追求,更倾向于自我的现世人生,相较于东晋以及南渡之后将生命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的生命意识状态,又无法从生命的忧惧中将自身抽离,他们试图从生命价值的体认与实现中寻求自我救赎的方法,而这种努力事实上是一种独立人格在精神上的衰变。西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主题,无论是感性的体验还是理性的审视,都表现了西晋士人对生命的特有感悟,相对而言,感性体验更侧重于展现他们对死亡的忧惧心理,而理性的审视则更着重于表达寻找自我救赎途径的探索。西晋士人对生命主题的特有诠释,是生命意识达到进一步自觉和成熟之前的阵痛,也是生命意识逐渐达到充分自觉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中文系(273155)】
①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1页。
②④⑤⑥⑦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0、57、56、1069、1479页。
③⑨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151页。
⑧本文所引诗歌作品出自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赋文作品出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商务印馆1999年版。
本文为2015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潘岳辞赋的文化考察”(编号:J15WD15)阶段性成果】
——关于潘岳婚姻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