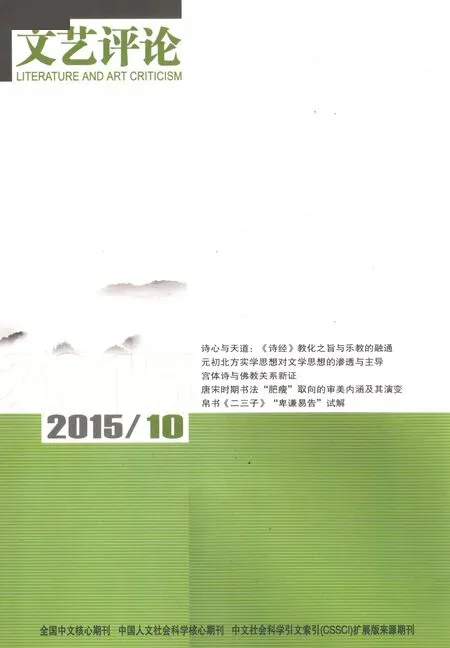诗心与天道:《诗经》教化之旨与乐教的融通
徐向阳
诗心与天道:《诗经》教化之旨与乐教的融通
徐向阳
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如果说《诗经》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日常家庭生活、男女咏歌与伦理教化的经学义理关系如何?其编诗之义是什么?其与音乐的关系是什么?自晚晴以降,经学地位的降格,《诗》被置于文学科,视为民歌,与苏俄文学反映文论结合起来,诗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镜子,有意或无意抹杀《诗经》文教的本旨。正确认识《毛诗》、郑笺的意义,而非简单将其视为“情歌”和“民谣”而曲解传统,均需重新思考。
《韩诗外传》云“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朱熹《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又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乐记》“声五音八何?声为本,出于五行;音为末,像八风,故《乐记》曰:‘声成文谓之音,知音而乐之谓之乐也。’”(《白虎通义》)只有尽善尽美、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音乐才能达到规范人伦的效果。亦即,蕴涵丰富道德思想和完美形式的音乐才是艺术的标准与典范,才能全面地培养和提升人的内在情感力量。其对人来讲,效法天行之健,法地之包容,尽性知天,出处有时,天人一贯的君子德性提供了重要面向。
一、《诗经》性情之显与诗乐功能
情由性生,一切皆与度有关,这正是诗教的核心。《礼记·祭义》说:“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物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诗经》中的礼乐文化与祭祀或婚嫁、宴享等场合紧密联系,以诗兴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始于衽席”,齐诗说:“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①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用礼义说《诗》,使《诗》成为礼义的载体。
“乐象阳,礼法阴”,以五音配五行,效法天地阴阳而成的乐与人的先天五常之性相对应,故能感化人的先天善性。音乐之成有感于心中情感的抒发,与通过歌舞抒发情感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情感交流。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同志和敬,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下,古文经学家班固保持了对谶纬编造者对灾异符命的批判,以及对天命、目的论与天人感应的敏锐洞察。《白虎通义》说“琴,禁也。”《乐记》把音乐分为心、声、音、乐、礼,从发生学角度把音乐分为五个层次,又把五音比附为君臣民事物,从而把乐与礼联系起来。音乐的一整套复杂操作象征了国家政治的复杂运作,从而表达了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在统一性,这就在乐性上论证了音乐的教化功能。《乐记》把音乐的政教属性表达得十分充分,但同时也把音乐的本性限制在此在的俗世层面上,与《白虎通义》把五音与五行相配合有本质的不同。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抒发得当为和,过当为淫,先秦古籍往往以“情伪”对言,“情”为真情,“伪”则变化为人为造作的情感。《乐记·乐本》:“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然而并非只表现审美愉悦功能,还重在表现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因。“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在揭示出时代社会与诗发生关系时,要求诗本身须合乎礼义的深处,诗人以合乎礼义的情志去感物,从而使诗也合乎礼义。
作为诗之始的《关雎》,用水的意象将君子追求好女的性情予以涤荡,节情以达至性。同样出自《国风·周南》的《采蘩》,讲夫人的亲蚕之礼,“被之僮僮,被之祁祁”,以发髻的僾然髣髴状夫人敬诚之状,亲蚕之礼在《史记》中均无,《诗经》用至微至薄之物极言礼对后世生活的修身、养心之意。有感有应之谓兴,阴阳往来之谓性,祭祀活动有盛大乾的一面,又有精微的坤的一面,足见诗为天地之心。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关雎》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给人展现出这种富有色彩感、却“乐而不淫”的嘉礼场景,正是诗经中对礼乐教化的一种宣扬。
《桧风·素冠》篇,描述丧礼情景,从服装到形体,孔子以“祭如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申明凶礼对人伦秩序的构建意义。诗中反复渲染衣冠的素色,通过一系列繁琐的礼仪,彰显以礼居丧孝悌之道的重大价值。《卫风·淇澳》吟咏君子仪态,就有诸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其实是对文王修明德行,行为合乎天道的行为的礼赞。《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予礼仪者三百五篇”,王先谦认为,“可施予礼仪”,谓“可以入乐,凡宾客宴享皆用之也”②《宾之初筵》展现祭祖之礼的隆重繁缛、热烈非凡,形成神人共乐的氛围。诗中突出了合乎礼之乐才是真正的乐,对宴饮中失礼丑态的描绘,更体现了礼乐之和的重要性。《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③
制礼作乐的基本目的在于维系群体和谐稳定的秩序。“从一开始,华夏美学便排斥了各种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悦和种种反理性的情欲的展现,甚至也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种具有宗教性的情感洗涤特点的宣泄——净化理论。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是情感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和谐协同,排斥偏离和破坏这一标准的任何情感和艺术。”④声音之道与政通,祭社有乐,《乐记》曰:“乐之施于金石丝竹,越于声音,用之于宗庙社稷。”而君子进德修业,多采用音乐的比喻,“乐者阳也,故以阴数。法八风、六律、四时也。八风、六律者,天气也,助天地成万物者也,亦犹乐,所以顺气,变化万民,成其性命也。……乐所以作四夷之乐何?德广及之也。”(《白虎通义》)面对礼崩乐坏,孔子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仁是统领礼乐的灵魂,用“仁”的理念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通过个体应该自我约束,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君子。
二、治心易俗之教与君子大人人格之养成
孔子认为诗与政通,“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乐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礼记·明堂位》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名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情志在“物——心——乐(诗)”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其并非只表现审美愉悦功能,还重在表现背后的社会政治动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当时代社会与诗发生关系时,诗本身须合乎礼义的深处,诗人以合乎礼义的情志去感物,从而使诗也合乎了礼义。
诗乐舞三位同源,诗教包含于乐教之中。乐治心性,使之和乐;礼治行止,使之庄敬,其结果就是使人内心和乐而无怨,行止庄敬、有序而不争。儒家注重乐情,即乐舞与诗情感的一致性。“礼节民心,乐和民声”,诗“主文而谲谏”,金声玉振是道德、性命学说的宗庙乐章,至于郑卫之音则属于俗乐、淫乐,对人的心性情感具有阻斥作用。《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抒发得当为和,过当为淫,反之,过犹不及,真情就为“伪”,变化为人为造作的情感。《说文·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这种对待礼的外在表现行为更多的排除了强制性。如何达到“民不教而自化”的目的,《诗经》中展现的这些周人在日常生活中,集中表现在《诗经》中往往透露出的人格美外化为文质彬彬、威而不猛等行为仪表。君子精诚内专,礼有节度、贞定之义,万物相遇而感通,独阳则亢,独阴则浊。王夫之说:“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诗广传》)
儒家善与美合一的观念是中国美学的主流,音乐所发挥的正是这种“以美导善”的教育功能,所以《白虎通义》特别重视人心的“和乐”。“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代表礼乐表演性质的金声玉振是其道德、性命学说的音乐譬喻,音乐一般指的是宗庙乐章,至于郑、卫、宋、齐之音,则属于俗乐、淫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礼记·郊特牲》曰:“歌者在上。”从人的发展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在一整套文化模式的实施中,进行人的完整培养和教育,这也就是上古乐教人体系的实质性内容。
“乐者,所以象德也”,但并不把诗摆放在像礼乐那样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地位。“可以观”,就是允许诗表达自由情志;“可以怨”,则诗更可以怨刺上政,发表不同见解。中国古代关于音乐审美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情感塑造这一中介,把作为艺术之乐与政治教化直接密切联系起来。⑤好的音乐是各声部秩序协调的产物,五音之于各种人物,恰如要有和弦之韵律,才能奏出和谐之乐。礼乐并非徒重形式,礼乐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音乐原是为了心中情感的抒发,表达心中喜乐之情,《白虎通义》认为乐对人性情具有陶冶作用,礼乐与刑政一样,都是王道政治所必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但两者作用不同,乐的作用是协同好恶,使上下协调一致;礼的作用是别贵贱,严等级。《礼记·祭义》云:“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物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礼器本身是权力、地位的等级标志,孔子认为器、名均属于“不可假人”之列。礼制的作用,莫过于维护血缘联系以及上下尊卑关系,建立社会秩序以立民纪,调和社会矛盾。礼乐是辅助治国治民的工具,音乐可以治心而易俗。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故邪僻声,皆淫色之声也。”(《白虎通义》)美好音乐具有涵养德性的功能,推而广之,可以有效地敦厚民风,引领民众向善,达到“民不教而自化”的目的。这正是音乐化民成俗的社会作用。乐教不仅是社会性、人文性的情感,更是重要的美育工具。“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言作、礼言制何?乐者,阳也,阳倡始,故言作;礼者,阴也,阴制度于阳,故言制。”《白虎通义》可见,音乐对于人的怡情作用,对于社会的范导作用,有利于人们积极向善。“乐者,所以象德也”,但并不把诗摆放在像礼乐那样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地位。“可以观”,就是允许诗表达自由情志;“可以怨”,则诗更可以怨刺上政,发表不同见解。中国古代关于音乐审美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情感塑造这一中介,把作为艺术之乐与政治教化直接密切联系起来。⑥雅乐是各声部秩序协调的产物,五音之于各种人物,恰如要有和弦之韵律,才能奏出和谐之乐。礼乐并非只流于形式,礼乐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
不论是《殷其雷》中的“振振君子”,还是“泄泄其羽”的《雄雉》,或是“报之以琼琚”的《木瓜》,都成为诗人创作的情感枢机。这种情感与生活的交融使《诗》之情炽热感人、《诗》之境素朴执著。《诗经》教化个人的最高标准是成就“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只有尽善尽美、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音乐才能达到规范人伦的效果。君子人格形态体现了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教养。《礼记·礼器》注:“君子,谓大夫以上。”《月令》孔疏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君子谓人君以下至位士也。”《荀子·大略》:“君子听律习容。”注云:“君子,在位者之通辞。”可知君子泛指一切占统治地位的人。以《诗经》雅诗中的君子已经指有道德的男子,风诗则借用雅诗中的君子指丈夫或意中人。《白虎通义》认为在特定的场合,如“宗庙”、“族长乡里之中”、“闺门之内”欣赏乐舞,人们互相间的“和敬”、“和顺”、“和亲”情感心理可以彼此共鸣,可“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缓解君主专制政体中上下贵贱等级之间的矛盾,巩固“百王不易之道”,这就是“先王立乐之意”,即礼乐教化的目的所在。⑦
三、诗心之“仁”与天人之贯
“诗者,天地之心也”(《诗纬》),“据道游艺”的六经传统,音乐与礼仪相辅相成,乐以感发情感,在各种礼仪场合中,音乐不仅成为整个礼的过程的不可缺少的要素,礼别异,乐和同,礼的存在的根本意义就在传统与时代之间,质文代变,皆根植于君子中道德性的培育与养成。
《论语·泰伯》载孔子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孔子对《诗经》功用的另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法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推崇文王之化和周公懿德,《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为德之华,他认为周礼是礼制的典范,立志要“克己复礼”,重新回到礼制“仁”的践行轨道上来。《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的阴阳哲学是一种强调二元互动从而生生不息的哲学,阴和阳处于不断互动、变化的过程中,互相转换互补。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尚和守中”。“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中庸》)《召南·羔羊》用礼教使人群而不党,孔子以礼乐文教培育人的能群、能养之德。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阳主阴从,阴阳对当,一体而同尊,在扮演自己的特殊角色的同时,也享受着以此为前提的社会认同。“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诗是气的发端,使六经成为一个整体。
《毛诗正义》“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是关于“诗”的一名而三训。观诗不可不察人情,自然人心与天相通的观念,开启了六经“引譬连类”、“合乐而歌”、“托事于物”的传统,天地万物气化的“起兴”模式最终转化而为“起发己心”的诗学渊薮。礼乐同中国原始宗教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所有的祭祀同五礼具有同样的礼典性质。在周代先民的人格形成过程中,“陈诗以观民风”,礼乐文明的熏陶一直是持续贯之的,人人都在礼的制约、规范之内。正因为“无邪、美刺”诗教与的礼乐文化的精神力量,才生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强烈依赖和崇拜,这同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中文教精神也有类似的地方。
《毛诗大序》有云:“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儒家看来,玉帛钟鼓、揖让律吕,都不过是些礼之仪和乐之表,远非礼乐之原。诗与礼乐不同,诗并不像礼乐那样拥有正统、绝对而单一的居高临下教化百姓的崇高地位。孔子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故《诗》之失愚,《乐》之失奢,《礼》之失烦;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礼记·经解》)《孔子家语·问玉》、《白虎通义·五经》均有载录这段话。乐教更倾向于对天道情感的体贴,使人品性善良,二者共同指向道德情感的锻造。
《诗经》通篇讲“天人、时运、性命”之义,言圣人教化之成。君子因知时而出,出处因时而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梅子落谁家其命攸同,天地一贯,仁内主化。万物各异,方显天地之公,性同然命不同,惟人能法天之健运,法地之厚德而载物,以达天运之同,因人(仁)有心矣。《召南·小星》讲差等之爱与人性之同,乃时运不同,不同之中又见同也。《礼记·乐记》:“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礼记·经解》借孔子之口,提出《诗》教的在于培养温柔敦厚君子德性的特点,朱熹《论语集注》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孔子寄语子弟:“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君子尚消息,盈虚天时也,从《国风》通篇均可见从山野至庙堂、少女到妻子的化育,《周南·汝坟》篇,用金克木比附礼乐对于欲望修束的重要性;《召南·采蘩》篇,用土克水象礼之大防。李泽厚指出周代“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与人民性。”⑧夫妇、君臣有义,实现“男有分,女有归”,《召南·行露》讲女子择礼而嫁,《召南·摽有梅》讲“相婚不禁”的待嫁之仁。“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首诗出自《国风·召南·甘棠》。召南是召公治理的地域,这首诗作抒发的是对召公的崇敬之情。由树及人,通过描写召公对树的保护及对召公德政的赞美,体现着德化乐施对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言而总之,无处不在的礼乐,说到底,其实就是中国古人在《诗经》中所流溢的达情与至性的文教观念。“周文诗教和礼乐之教的要点就在性情、物我、内外之间的疏贯与通达。通性情、物我、内外,则可以通天人、古今。”⑨综合所有的这些关系,《诗经》无不体现了其与先民心中宇宙秩序一致的和谐原则。在周代先民的人格形成过程中,礼乐的熏陶是持续贯之的。《孝经》对统治者礼制的规范可以说是义正辞严,比普通百姓更为严苛。《周颂》中,音乐、舞蹈、仪式的庄重舒缓、上下和谐、天人和谐、神人交通,让今人看到了我国古代充满和谐之美的原始“小康”社会。⑩面对现代性以来情盛弊天而不知性的时代,思考“无邪”之诗,矫正伪情,复行诗教文质,协和天人古今之关系,当是《诗经》经学解释最为核心和迫切的地方。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200092)】
①②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页。
③张勇《〈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④李泽厚《美学三书·华夏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⑤⑥杨兴华《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⑦苏志宏《〈白虎通〉的礼乐教化观》,《四川师花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⑧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