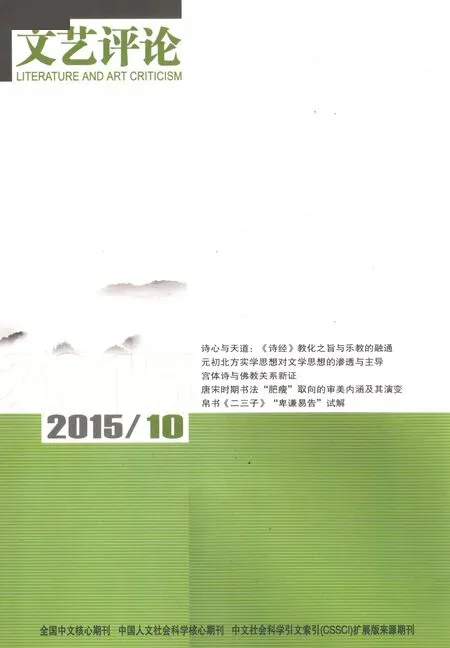汉字与古代文论表达方式的东方特性
袁文丽
汉字与古代文论表达方式的东方特性
袁文丽
汉字构造体现了天地万物之神髓,蕴含了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命的形式符号。汉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汉字极富诗性的思维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文论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意象、直观、整体等思维特征,都能从汉字的类型、性质、构造方式、发展演变、形义关系等方面得到印证。汉字作为生命符号的形式特征及其诗性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古文论“生命化范畴”的生成,促进了独具特色的“生命之喻”①和生命化批评范式的形成。
一、汉字的生命符号特征与古文论“生命范畴”
汉字的创设源于先民的仰观俯察,由观象而取象、味象,最后形成汉字。象形构成了汉字的骨干,其它结构皆因它而成,故汉字最早叫“文”。故古人说:“文者,象也”(《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文者,物象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序》)。汉字虽有六书之说,但最后都可统之于象物的本性,所谓“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②。当代学者成中英在《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一文中论述道:“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来,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③
诚然,不同于拼音文字以抽象代码的组合去记录语言,割断了自身的象形根基,汉字符号的创造是本乎自然、象其物宜的产物。许慎在《说文·叙》中开篇便从“作八卦”到“造书契”的历史叙述来论说这一现象: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汉字符号直接取法于自然人事,其所取之“象”,是活生生的自然万象,是生命之象,“由心灵创造出来”,赋诸“笔墨”,经过高度的概括和简化的具象的符号形体。如“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说文·日部》)。“雨,水从云下也。一,象天;冂,象云;水零其间也”(《说文·雨部》)。如“祭”字,在甲骨文中其形像手持肉醴酒,表祭事,把一个事件的动态过程就浓缩为一个字象符号。符号包涵人们的道德、宗教、现实、审美生活等内容,符号是传播语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载体,它记载着生命。而汉字形式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其净化和简化的形式是对自然万物的概括,在这种概括中,凝聚着人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体现了浓厚的生命情调。因此,汉字是一种生命符号,凝固着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如“交”《说文解字·十下·交部》云:“交胫也,从大、象交形。”“交”字显然描绘的是一幅“一个人两腿相交”的图景,表示两种事物之间发生的一种关系,如交叠、交换、互换等。在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中,此字义进一步扩展和隐喻关联,于是有了“交易”、“交谊”、“交锋”、“交谈”、“交情”、“交涉”、“交往”等,这些都是“交之象”在人类文化领域中的隐喻延伸,隐含着生命的本根。总之,汉字作为具有强烈感性特征的象形符号,其不“指谓”世界,而“显示”世界,将客观世界凝固进象征的符号中;不去割断自然的内在生命,而是力求保护自然生命的原初状态,这种显现虽来自于客观对象,又经过人的心灵过滤,融进了人类对宇宙人生的体认。又如“秋”,在古代总是和愁联系在一起,所谓“悲哉,秋之为气也”,“自古逢秋悲寂寥”,人心与自然同态对应,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融为一体,表示季节的“秋”字从而赋予了别样的文化内涵。
人的体格通于万物,人的生命中的一切都处于和万物共通的生命游荡中。语言文字中就反映了人与万物共通的生命品格。每个汉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隐喻结构,它通常不指向抽象的事理,而指向具象的世界及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真谛,并且主要是生命主体生生不息的运动结构。如果说,汉字可以称作“生命符号”,那么传统哲学、文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称之为“生命范畴”。④所谓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⑤道法天地,人法自然,人类对文学创作规律进行概括,使文学概念、范畴自然沾上明显的生命化象形意味,并由此建构起一个不离美感的符号系统。“气”范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气”,本是一个象形字,象云气之形,如云腾漂流之状,“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见《说文解字段注》)。古人以此云气在天地间流动之状,衍为“精气说”,或“元气说”,“精气为物”(《周易·系辞上》),以为它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体现了中国先人对宇宙万物生命本质最本原的认识。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模式下,先哲们又由物及人,视之为人的生命本原之气,孟子就提出“养浩然之气”,此气就是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和品格,正如《淮南子》曰“气者,生之充也”,《乐记》曰“气盛而化神”,气具有了生命运动的属性,表现出古人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肯定和弘扬。最早明确把“气”作为文学批评理论概念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既指向创作主体的精神个性和生命活力,又指作品生气弥漫、意气周流的健旺征象。基于人、文化、自然的同构性,“气”通过结构性隐喻扩展,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演绎出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语词,如气韵、气象、气势、气格、气调、气力、神气、体气、逸气等等,均指向作品的风格气韵和呈现出的精神气貌,虽每个语词在具体的涵义上各有偏重和不同,但在本体上却不离天地间流荡不息的元气这个本原之“象”。因而“气”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具有了象形意味,它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生命符号表征,能唤起人们心中对一种生气弥满的生命活力的向往。
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许多其它范畴,如风、骨、大、美、善等,大都类乎此。譬诸“骨”,甲骨文为象形字,像骨架相互支撑之形,本义是人或动物的骨骼,是生命的一部分,给人以“力度”之感,常用之观察人的生命力的强弱,因而关涉到骨相之说,继而发展成魏晋盛行的人物品评术语,由实用转向了审美的角度。骨,作为人体骨骼的喻词,代表刚健有力的内在精神品格,是一种坚韧力量的象征,用之于诗文批评,则有“骨气”、“骨力”、“风骨”、“神骨”等,本质上都不离“骨”刚健有“力”的本源之象。此外,虽有些属于形声、会意、指事字,但实质上都是由象形延伸而来。如“性情”、“意志”、“性灵”、“悟入”等范畴,皆以“心”为偏旁意符,为“心”这个象形范畴所统属,“凡心之属,皆从心”(《说文解字注》),自然在人心目中呈现为一种关乎主体境况的生命境象,从而构成一组与创作本原和主体心理相关的范畴。
二、汉字的创构思维与古代文论的表达特性
在林林总总的汉字形体背后实际上横亘着一种“汉字思维”,它是民族思维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汉民族在自己思维习惯的影响下选择了汉字,同时,汉字反过来深深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强化了汉民族的思维习惯。⑥因而,作为这么一种具有生命表征的诗性文字,汉字的创构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传统文论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滋养着诗性化而又生命化的古代文学批评的形成。
1.具象思维的表现形式
中国人往往执著于感性之中表达精深的理性思考,通过形象的巧妙类比来呈示意念,以模糊整体的生命化语言去复现世界的形象,这即是具象思维的核心。它不同于逻辑思维,不是凭借抽象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而是借助具体形象进行思维的认识方式,带有浓厚的直观体悟色彩。简而言之,具象思维,本源及其根本指向在“象”。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思想领域,还是科学技术园地,抑或文学艺术范畴,几乎无处不有“象”的形影。论天体,讲“天象”;说人体,讲“脉象”;谈思维,则有想象、表象、意象、印象、具象、抽象等等。至于作为民族文化之典型代表的汉字,更是与“象”存在着深厚执著的意绪与难分难解的情缘。
如前所述,汉民族的先民们是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法,通过对外界事物和自身的观察、模拟、比类来构造字形。因此,甲骨文里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以一幅生动形象的图画来示意的。如“监”字,下方的器皿表示水,上方一人弓腰监视,水中还隐约有倒影,活脱一幅临水照形的形象,既表示临水正容之义又指称盛水正容之器;“保”字,其左边为一人形,右边为人手托一小儿,意在背负其子;再如“早”的初文“杲”,表万物初醒,朝霞映红了树丛的顶端;“夜”的初文“杳”,表最后一抹余晖被树丛吞没,黑夜笼罩了大地……可以说,汉字较好地保留了原始诗性文字中“绘声绘影”的倾向。
在这里我们也用最小的调整次数nk去保证在新一轮的仿真中解算器不会增加缓冲器的数量.在式(17)~式(20)中,下限已经固定,所以我们仅仅压缩这些调整值向其均值逼近即可降低缓冲器调整值的大小.
同时,由于符号特征的要求,汉字在发展中图画性逐步淡化,首先表现在汉字字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隶变以后,圆润的线条被改为方折的笔画,大大简化了形符。另一方面,汉语言驻足观察的经验性归纳,巧妙运用隐喻关联实现了抽象概念地传达,解决了象形字符表达抽象概念的难题。此一系列变化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其实质是一种具象的抽象。如:甲骨文中,“祭”像手执物置于神案前。“即”像人跪坐而就食;“饮”像人俯身,引颈神舌,就饮于“酉”形器皿上……于是抽象中有具象,具象中有抽象,从而使无形意念、动作行为、物性特征乃至为抽象的概念都呈写意之象。汉字创构的这种具象抽象的致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当代日本比较思想家中村元指出:为什么中国人重视具象的知觉,因为,“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是具象的,而在概念表达方面,他们也喜欢作具象的表达,即使是理论性的证明,也依赖于知觉表象,喜欢作图例式的说明。”⑦中村元先生的话是颇中肯綮的,这也正契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致思方式。古人们把象作为表意的符号,借助具体可感的外界物象比拟、推演出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内在和文学底蕴,恰是具象思维特征在传统文论中的运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文论常用具象来表达审美感受,正如《文心雕龙·诠赋》中说:“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具象批评调动大量可以经验的物象、事象,象拟和比拟艺术作品的体裁、风格以及各种创作方法等。如杜牧《李贺集序》对李贺诗歌的品评: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箓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垅,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⑧
钟嵘《诗品》:
评谢灵运诗为“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评范云、丘迟诗为“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⑨
徐寅《雅道机要》云:
体者,诗之象,如人之象,须形神丰备,不露风骨,斯为妙手矣。⑩
诗歌阐释者与批评家们往往把对诗性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创作合二为一,把解释对象的艺术风貌作为自己创作的表现对象,对诗性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成了可以充分发挥批评者想象力和创造力并灌注批评家生命激情的方式。这种批评建立在共同的生命体悟和审美体验基础上,象写意画一样,以生动具体、含蓄隽永的形象喻示着批评对象的内在风神和审美趣味,譬诸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既是经典的理论著作,又是生动形象、情辞激越的文学性作品。批评家们驾轻就熟地穷尽自然万象来取譬引喻,立象尽意,来传达超验性的审美感受。所取之象自然包揽生机勃勃的宇宙万物,如天地山川、动物植物、社会人事、人文景观、人体自身等等。在中国古人看来,不仅如植物、动物、人是具有生命的物质,其它与人的生命的存在、发展不能分离的万物,由于都具有异质同构的共通的生命精神,都被打上了诗性的生命烙印,即都是生命符号之“象”。批评对象与所喻物象之间,在宇宙自然的博大广袤之中实现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诗性交往、平等对话乃至交融统一,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共振与交融,这正是具象批评的内在机制,象与象之间在绵延不绝的“生命精神”之流中相溶互释。
2.整体思维的表现形式
汉字构形的以人示物,如“眉”,《说文·目部》:“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额理也。”而“目”者,“人眼,象形”。“眉”取象之源本在人。以此为标音形位,可与“木”组合构成“楣”。《说文·木部》:“楣,秦名屋边联也。齐谓之檐,楚谓之相。”屋之边联与人眉有相似性,援“眉”以为楣,透露有施人于物的消息。汉字构形以物示人,如“支—枝—肢”的取象构形和分化衍生。《说文》有“枝”、“肢”,当即“支”的后起分别字。“支”,《说文·支部》:“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由此观之,支的初文约指植物。林义光《文源》⑪说:“‘支’即‘枝’之古文,别生条也。”可谓得其本旨。人身有手足,约如草木有“支”(枝)。《易·坤》:“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唐孔颖达疏云:“四支,犹人手足。”此“支”,后即增“肉”(月)作“肢”。那么在“肢”字未出之前,以“支”表“肢”,即为由植物转类指人身。
汉字整体思维方式,还表现在汉字构形时,通过诗性的隐喻关联,使实象与虚象融为一体,使抽象无形的事物变为具体可感的情态。具体可感的人物体态,比较容易以“象”来描述,而性情神态则难于在简约的视觉形象里加以表现。但是,作为一种意象性的符号,汉字在表达此类情态时,仍不回避“象”的表现作用,这时便使虚实之“象”融合为一了。如“夭—枖(芺、笑)—妖”则反映了虚与实的统一。《说文·夭部》:“夭,屈也。从大,象形。”参甲骨金文,知“夭”为两臂挥摆的人形,寄寓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意义要素。“奔”、“走”字从夭,约可反映这一内涵特征。基于此,转附于植物,即有“枖”字。枖,初约指富于生机与活力貌,故《说文·木部》云:“枖,木少盛貌。”引《诗经·周南·桃之夭夭》证之曰:“桃之枖枖。”枖,通作夭,表少壮之意,常施于鲜花。故毛传曰“花之盛者”。寻绎认识的轨迹,大概是将自然对象在自己身上所激起的感觉,与对人自身的某种具体可感的姿态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引申出女性的妖媚姿态。在文字表现上,区分类属,从而孳生了从“木”的枖字和从“女”的妖字。
汉字这种整体的结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万物“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万物都是由气而生,同时又一气相连。万物从根本上均来自一气,因而气氤氲流荡,溥遍万物,使得万物均处于庞大的宇宙气场的阴阳沉浮当中,故而物物相连,生生相通,旁通互贯,略无间隙。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学之道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道、人道、诗文之道相通相协。正是受此“生生”宇宙观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特别强调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或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天地万物在“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大化流程中表现出的“神”、“韵”、“势”,推崇“传神”、“气韵”,标举“气势”成了华夏美学纵情讴歌生命的主旋律。传统文论家又常把文学作品视作血肉丰满的生命整体,与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联系起来,展示出一派“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混沌视域。如古人把文学作品比喻成自然景象,“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⑫或比喻成动植物,说文学作品如“芙蓉出水”、“鸾凤之音”;或把文学作品直接比作人体,用表示人身部位的骨、筋、气血、肌理、眉目等构成批评术语,如“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懵,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之成全。”⑬“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⑭之类的言述不胜枚举,由此形成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评论现象——“生命之喻”。即古代文学批评在研究文学本身时,由物及人,以为“人”、“文”异质同构,把文学视为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用人体、人之生命气质比喻文学作品的形式。黄霖等现代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生命化文论观的观点,并指出:“宇宙创生论赋予了中国古人以极强的生命意识,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以生命态度对待宇宙自然、天地万物,从而认为世间万物无不生命充溢,活力弥漫,这种生命意识也必然使他们以生命态度对待文学。一方面,使他们往往把文学同自然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文学同自然万物一样,都是生命灌注的生命体。”“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多更直接地把文学看作与人一样血肉完整的生命体。”⑮
东方式的整合思维方式,还制约着中国文学批评注重整体领悟与品鉴,不主张抽象的分析、阐释与肢解的批评风格。如钟嵘《诗品》卷下评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纤秾”风格的描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都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和论述,通过营造一个具体的意象和意境去体味其内蕴,而不作具体的、微观的分别之论。因为任何理论的严格界定,都难免条分缕析下的支离破碎。此外,出于对作品的整体性观照,古代文论诸多的整体性范畴应运而生。譬如上述之“气”,以及“韵”、“神”、“味”、“境”、“圆”等都以整体流动性味美。“韵”有多层含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着一字”、“无迹可求”的“神韵”,其实就是说决不能拘泥于外在的手法和形似特点去理解作品,而应立足于作品的整体去感受与把握它的风神韵味。作品的风神韵味固然难以表述,但通过对整体的审美关照,人们又可能确切地体会,并领略那清远的味外之味。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510521)】
①吴承学最早在《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中提出这一观点。
②郑樵《通志》卷三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③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收入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④汪涌豪《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⑤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第一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
⑥苏春新《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⑦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⑧杜牧《樊川文集·李贺集序》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⑨《诗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9-50页。
⑩徐寅《雅道机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⑪林义光《文源》,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卷十二,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版,第206页。
⑫谢榛《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9页。
⑬李廌《济南集》卷八《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清钞本),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30册),线装书局,第727页。
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收入申骏编著《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⑮黄霖等《原人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