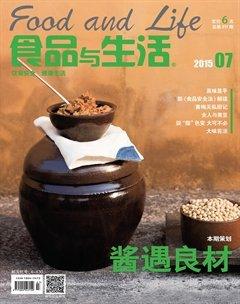一碗苏式红汤面
曹语庭

记得五年前天寒入冬,食堂厨子的脸部表情也如这天气,分外冰冷。朝厨房吼两声,机械地扔出一碗碗冷菜冷饭,让人不寒而栗。冬天,食物的味道固然重要,但食物的温度似乎更胜一筹。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学校隔壁的面馆吃了一碗苏式红汤面,本来就很喜欢吃面的我简直被它勾了魂,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得知,苏式红汤面并非光靠酱油上色,正宗的汤底配方大概是由鳝骨、鸡架、猪骨、螺蛳等熬制而成,汤色清澈、码放规整的细面上撒着细细的葱花,搭配各式浇头,是一款尤其适合严冬的美味佳肴。
再之后,我的一位苏州籍同窗分享了观前街“朱鸿兴”的苏式红汤面如何好吃,听得我浮想联翩,立即搜罗上海分号。可是,上海的朱鸿兴好像没什么人气,终究没去。倒是经常路过开在万体馆旁的“鸿瑞兴”,楼上楼下宾客满堂,大酒楼排场。这阵势,不太像印象中那些猫在深宅小巷里的平民小吃,高贵得让人望而却步。
如果说食物只是单纯的食材,那么品尝食物的环境和心情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情怀,还未举箸,就让人不自觉地主观臆断食物的优劣,然后在一份食物中挖掘得之幸甚的乐趣或是嚼之鸡肋的无趣。学校隔壁的那家面馆,环境很一般,桌子摆放得如同上世纪80年代国企办公室,四张桌子往当中一拼,成了张大方台面,如此这般地将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凑到一块儿,虽然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尴尬,却少不了冬日共取一桌温暖的美意。
记忆中的面好像都是关于苏式红汤面的,不晓得这其中是否有心理暗示在作祟,或仅仅是我与苏式红汤面有缘。一回是工作第三年的年初,家母开刀,当时的我心情之悲痛难以言表。在得知母亲转危为安的那个夜晚,我的心犹如一块沉石落地,不知不觉久违的饥饿感重扫而来,于是在住院部底楼一家苏州夫妇开的面馆里吃了碗大排面。当时去得晚了,只有我一位客人,没想到夫妇俩还是尽心招待。虽然大排面并不是苏式面的典范之作,但毕竟一个多月没有如此酣畅淋漓、心无旁骛地吃顿饭了,那浓郁鲜香的红汤面,无论世道如何光景,我想自己这辈子都无法忘却那温柔明媚的美味。另一回是去年秋天,在苏州十全街上一家临水的馆子,门面不大,装修古典。要了硬面宽汤,配鳝糊浇头。吃时先将鳝糊放入热气腾腾的红汤中浸透,丰盈浓厚的鳝糊在面汤渐渐化开,夹一箸是浓浓的甜味,面汤鲜美香醇,配着评弹做背景音乐,惊艳,惊艳!这就是食物带给人的感觉,超越了任何物质与理解范围,只要一尝到红汤面,顽强的回忆就会被拉到某个画面,如香水一般有持久的记忆。
除此以外,苏式红汤面还让我想起栗良平的《一碗阳春面》,非常简单的故事情节和质朴的人物对话,却展示了在困境中依然坚守希望以及陌生人之间高度尊重的美好人性。苏式红汤面还让我想起一位身在北京的苏州姑娘,周末她会挑一家苏州人开的馆子,吃面听评弹忆童年的石板路,满是对故乡的翩跹思念。
一碗苏式红汤面,直叫人盼着春风又绿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