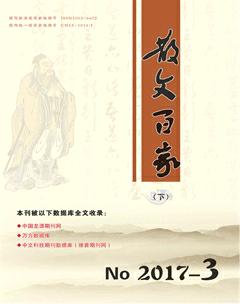馏面汤
张玉军
小时候放学回家,太阳的余晖还没完全消退,家家戶户的屋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升起了炊烟。刚拐进门前那条胡同,就闻到了油炸葱花儿的香味,我知道,娘又在家做面汤了。
我们那地方,把面条叫做面汤。
面汤是地瓜干粉做的,粗糙的灰暗里泛着一点青褐色。地瓜面淀粉多但没有筋,缺少黏性,用它做面汤容易碎,如果直接放进锅里煮就会稀成一锅粥。所以,地瓜面面汤要先上锅馏,熟了再加汤,我们习惯叫它“馏面汤”。
娘把和好的地瓜面放在桌子上,用擀面杖一点点的往外推压,擀成一张大饼。擀着擀着,面饼四周就开始裂开一个个口子,饼越薄口子越大。这个时候娘就停下不再擀了,用刀比量着划成筷子粗细的一条一条。
锅里添了水,娘把切好的面条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篦子上,然后盖上锅盖烧火馏,十几分钟的光景面条就熟了。馏熟的面条就变得筋道了许多,随便翻弄也不会那么容易碎了,把它们放进热汤里,加盐调味,馏面汤就做好了。干巴巴的面条泡进汤水里就变得柔软了,吃起来才不会觉得拉嗓子。
葱花靠油是吃馏面汤必不可少的佐料。花生油倒进一个长把的铁勺里,然后伸进锅洞子用火苗燎,油开了再把切好的小葱段丢进去,香味立刻随着翻滚的油花扩散开来,香气满屋,屋里装不下又飘到院子里、飘到胡同里去了。
吃面汤的时候,把炸好的葱花油浇到面条上,粗糙的黑面条马上就成了一道美味,吃起来爽滑了很多,而且特别香。
我喜欢吃馏面汤,不是因为地瓜面好吃,而是稀罕那个油炸葱花儿的香味。如果看到自己碗里有一块炸的发黑的葱花儿,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心里美滋滋的。碗里没有,就吵着让娘把盆里漂着的葱花叨给我。慢慢咀嚼着香香的葱花儿,感觉唇齿间的香味会慢慢浸润了全身。
馏面汤是我们的家常饭,日常除了地瓜就是地瓜干,馏面汤算是粗粮细作的好饭了。不过偶尔会有例外,那就是亲朋家添了喜,分到家里的“喜面汤”。
我们那儿有个习俗,谁家添喜生了小孩,不管男孩女孩,孩子三日那天,都要给本村的一家当户送喜面汤,算是报喜。喜面汤与平时吃的馏面汤不一样,它是白面做的,而且很宽、很薄,又长又筋道。盛面条的碗里,会放一个剥了皮的鸡蛋,面条上面撒了芝麻盐,用一个方形的木质托盘端着,一家一家地送。收下这个喜面汤,要放在碗里五个鸡蛋或者二毛钱给押回去。
我不知道娘攒五个鸡蛋有多么不容易,也不知道二毛钱意味着什么,只记得那个喜面汤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美味。收到喜面汤,娘会把它分成好几份,一份大的给我爷(我们习惯把在家排行老大的爸爸喊爷),其他几份小的给我们姊们几个,娘不舍得吃只叨一点尝尝,嘴里念叨着:嗯,好吃。
如果哪一天村里突然飘着芝麻盐的香味,我就知道又是谁家生小孩了。我多么盼着是我们家的本姓或者亲戚添了喜,那样我就可以吃到撒了芝麻盐的又白又滑的宽面条了,可是张姓在我们村是小户门,大概就十几户人家,不可能经常有生孩子的,所以每每会令我很失望。
一年中还有一个可以吃到白面面汤的日子,那就是过生日。小时候有几个日子记得比较牢,就是过年节、过生日,都与吃好饭有关。每逢生日,娘会单独给我擀一碗白面宽面汤,再煮两个鸡蛋。
过了夏天开始穿长袖褂子了,我就开始扳着指头数日子,数混了就会问娘:娘,还有几天我过生日?问的次数多了,娘就会用指头戳着我的额头说,不就是想吃面条鸡蛋嘛,放心,少不下你的!我就嘿嘿嘿地满足地笑,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娘的这句话。
娘曾经跟我讲过一个父亲吃面汤的笑话。
大集体的时候社员们一起吃面汤,滚烫的面汤装在一个个水桶里,人手一只碗自己去盛。每个人都狠狠地盛上满满一大碗,满到连半根面汤都装不下为止,然后端到一边去凉着吃。父亲跟别人不一样,他拿着碗先抄一筷子面汤,连翻带吹弄几下,然后几口吞下去,接着再抄一筷子,翻着吹着再几口吞下去,眼看着桶里面汤不太多了,他才狠狠地抄上满满一大碗,退到一边慢慢吃。这样算起来,他至少比别人多吃半碗面汤。
这个极具灰色意味的笑话,我也讲给我的女儿和儿子听过,他们似乎不太懂得爷爷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啊,没有缺肚子的经历,又怎能理解的了呢?于是我就笑着跟他们说:这是吃面汤的智慧。
周末陪娘唠嗑,说起浇了葱花炸油的馏面汤,还真有点想吃。娘说,如今地瓜面倒成了稀罕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