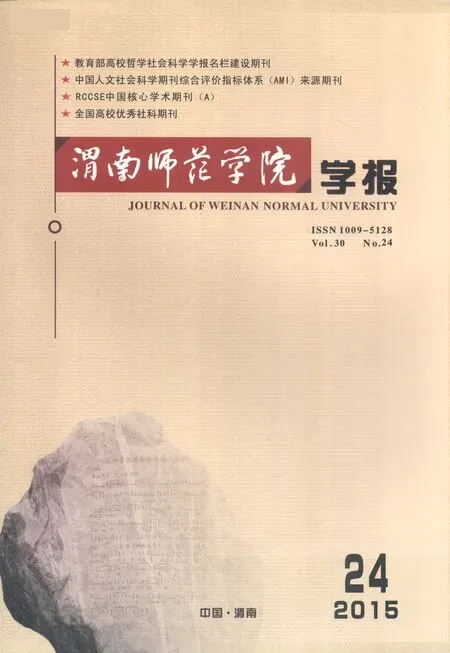略论京兆老秧歌的传承与保护
吴兴洲,韩志伟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略论京兆老秧歌的传承与保护
吴兴洲,韩志伟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京兆老秧歌是京兆村人民经济文化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洛川民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间艺术。它形成于黄土高原,蕴含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文化因子。作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性地保护成为当下的必然选择。
京兆;老秧歌;文化;保护
京兆老秧歌是以洛川县交口镇京兆村为中心形成的一种独具魅力的陕北秧歌舞,其发展传承已历百年。它是体现农村生活的民间技艺,是丰收喜悦的庆贺、代代相传的习俗文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生存意识发生了悄然改变。人们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思想结构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他们不再重视原本世代传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那些传统习俗,而是更多地关注金钱、商业和其他物质、文化方面的享受。于是老一辈秧歌者找不到传人,年轻后生因秧歌形式的老旧传统而不愿意参与其中,因此,京兆老秧歌的传承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于农村,在当前背景下探究京兆老秧歌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于传统习俗和现代文明之间找到文化沿袭的衔接点,发掘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并将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地融入或传承于现代生活之中,既不丢失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又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本文所要着重阐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京兆老秧歌溯源
京兆老秧歌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洛川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是典型的高原沟壑区。京兆老秧歌正是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班固《汉书·地理志》曾提到:因自然环境而形成之习尚谓之“风”,由社会环境相殊而形成之习尚谓之“俗”。一个地域风俗文化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1]1洛川虽然隶属陕北,但从地理环境看,它却地处陕北和关中的交界地带,是介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地方。
从历史角度考查,先秦时期,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而北魏至北周时期,洛川地区则属鲜卑族统治地区之一。[1]15清嘉庆年间,达鲁花赤武威将军贠不花夕督洛川,其后人改姓贠,洛川县境内的贠姓便由此而来。至于洛川县屈氏家族,则是宋末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时,蒙古宣德王郡马、行军大元帅任洛川县令,其后代定居于此,遂形成屈氏一族并繁衍至今。再考之以文物史籍,稽之于现存的村名姓氏,洛川历史上的民族构成,择其要者有羌族、匈奴、鲜卑、蒙古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在洛川地区的生存、繁衍、发展,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文化传承、风土民情的形成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由此不难看出,京兆老秧歌的形成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发达的耕作技术、铁器农具等农业文明、习俗文化,伴随着生产贸易的往来以及战争冲突的蔓延,融入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织,多民族杂居,各种风俗习惯相互融通,造就了颇富地域性的洛川民俗文化和秧歌舞形式。因此,洛川地区既有陕北粗犷文化的底蕴,又有关中农业礼仪文化的因子,特色独具,魅力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京兆老秧歌乃洛川老秧歌之一种表现形式,它之所以依然延续口耳相传的传播形式,是因为其独特的传统性。洛川虽然地理上属于延安市辖区,但严格意义上又不属于革命老区,因此其本身所蕴含的一些习俗特点一直沿袭传承,以致直到今天它仍然保留着其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题材内容、活动时间、演出形式及艺术特色。2004年,洛川县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老秧歌之乡”。
洛川老秧歌,广义上泛指春节前后或其他节日中各类形式的庆祝活动,如迎神赛会、闹社火、耍狮子、跑旱船、闹花灯等,俗称闹秧歌。狭义上则包括特点各不相同的各区域性地方秧歌,属于地方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舞蹈活动。[2]170洛川老秧歌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新秧歌,它主要分为京兆老秧歌和城关老秧歌两支,各有特色。2007年4月,洛川老秧歌被陕西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京兆老秧歌则是流传于洛川县交口镇京兆村的秧歌舞,它是当地“提裙子”老秧歌的另一种风格奇特的表现形式——大场秧歌。
二、京兆老秧歌的文化特征
与陕北秧歌和其他地域的秧歌舞不同,京兆老秧歌体现出由形式到内容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反映出其独具风俗文化特征的魅力。
1.表演人数
京兆老秧歌表演人数一般不限,但秧歌舞必须是五人一组排列成行的队伍,每组形式上分为两男三女,分别饰演伞头、提裙、走扇、马锣手、饺子手等角色,其中伞头、马锣手为男角,走扇和提裙为女角,饺子手为男扮女装。秧歌队少则由五六组构成,多则可由十多组组成,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2.表演服饰和道具
由于扮演角色不同,舞蹈形式各异,因此所着服饰和手持道具也不一样。一般而言,领舞伞头头戴黑色瓜皮帽,脚蹬黑布鞋,身穿蓝色大花绸长袍,右手执绳子,左手持灯笼彩伞。马锣手头戴黑色瓜皮帽,额前插红绒球,身穿橘红色镶黑边的秧歌男上衣,下身着中式裤,脚穿黑布鞋,执马鞭,扮丑相。走扇、提裙、饺子手则梳长辫,戴绣球花额子,身穿各色大襟女上衣,腰系长彩裙,脚穿彩鞋。其中走扇右手执彩扇,提裙腰系白色两片长裙,扮女装的饺子手则手持小镲。
3.伴奏音乐
京兆老秧歌的伴奏音乐以打击乐器为主,表演者所用小锣、小镲等小件既是道具也是伴奏乐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秧歌表演至高潮时,鼓点戛然而止,所有队员停止不舞,围场而转,这时由一个或几个人高声唱起具有本地生活和乡土气息的秧歌曲,给人们送上节日美好的祝福,歌声停止时鼓声重新响起,欢快的秧歌又再次扭起来。
4.表演队伍
秧歌舞表演队伍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前行者为仪仗队,紧随其后者是表演队。表演队伍的队首是秧歌表演的灵魂人物——秧歌队的总指挥,负责指挥秧歌队的全部节目安排和演出,同时也不时做出调动演员情绪、编排节目以及秧歌队答谢、颂唱祝贺词等一系列动作。
男女领头大多都是模样俊俏、舞姿优美的佼佼者,洛川人谓之“秧歌头”,做秧歌头理所当然是很有脸面的事。一般秧歌队伍前方有一条横幅,主要书写秧歌队所属村名,若在夜晚,秧歌头前方则需高举两到四盏大红灯笼。秧歌队伍后方紧跟锣鼓队,过去锣鼓都是由一人背着或几个人抬着,现时大多都是由车拉着。秧歌队伍尾部则是由一些老人和小孩装扮成戏剧人物,同时还有跑竹马、驾旱船、浑身响等演出队伍相随。
洛川人跑的竹马是用竹子或者板材做成的马形架子,蒙上布子,用色彩画出马或驴的脸谱,再用彩绸和彩纸装饰身子,同时在背部中央留一圆孔。跑竹马的人利用圆孔将竹马套在身上,用布带挂在双肩,手拉着马头缰绳进行表演。表演人数可多可少,多则二十余人,男女成双成对,跑起来竹马身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异常热闹。也有一人骑马,扮成小媳妇,另有一小伙牵着竹马,两人表演男欢女爱、回娘家等小故事,为秧歌表演增添色彩。
旱船的形成是因为洛川地处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水资源比较贫乏,因而旱船的表演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水的强烈渴望。旱船的形式是完全依照船的形体做成木架,在木架四周用布料装饰,作为船帮,船帮上扎上弓形木条,上面以彩花和绸飘带装饰,并挂上花灯。最巧妙的地方在船的前部,一般将船艄盖住,上面再用棉裤做成人盘腿的样子,裤腿下还穿着一双精致的绣花鞋。而驾旱船者立于船中间,其裤腰正好与船平齐,将船架用一条红布带子挂在游船者的肩上,双手抓住船帮即可巡游。驾船者一般都是男人扮演成姑娘、小媳妇等戏剧人物,但是由于跑旱船很累,所以常常选择模样俊俏且健壮的小伙子担当,装扮成姑娘样子。跑旱船时,船的前方有一头戴毡帽、长长胡须的艄公具体负责操作,后方则紧跟跑着小碎步的跑旱船者,船犹如在水面上荡漾,栩栩如生。
浑身响乃霸王鞭的俗称,因霸王鞭一般用长约0.8~1米的竹竿做成,竹竿的两端有多处空槽,槽内装有可以来回活动的铜钱数枚,稍微在身上击打便可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所以又称为浑身响。参加表演的人数不限,可以一人单打,男女对打,也可以集体分组对打。表演时舞鞭者手持霸王鞭,用鞭击打或者碰撞身体各部位或者地面。一般会有一个人领唱,舞鞭者边舞边合唱,霸王鞭发出的声响伴着秧歌小调,场面气氛十分热烈、活泼。
5.送秧歌
送秧歌是洛川地区一种独特的年俗活动,一般会在正月初开始组织秧歌队伍,之后便进行紧锣密鼓的排练,等到秧歌舞编排整齐有序后,便开始送秧歌活动。但京兆老秧歌有其特殊的风俗禁忌,传统上“人七”不进行送秧歌活动。因为在洛川民间习俗中,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六,是神灵在过年,只有正月初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过年,所以洛川人谓之“人七”,“人七”这天不会举办送秧歌活动。
送秧歌的队伍进入院户之前,村民会早早在家里准备好烟茶酒菜,等候秧歌队到来。秧歌队进庄院时,主人燃放鞭炮以示欢迎,洛川人谓之“迎秧歌”。队伍进入院子,便拉开阵势表演,扭上一阵秧歌舞后,会空出中间场地进行驾旱船、跑竹马、浑身响等各种形式的表演。常规表演结束,领头的人将根据主家的实际情况,即兴编一套适合主家的秧歌词高声唱出,赠予主家以示祝福。而主人则在秧歌表演完毕后,欢欢喜喜地给秧歌队员发放烟糖水果等,同时也会给秧歌队一定数额现金酬谢。此时秧歌队领头人高声喊出主家馈赠数额,秧歌队员则齐声回应答谢,随之转向另一家。有时村与村之间相互送秧歌,常常会出现两支秧歌队相向而行的情况。尽管平时大家都是熟人,但此时两支秧歌队往往会拼命敲锣打鼓,试图以声音压倒对方。因此洛川有一句因为闹秧歌互不相让的老话,“外甥把舅舅的头打烂,过了年再提上东西把舅舅看”。[1]346到了正月十五,人们乘着元宵节热闹的氛围,各个村镇的秧歌会齐聚县城进行秧歌会演比赛。
秧歌表演主要是扭和唱两种形式,两方面常常单独进行,扭秧歌时不唱,唱时不舞,所以洛川老秧歌的一大特点是“唱则不舞,舞则不唱”。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敲得紧扭得欢,不敲不扭唱起来。”[3]152秧歌队伍里唱秧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样,题材大多是故事、说教、爱情、逗趣等。一般常见的曲目有《十盏灯》《绣荷包》《八仙过海》《十二英雄》《小女子告状》等,也有针对专门活动进行即兴创作,[1]346这也是洛川秧歌的一大特色。
6.人物象征
相传五人一组的表演队伍,其所反映的内容是过去富户人家逛庙会途中的场面。伞头似花花公子,提裙子者似丫鬟,走扇子的似小姐,其他两人为丫鬟、家院一类的人物。表演中伞头在前面开路,一手甩着蝇子,一手转着大花伞;马锣手边扭边敲,步履刚劲;提裙子者舞动裙角,边扭边舞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分外妖娆;走扇子的左手叉腰,右手拿着彩扇,边走边扭;另一名男扮女者手持小镲边舞边敲,整个队伍栩栩如生地展现出花花公子向小姐戏耍调情的场景。
三、京兆老秧歌的发展现状
京兆老秧歌的传承是以京兆行政村为基础,通过家族代代相传保留至今。据学者考证,该秧歌舞已历七代之久,具体情况见表1。[3]172
从表1可以看出,京兆老秧歌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堪忧。
其一,老秧歌早期传承有其历史局限性——传男不传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时代发展特征和文化风习。第六代传人开始出现女性,表明社会风气的变迁和进步,尤其是男女平等。从具体的实地探访和深入调查情况分析,尤其是一些年长者代代相传的说法,早期秧歌表演选择男性避开女性,似乎映射出早期的秧歌表演带有某种宗教意味和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改革开放后,由于新文化的冲击,封建余毒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习俗文化、宗族文化增加了新内容,女性逐渐加入到秧歌的传承中。
其二,从早期秧歌者到其后的每代继承者,京兆老秧歌的表现形式和传统内容虽然基本得以保持、延续,但这些传承风俗文化的民间艺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七代传承者中只有两人是高中文化程度,其他多数为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甚者出现了文盲、半文盲的秧歌传承者。这种状况导致老秧歌的继承和发展产生矛盾,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创新出现断层。要么一知半解,因循守旧,要么喜新厌旧,抛弃传统,甚而有之对民间艺术的继承不能完整地加以保存,对风俗文化的发展不能创造性地开发。由于对京兆老秧歌的接受和认知能力有限,一方面一些秧歌者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民间艺术之宝贵,当然不会悉心予以发展、保护,也就没有迫切的心态在下一辈年轻人中寻找可造之才传承这份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他们更不会有危机感,进而殚精竭虑地给现有的京兆老秧歌注入活力,推陈出新。

表1 京兆老秧歌传承人历史沿革表
其三,二十三位继承手艺者中,前两代均已亡故,第三代到第五代年龄基本在五十岁以上甚至九十多岁,第六代至第七代中年龄最小者也已三十多岁,整体年龄结构偏大,不利于京兆老秧歌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所以老秧歌的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尤其是新时代有理想、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加入,这是京兆老秧歌目前继承、发展、保护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四、京兆老秧歌的传承与保护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民间文化机构的介入,京兆老秧歌的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其一,进行了博物馆式的保护。1985年,洛川县委、县政府着手建设洛川县民俗博物馆,1994年建成开馆。2007年4月,洛川老秧歌被陕西省政府确认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洛川县文化馆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对于包括京兆老秧歌在内的洛川民间艺术、民俗文化起到了应有的发掘和保护作用。
其二,进行了档案式保护。洛川县委、县政府对所有经普查确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纸质、电子、音像、实物的形式分门别类,进行永久保存。
其三,开始了传承式保护。虽然国家实行了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但就目前的实际保护情况而言,效果甚微,只是某些有条件的传承人在文化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传习所,真正做到了传承和创新兼具。
其四,进行了创新式保护。20世纪80年代,当地成立了洛川民间工艺美术公司,但遗憾的是该公司仅仅维持了几年时间。最成功的方式应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洛川县每年举办的元宵节秧歌会演,这一活动坚持至今,从未间断。每年元宵佳节,不论是广场会演还是过节巡演,锣鼓震天,彩旗飘扬,人山人海,到了晚上到处灯火通明,人们欣赏灯棚、敬财神、奉观音,有趣的灯谜,精美绝伦的面花,把传统文化和节日庆典有机融合在一起,让元宵节实实在在地成为洛川人的一道文化大餐。让民众通过表演仪式或者观摩表演过程亲身参与或体验参与,在现实效果上既简单又安全。
从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中不难发现,这些措施其实都是在政府协调和主导下进行,民众的自觉、自发性并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笔者以为,要真正做到保护京兆老秧歌,尚需实现民众观念的改变,要让人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真真实实就在自己身边的京兆老秧歌是块宝,值得骄傲,值得尊重、珍惜和拥有。只要人人自觉、自愿地去接近、学习和传承它,并与时俱进地有所创新,那么京兆老秧歌的保护性开发才算真正步入了正确轨道。
当然观念上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和追求。不同乡镇秧歌代表队都从心底里认为自己乡镇的秧歌是最好的,因而他们便能很享受地,全力地去表演,而且每年的表演与往年相比,在技艺、表演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改变、有所创新。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几个村民知道京兆老秧歌已经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了解者中几乎没人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以及乡镇、村级领导班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使京兆村的文化活动办起来,而不是仅仅建成一个文化活动中心那么简单。
同时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京兆老秧歌本身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是保护工作中常常被忽视的问题。保护者往往把目光集中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还原和复制,很少关注到艺术的发展应该是彰显时代特征,反映社会发展的缩影,所以京兆老秧歌在不同阶段接受变化式的传承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保护京兆老秧歌的同时,也应注意开拓其现代性,不能单一强调对京兆老秧歌的传承和延续,也可将现代新式舞曲音乐和社会生活内容加入到京兆老秧歌的表演中,这样不仅提高了京兆老秧歌在现代农村生活中的接受度,而且使京兆老秧歌能够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永保其生命力。
调查发现,传承者大多年事已高,村里年轻人很少自觉自愿地去学习、参与秧歌舞表演,即便是传承者的儿孙辈,也不愿了解它、接受它,更不愿参与其中,这是民间艺术保护中最尴尬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国家实行了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但观其结果,收效甚微。现实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时俱进,在原有京兆老秧歌的基础上加入现代社会的艺术元素势在必行,文化投入、经济投入应并行不悖。
不论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还是从京兆老秧歌的实际保护现状看,适当的经济投入、新鲜艺术和文化元素的注入,是确保其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对文化工作者而言,在保存原有老秧歌“味道”的基础上,如何创新式地加入新的调味剂,复杂而又颇具挑战性。要想真正意义上普及、传承这一民间艺术瑰宝,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一要打破传统的家族、宗族界限,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成为传承人,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二要考虑使京兆老秧歌走进校园,丰富学生的课外文体活动,既愉悦身心,又增加了艺术传承的群众性、参与度;三要走出当地,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感知其艺术魅力,自觉自愿地为其传承、保护出谋划策;四要将老秧歌的发展、创新与当地新农村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动员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打造特色。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这种近乎神秘的民俗文化凝聚力,不但要使朝夕生活、呼吸一起的成员,被那无形的仙绳捆束在一起,把现在活着的人跟已经逝去的祖宗、前辈连接在一起,而且它还把那些分散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华裔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4]6
另一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很多保护工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统筹事务上,具体的、实质到位的措施不多,很少有人注意到老秧歌的社会功能,更谈不上关注对其经济价值的利用。秧歌舞的社会控制功能,是通过大众群体参与秧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精神的感召、理性的教化、民族或区域文化意识的灌输以及自觉规范和习俗民风的制约,从而加强社会成员的自控能力和群体意识。[5]秧歌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活有很大帮助,要真正展现出京兆老秧歌的艺术魅力,就必然打破表层,深入底层,大胆地进行新的艺术和实践尝试。
利益驱动永远是经济活动不变的法则,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有益尝试。在京兆老秧歌的保护方面,不妨考虑将其打造为一个旅游品牌,使文化传承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一是在京兆老秧歌传习所的基础上适度扩大规模,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或民间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将京兆老秧歌的静态展示、动态表演与洛川会议旧址、洛川博物馆、黄土地质公园等景点共同纳入旅游规划,开发新的旅游线路,在展示老秧歌艺术魅力的同时造福当地百姓,提高其保护民间文化的积极性、自觉性,扩大老秧歌的影响力;二是将京兆老秧歌进行文化再生产,发掘其民间民俗价值内涵,启动经济与文化链接,生产非遗文化纪念产品、秧歌表演服装、道具等,使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良性循环;三是集休闲娱乐与文化建设为一体,广纳八方来客意见,参照其他非遗保护的成熟经验,从形式到内容创造性地发展和传承京兆老秧歌。
总之,京兆老秧歌形成于广袤的黄土高原,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将其变得特色独具,而且经过岁月的洗礼,其艺术魅力愈发光鲜照人。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增加,规章制度日益健全,相关保护措施和机制逐步走向完善,政府尤其文化部门的投入不断增加,民间参与度和参与热情逐渐提升,京兆老秧歌的传承、发展和开发性保护前景将日益光明。
[1] 刘忠民.洛川民俗要览[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2]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3] 李小龙.大源风情[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4] 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5] 许凤英.论秧歌的文化性质及其功能[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8,(4):91-93.
【责任编辑 曹 静】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Jingzhao Yangge Dance
WU Xing-zhou, HAN Zh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 old Yangge dance in Jingzhao Village is a treasur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people’s common wisdom, and it is also the indispensible folk art of folk culture in Luochuan. It is formed in Loess Plateau, which is embodied with the cultural factor of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A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anxi province, it is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while developing.
Jingzhao Village; old Yangge dance; culture; protection
J722
A
1009-5128(2015)24-0087-06
2015-09-06
吴兴洲(1965—),男,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