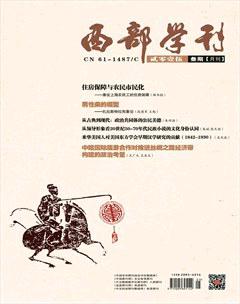从领导形象看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认同
朱斌++张天佑
摘要: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从其领导形象角度看,表现了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倾向。这使少数民族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身份,但也遮蔽了少数民族自我的传统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畸形发展。这为今天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书写留下了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关键词:民族小说;领导形象;文化身份;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根据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研究,社会文化系统主要由三种成分构成:主导成分(thedominant)、残余成分(theresidual)和新生成分(theemergent)。主导成分,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成分;新生成分,则是崭露头角的价值观和社会体验;至于残余成分,则主要指过去遗留下来的、未被主导文化所收编但仍然发挥作用的成分。 [1]以此观照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的少数民族小说,其主导文化成分应是当时主流的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同时,它又是新生成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等,它们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系统的时间并不长,在少数民族都属崭露头角的价值观和社会体验。所以,当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主导成分和新生成分是合二为一的,唯有残余成分,才显得郁郁寡和。而当时,这种文化残余成分,基本指向了各少数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因为无论民族作家们在主观上如何强调与主流文化和新生文化的一体化认同,但在客观上,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文化成分,依然潜移默化发挥着作用,总在小说文本中留下了证明其客观存在的裂痕。
这导致当时少数民族小说在文化身份书写方面存在一种隐性的自我认同。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一些民族作家自我的文学观与当时主流文学观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缝;其二,许多民族作家坚持从自我生活体验出发的创作实践与当时从政治出发的主流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其三,许多民族作家都具有双重文化背景或双重文化眼光。无疑,这对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保存作用,为传统民族文化身份属性在文学叙事中的留存提供了可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流时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过于强大,所以,就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中,突出而显明的,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2]在此,我们聚焦于20世纪50-7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领导干部形象,拟认真追问这么几个基本问题:从当时民族小说领导形象的相关角度看,其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倾向有哪些主要表现?它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其中又存在怎样的缺陷和不足?今天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书写,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一
具体而言,当时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的主流政治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双重改造”,“一切围绕意识形态斗争而运作,它确立的中心词是‘工农兵,其基本语式则是‘阶级斗争和‘革命”。[3]68而且,当时广场式的集体生活、普遍的政治效忠心理,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律令,使整个社会文化日益同质化、单一化,以至于形成单一性政治文化:不但使社会文化身份单一化,而且使人们的政治文化身份本身也单一化。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人们被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革命的朋友和爱国者,另一个阵营是敌人和叛徒”。[4]69因此,当时少数民族小说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对工农兵革命群众的一体化认同,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等——的一体化批判。这些,其实都是当时少数民族小说总体上的主题倾向。所以,当时少数民族小说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首先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内容上。
而众所周知,人物是小说主题内容的主要承载者。为了突出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认同,当时的民族小说常常都有意识地塑造了诸多高大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他们往往都具有突出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是工农兵或无产阶级革命者,尤其塑造了诸多党和政府的化身——各级领导干部形象。这些领导干部,往往作为党和政府的象征,都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着极高的阶级觉悟,常常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发挥着先锋和模范带头的作用,因而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代表,是主流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权威代言人。所以,当时民族小说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为对领导干部身份的一体化认同。
这在讲述阶级斗争——尤其是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类故事中,各族人民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斗争的最终胜利,几乎都与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这样,小说中的领导干部,往往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宣讲者,小说强调突出的常常是其权威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乌兰巴干(蒙古族)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1958)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在共产党员李大年的教育和领导下,蒙古族奴隶巴吐吉拉嘎热等人逐步觉醒,同蒙古王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显而易见,李大年是发动草原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此,叶圣陶有准确分析:“李大年来到阿都沁,党交给他的任务是恢复地下组织,‘把灭了的火重新燃起来。……他能深入群众,在极平常的一言一动之中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叫人受到启发和教育”。[5]5李鸿然对此更有明确论断:“李大年是以党的领导者形象出现的。他临危受命,……使科尔沁草原重新燃起民族解放斗争的烽火”。[6]280因此,李大年的具体身份虽然是多重的,比如,从族裔身份看,他是一位汉人,从亲属身份看,他是王爷府女奴小兰的哥哥,从日常人际身份看,他是乌云琪琪格和巴吐吉拉嘎热的干哥哥,是诸多牧民的好朋友。但小说重点突出的,是其政治文化身份: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宣传者,蒙古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这使他在草原群众中深得人心:桑吉玛一家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许多牧民都将他视为民间传说中的民族英雄黑龙;得到过他帮助的老奴隶道不钦甚至将他视为神仙;原本视他为仇人的巴吐吉拉嘎热也越来越亲近他。草原牧民们对李大年的这种由衷认同,其实正体现了他们对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的由衷认同。因此,他们视李大年为共产党的代言人,比如,好喝酒的扎木苏荣对李大年说:“大年呀!现在你是代表党来劝我少喝酒,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5]243;而王爷府的家兵巴特尔则认定:“李队长是共产党毛主席派到内蒙古草原上来的,是来帮助草原上的人民翻身的”。[5]440
这在20世纪50-70年代表现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民族小说中,是极其普遍的。因此,我们能发现许多深受各族人民一致认同的领导干部形象。譬如,在扎拉噶胡(蒙古族)长篇小说《红路》(1959)中,有领导内蒙古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额尔顿,在李根全(朝鲜族)的长篇小说《老虎崖》(1962)中,有领导朝鲜族人民战胜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八路军指导员——共产党员王为民,而在柯尤慕·图尔迪(维吾尔族)的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1975)中,则有领导维吾尔群众与被打倒的各种反动势力斗争的党支部书记沙比尔。这些领导干部,也都具有共产党员鲜明而突出的政治文化身份特征:英明,坚毅,沉稳,果断,无私无欲,克己奉公,不怕牺牲,嫉恶如仇,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各族人民对他们也都充满了由衷的认同。所以,有论者明确指出:“要讲述一个革命的故事,斗争的故事,领导者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领导者的形象可以基本上等同于政党的形象,因为他体现的不仅是政党意志,而且也包含着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力量”。[7]33这样,领导干部形象常常成为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的象征。
此外,通过讲述新社会落后群众在领导干部的帮助教育下不断成长,表现各族群众克服落后与保守,转而认同新的政治文化体制,并展现他们获得新制度文化身份后积极而健康的精神风貌,这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小说中也极其普遍。这可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故事”,主要是将“旧人”改造成“新人”的故事,其“旧人”——各民族落后群众——的觉醒与成长,也离不开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引导。因此,这类作品往往也塑造了诸多领导干部形象,他们常常以“新人”的身份出现,也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的化身。作为“旧人”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他们往往也都是高大光辉的形象,在情感层面对“旧人”动之以情,在理性层面则对其晓之以理,旗帜鲜明地体现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身份认同倾向。“旧人”最终都被他们感化,成为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要求的新人。
因此,在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的《锻炼》(1957)中,维吾尔农村落后农民麦提亚孜,在互助组干部沙吾提江和艾木拉的帮助下,最后成为合作社带头人。在安柯钦夫(蒙古族)《新生活的光辉》(1955)中,思想落后的山帕拉老太婆,在牧业组组长乌兰吉达姑娘的言行感召下,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加入了互助组。而在刘荣敏(侗族)的《忙大嫂盘龙灯》(1963)中,调皮懒散的侗家孤儿岩生,在共青团支部书记忙大嫂的帮助下,最终走上了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的正道。可见,在这类作品中,具有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领导干部的最终胜利,正体现了新的政治体制及其所要求的政治文化身份在各民族地区的胜利。总体上,作品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倾向,也是极其明显的。
因此,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小说虽然题材多样,人物繁多,但总体上却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主流文化身份的一致认同,这集中体现在各族群众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领导干部的由衷认同上。所以,冰心在回顾当时的少数民族小说时,曾明确指出:其“高出一切之上的”,“是那对党和毛主席的颂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歌,和各族人民在集体劳动中的欢歌”。[8]2
二
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也体现在小说话语上。小说话语主要由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两部分组成,而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它们大多具有浓郁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当涉及具有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领导干部时,无论是叙述者话语还是人物话语,往往都充溢着毫不掩饰的肯定与赞美,其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明显。
我们看几例第一人称叙述者对领导干部的叙述。在李乔(彝族)的《竞赛的第一天》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合作社主任贾撒热多的叙述,就充满了明显的认同。譬如:“我望着他那黑影,觉得这个人又胆大又机警,什么困难也不能阻挡他,大概江水见了他也会让开”。[7]6在敖德斯尔(蒙古族)《“老班长”的故事》(1959)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总务科副科长兼党总支副书记“老班长”的叙述,也充满了明显的赞美,譬如:“他是多么善良,多么可爱的人啊!……在他的脸上,我从未见过苦闷、悲伤的表情”,“那么乐观,那么愉快”,“像一棵高大的松树,屹立在那里”。[9]56在伊敏江·艾克热木(乌孜别克族)的《洪流》(1962)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对领导干部包部长的叙述,也渗透了明显的肯定:“他说话斩钉截铁,是一个确信自己力量的人”,制服洪水后,“包部长站在大堤上,两眼望着洪水,灿烂的阳光洒满了他的全身,看那神气,多像一位传说中的无畏骑士”。[10]无疑,这种叙述者话语对具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领导干部的一致认同,正体现了作品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小说中,许多第三人称叙述者也充满了对领导干部的赞美与认同。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作为草原革命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大年一出场,叙述者就叙述道:“李大年身材魁梧”,“手臂粗大,大铜锣似的脸庞,黑亮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他沉着、坚定”;而且,叙述者还直接点明了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者”,虽然“意识到已经又走进了另一个艰苦的环境里来了。可是,他没有一点儿泄劲的感觉……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5]3这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叙述者对李大年及其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这种第三人称叙述话语,在当时的民族小说中极其常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革命熔炉,把一个不懂事的牧童培育成坚强的红色战士。……如今,在这繁忙的收割季节里,他白天领着几十名突击队员收割,晚上又在煤油灯下制造、改装和修配各种收割机器……成了饲料基地出名的土工程师”[9]88——这是敖德斯尔《金色的波浪》(1960)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对领导干部孟根乌拉人生经历的叙述。而“孙振兴带领山村的受苦人民,砸碎了束缚他们的锁链,打倒了巴依、伯克,从此获得了解放的人们做了山村的主人。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与山村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带领群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11]210——这则是柯尤慕·图尔迪《克孜勒山下》(1975)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对党委书记刘振兴人生经历的叙述。在这些叙述话语中,叙述者对新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文化的赞美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因而,其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也不言而喻。
而且,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小说中,无论是普通人物还是领导干部,其话语往往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领导干部话语,其意识形态色彩常常更加浓郁。在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中,发动蒙古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李大年,其话语往往就是毫不掩饰的主流政治话语。比如,当桑吉玛大妈哀叹日子过不下去时,他教育大妈:“大妈,鬼子和王爷存在一天,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一天,只有我们蒙族人和汉族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扭成一股劲儿,对付这些豺狼,打倒这些豺狼,我们才有出路,才有希望”。[5]175当听见巴吐吉拉嘎热和乌云琪琪格充满了悲愤的歌唱时,他鼓励他们:“只有走斗争的路,才是奴隶们的活路!要挺起胸膛来,把眼光放大,放远,朝前看!奴隶一定要翻身!”[5]223不难看出,这些话语都具有鲜明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因而都体现了小说人物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身份的认同。
这样的领导干部话语,在当时民族小说中可谓不胜枚举。在李乔的《竞赛的第一天》中,合作社主任贾撒热多的话语,也多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譬如,他以彝族山歌的形式,直接抒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与认同:“我们种出水稻来,\要带给毛主席尝一尝,\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怎么能解放?\奴隶已经做了主人,\我们要在凉山上建设人间的天堂”。[8]17而在柯尤慕·图尔迪《克孜勒山下》(1975)中,维吾尔族青年干部沙比尔的话语也如此,譬如,他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任何麻痹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敌人不斗不倒,胜利不斗不来”。[11]121显然,这些话语,也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回响,因而也都表达了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
可见,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话语固然多种多样:有风格迥异的各种第一人称叙述话语,也有风格迥异的各种第三人称叙述话语,还有个性不同的各类人物话语。但从本质上看,这些话语(除了反面人物话语和落后人物的话语之外),却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从总体上表现了各族人民对新政治文化制度的一致赞美和认同。因此,当时民族小说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倾向,在小说话语层面也有着极其鲜明的体现。
三
当然,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一体化认同,在当时民族小说中,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表现,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通常,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浸透了“自我”民族独特的思想情感、心理素质,常常都会烙上深刻的民族印记,体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因而是独特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这样,其人物形象便常常成为特定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标志,读者很容易就能领略到人物形象的民族风采、民族性格,从而一下子就能辨认其民族身份归属。然而,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小说,其人物形象却并非如此,他们体现的,主要不是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而是对当时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因而往往只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情感,却匮乏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这是当时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民族文学领域的一种必然反映。
当时的民族作家同时面临着两种文化:自我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来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族共同体成员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主要标志,也是自我区别于他者的重要文化身份符号;而后者则是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渗入少数民族本土的一种“他者”文化。二者虽然存在诸多契合,但从本性上讲,却是异质的。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特殊语境下,主流政治文化强大而不可抵挡,二者碰撞的结果,是主流政治文化大获全胜。这样,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强调突出的,自然就是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这促使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巨大变革,导致了各少数民族对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身份的普遍认同,使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身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契合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实际: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冲突,确确实实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身份冲突,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身份认同,确确实实是对主流政治文化身份——“工农兵”无产阶级文化身份的认同。可见,当时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那种一体化认同倾向,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12]
然而,这是以淡化、消解各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身份为代价的,各少数民族现代政治文化身份的获得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文化身份逐步丧失的过程。[13]其基本认同方式是政治主导的,以服从和改造自我民族为根本特征,因此,当时民族小说虽然数量庞大,但几乎千篇一律,都是认同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作品,在当时工农兵文学的时代大合唱中,难以发出少数民族“自我”独特的声音,小说塑造的诸多少数民族人物也因过多地涂上了主流政治文化身份色彩而失去了突出的民族特征。因此,当时民族小说在文化身份方面的一体化认同,存在明显偏颇:大多只是对“他者”文化身份意识的单纯迎合,而其自我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并未真正觉醒;只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认同新政体、赞美新制度的主导倾向,但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留下了诸多遗憾,从文化张力的角度看,其中最主要的是:片面追求自我政治文化身份的现代化,而忽视了对自我传统文化身份优秀属性的认同与继承,因而未能维持认同“他者”与认同“自我”之间的必要张力。同时,对异质的“他者”——主流政治文化身份——的认同,缺乏一种必要的反思眼光,因而未能维持认同“他者”与反思“他者”之间的必要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我”文化身份的反常变革——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政治自我”。这些,都值得今天的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化身份书写时认真吸取、深刻反思并批判地借鉴。[12]
参考文献:
[1]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J].文艺理论研究,2005(2).
[2]朱斌.20世纪中期民族小说一体化认同的自我原因探析[J].山西师大学,2013(1).
[3]孙先科.颂祷与自诉:新时期小说的叙述特征及其文化意识[M].上海:上海文艺出
版社,1997.
[4]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乌兰巴干.草原烽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6]梁庭望等编著.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7]程文超等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民族文学编选组.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1949-1979)[M].成都:四川民族出社,1979.
[9]敖德斯尔.敖德斯尔短篇小说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10]伊敏江·艾克热木.洪流[J].新疆文学,1962(6).
[11]柯尤慕·图尔迪.克孜勒山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2]朱斌.回顾·反思·展望:50-70年代民族小说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J].西部学刊,
2014(1).
[13]朱斌.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作者简介: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
张天佑(1962—),男,甘肃会宁人,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与审美转化研究”(批准号:11BZW127)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批准号:SKQNGG12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