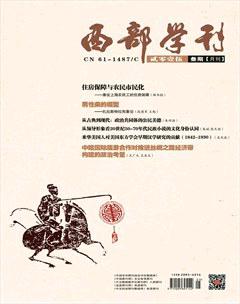《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论
摘要:《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和《伯夷列传》。这“三始”的写作并不以精彩叙事见长,但写得凝重典雅,富有意蕴和高致。由此彰显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反思质疑精神。“三始”的深层意蕴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构筑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石;弘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确立了价值评判的尺度。《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可谓《史记》112篇传记文的“文眼之文”。
关键词:《史记》;“三始”;史家精神;深层意蕴;成一家之言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原始察终,隐约至显,乃古代诸多有识之士著述的深切诉求。作为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史记》的写作诉求之一更是如此。《史记》人物传记主要体现在“本纪”、“世家”和“列传”这三体之中。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12篇。本纪之始为《五帝本纪》;世家之始为《吴太伯世家》;列传之始为《伯夷列传》,兹称为《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始”,不仅是司马迁编排《史记》三体次序上的开始,而且还包含有提挈每一体主题意义、深层含义、确立主调的良苦用心。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学界整体研究这“三始”的成果微乎其微。因此,从文本分析出发,探询这“三始”的深意就显得格外有意趣。
一、写得怎样
从文学叙事层面看,《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文学特色并不鲜明。如《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常常流于粗线条的勾勒,缺少人物活动之细节性的展示,而《伯夷列传》也缺少必要的描写手段,传主形象不生动等。这样的文本效应似乎不足以彰显司马迁的才情。然而,立足史学叙事层面看,这三篇文本的肌理却互相勾连,有效地支撑起《史记》行文的根本走向,加之暗暗地与“表”之“始”《三代世表》、“书”之“始”《礼书》的事实评判和道德诉求相照应,故“三始”之中别有深意。
《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百家》、《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当时的存世文献,加之司马迁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梳理原委,整齐缺失,笔则笔,削则削,择善而缀文。主要内容是:黄帝统一各部,初创国家;颛顼和帝喾的政绩;帝尧的品德、功劳和选拔官吏及禅位的情况;帝舜经历重重磨难和考验之后登上帝位,放逐凶族,广用贤才,行厚德,远佞人,完善了国家组织。全文文学性叙事的手段比较单一,叙事的曲折性也不凸显,但条贯清晰,过渡自然,且语言典雅简洁,敦厚有力。或者说,贯通全文的文气是神圣和古雅。这神圣、古雅当然来自于五帝的功绩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书写线条是:“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引文皆出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1959年版,下文不注)这些话的深意是:黄帝草创国家之后,虽历经颛顼、帝喾、尧、舜、禹不同的帝王谱系,但皆属同姓而延续大统,自此,一个华夏统一的国家形态已经出现。
《吴太伯世家》取材于《春秋》和《国语》的成分很明显。主要内容是:吴太伯、仲雍创建吴国,以及吴称王之前的世系;寿梦称王之后的承续及季札之贤;伍子胥奔吴促成阖闾发动政变,并突出吴、楚、越三方的交错争斗;夫差不听劝谏,任用佞人,骄奢而亡国。全文也不以叙事色彩浓厚见长,但写得很干净,线条明朗而承接有序,且突出重点人物的形象。如延陵季子的形象和后期吴王阖闾、夫差的形象就格外突出。司马迁很擅长细节描写和截取事迹聚焦点来书写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他通过“季札观乐”、“解剑赠徐君”、“哀死事生复位而待”等几个重要场景的叙述,自然塑造出季札所具有的仁义、智慧、博学的君子形象。正如司马迁《吴太伯世家传赞》所云:“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同时,司马迁又善于“寓论断于叙事”中,他通过描述季札三让王位的过程,暗暗指摘了包括阖闾、其弟夫概争权夺利的不义行为。通过史实的勾画,也讥讽了吴与晋本为一家而互相争霸的恶行。全文的重点段落是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争斗的描写,通过夫差报仇不彻底、勾践深谋远虑、夫差骄奢淫逸、勾践复仇而灭吴等几个重要场面的叙述,夫差昏庸失国的形象就自然地塑造出来。《吴太伯世家》以太伯让国为始,以夫差失国为终,古今之变的轨迹鲜明,显示的要义是:礼让的重要性和华夏一体的思想。如《吴太伯世家传赞》所云:“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要义又与《五帝本纪》的主旨思想相互联系,从而使文脉延续井然。
《伯夷列传》写得很奇特:议论成分较多,而叙事成分较少。传主虽然是伯夷,但直接叙述他行迹的文字数只占全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表达司马迁的感慨和议论,从而构成司马迁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上好文本。本文虽取材于儒家典籍等先秦文献,注重史实和论辩的链接,但不乏跌宕起伏的文气,颇有识力。主要内容是:对先秦典籍不载许由等高士的事迹提出了疑问;叙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录《采薇》之歌对孔子称述伯夷的“无怨”之说提出了质疑;以伯夷洁行而遭困顿,颜回好学而早夭,盗跖恣睢而寿终为比较的案例,联系近世以来社会的种种不平,对惩恶佑善的天道观提出了质疑;砥砺道德操行以自勉,若立名后世,必附青云之士,感慨世情纷繁,寄托司马迁述史立言的重任。全文是一篇充满“问题意识”的奇文,问句有:“何以称焉?”、“何哉?”、“怨邪非邪?”、“是邪非邪?”、“恶能施于后世哉?”等,问题有:许由等高士存在不存在呢?伯夷、叔齐是有怨呢,还是无怨呢?天道是对呢,还是错呢?君子的名声怎样才能立于后世呢?这些问句和问题如同屈原的《天问》一般,具有扪心反问的苍茫感和悲剧色彩,字里行间与司马迁遭受的困苦但历史使命感永不泯灭的精神相沟通,形成一股股的愤懑之情。而且,最值得肯定的文笔是:司马迁借伯夷、叔齐的事迹,对儒家经典和圣人之言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对天道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对如何立名提出了建设性的质问。这些质疑和质问正是70列传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因而,《伯夷列传》的文气奇特而苍凉,虽不以人物的形象塑造见长,却以人物命运的多舛见深。甚至可以说,此文的旋律可以统领70篇列传的主调。并且,《伯夷列传》中所论及的大一统思想和太伯让国的善行,自然又与《五帝本纪》和《吴太伯世家》的主旨相互照应,从而使文章气脉连贯而充满深邃的朴素辩证思想。
总归《史记》人物传记这“三始”的主旨内容和叙事笔法可以想见,司马迁是带着深刻的创作理念来书写这三篇奇文的,他既信仰大统、天道,又暗示人事的力量;既折中儒家孔子,又心存独立的判断;既“疾君子没世而名不称焉”,又寄寓自己的名实思想。他反复思虑,考究严密,文脉线条足以贯穿112篇传记的文字笔墨,精神旨趣足以携领112篇传记的哲理议题,从而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物化为一体。同时,仔细阅读《太史公自序》的文辞又可发现,序列第130篇的自序之文常常与“三始”的核心思想也互相照应,如:“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等等。于是,原始察终,首尾呼应,112篇传记构成一个互相支撑的统一整体。
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看,司马迁重视这“三始”的写作工作,自然与史家的身份不无关系,即:历史观念成熟,历史意识自觉,历史使命强烈。此外还与战国秦汉之际学术界慎始敬终的时代风气、思维习惯、文化传统等要素密切相关。然而,还有一个写作因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轻易不为人所论的,那就是:《史记》人物传记之所以重视“三始”,与司马迁领悟《诗经》的“四始”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创作现象。
《诗经》四始为:《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根据汉儒的说法,这“四始”是由孔子编定的,并寄寓着孔子深刻的治世思想。汉代齐、鲁、韩、毛这四家《诗》都曾言及“四始”的重要性,如《毛诗序》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1]63
“四始”的这一名词即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当然,最早提出“四始”概念的并不是司马迁,而是以汉初《诗》学大师申培公为代表的《鲁诗》派。根据陈桐生的研究,《鲁诗》提倡“四始”所揭示的四大主题是:《关雎》的特殊意义在于重视帝王婚姻伦理;《鹿鸣》倡导尚贤;《文王》倡导尚德;《清庙》推崇孝道。其目的是,“要将《诗三百》纳入礼乐思想的轨道,使《诗经》成为王道政治的范本,所以,《史记·孔子世家》在叙述‘四始之后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2]114陈先生的这些看法是中肯的,因为清代的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就已经指出,论“四始”之说的要义当遵从《史记》所引的《鲁诗》。要之,“四始”不仅提炼了《诗经》的主题,而且概括了战国秦汉之际儒学思想的精髓,值得后人研究。
正因为司马迁了解《鲁诗》“四始”之说的精髓,也领悟到孔子重视“四始”编定的深意,因而,《史记》格外看重人物传记之“三始”,就有了认识论方面的学理支撑。而且,恰如《史记》人物传记的“三始”精神融化为《史记》的血肉一样,《诗经》的“四始”精神也融化于《史记》之中,举凡涉及帝王婚姻伦理、尚贤、尚德、崇孝的内容,司马迁都格外重视,并写下《外戚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自序》等与这四大主题内在关联的名篇佳作。也就是说,《诗经》的“四始”和《史记》的“三始”都可视为是寄寓着作者言外之意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写作理念追摹着《诗经》之“四始”的编定方式,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使这三篇文章的风格显得既凝重典雅,又开阖自如,富有意蕴和高致。
二、史家精神之显现
尽管《史记》之“三始”在叙事层面并非人物传记中的上等之作,甚至也并非是详略得当、笔墨精到的才子之文,但是,通观这三篇作品的内在肌理,“三始”依然拥有感动后人的力量,一种洋溢着史家“实录”精神和反思质疑精神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已超脱叙事层面的考量,正如鲁迅的小说以唤醒人的筋骨为上一样。
《五帝本纪》放眼远古,所述的时间横跨三代,围绕五位传主所写的人物不少于40人,然而,司马迁总是力求做到考信于史实,折中于六艺。《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段话至少说明司马迁撰写五帝谱系的历史理由是:一、重视文献考索,即重视《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存世文献所说的黄帝谱系,又重视《尚书》不载黄帝之事的特例,两相折中之后加以考索。二、依据实地考察。即司马迁通过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后,确定了黄帝谱系的合理性。三、择善而从。即剔除《百家》不雅驯的成分,弥补《尚书》不记述的缺失,著述自黄帝始。四、保留空间。即五帝古史遥远,非好学深思、心领神会之士可以为同道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具有一种朴素辩证的历史观:他既折中于六艺,又保持独立的立场;既重视存世文献,又重视实地调查;既述往事,又思来者。对比汉初盛行五德终始论、神异论的风潮,司马迁的这些言说的确是清醒的,也是合理的。
尤其为人认可的是,《五帝本纪》显示出司马迁独立的古史辨伪及取舍精神。战国、秦汉时期是古史系统众说纷纭的时期,帝王世系始于何时?帝王谱系由谁建立?禅让和承袭的轨迹如何?等等问题一直是那个时期的士人关注的话题。况且,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言说目的,百家之语并不相同,出现话语众多的情形也属难免。更甚一步,众语喧哗的局面有时也会出现伪造古史的现象。为此,顾颉刚先生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中说:“战国、秦、汉四百余年间,为了世官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3]171其中,古代帝王史迹就是一个值得争辩和争相建构的重大问题。于此,儒家有儒家的帝王行迹学说,墨家有墨家的帝王行迹学说,而道家有道家的帝王行迹学说,各家的观念和谱系并不相同。置身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司马迁编写《五帝本纪》是需要花费一番气力的。
由此看出司马迁的写作标准是:在折中于六艺、整齐百家之语的基础上,采用信、雅、达的策略完成这个时代难题。信,即信实、史实和信服。“信”的途径是将历史文献、实际考察和民间传说结合起来。雅,即言说雅正不荒诞,剔除怪、力、乱、神的成分。达,即通达而留有话语空间,为后来者提供再研究的可能。所以,他一提到上古,常常叹一声“尚矣”,于是,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等信实的感慨就落下笔端了。这磊落的态度是那个时代的人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成一家之言”是需要大魄力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借用刘向、扬雄的话语而评价司马迁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此话可谓知言之语。“文直”、“事核”突出了司马迁的考信原则;“不虚美”、“不隐恶”突出了司马迁的求实原则。两者结合构成“实录”精神的核心。《五帝本纪》已经体现出“实录”精神的一斑,而在《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之中,同样显现出这种精神的风貌。《吴太伯世家》记录吴国自太伯创建至夫差国灭的大事。书太伯十九传国至寿梦;书寿梦六传王位至夫差亡于越;书吴与诸侯相交相攻;书吴国统治者既有让国之举又有篡位之罪;书季札等贤人事迹;书吴越争霸过程,皆详略得当,言说有据。文中所列的“太伯让国”、“季札观乐”、“季札之贤”等事迹绝非虚美之词,而所记的“阖闾与王僚争位”、“阖闾与其弟夫概争国”、“夫差昏庸失国”等事情也没有隐讳“不仁不德”的性质,并与初始的“太伯让国”之事形成强烈的对比效果,令人感慨。并且,记事详于寿梦称王之后,与《十二诸侯年表》记年起吴王寿梦元年相照应,由此见出司马迁谨慎求实、略含刺讥的良苦用心。诸事皆取材于《春秋》、《国语》、《论语》、《左传》等存世文献,清晰地勾画出吴国世系承传的轨迹,由此也彰显出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写作用意。《伯夷列传》中曾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司马迁也亲自在箕山上见过他的坟墓,但史公决定还是不为其立传,原因在于三点:一是此事不见于虞、夏之文,禅让之事也不会这么草率;二是孔子列举让国的古代圣贤如太伯、伯夷类,但不曾提及许由;三是许由没有文辞流传,并牵涉卞随、务光的虚拟性。这三点认识乃打破传统信仰而来,胆量足以使人钦佩,所以,顾颉刚先生曾称赞司马迁:“他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3]178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夷列传》的内容虽写得自由洒脱,但论及史学问题,司马迁终以“史家”之眼光择别真伪,并没有逾越信实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说,《吴太伯世家》是司马迁践行“不虚美”、“不隐恶”求实原则的典型文本,《伯夷列传》则是司马迁践行“文直”、“事核”考信原则的典型文本。
在司马迁身上彰显的史家精神还体现在反思质疑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史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从事了深度的调研工作,甚至走访民间进行实地考索,但是,笔下之文依然会存在诸多的空白点和存疑之处。这是难以避免的书写现象,也是当今“新历史主义”质疑历史著作信实程度的理论依据。然而,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避讳这样的理论问题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G·R·埃尔顿所说:“历史学家如果专心于诚实和正直——留意未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意识到他不是一架机器,他能够被爱、愤怒、屈辱和虚荣所打动——那么,他就适当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必须成为一位学者,也就是说,他必须为他的人性增添(而不是消除)一种维度。只要有可能,他会明智地培养怀疑的精神,也就是对所有断言的确定性持保留和质疑态度。”[5]119因而,反思和存疑反而成为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应当秉持的优秀品质,司马迁的表现即如此。如在《留侯世家》中,司马迁曾记述张良出奇计以成“马邑之战”破敌的故事。由于隐秘之事难以言说,司马迁便曰“故不著”。又如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曾记述高祖窘迫的“平城之围”之事。他说:“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这样的空白法才称得上是审慎之举。
《史记》“三始”中,司马迁反思和质疑的精神尤其引人深思。《五帝本纪传赞》中所说的“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思辨方法、《吴太伯世家传赞》中所说的“见微而知清浊”的警醒意识,都有近于现代人所推崇的历史哲学的味道。或言之,他的历史观已经触及人的心灵问题,力求在历史过程的演进之中加入一种“深谋远虑”式的探询。而《伯夷列传》中的“三个质疑”和“一个反思”更是达到一个历史与思想融合共生的高度。这“三个质疑”是:远古贤能许由等人存在否?孔子称颂的伯夷“无怨”之说果然如此乎?天道果真惩恶佑善否?这三个质疑涉及的问题包括:古史辨伪、既折中孔子又消解权威的勇气、天人关系的复杂和多变。探其实质便是:大胆的疑古精神、冲破传统礼义的怀疑精神和“究天人之际”的哲学精神。“一个反思”是:如何立名和成名?此思虑上接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名实思想和《左传》所言的“立德”“立功”“立言”思想,中接司马谈所要求的不辱先人的思想,下接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引人驰骋古今,浮想联翩。要之,司马迁反思和存疑的精神不仅仅在探求历史的外延,而更在于探求历史的内涵,所以,正如李长之评价司马迁所说:“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6]206
三、折射出的深层意蕴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史学作品,衡量其优秀程度的一个标准便是有无深层结构。具有了深层结构,便具有了内蕴,便具有了力度、广度和深度。我们说之所以称鲁迅先生的诸多作品具有深层结构,乃是因为他的作品暴露出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同理,之所以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是因为这部著作具有一定分量的彰显明代中后期官僚政治运行体制得失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脱胎和脱离表层结构而展现,突出了文本存在的肌理和骨力。深层结构孕育出深层意蕴,深层意蕴显示出深层结构的脉络。而《史记》的深层意蕴更值得后人深思,从而归纳出一般的“中国问题”。于此,我们仅仅结合这三篇文本的思想史价值来分析一下其中的滋味。具体而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三始”的深层意蕴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构筑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石。中华文化精神的基石是多棱面的,其中,统一的多民族互相融合的大家庭观念是延续中华文明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这一共性认识即由《史记》初步完成。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所宣扬的正史“自黄帝始”的大一统观念的确具有思想史的建构性质。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一贯倡导的仁义道德精神、重视人事的精神,也是时至今日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体现。
按照司马迁《五帝本纪》的记载,自黄帝至虞舜同姓而非一家,典章制度一步步完善,最突出的观念是大一统思想和以德治国的理念。《吴太伯世家》着重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谦让精神和仁义道德的重要性,并显示了华夏一体的血脉关系,与《五帝本纪》的大一统思想密切关联。《伯夷列传》最值得后人继承的史学财富是怀疑精神和名垂后世的思想,同时又颂扬“奔义、”“让国”,谴责“争利”、“争国”,这又与《吴太伯世家》中的思想相照应,故陈直在《史记新证·自序》中说:“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7]2因此,这“三始”共同的文脉主调是:强调大一统思想和王道观念,推崇仁义礼让的儒家精神,激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思想,并且,对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提出质疑,感慨世情的纷繁复杂和多变性,突出“世家贤大夫倜傥之人”的生存意义。可以看出,这一主调一方面可统领《史记》这112篇人物传记的内容要义,具有导引、牵连和组织架构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可显示出《史记》历史哲学思想的厚重与伟力。《史记》“三始”中所蕴涵的大一统观念、原始察终的历史意识、谦让精神和怀疑精神;《伯夷列传》中关于人道、天道统一与分歧的哲理思辨,也是当今我们思考的“中国问题”。这些思想无疑具有穿越时空的性质,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我们作出解答。站在时代的坐标上,司马迁的这些深刻思想,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有穿透力的话语资源。尽管这些思想基石并非由司马迁一人来书写完成的,如他的父亲司马谈也在这些思想的凝聚时发挥过整合作用,但书写篇章的大手笔毕竟是由司马迁来完成。换言之,司马迁至少是一位探讨中华文化精神的总结者、传承者和发扬者。从这个层面讲,司马迁可称得上是一位具有哲学家资格的历史学家。
其二,弘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史记》“三始”中,最为鲜明的思想旨趣便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推重儒家思想。不论是《五帝本纪》对《尚书》、《春秋》、《国语》以及《五帝德》、《帝系姓》的推重,还是《吴太伯世家》对太伯、季札仁义礼让的颂扬,还是《伯夷列传》对孔子言论的信任,都可谓司马迁尊儒思想的写照。有学者甚至说《伯夷列传》明写伯夷,暗衬孔子,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互证,阐明义例。“伯夷和孔子两人都是本传的中心人物,而伯夷却又只是用来陪衬孔子,借以抒发议论的。”[8]1316所说颇有见识。《孔子世家》曾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太史公自序》曾转述其师董仲舒的学说时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名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既是公羊春秋学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当一王之法的要领,也是司马迁从内心深处秉承孔子思想的理论依据,并由此显示出司马迁弘扬儒家思想的自豪心和归属感。
司马迁的这种弘扬,与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尊崇黄老道家的思想旨趣并不相同,由此见出司马迁独立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这种弘扬,与汉武帝时期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一尊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又可见出司马迁顺应时代潮流的远见卓识。正因为如此,《史记》中推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在夷夏关系上,司马迁肯定蛮夷民族对华夏的归附,反对蛮夷民族的离心倾向。在四夷不肯归附的情况下,司马迁不同于一般腐儒拘执于德化,而是赞成汉武帝用武力平藩的战略,以此来实现用夏变夷和天下一统。”[2]85同时,司马迁对汉初的吕氏之乱和七国之乱等分裂行为表明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以此显示他的政治观。当然,《史记》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非全盘继承儒家思想,而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态度,正如《伯夷列传》之中的质疑精神一样,富有批判意识。这才称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高明之处和难度之处。
其三,确立了价值评判的衡量尺度。经过司马迁精心的安排,《史记》112篇人物传记的内容既丰富又多彩;人物形象既有王侯将相又有布衣百姓,涉及面广,各阶层的人士都有,从而构建起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面目。如何评判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何评判人事的复杂多变?如何评判天人关系?如何评判古今之变的一般规律?等等难以作答的问题必然是司马迁思考的重大问题。司马迁的回答自然是通盘考察的结果,然而,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他常以这“三始”的精神,即大一统原则、仁义道德、谦让拱卫、折中于夫子、原始察终、重天道亦重人事的思想所构成的观念体系,来评价本纪、世家、列传这三体中诸多传主行事的是非曲直和功过得失。如《项羽本纪》论赞曾评价项羽云:“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评价因素中即以项羽不施仁政、不重视人事为标准,指摘项羽的功过是非。恰如《太史公自序》所言:“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再如《魏世家》论赞云:“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这些评价突出两点,一是赞赏秦一统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相信天意的抉择。这两层意思司马迁兼而有之。大一统的思想自然显明,而既相信人事又相信天命的思想同样是《史记》“三始”的精神之表现,后人不必各执一端,曲解那个时代的司马迁。再如《张耳陈余列传》中曾提及《吴太伯世家》所倡导的礼让精神,司马迁讥讽张耳、陈余虽然有朋友之交的往事,但是终乏仁义之士的高节,故曰:“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意思是,两人为势利之交,有失古风,名不副实。诸如此类的评价之语和评判理由,都是司马迁以《史记》“三始”精神作为衡量尺度的一个个呈现。甚至可以说,《史记》人物传记受这个价值取向的影响不是某几个篇章或一枝一叶,而是渗透于整部著作之中。
进一步说,《史记》人物传记这“三始”可谓是《史记》“三体”文重要的“文眼之文”,经由这个“文眼之文”可窥探许多人物传记的思想内核。《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中的责任感、使命感可见一斑。而这“三始”也真正体现了史公之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作目的上好的文本体现。本于此,我们重温《史记》的风格和司马迁的人格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陈桐生.史记与诗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G·R·埃尔顿著,刘耀辉译.历史学的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7]陈直.史记新证·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孙纪文(1967-),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文学要籍研究”(编号:2013RC06)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