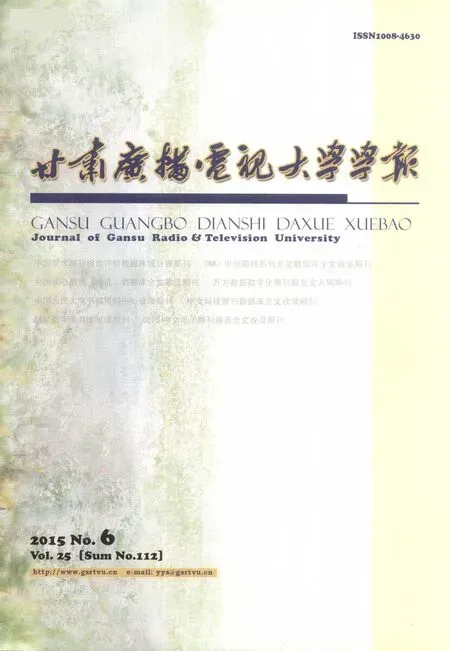汉代四言诗的《诗》学背景
张 侃(上海商学院 文法学院,上海 200235)
汉代四言诗的《诗》学背景
张 侃
(上海商学院 文法学院,上海 200235)
《诗》学是汉代高雅形式的四言诗的创作背景。从《诗经》本文的实用典雅到春秋以来的“赋诗言志”,再到战国以至汉代的《诗》学理论的宗经、征圣、明道到“美刺”的批评,主旨皆在遵循传统而付诸实用,未曾出现四言诗创作的新见,使四言诗在汉代走向衰落。
《诗经》学;“美刺”;四言诗
历经战国动荡、楚汉相争的数百年动荡,汉王朝的建立,终于迎来了王朝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传统文化也进入劫后复苏的阶段,然而其基础却相当薄弱。一是刘邦草莽出身,轻慢儒术,遑论文教。人笑项羽“沐猴而冠”,同是楚人刘邦未必不是如此。二是汉承秦制,至惠帝时始除秦挟书之律,风雅文教才得以传播和实行。以《诗》《骚》两大传统文学为背景的文学才得到发展。因而在对《诗经》与屈《骚》阐发与批评的基础上,属于汉代自己的诗歌创作渐次生成,并首先影响到作为汉代主流诗歌形式四言诗的创作。汉代诗学理论的建立,是基于对先秦典籍的发现与整理,并与当代经验主义的思想基调一致,而对《诗》《骚》的阐释与仿制,就成为汉人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所以,《诗》《骚》尤其是《诗经》的批评理论,直接引导着汉代四言诗的创作。
汉初即以鲁、齐、韩三家今文诗立于学官,《毛诗》是古文经,在西汉初年已行世,至东汉尤其是经郑玄笺注之后,才将三家诗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但无论古、今文《诗》的兴替如何,其对政治教化功用的强调却属一致。而汉人特别重视《诗》学这一功用的其因,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梳理。
一、《诗经》本身的实用功能特征具有典范意义
周民族在早期持续不断的迁徙生活中,农业生活造就了其重实际而轻玄想的气质,形成了重事功而黜文饰的作风,这使得诗人的激情往往是通过质朴的语言以含蓄蕴藉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上也是以节奏质朴而工稳的四言为主。在此意义上,《诗经》正可谓纯文学。而四言诗这种以两个节奏组成一句为主体的音律节奏形式,既是汉语诗歌发展早期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恰适于表达那种温雅醇厚的宗法伦理精神。当然,《诗经》中并不乏四言以外的各种语句(节奏)形式,说明《诗经》时代的人们并非不能创作出四言以外的诗句,而从人们多采用四言形式写作并普遍地欣赏这种形式的诗,可知其审美观念为时代主流。换言之,这种简短而且明畅的节奏,与宗法贵族体制的社会中人们庄重、舒缓的感情和气度相契合,也与这个时代的审美需要相一致。
从其深层的文化功能看,由于《诗经》的时代是贵族宗法伦理精神统治的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宗法制度下的子民,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取向与社会体制基本保持一致,诗人宛如家庭成员,负有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如《大雅·公刘》谓:“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何楷释云:“君、宗,即燕饮中事。公刘自以一身为君臣之君、宗也。对异姓之臣称君,对同姓之臣称宗。”因此,关注社会生活是每个诗人的天职,“诗言志”,所以《颂》诗希望通过对先民与部族英雄的感念以培固今日的社会秩序,如《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雅》诗褒扬兢兢于王政朝纲,扶正纠偏的政治举措与美好愿望,如《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富万邦。”《风》诗虽然“感物道情,吟咏情性”①,但更多的则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所以,以四言节奏为主的旋律,使《诗》的本事本旨借音乐的翅膀飞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进一步为《诗》提供了酝酿与生长的沃土②,所以诗人能够“作此好歌”(《小雅·何人斯》)、“穆如清风”(《大雅·烝民》),出于自然的吟唱,却不期然而然地具有了“动天地,感鬼神”(《诗大序》)的艺术力量。因此,《诗》便发挥着以乐教、言教相期“神人以和”(《尚书·虞夏书》)的巨大社会功用,是诗人的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津梁,也是引导全社会和谐共存与向前发展的精神指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说,《诗》几乎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全部。
二、春秋战国以来的板荡格局,使《诗》的功用发生新变
《诗》曾经维系着西周至春秋初期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当王纲解纽、社会出现危机时,诸侯争霸成了社会政治的常态。因此朝聘盟会之际,诸侯卿大夫于折冲樽俎之间,必赋《诗》以言志。因为他们表面上都打着代天子征伐的旗号,所以最初必须申述一个各方不得不认可的观念标准,故所言之志也许尚与《诗》的本旨本义相近,以示师出有名。后来则于针锋相对之中,抛弃了尊王的观念,只将赋诗言志这一形式存留了下来,大家都借《诗》以陈意,《诗》于是有了诗外之旨,所谓“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须称《诗》以喻其志”(《汉书·艺文志》)。隐幽难表之意借发挥《诗》而得以晓畅明白,于是《诗》本旨本义成了喻体,而所赋之志成了主体。而因为《诗》成了喻体,所以咏桑间濮上男女风情之《诗》也可用在外交迎接的场合③,同一首诗也可言不同之志④,听者不能知志且未能答赋者,等于在这个驰骋争霸的时代缺乏一种沟通交流的手段,等于漠视被吞并覆没的危险,被断为“必亡”之兆⑤,所以“不学诗,无以言”,不仅是不能“使于四方”(《论语》),且不能“明志”⑥,不能“兴于诗”而致知⑦。因此孔子也以断章取义之法教《诗》。从此,《诗》成了交际中一种用以沟通的具有实用意义的经典。
到了战国时期,朝聘赋诗已成历史遗迹,诗乐分家,世俗之乐兴起,于是《诗》的文字意义凸现,断章取义的局限也就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孟子认为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做法有碍于学《诗》修身,他指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他认可诗乐的分家,“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强调对《诗》的整篇本义的理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法先王”,以至于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境地(《孟子·告子下》)。其次是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以为“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王制》),只有学(劝学),才可为“天下列士”(《荀子·大略》),而圣人的治理经验则反映在《诗》、《书》、《礼》、《乐》、《春秋》之中,所以要“宗经”,并由此途径而体会圣人之道,即“征圣”,而“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可以使人进而明道。将《诗》的功用归诸宗经、征圣、明道的教化系统之中。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主张复古,以为“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针对当代的社会实际,他强调“礼”:“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礼因文饰能使人在愉悦中接受,而礼义之文中,正包括着诗乐等等,“乐合同,礼别异”,乐对于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亲和具有重要作用,乐教是礼制的辅助,而由于乐是“人情之所必不能免”,所以“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移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乐论》以为诗、乐、舞本是三位一体,所以对于《诗》,他更强调音乐的因素,看到音乐巨大的社会作用,进而主张用强制手段将“圣王之迹”通过“乐”推行,在系统强调《诗》的实用功能的同时,启汉代文化专制观念的先河。要言之,这是一个“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时代⑧,一方面使《诗》成为经典,另一方面诗义被曲解,成了这个时代诗学衰落的诱因。而到荀卿的《诗》学理论,则对汉代诗乐观念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三、汉代《诗》学理论与批评的实际
从汉初至景帝末,汉朝贵黄老而尚无为,各家学术继战国余绪而发展,儒家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但儒家经典还是受到相当的重视⑨,荀卿的学生浮丘伯在高后时仍然在长安讲《诗》,他的学生鲁国申公一直活跃于汉廷与诸侯王国之间,其所传《鲁诗》,与《齐诗》、《韩诗》并立于学官。承荀卿的学术传统,汉代《诗》学仍然主要就文字立论。
首先,从《诗》学理论而言,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今存十一篇。因为先秦时代所谓“乐”往往是指诗、乐、舞三位一体,所以《乐记》论乐,实际上包含着它的诗学理论⑩。《乐记》继承了荀子《乐论》中对“乐”的重大社会功用的强调。荀子以为乐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记》进一步指出“唯乐不可以为伪”皆“人心之感于物”,所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鉴于乐“其感人深”,所以乐具有“礼乐刑政”而达于王道的政治意义:“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具有“移风易俗”导民向善的教化作用:“乐者,所以象德也。”郑玄注:“乐所以使民象君之德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乐施》)因此,对乐的强调也就是对《诗》的重视。《乐记》诗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不能诗,与礼缪”(《礼记·仲尼燕居》),“志之所之,诗亦至焉;诗之所之,礼亦至焉”。从诗之“志”可知先王之礼(《礼记·礼器》),以求得“明于礼乐”(《礼记·仲尼燕居》),使诗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二是指出诗之志的品质,“志之所之,诗亦至焉”,而“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诗》具有了“美刺讽谕以教人”的功用和“温柔敦厚”的品质。
其次,就《诗》的具体批评而言,齐、鲁、韩三家《诗》仍然依文字立论,其共同特征是对《诗》的阐释紧密结合现实,掺杂了当时的政治观念,并非就《诗》本义立意,而是引诗证“序”,“序”重事理,而所谓事理多为当时的政治观念乃至阴阳灾异谶纬,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教化服务,故其实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赋诗、引诗相一致。所以对《诗》的功能的认识,重在美刺,参与现实斗争,讽谏朝政。大儒董仲舒的《诗》学与三家诗说相去不远,他将诗的“美刺”的根源附会以天之谴告,他指出“《诗》无达诂”,然而并未就诗艺的含蓄蕴藉进行探寻,只是为主观随意的附会和曲说拓展了更大的余地。在此理论引导下的创作,不论是王朝的雅乐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还是诗人韦孟、韦玄成等的诗作,以四言形式为主的高雅诗歌都竭力展示其“美刺”的用意。
毛诗属古文经学,西汉末年平帝时始立于学官。毛诗结合乐、舞论诗,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指出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对诗的感情以严格的限制,其目的在于标举诗的教化功能。《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于强调诗具有讽谏功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对《诗经》“六义”的分析尤其是对赋、兴、比的分析,几近于真正诗学意义上的剖析,但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说明诗具有“主文而谲谏”的功用与风格。《毛诗》对一些不合“主文而谲谏”的作品,以“变风变雅”释之:“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与三家诗相比,毛诗则侧重于采诗、编诗之意的发掘,似乎更重于述古,但目的还是为了阐明教化功能。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对《毛诗》尤其有发扬光大之功。郑玄以为,因礼而制作诗乐,为的是宣扬圣人贤德,以达到“风化天下”的目的,“歌诗所以通礼意,作乐所以同成礼文也”(《礼记·仲尼燕居》),“大合乐者,所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礼记·月令》)。所以古诗是“风化之源”、“教化之源”。诗歌风教又体现为美刺讽谕的手法,郑笺云:“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据孔颖达《正义》,就是借诗歌音乐的特性不直言君主的过失,而是委婉曲折地规讽,以维护君主的尊严。所以毛郑《诗》学仍然在“美刺”,与三家诗重视《诗》之社会功用方面殊途而同归。

注释:
①《朱子语类》卷八十:“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
②参见顾颉刚《论诗经所收录全为乐歌》,《古史辨》三下。
③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参见闻一多《诗言志辨》。
④参见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第8页。
⑤《左传·昭公十二年》:“宋华定聘鲁,鲁之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
⑥明志即修身。《国语·楚语》:“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
⑦《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⑧《孟子·离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⑨如文帝前元九年,诏命晁错往齐从秦博士伏生学《尚书》。
⑩《乐记·乐象》:“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方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记·师乙》:“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古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5-11-02
上海商学院科研项目“基于中本贯通改革的大学语文课程设计研究”(JX2015A0214)。
张侃(1962-),男,甘肃通渭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7.22
A
1008-4630(2015)06-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