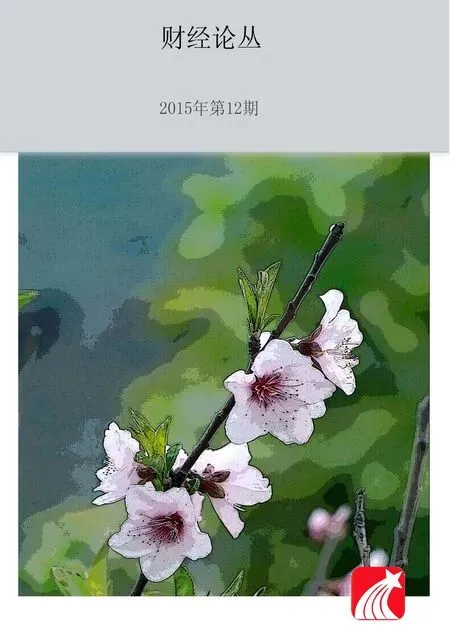新房产税的累进性与充分性测算——基于家户调查数据的微观模拟
刘金东,王生发
(1.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2.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引 言
房产税改革试点至今已经四年有余,但无论是试点方案的推出还是征收办法的落地都进度缓慢,这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在于对房产税的职能界定有所争议。冯海波和刘勇政(2011)[1]、安体富和葛静(2012)[2]等国内学者对房产税职能总体持“三元论”观点,一是调节财富分配(税收公平性),二是充实地方税主体税种(税收充分性),三是平抑房价(税收矫正性)。不过,目前针对第三种功能仍然存在争议,刘金东(2014)等人认为,国内房价的高涨源自于供需多方面因素,无论是参考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对照国外的历史经验,房产税都不可能是平抑房价的政策良方,如果将新房产税定位为整治高房价的政策工具反而有“以税治代替法治”之嫌[3]。从根本上来说,房产税最为基本、也最为大家所接受的职能仍然在于前两种。
遗憾的是,国内外针对房产税的实证研究大多着眼于房产税平抑房价的“非典型”职能,对于房产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公平性和充实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可行性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目前来看,仅有李文(2014)[4]、司言武等(2014)[5]分别利用全国层面宏观数据和浙江省某县宏观数据测算了未来房产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中的比例,对房产税的收入充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房产税未来的收入规模并不足以成为地方税主体税种。考虑到新房产税的征收方案将会以人均扣减面积为依据进行累进性设置,宏观数据的计算无法考虑到国内居民住房的面积和价值的分布特征,从而给测算带来一定的高估。相比较而言,利用大样本微观调研数据来分析税收累进性和征收比例历来是一种绝佳手段,这一方法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研究上已经获得了充分运用(如岳希明等,2012[6];岳希明和徐静,2012[7]等),但在房产税方面的运用仍然空白。基于此,本文的写作主要有如下三点创新:一是利用中国家庭健康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的家户调查数据对新房产税进行微观模拟,考虑了居民住房面积和价值的分布特征,能够更加合理地估算出房产税的累进性和征收比例;二是在税收累进程度最大化目标下为最优人均扣减面积的取值提供了精确的参考依据;三是以微观模拟为基础计算出的房产税征收比例能够更加合理地衡量未来新房产税的税收规模。
利用微观模拟的测算结果,本文发现:在不同税率下以MT指数衡量的房产税累进性程度均随人均扣减面积的递增呈现倒U形曲线变化,人均扣减面积为35平方米时,房产税累进性最佳;根据房产税不同税率、不同扣减面积的若干种组合估算出的房产税规模,在地方税收入中占比均不超过10%,根本无法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上述研究结果为下一步房产税方案的出台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余下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利用MT指数测算了不同税率下房产税的累进性,根据MT指数随人均扣减面积的变化趋势,确定最优的人均扣减面积;第三部分根据房产税不同税率、不同扣减面积的若干种组合估算房产税规模,衡量房产税的税收充分性;最后得出本文主要结论和启示。
二、房产税的累进性:最优人均扣减面积的确定
首先,我们要明确新房产税的征税思路:对比沪渝试点的不同方案,上海房产税中的单一税率、人均扣减的累进性设计更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如胡洪曙(2011)[8]、骆永民和伍文中(2012)[9]、胡海生等(2012)[10]、李文(2014)等学者的研究均以单一税率设计为计算依据,本文的研究也将延续这一思路。一方面,单一税率计税简便,能够与现行的营业用房房产税实现兼容对接;另一方面,Bai等(2014)利用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沪渝试点对两地房价的政策效应,发现重庆试点中针对不同类型住宅设置的差别税率容易造成购房人群的溢出效应,助涨低税率房屋的市场价格[11]。因此,这一部分将主要针对多种税率下不同人均扣减面积的计算来测算房产税的累进性,而不会考虑差别税率情形。
我们对新房产税进行微观模拟测算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健康营养调查(CHNS),该调查覆盖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共9个省份,最新调查年度为2011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样本的代表性更强。与其他微观数据相比,CHNS数据不仅包含针对所有18岁以上成人的个人调查问卷,还以家庭为单位做了详细的家户调查问卷。房产税的征收一方面要考虑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市场价值为征税依据,同时在人均扣减面积的计算上需要用到家庭房屋面积和家庭人口数量的数据。CHNS家户调查问卷中有针对住房使用面积、当前市场价值、家庭人口数的数据,这给我们的微观模拟计算提供了可行性。
2011年度的家户调查包含了5864个有效样本,考虑到房产税未来将主要针对城镇地区房产征税,所以剔除掉农村地区1396个样本,还剩下4468的样本容量。图1是我们按照人均居住面积计算的样本分布(折线,参照右坐标轴)和每平米单价分布(直方图,参照左坐标轴)。可以看到,人均居住面积的样本总体呈现倒U形分布,这与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宏观数据特征相符。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达到32.9平米,恰好在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附近。每平米单价的分布则较为复杂,在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平米之前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在达到50平米之后,则不再有单一的变化趋势,而是围绕5000元上下波动。究其原因,在于房价越高的地方,普通工薪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越小,但一旦超过一定的范围(如50平米),人均居住面积偏大就不能再简单归因于地区房价偏低,还可能是富人阶层为提高个人效用而购置大面积高档住宅的原因。虽然人均扣减面积越大,能够越多地将居住面积标准达不到全国平均值的工薪阶层排除在房产税征税范围之外,但随着人均扣减面积超过全国平均值,也开始有更多的富人阶层被连带排除出征税范围。所以,在起始阶段,人均扣减面积与房产税累进性呈正相关,但随着人均扣减面积超过一定标准,二者的变化关系将存在不确定性。

图1 按人均居住面积计算的样本分布和每平米单价分布
税收累进性测度大多采用的是Musgrave和Thin(1948)[12]提出的MT指数方法。这一方法通过对比征税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来衡量税收累进程度。运用到房产税,MT指数可表示为:

Gi为征收房产税之前房产价值在居民之间分配的基尼系数,Gt为征收房产税之后房产价值在居民之间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房产税是累进性的,则征收房产税之后,房产价值分配的不公平性将得到改善,基尼系数必然变小,而且房产税的累进性越高,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也就越大。因而,MT指数能够很好地反映房产税的累进程度。

图2 MT指数随人均扣减面积的变化
图2 是我们按照0.6%、0.8%、1%三档不同税率计算的MT指数。这三档税率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情景假设:0.6%是上海房产税试点执行的税率,相比最终落地的方案,属于较低的优惠税率;0.8%是学者们广泛认同的税率,如胡海生等(2012)、李文(2014)的研究均以此为基准税率;1%则是偏高的一档税率,考虑到我们在本文的计算中没有再另外设定扣除比例(扣除比例=1-房产余值/房产原值),按各地采用的20%或30%的扣除比例计算的话,此处1%的税率实际上超过了原有房产税从价计征的1.2%的法定税率,已属偏高水平。
从图2可以看到,无论是按照哪一档税率来计算,MT指数均随人均扣减面积呈倒U形曲线变化,这与岳希明等(2012)计算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之于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关系非常类似。值得一提的是,三档不同税率下,MT指数最大值均对应于35平米的人均扣减面积。这意味着,在单一税率下,如果将人均扣减面积设定为35平米,房产税调节财富分配的税收公平性职能将发挥到最大效应。这一人均扣减面积略高于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保证税收利益的同时也照顾了工薪家庭住房的基本需求。遗憾的是,无论是沪渝试点还是媒体报道中北京等地上报的试点方案都与这一最优扣减面积相去较远,上海人均60平米的扣减面积显得过于宽松,而北京拟定的20平米扣减面积则显得太过严厉,均没有兼顾国家税收利益和工薪家庭住房需求。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2011年CHNS数据是该项追踪调查的最新数据,也是可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同类调研中能够囊括以上几项指标的最新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统计数据目前只能更新到2012年,2012年该项指标为32.9平方米,而2011年为32.7平方米,两者相差无几,这意味着我们基于2011年CHNS数据计算出的最优人均扣减面积对当前年度仍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房产税的充分性:能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吗?
全口径房产税包括住宅房产税和营业房产税两部分,其中针对营业用房的营业房产税一直征收,目前要开征的是针对居住用房的住宅房产税。因此,要估算全口径房产税的收入规模,关键是估算住宅房产税,我们只需要利用CHNS家户调查数据计算出房产税占房屋总价值的平均征收比例(平均征收比例=住宅房产税收入/房屋总价值),再以全国城镇存量住宅房产总价值乘以该征收比例就得到住宅房产税收入。根据家户调查样本数据,我们按照较高的0.8%和1%两档税率来计算征收比例,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2011年全口径房产税规模估算
可以看到,由于人均扣减面积的存在,样本平均征收比例必然性地低于法定税率,人均扣减面积越大,则样本平均征收比例越低。按照李文(2014)设定的标准,在地方税中比例达到30%以上的可以称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在地方税中比例达到20%以上但未达到30%的可以称为地方税重要税种。而表1结果显示,以我们确定的最优人均扣减面积35平米计算的话,全口径房产税规模在1%高税率下也仅达到3338.47亿元,占地方税比重为7.70%。若按照学者们广泛认同的0.8%的税率来计算,则即使将人均扣减面积降低至10平米,全口径房产税也仅仅占到地方税的15.49%,相比营业税和增值税而言,非常有限,根本无力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连地方税重要税种的20%比例都没有达到,这一结论与李文(2014)基本一致。李文(2014)按照0.8%的税率利用全国宏观数据估算的房产税占地方税比例为10.56%,与本文利用微观模拟测算的结果略有偏差,高于人均扣减面积25平米以上的情形,低于人均扣减面积20平米以下的情形,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宏观数据无法考虑住房面积的分布特征造成了测算误差所致。
为使本文的结论更具稳健性,我们利用《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户数统计数据来估算房产税规模作为对比。考虑到《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户数统计是分城市家庭户和镇家庭户,我们分别按照城市家庭户的户数统计数据和镇家庭户的户数统计数据估算平均征税比例,由此来计算房产税规模与我们表1中的微观模拟测算数据作对照。《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仅仅提供了按照每10平米分组的户数统计数据,以城市家庭户为例,当人均扣减面积为35平米,我们的计算原理如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0-39平米的户数然后将全部征税面积加总除以全国城市家庭户住房建筑总面积,该比例即为平均征收比例。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组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70及以上”,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我国别墅和高档公寓每套平均面积为188.91平方米,按照家庭最低两口人来算,则别墅和高档公寓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95平方米,我们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70平米及以上的全部看作是别墅和高档公寓,以平均95平米来计算,若其户数为S5,则其征税面积为S5× (95-35)。上述处理方法有两处高估:一是70平米以下各组的处理假设每组内总户数均匀分布,但实际上户数总体呈线性递减分布,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大,户数越少,如图3所示;二是对70平米及以上的情形全部按照别墅和高档公寓来算,这也对数值产生了高估效应。按照人均扣减面积35平米和0.8%税率按照城市家庭户和镇家庭户数据估算的全口径房产税占地方税比例分别为8.21%和9.05%,略高于我们微观模拟的计算结果(6.74%),低于李文(2014)的结果(10.56%),但依然支持我们关于房产税充分性的结论。
上文中针对房产税规模的测算都是针对2011年单一年度进行,属于静态分析,没有考虑到各个因素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住宅房产税的规模是利用居民房屋总价值乘以平均征收比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住房建筑面积分布变化较小,可以假定平均征收比例不变,但全国居民房屋总价值却会随着居民房屋总面积和单价增长而不断变化,税收连年超GDP增长也促使地方税收入大幅攀升,因此,要衡量房产税在地方税中的占比还需要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

图3 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的户数统计
我们通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到1996-2012年的地方财政税收收入、营业房产税收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年末城镇人口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时间序列。通过(年末城镇人口数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平均征收比例+营业房产税收入)计算出全口径房产税收入,通过(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住宅房产税收入)计算出地方税收入。全口径房产税收入和地方税收入做对数化处理后基本呈直线趋势。我们将它们的对数形式对时间(年)做回归,发现时间(年)系数和常数项均1%水平内显著,且R2分别达到了0.9979和0.9906,表明拟合效果非常好,我们以此回归方程来估算未来年度的地方税收入规模和全口径房产税收入规模,根据图4所示,在2014年之后,全口径房产税收入在地方税中占比逐年平稳下降,从7.26%逐渐接近6%。我们以1%和0.8%两种基准税率和10-35多种人均扣减面积的其他不同组合计算的结果与此类同。由此可见,根据现有的征收方案,即使从长期来看,房产税仍然不具备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可能性。

图4 未来房产税收入在地方税中占比的长期变化
当然,以上分析均未考虑到未来税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变化。就“营改增”来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虽然地方税最大的主体税种消失,但现有的业已稳定化的财政格局并不会发生突变,中央政府会通过重新修订分税制方案来保证原有的地方政府财政利益不受影响,如此才能推动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起初提出以新房产税来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设想即是出于这一目的。换言之,未来“营改增”等税制改革均不会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断崖式跌落,因此,我们上文中估算的新房产税在地方税中占比具有合理性。如果以最高1%的税率和最低10平方米的人均扣减面积来计算,新房产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也仅能达到9.9%,无论未来地方税规模如何,10%占比都不可能达到的税种短期内显然无法承担起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角色。
四、本文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CHNS家户调查中的家庭房屋面积和房屋市场价值数据对我国新房产税分不同税率、不同人均扣减面积的征收方案进行了微观模拟测算。首先,MT指数显示,新房产税的累进程度随人均扣减面积呈倒U形趋势变化,当人均扣减面积为35平方米时,新房产税的累进性程度达到最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微观数据估算了房产税的收入规模,发现以现有的税率设计,全口径房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入比例不足10%,无论是短期内还是长期内都无法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户数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一方面,本文的研究肯定了房产税的税收公平性职能,在税收公平目标下为最优人均扣减面积的取值提供了精确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也否定了房产税的税收充分性职能,即国内学者对新房产税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设想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司言武等(2014)认为,虽然新房产税无法独立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但可以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四个房地产相关税种纳入进来构建广义房地产税税收体系,以此来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就具有了可行性。不过从本文全口径房产税收入规模的测算结果来看,这四个税种在地方税收入中占比仅在10%左右,与全口径房产税合计也只能占到地方税收入的约20%,只能达到重要税种的层次,离主体税种的标准尚有较大差距。当然,换个角度来讲,在中国实现向单主体税制的过渡之前,新房产税在地方税中规模也并不宜过高: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效应上,货劳税要好于房产税,前者能够促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后者则有可能促使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转向,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房价进而提高房产税收入,较高的房产税收入进一步反哺高投资率。这种情况下,新房产税就变得与分期付款的土地出让金毫无差异,容易触发地方政府的“房地产依赖症”。因此,未来改革中,不应当再强调新房产税的税收充分性职能,而应当将新房产税职能简单限定在税收公平性范畴之内,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税收实践和税收理论中最被普遍接受的一点。
[1]冯海波,刘勇政.多重目标制约下的中国房产税改革[J].财贸经济,2011,(6):24-31.
[2]安体富,葛静.关于房产税改革的若干问题探讨——基于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2,(45):12-21.
[3]刘金东.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因素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4.151-152.
[4]李文.我国房地产税收入数量测算及其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可行性分析[J].财贸经济,2014,(9):14-25.
[5]司言武,朱伟松,沈玉平.中国房产税税率设计研究——基于浙江省Y县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14,(4):9-17.
[6]岳希明,徐静,刘谦,丁胜,董莉娟.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2,(9):113-124.
[7]岳希明,徐静.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 [J].经济学动态,2012,(6):16-25.
[8]胡洪曙.开征财产税后的地方财力缺口测算研究 [J].财贸经济,2011,(10):17-24.
[9]骆永民,伍文中.房产税改革与房价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J].金融研究,2012,(5):1-14.
[10]胡海生,刘红梅,王克强.中国房产税改革方案比较研究——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分析 [J].财政研究,2012,(12):30-34.
[11] Bai C.,Li Q.and Ouyang M.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A tale of two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14,180(1),pp.1-15.
[12] Musgrave R.A.and Thin T.Income tax progression,1929-1948[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8,56(6),pp.498-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