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卢姆的一天
吕宗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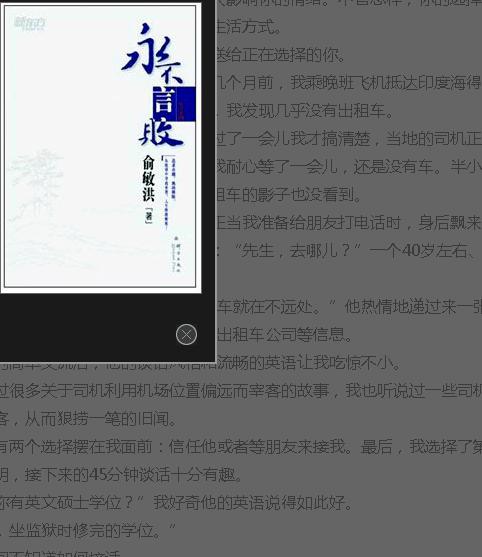
这舞台就是一个房间,沉浸在黑暗里,只被单排灯光斜照着,灰尘扑簌簌落满家具:一排半圆弧形状的旧木组合柜,阶梯状向左上方延展,塞满书籍、钟表、灯盏、茶壶、地球仪等破烂杂物,下方摆着一架木梯;中央有一张大铁床,外套搭在栏杆上,在这个狭小、杂乱的空间里,地板上整整齐齐放了一顶男帽和一双皮鞋。
仿佛凝固在永无晨曦降临的静谧中,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和妻子莫莉·布卢姆躺在床上,突然从柜门里闯出几个人,地上的帽子凭空升起,梦魇的召唤连接着新一天的序幕,我们的男主人公从床上坐起,开始想念早餐炙羊腰子独特的尿骚味儿。
另一边的木梯下,或者说那也是一座出租的圆形炮塔楼,青年诗人斯蒂芬和他的朋友、医学生壮鹿马利根也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这房间、这舞台是一个交错的时空,将文学的平行叙事在一个现实平面内呈现出来。此刻是2015年4月1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剧院,我们观看苏格兰特隆剧院将文学巨著《尤利西斯》搬演至舞台;此刻也是1904年6月16日,原著者詹姆斯·乔伊斯第一次与妻子诺拉·巴纳克尔约会的平凡一天;或者此刻,永恒的6月16日,被后世人景仰纪念的“布卢姆日”;此刻,我们还可以畅想,或许时光回溯到公元前8世纪末,在盲眼吟游诗人的短歌中,一位名叫奥德修斯的英雄正在海上漂泊,不知归途何方。
将《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改编成舞台剧着实是一场冒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见底气。我们通常习惯在舞台上观看完整的故事,跌宕起伏,爆笑或流下眼泪,有即时性的反馈和共鸣。而《尤利西斯》,尽管鼎鼎大名,却只有少数读者去尝试阅读,专家学者更要经年去钻研它的奥秘。在那砖块儿一样厚重的三部十八个章节中,乔伊斯用不同的写作技巧和风格构建了无数意识流的碎片,英语语言还夹杂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爱尔兰语。即使搬至舞台,这仍然是一部需要做足功课的作品:你要知晓其与《奥德赛》之间人物命运的隐秘联系,你要分辨得出人物似乎前言不搭后语的对白中暗藏的莎士比亚、王尔德、叶芝、布莱克和柏拉图,你得明白为什么演员们说着说着就唱起来,没有翻译出的台词里是什么样的歌剧或神圣诗篇。否则,你只是困惑地看着台上的人们忙忙碌碌,大脑烧焦之后仍然讲不出这个故事是何所以然。
即便上述条件全部成立,作为普通中国观众的我们,还是无法在这一席舞台间即时抵达《尤利西斯》的核心。连乔伊斯自己都戏谑地说,这部作品要让评论家们忙上几个世纪。作品本身的命运,甚至要比它书写的故事戏剧化得多,连载后因有伤风化而被禁,经法庭判决后又解禁。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加速了这部充斥不解之词的作品成为经典。曾有评论家说:“在有趣的小说中,它是最难懂的;在难懂的小说中,它是最有趣的。”倘若戏剧改编能够达到一种虽令人费解却感到有趣的境地,也算是极大的成就。最引起中国观众发笑的一刻是这样:主人公布卢姆爬上床头铁栏杆,像站在腾空的战车上一般身披金光,人们高呼着“以利亚”,字幕显示这被天使簇拥升向金光圈的一刻,是以“四十五度的斜角”。可见,中国观众的笑点并不在戏剧本身,这之间,无论文学还是文化上的隔阂都太大了。到最后我们能记得的只言片语,唯有敏感关键词“犹太人”;捕捉的浮光掠影,只是妓女灯红酒绿中撩起的性感丝袜,只是布卢姆的帽子遮掩着的不雅举动,这不明所以的荒唐一日终结于家中絮絮叨叨的女主人公,在那散漫灰尘的阴暗房间里,可怜的夫妻同床异梦。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碎片情节中,跳脱出的是演员们精彩绝伦的演绎、道具出其不意的使用和整体场面异彩纷呈的调度。这让《尤利西斯》成为特隆剧院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专属戏剧。仅仅八个演员,凭借一流的演技和表现力,完成了原著纷繁复杂的数十个人物的分饰。原本看似一成不变的道具摆设,随时可以转换用途,单调的舞台设置空间有了妙用。演员们在柜门后消失,再出场时已经更换了身份。他们操着不同的音色,连步伐姿态都随着设定而明显转变,时而舞蹈、时而歌唱。最纯粹的演绎成为了打通晦涩文学的关键钥匙,灵活自如地还原了部分原著语言特有的风貌,低俗词汇与高深言论在台词上有了一种相对容易被大众接受的中和。
观看这样的戏剧,那些斤斤计较故事究竟讲了什么的观众反倒像是最不知享乐的傻瓜。不如就承认自己无知,放弃刨根问底,接受乔伊斯的游戏,至少能在演绎中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乐趣。总有这么一部分艺术是要在它的圈子中宣称特立独行的,像电影眼睛派彻底放弃了剧本和演员单纯呈现电影语言那样,话剧版《尤利西斯》脱掉故事本身令人不解的枷锁其实也是一场视觉演绎的盛宴。有些艺术,与其去分析,不如去感受。
相信那些摆脱了固有的观戏心理的观众,一定还是可以从这样的舞台呈现中获得一些感动。当布卢姆与斯蒂芬并肩坐着,长谈关于理想与人生,我们仿佛能看到,那正是现代版的忒勒马科斯终于与父亲奥德修斯团聚。当莫莉从睡梦中醒来,回想过往,怀着一颗少女初心诉说当年丈夫向自己求婚那一刻的亲吻——那是舞台最温柔美妙的一刻,一天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的黎明——古希腊神话中历经艰险磨难的一家人最终还是团聚了。
《尤利西斯》究竟讲了些什么?“粗俗、激情、浪漫、孤独、迷茫、绝望”这不过是宣传册上作为噱头的关键词。在这样集中表现的一天里,在这三小时左右的方寸舞台间,要想解决困扰了评论家们一个世纪也无法统一定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布卢姆的一天结束了,你看完话剧《尤利西斯》,困惑不解,走出剧院,天已经黑了,你的这一天也要随之过去。如果有一天,你能幸运地成为那少部分能认真翻开厚重书页的人,会在字里行间发现一段斯蒂芬和马利根讨论莎士比亚时说的话——你甚至都不记得它有没有在台词里出现过了:
“那些有可能在他那内部世界中出现的现象,外部世界中已经实际存在了。梅特林克曾说:如果苏格拉底今天离家,他会发现哲人就坐在他门前的台阶上。如果犹大今晚出去,他的脚步也会走向犹大。每一个生命,都是许多日子组成的,一日又一日。我们通过自身往前走,一路遇到强盗、鬼魂、巨人、老人、年轻人、寡妇、慈爱兄弟,但永远都会遇到的是我们自己。”
编剧的话
我意识到,我作为编剧面对改编《尤利西斯》时感受到的这种恐惧,也折射出很多读者面对这部小说时的恐惧。《尤利西斯》的神秘毋庸赘言,谁也不能说它易读。乔伊斯也开过玩笑说要让评论家们忙上几个世纪。
作为读者我印象最深的部分也正是作为编剧我最为恐惧的一切。乔伊斯不单单在书中创造了各色充满矛盾的人物,同时这部小说也涵盖了整座城市的生理和心理背景。我们可以说《尤利西斯》中没有小人物,因为即使是转瞬即逝的人物,乔伊斯也为他们想象出了一整套生活。这种宏大描绘是小说的特权:次要世界也能得到探索,虽然它对于整体叙事没有关键作用,但由于人物生发于其中,它能使叙事更为丰满。
然而戏剧却不能舒舒服服地跑题,明目张胆地远离中心思想。编剧与戏剧观众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也有一场沉默的决斗。观众只要有好奇心驱动,就会跟着编剧走向任何一方。但如果观众走得比编剧快,那么魔法就会被刺穿。紧绷着一部作品那条绳子如果失去张力,所有的戏剧都会丧失生命。
《尤利西斯》编剧 德莫特·博尔杰 赵晗/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