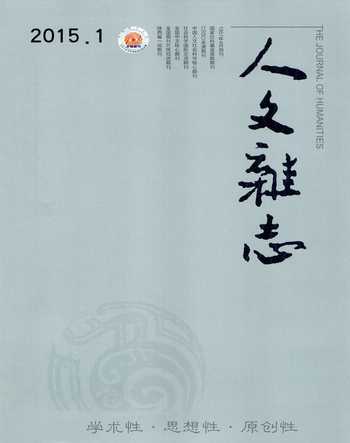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邹振环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相关材料,就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秦始皇的造神以及水神与海神信仰三个方面,指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意识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他不断到海边巡游,甚至不惜进行海洋航行以战胜“海神”之恶神,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着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中国并非如日人所述系“南船北马”的“两个中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从内陆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说,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关键词秦始皇海洋意识徐福海陆文明一体水神海神
〔中图分类号〕K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1-0081-09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多次巡游各地,其中最多的地方是海边,从北面的芝罘、碣石,到南面的会稽,并多次与议于海上,且每遇不顺心之事,他也是通过在沿海地区的刻碑来舒解自己内心的郁闷。秦始皇生前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中,设计了人间的六合世界,其中就有水银建构的大江大海。可以说,秦始皇是历代帝王中最重视海洋的皇帝之一。一个原本属于内陆地区成长起来的帝王,何以会对海洋世界有如此之大的兴趣呢?
海洋意识是指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关于海洋知识的积累,以及如何利用海洋的认识。海洋意识研究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海洋地理的海岛海域、海洋自然资源、海洋动物、海洋经济、海上交通与海洋信仰等。关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王子今已撰有《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载2012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就秦始皇“天下”与“海内”的理念、“议功德于海上”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梦与海神战”的心理背景,作了初步的讨论。卜祥伟和熊铁基的《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载《兰州学刊》2013年第9期),也以秦始皇为例,指出秦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海神信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海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使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呈现出了人格化、世俗化、社会化的新特点。随着海神信仰的发展,秦汉社会的海洋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海洋控制为主体的海洋政治观得以践行,而海洋文化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海洋意识的范畴。
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充分体现为他对徐福东渡计划的全力支持。学界关于徐福的研究虽已汗牛充
栋,关于徐福东渡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连云港徐福研究会编《徐福研究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山东徐福研究会、龙口徐福研究会编《徐福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朱亚非主编《徐福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但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笔者认为是值得专门加以讨论的。本文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相关材料,就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秦始皇的造神以及水神与海神信仰三个方面,尝试讨论徐福东渡与秦始皇海洋意识的关系,指出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一、 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华文明是“大陆文明”。其实,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我们不能因为明朝以来若干时段的禁海而否定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早在商朝末年,据说殷人就有过大规模的渡海跨洋的美洲航行,如果殷人是美洲文化的开创者,有些玄乎的话,那么已有充分和确凿的材料证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比较发达的近海航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夫差“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徐广《集解》称是“海中败吴”。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3页。这条材料足以说明齐国拥有比吴国更强大的海上力量。齐国是位于东海之隅的滨海之国,其海上交通比较发达,史载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且“盖尝有至者”。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9页。关于“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究竟在何处,学界看法不一,或说是蓬莱之外的长岛,或说是日本列岛,或说是朝鲜等,或说是美洲的墨西哥海岸。(参见连云山:《谁先到达美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4~95页)最极端的说法是指“北极漂出的巨大冰山”。(参见王颋:《圣王肇业——韩日中交涉考》,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0~23页。越国吞并吴国后,在山东半岛的琅邪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勾践“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袁康、吴平:《越绝书》卷8,“外记·记地传”,岳麓书社,1996年,第122页。可见,当时越国的航海业也非同小可。可知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对海洋有了自己的了解,且已有若干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并初步开始利用海洋的资源和力量。
正是在大量有关海洋知识的基础上,《管子·禁藏》阐述统治者可以海洋之“利”引导百姓致富:“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戴望:《管子校正》卷17,“诸子集成”本,第5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91页。《荀子·王制》篇更是提出如何来利用中华大地周边的“北海”、“南海”、“东海”与“西海”:“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王先谦:《荀子集解》卷5“王制篇”,“诸子集成”本,第3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02~103页。古人多以为中国的大地周边环海,所谓四海中的东南西北,一般“北海”指北方的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和黑海;或以为是鞑靼海、鄂霍次克海至北冰洋;“南海”指今天的东海与南海;“东海”指今天的东海与渤海;“西海”比较复杂,或指西部沙漠的瀚海,或指青海湖、博斯腾湖、咸海、里海乃至于红海、阿拉伯海和地中海。(参见舟欲行:《海的文明》,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53~54页)四海说是与华夷说和天朝中心主义的理论紧密相关的。这里的四海之地,包含着中原周边近海和海边地区的出产,可见学者已经注意到海岸、海洋对于中原文明的特殊意义。
战国齐威王和宣王时代有著名的思想家邹衍,著有《邹子书》,其中有“五德终始”和“主运”篇,讨论“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和“五行相次转用事”等理论,其“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由齐人上奏秦始皇,“始皇采用之”。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及其《集解》、《索隐》,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8~1369页。秦始皇对阴阳五行学说非常推崇,《史记·封禅书》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六为名。”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6页。《秦始皇本纪》中亦有类似记述:“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中华书局,1975年,第237~238页。秦始皇按照水、火、木、金、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终始循环的理论进行推求,认为周朝为火德的属性,秦朝既然取代了周朝,就一定是取周朝火德而代之,因此应该是“水德”。作为“水德”的起始之年,应该顺承天意,更改一年的起点,群臣朝见拜贺都安排在十月初一那一天。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崇尚黑色。因为水德属“阴”,而《易》卦中表示阴的符号阴爻叫做“元”,把数目以“十”为标准,改成以“六”为计量单位,符节和官员的法冠,都规定为六寸,车的两轮间的距离宽为六尺,六尺为计算单位,一辆车驾六匹马。甚至把黄河也改名为“德水”,以此来表示“水德”的开始。实行的政策法令非常刚毅严厉,一切事情都依刑法等法律为准,刻薄而不讲仁爱、恩惠、和善、情义,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五德中水主阴的命数。于是采取的法令极为严酷,关在牢狱中的罪犯久久不能得到宽赦。
秦始皇不仅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也接受了邹衍在荀子“四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大九州”说。这是《禹贡》九州意识向海洋世界的直接放大,由“九州”推论出八十一州和大瀛海,提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卷74,中华书局,1977年,第2344页。邹衍关于“大九州”的地理学思考,很可能一方面是来自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的观察,因为从《穆天子传》《山海经》的传说中可知,战国时对西北地理知识已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开拓;另一方面是依据了齐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水平。位于东海之隅的齐国已有比较发达的海上交通,根据考古资料证实,辽宁旅顺郭家村下层文化遗存中,有鼎、规等大汶口文化一致的器物,说明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间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了海上交通。参见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邹衍的这一推论是中国古代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关于海洋和海陆关系的猜想,是以中国内陆九州划分为经验,更是以春秋战国时代大量齐人的海外航行,春秋战国时代对海外世界的广大无穷的初步认识,以及地理视野的拓展为基础的。杨国桢将之称为“海洋型地球观”。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虽然这一大胆的想象,是建立在天圆地平的基础上,但它首次打破了狭隘的世界中心论,把世界假想成一个多元的广大区域,是对传统华夷说和天朝中心论的激烈批判。
邹衍的“大九州”和“大瀛海”的理论,是秦始皇理解海洋和海外世界、建立自己海洋意识的重要依据,正是在这些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的支配下,出生和活动于内陆的秦始皇才会把眼光投射到沿海地区,才能同意徐福率领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携带着各种工具、武器和种子,两度下海,进行所谓获取仙药的航海活动。如果没有关于海洋的基本知识,徐福及其随行人员根本不可能制订这样宏大的计划,秦始皇也不可能同意这样庞大计划的实施。
二、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
秦王朝建立后,沿海具有海洋型特征的齐地、东夷、百越先后纳入其版图,成为中央王朝的海疆。秦始皇本人则有多次大规模的沿海和海上活动的实践,他曾多次巡视渤海和东海地区,他的巡视活动,多被古代学者解释为是单纯为了寻求海上神山和长生不老之仙药,其实这种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透露出很多信息,即秦始皇其实根本不相信自己能长生不死,所谓“二世三世”,所谓“后世循业,顺承勿革”,以及营造骊山墓地,都说明他不相信自己会长生不死。海神需要童男女陪侍尚能理解,但需要五谷种子和百工随行,就很难说得通。如果秦始皇仅仅为了寻找神仙谋求仙药,似乎也不能同意徐福携带数千童男女下海,而且还携带五谷种种和百工随行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开始大规模的巡海活动,一方面是处在中原核心地带的新征服的燕、齐、越三个濒海之国,在秦统一后尚未完全平定,不少地方有反叛活动,秦始皇的巡游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同时,秦始皇有很强的海洋意识,有开发沿海地区、发展海岸港口的想法,如他从内地向濒海地区大量移民三万户:“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②⑤⑥⑦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44、247、258、263、263页。用免征赋税十二年的厚利,鼓励内地移民定居海疆,并扩建琅邪港口,开辟海运。
尽管关于徐福(或作“徐市”)的出生地至今学界争论不休,但他是生活在齐地的方士,则无争议。齐人徐福第一次上书是在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仙人居之”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在战国时代颇为流行,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或说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且“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则引去,终莫能至云。”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9~1370页。海中蓬莱最早见之《山海经·海内北经》,是与地中陆上昆仑相对的神山仙岛,两者都被古人视为远古的两大仙乡。高莉芬在所著第三章“蓬莱神话的海洋思维及其宇宙观”中认为相对于海上文明发达的文明古国,古代中国与海洋有关的神话并不多见,但在《山海经》的海中神灵、海上异域与海上乐园的书写,也投射着先民对于海洋的自然观察与神话想象。而《山海经》中的海中“蓬莱山”,发展到秦汉时期,以海中的“三山”或“五山”的地貌形式,寓托初民对不死仙境的企求与相望。日益增衍的蓬莱神山神话,其中对海底大壑、海中巨灵、海上他界的书写与想象,积淀着先民对于大海的宗教情怀、哲学思辨与宇宙思维,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参见氏著:《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第57~123页。蓬莱等三神山是海中圣山,被认为是长生不死的空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古人关于海洋世界的想象。徐福应该非常了解秦始皇对于海中蓬莱为代表的海洋世界的向往,也了解秦始皇所具备的海洋意识和秦朝执行的海洋政策,否则很难想象他会提出这样一个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的计划。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决定了他会同意由徐福挑选童男童女几千人,造出能够运载数千童男女的大船到海中去寻找仙人和仙药,并将这一“费以巨万计”计划很快付诸实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秦王政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发布了焚书令之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等私下攻击秦始皇专权,秦始皇“日闻”这些方士私下诽谤他并最后出逃,感到非常愤怒:“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他派遣御史逐一考问这些攻击他的方士和儒生,最后下令对方士和儒生实行了极为残暴的活埋措施,在咸阳坑死了460多人。⑤这一材料可见他对“徐市等”耗费了巨额资金,但始终没有带来海外的消息,非常恼火,特别是侯生、卢生等方士还“徒奸利相告”。但奇怪的是当徐福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秦始皇并未惩罚他,而且对徐福重新提出再次率领童男女以及“善射与俱”出海的计划,非常重视:“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⑥甚至下令组织武装力量携带着新式武器和“捕巨鱼具”,帮助徐福破除阻碍他再次入海寻土的障碍:“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⑦这里的记载表明,秦始皇还亲自携带“连弩”乘船航行,以寻找并除去所谓“以大鱼蛟龙”为替身的“恶神”,或以为文中“以大鱼蛟龙为候”之“候”作“封侯”解,认为海神作为一种神灵受到秦始皇的封赐,并以侯的待遇加以拜祭,这足以说明海神在秦始皇心目中的地位。(参见卜祥伟和熊铁基:《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兰州学刊》2013年第9期)其实这里“候”应作“替身”解。以迎接“善神”,最终在“之罘”发现了“巨鱼”,并将之“射杀”。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了西汉武帝时代楚国谋士伍被给淮南王刘安谈论天下形势,规劝刘安不要搞谋反,伍被对他谈到了徐福第二次东渡出海的经过:“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皇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86页。伍被距徐福东渡仅60多年,徐福与伍被之父是同时代人,所谓“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应是与徐福同去者回国带来的消息,基本属于信而有征的说法。
奇怪的是秦始皇坑死了几百个方士,而同样是方士的徐福,耗费巨资并未完成其使命,秦始皇却全然相信了他的陈述,不仅没有惩罚所犯“欺天大罪”,而且竟然再次同意他重新组织人员,除了三千童男女之外,还允许他携带“五谷种种”,和各种具有专门技艺的“百工”同行。联系《秦始皇本纪》中的徐福“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可见徐福所说的“为大鲛鱼所苦”,很可能是第一次迁徙过程中,徐福一行在登陆前后都受到了当地土著在海上和陆上的强烈抵抗而遭到失败,因此,第二次他企图携带着“连弩”的“善射”者同往。从前后文看,秦始皇应该是同意了徐福的请求,第二次徐福东渡是有武装力量同行的。如果秦始皇仅仅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很难想象他会两次同意徐福率领如此之多的童男女,还有大批掌握着技艺的“百工”随行,因为这是非常明显的辟土安居的行为,只有一种解释,即具海洋意识的秦始皇,是在邹衍这种“大瀛海”知识的支配下,秦王朝已经确立了以山东为基地向海外世界开拓的海洋政策。如果不了解秦始皇海洋意识支配下所确立的海洋政策,徐福及其随行人员根本不敢向秦始皇提出这一率领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携带着各种工具、武器和种子,两度下海宏大的出海计划,秦始皇也不可能两次同意如此庞大计划的具体实施。
后人因为秦始皇的残暴,故意贬低秦始皇的智力和判断力,将徐福两次如此大规模的航海,解释成仅仅是因为寻找仙人和获取仙药。事实上,这里所谓的“仙药”,不仅仅是一种长生不老之药,应该也是多种海洋资源的象征物。所谓“仙药”究竟何指?东方朔《十洲记》中称:“祖洲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长三尺许。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此说未免夸大,但海洋中的药物,历代医书多有记载。对海洋生物的药用,被航海者发现,后来被记载下来,服用有效则又被夸大为“仙药”(参见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74页)。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中记录了120种多药物,涉及动物药、植物药、矿石药、水类、土类等多个领域。其中很多属于海洋中的鱼类,如“其状如牛”的“鯥”,“食之无肿疾”;“其状鱼身而蛇尾”的“虎蛟”,“食者不肿”,可以治疗痔病;“其状如鱼而人面”的“赤鱬”,“食之不疥”;“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的“文鳐鱼”和“鱼身而犬首”的“鮨鱼”,都有治疗“狂”病的作用;“其状如鱓”的“滑鱼”、“其状如鲤”的“(鱼巢)鱼”和“其状如鲤”的“鱃鱼”,食之都可以治疗“疣”;“其状如倏而赤鳞”的“鮆鱼”,食之可以治疗骚臭;“其状如(鱼帝)鱼”的“人鱼”,“食之无痴”;“其状如鮒鱼”的“滔(鱼字旁)鱼”,食之可以治疗呕吐;“其状如倏”的“鰔鱼”“食之无疫疾”;有些鱼类有某种治疗精神疾病和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如“三尾、六足、四首”的“倏鱼”,食之可以治疗忧郁;“鱼身蛇首”的“冉遗”,“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其状如鹊而十翼”的“鰼鰼”,食之“可以御火”;“其状如鮒”的“飞鱼”,“食之不畏雷”;“(鱼帝)鱼”,“食者无蛊疾,可以御兵”,等等。(参见薛愚主编:《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第35~41页。)虽然其中没有提及这些鱼类中是否具有长生不死的神奇功能,但这些治疗疾病的功能,一定会给秦始皇和秦宫中的博士官和方士留下深刻的印象,秦始皇企图通过这些方士如徐福出海的巨大工程,来寻找各种所谓“仙药”的海洋资源。秦始皇同意徐福率领如此之多的童男女和百工,甚至武装力量同行,应该有希望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海上移民活动,求得海外的土地,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
三、秦始皇的造神与水神、海神信仰
所有的生命都从海洋中孕育而生,海洋浩渺辽阔、神秘莫测,代表着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远离中央陆地的海洋和海滨之美景,常常成为人们寻求解脱现实世界中生命不能自主的心灵桎梏和寄托生命的归宿之地,因此往往会与死亡联系而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与神仙和神话联系在一起,海洋意识也包括缘于海洋而创造出的神灵和生成的海洋信仰。
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朝的同时,就极力推进造神运动。秦国统一天下伊始,秦始皇要求臣下讨论帝号时,就强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是赖祖宗的神灵保佑,六国诸王都依他们的罪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涉及是否要采取分封制度时,廷尉李斯则进一步将统一全国的功劳归功于秦始皇的“神灵”:“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听后非常赞同,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②③⑥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239、246~247、254、252页。并确定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以碑文的形式流芳百世:“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休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②秦王政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他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来祝寿。仆射周青臣再次赞扬秦始皇的“神灵明圣”,进颂道:“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大悦。③
水创造了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奇力量。在遥远的时代,中国人因为水而形成了所谓的水神信仰,水神信仰在中国古代又与水利工程的利用和治理有关。战国时代水神流行,秦代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水神庙来供奉当地的水神,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汉水),祠汉中;湫渊,祠朝阝丹;江水,祠蜀。”《史记索隐》称其中“临晋有河水祠”,其中供奉水仙冯夷。⑤⑦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71~1373、1374、1367页。这些是列入官方祭祀名单的水神,另外还有因为临近首都咸阳,于是所谓“霸、产、长水、澧、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⑤也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秦始皇统一天下,三十二年记述“坏城郭,决通堤防”,并将这些事迹镌刻在碣石门碑石上:“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⑥一方面是通过决通河川、兴修水利来实现政治统一;一方面也是在社会上倡导一种“尊卑有序”的礼制秩序。这种社会尊卑的秩序也投射在神灵世界中:“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⑦所谓“八神”,祀所大致有一半在滨海地区,行礼祀“八神”,也体现出来自西北内陆的帝王对东方沿海神学系统的承认和尊重。
在秦始皇看来,自然神灵固然神圣,但神圣的信仰应该还是应在政治统治的规范之下,他自认为世俗的力量可以胜过水神的力量,甚至认为自己作为神灵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一般的水神,表现出对水神和海洋敬而不惧的无畏态度。政权的力量高于水神的力量的又一例证见之《史记·滑稽列传》。该篇有一段记述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破水神的故事,称邺地祭祀水神河伯,竟然将民间少女投入河中溺死作为水神之妾。结果西门豹将巫婆、三老等投入河里,破除了这一陋俗。参见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1页。而如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在巡游海疆返回京城的途中,向西南渡过淮河,前往衡山、南郡。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湘山祠。战国楚国时代,湘君在屈原的《九歌》中已经作为江神被祭祀,即湘君具有“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的神力。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5~86页。秦始皇在横渡湘江时遇上了大风,几乎不能渡河:“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②③④⑦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61、253、257、263、263页。秦始皇对阻碍其渡河的水神湘君很不以为然,当他从博士官这里知道“湘君”仅仅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时,深感愤怒,在他看来一般的水神是应该服从其命令,而不是他渡河的阻碍,于是他不惜派遣了三千个服刑役的刑徒,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将水神湘君所居的湘山变为光秃秃的赭红色的土山。
秦始皇依靠这些方士造神,同时也为这些方士所愚弄,如韩终、侯公、石生与徐福一样,号称能够获得“仙人不死之药”。他派遣燕人卢生入海寻找仙药,结果自然无法获得,于是卢生就“以鬼神事”哄骗秦始皇,同时“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此“胡”实为“胡亥”,但秦始皇误解,认为应是来自北方的“胡人”,于是“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②卢生还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濡,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希望秦始皇学习做一个入水不沾湿、入火不点燃,而且能够腾云驾雾、与天地一样长久的“真人”,于是始皇高兴地说:“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为使自己成为如神仙一般的真人,秦始皇甚至不让大臣知道他的起居活动,显示出神仙的神秘性。③
在秦始皇的心中,“海神”为“人状”,而且博士官告诉他神灵有“善神”和“恶神”之分,且“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④秦始皇显然也认同“海神”有善恶之分的观点,在他看来,海神与其地位也是在互相平等、互相商议的层面。徐福第二次出海叙述的内容可能比较符合他的心愿:即“海中大神”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皇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⑥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86页。虽然其中有海神对秦始皇“礼薄”的批评,但似乎海神是把“秦皇”作为对等地位看待的。蓬莱山的“芝成宫阙”,有“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的“海神”,要求徐福携带“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去拜见,结果使“秦皇帝大悦”,显然秦始皇认为这是可以商议的“善神”,于是他同意“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⑥为了打击“恶神”,迎接“善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不惜率领将士最后一次出巡,有“渡海渚”“望于南海”,“并海上,北至琅邪”。并在徐福的鼓动下,“入海者赍捕巨鱼具”,亲自“以连驽侯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⑦王子今认为:对照历代帝王行迹,秦始皇的这一行为堪称空前绝后。而“自琅邪北至荣成山”,似可理解为当时的航海记录。王子今:《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光明日报》2012年2月13日。这条在秦始皇航海途中被射杀的“巨鱼”,其实就是他心目中属于“海神”的“恶神”。
秦始皇也自比与水密切相关的“龙”。秦王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19年)秋天,有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持玉璧拦住使者称:“为吾遗滈池君”。并称奉璧人还说:“今年祖龙死”。使者还想进一步询问缘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页。可见秦始皇也自认是“人之先”者的“祖龙”。《集解》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服虔曰:“龙,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应劭曰:“祖,人之先。龙,君之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260页。滈池,古池名。在西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丰镐村西北洼地一带。池水经由滈水﹐北注入渭水。汉武帝在池南凿“昆明池”。唐贞观中﹐丰滈二水入昆明池,唐以后湮废。“滈池君”即“镐池君”,或说指周武王。班固:《汉书·五行志》:“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颜师古注:“张晏曰:‘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镐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镐池之神,云始皇将死耳,无豫于武王也,张说失矣”。不管张晏的意思是奉璧人认为秦始皇无道,长江的水神不接受他奉献的玉璧,要将之交给像周武王那样的君王来替天行道,还是颜师古认为镐池在昆明池北,其实说的就是长江的水神将秦始皇将要灭亡的消息告诉“镐池之神”,意思都是“水神”或“镐池之神”都将抛弃秦始皇。这对于相信巫术的秦始皇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内心一直对作为“善神”的“水神”和“海神”存有很大的幻想,自己希望能成为呼风唤雨的“龙”之化身,所以由此引发的内心恐慌,应该比较严重,这也是他次年七月病死于沙丘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喜欢大川,更喜欢海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三十一年十二月:“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称:“《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265页。张守节根据《秦记》所记,认为秦始皇“夜出逢盗”之地,是在都城附近引渭河水注为池,在水中还营造着蓬莱、瀛洲等海中的仙山模型,又有“刻石为鲸”,即一人工鲸鱼的雕石像,是一种海洋的象征。王子今:《秦汉宫苑的“海池”》,《大众考古》2014年第2期。即使建造陵墓,也寄托着秦始皇的海洋信仰。他仍然不忘用水银来建造大江大海:“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驽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③王子今认为秦始皇陵地宫的设计,表明了秦始皇对大海的向往,至死仍不消减。“三泉”之下荡动着的“大海”的模型,陪伴着“金棺”之中这位胸怀海恋情结的帝王,而来自海产品的光亮,也长久照耀着他最后的居所。按照裴骃《集解》引《异物志》的说法,“人鱼”“出东海中”。宋人曾慥《类说》卷二四引《狙异志》“人鱼”条称之为“海上”“水族”。明黄衷《海语》卷下《物怪》也说到海中“人鱼”。而在三国时期人们的意识中,秦人已经获得了关于“鲸”的体态以及其脂肪可以用于照明的知识,秦始皇陵中“人鱼”,可能是鲸鱼。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四、结语
秦始皇不仅接受了战国时期齐国著名思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而且还接受了邹衍在“四海”说基础上提出的“大九州”说,认为大瀛海环九州之外,还有八十一州广阔的天地空间。邹衍的“大九州”和“大瀛海”的理论,是秦始皇理解海洋和海外世界、建立自己海洋意识的重要依据。正是在这些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的支配下,出生和活动于内陆的秦始皇才会把眼光长期投射到沿海地区,才能同意徐福率领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携带着各种工具、武器和种子,两度下海,进行所谓获取仙药的航海活动。
后人因为秦始皇的残暴,故意贬低秦始皇的智力和判断力,似乎徐福两次如此大规模的航海仅仅是因为所谓获取仙药,事实上,这里所谓的“仙药”,应该也是多种海洋资源的象征物。秦始皇同意徐福率领如此之多的童男女和百工,甚至武装力量同行,应该有希望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海上移民活动,求得海外的土地,获取更多的海洋资源。如果没有关于海洋的基本知识,徐福及其随行人员根本不可能制订这样宏大的计划,秦始皇也不可能同意这样庞大计划的实施。
海洋意识也包括缘于海洋而创造出的神灵和生成的海洋信仰。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同时,就极力推进造神运动。秦国统一天下伊始,秦始皇要求臣下讨论帝号时,就强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一方面是赖祖宗的神灵保佑,同时也是依赖他的威德和神灵明圣,才能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使日月所照之地,莫不宾服。战国时代水神流行,秦代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水神庙来供奉当地的水神,在秦始皇看来,自然神灵固然神圣,但他对海洋敬而不畏,认为自己的威德和明圣所形成的力量,也足以与水神、海神较量,甚至已超过了一般的水神。在秦始皇的心中,海神与其地位也是在互相平等、互相商议的层面。“海神”为“人状”,亦有“善神”和“恶神”之分,而“水神”不可见,是以大鱼蛟龙为自己的替身,除去恶神,则善神自然可以到来。为了打击“恶神”,迎接“善神”,秦始皇不惜率领将士携带着“捕巨鱼具”入海,并亲自用连驽射杀作为“海神”恶神替身的“巨鱼”。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在古代就形成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的两极分化,甚至认为中国是北方“大陆中国”和南方“海洋中国”两张面孔,甚至认为中国是“南船北马”的“两个中国”。[日]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刘军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38~140页。其实这是一种完全缺乏史料依据的想当然的说法。秦国发源于内陆,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秦国君主没有止步于偏隅的内地,有纳四海为一统的政治宏图,使秦代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页。伴随着向东南扩张,秦朝设南海、东海等郡来加强对沿海的控制,海也被纳入秦的统治范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也建构了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无论是秦朝的政治制度,还是文化习俗,影响都相当深远。“秦”的名声远播海外,欧洲人最早称中国为“秦尼”(Thina,Thinae,Sinae),此词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中期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1页。或以为英文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a……其源皆起于拉丁文Sina,寻常用复数,作Sinae,初作Thin;希腊文中的Sinae及Seres两名,和Tziniza及Tzinista,实与拉丁文同出一源。China是“秦”的译音,由公元前249年至公元前207年之秦国而起,经秦始皇传布于远地,该观点首先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提出,后来经由卫匡国(Martin Martini)重申,也得到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考证支持。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上,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6页。公元前5世纪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的“支尼”(`Cini)与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Cin,`Cinistan,`Cinastn,应相一致,或以为“支尼”(`Cini)也是“秦”的对译。参见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34页。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秦”在世界很大范围内都被认为是中国的象征。
秦始皇虽然是成长在以陆地为核心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地区,但他却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意识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他不断到海边巡游,甚至不惜进行海洋航行以战胜“海神”之恶神,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着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从内陆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说,秦始皇不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同时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附记:本文为2014年10月31日提交给由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主办,浙江省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海洋文化经济论坛”,并作了主旨演讲的论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