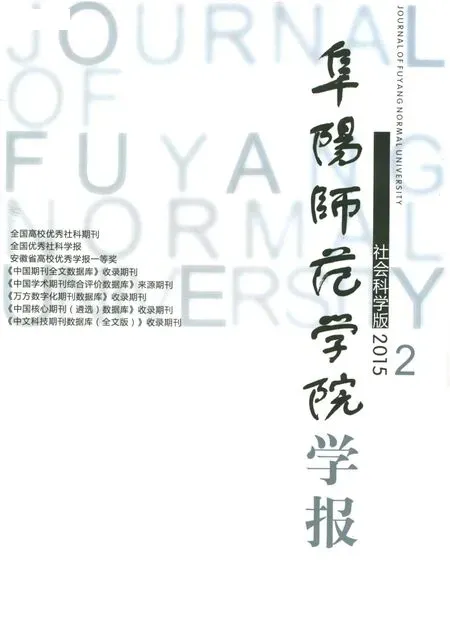他人即地狱:苏童《黄雀记》之存在主义解读
刘文婷(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他人即地狱:苏童《黄雀记》之存在主义解读
刘文婷*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苏童在其新作《黄雀记》中以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主要人物为中心,构建出复杂的三角关系,与萨特理论中有关自为与他人的存在主义理论相合。从存在主义理论中关于“注视”的初次注视与再次注视展开,揭示三人之间发生联系与产生冲突的最初征兆;进而将人物冲突深化到互为“羞耻”的层面,针对小说中多次提及的三个意象“跳小拉”“镜子”“绳子”分别阐释该意象对于主人公羞耻的意义所在;最后总结出苏童所构建的三角关系,实际上是对萨特“他人即地狱”理论的完美诠释,保润、柳生与仙女正是这种互为地狱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在他人那里得到的显现,他人的存在又限制了自身的自由,从而产生冲突并无法超越,成为地狱的象征。
自为;他人;存在;注视;羞耻
2013年8月,苏童新作《黄雀记》出版问世,延续了其以往作品中小人物、小故事的风格与节奏,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将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与白小姐的夏天,以此来讲述由一个强奸案所引发的三位主人公之间的命运纠葛。就情节来看,小说并没有过多紧张激烈的场面,苏童娓娓道来,然而在看似平静的外衣下,蕴含着作者对于自为与他人存在关系的深刻哲学思考,值得探究。
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萨特看来,人的自为“存在是超乎于自身之外的,存在是其所是”[1]25,而“他人,就是不是我和我所不是的人”[1]293。其表述虽然绕口,却十分准确地阐释了自为与他人的内涵。萨特认为超越性是人的特征,是人成为自身并拥有自由,而后不断超越自身的保证。作为自身的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通过超越而不断更新重塑自身,即成为“其所是”。因此对于“他人”的定义除了解释为不是我外,还包含着我所不是的含义。《黄雀记》中的三位主人公,保润、柳生与仙女之间正是这样一种自为与他人的存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展现。
一、注视——自为与他人关系联接的开端
自为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相互关联,最初是由注视开始的。我作为人的存在,是具有超越性的、自由的存在,而他人的存在亦是他人的具有超越性与自由的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如何如发生关系,萨特提出了注视的理论,他人原则上来说是“注视着我的人”,这里的注视并非简单地用眼睛看,而是“走在眼睛的前面”,不单单看我的表面,而是以介入我存在的目的扫视我。对于这种注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我不再独立,而是通过被注视无法抗拒地与注视者即他人发生联系,我的存在也因此得到揭示。与此同时,在他人注视我时,他人也处于被注视的状态,这种注视使我与他人的自由同时受到了限制。回归文本本身,作者在描写三位主人公相遇之时,皆由洞察世界的眼睛开始。
(一)初次注视:定义他人的存在
与萨特假设的情境略有不同,保润与仙女的初次相遇对视并非发生在两人间平等的对视,而是一次意外——照相馆的失误,将祖父的遗照与少女的照片装错,照片无意中掉落,使保润这个自由的存在与少女发生对视,照片中的少女“用一种忿忿的谴责性的目光,怒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保润”[2]7。正是这一怒视,使保润感到了不安而后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他最终舍不得将照片还给照相馆。尽管后文中仙女否认了照相一事,但仍可将此理解为保润对仙女的初次注视,因为萨特主张自我选择,这种选择使保润能够将照片上的少女定义为仙女,仙女无法逃避这种定义。可以说,保润单方面的注视,就已经对仙女的自由进行了限制,而他自身的存在也因此逃离不了被他人的定义,这无疑为下文埋下了伏笔。
保润与仙女真正意义上的相遇是在井亭医院中,雨中无意的相撞,放下伞两人相互注视对方,仙女“挑战的目光里有一丝明显的好奇,她从头到脚审视着保润”[2]27。“审视”一词恰到好处地指出仙女并非用眼睛在看,而是透过眼镜对保润这个他人存在的扫视,这时的保润作为他人的存在,存在于仙女的注视之下,被仙女以她的角度重新定义,保润无从选择,更无法逃脱。“赶紧给我回病房去,该服药了。”[2]27由于仙女的注视,保润的处境脱离了自身,即他不再是自身处境的掌控者,掌控权移交到了仙女手中,仙女不必与保润就其存在的定义展开沟通,保润的存在被仙女定义为精神病患者。保润初次感到的“亲近”与仙女定义的精神病患者,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让两个个体的存在发生联系又产生分歧,这意味着两人的共存必然带来不幸的结局,是对“他人即地狱”观点的最初印证。
相比之下,柳生与保润的初次相遇,并没有过多的细节描写,只提到柳生“虚着眼睛看保润,保润只当没看见”[2]40,简单的一句中许多细节值得玩味。柳生“虚着”眼睛注视保润,代表一种傲慢的个体存在,“大名鼎鼎的柳生来了”是作者对于柳生出场的介绍,柳生也将自己定义为这样的存在,他的傲慢实际上是其自欺的表现,作者简要介绍了柳生的家世,长期掌握着香樟树街居民饮食的命运,因此柳生将自己设为对象,力图在虚荣中作用于保润。但保润出乎他的意料,表现出的是不屑,保润作为个体自为的存在,是自由的,对对象的超越性使保润“只当没看见”,柳生对自我对象的定义因对象的无视而土崩瓦解,保润与柳生在最初的相遇中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潜在的不平等暗示着两人不同的命运。
(二)再次注视——冲突升级
人作为独立的存在,都具有其特殊性,自为与他人两个独立的存在,由于特殊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就演变为冲突。因为人的特殊性是无法改变的,因此相互独立的个体之间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萨特认为:“我活着就需要别人受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3]216《黄雀记》中,保润、柳生、仙女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初次注视时,自为的特殊就为人物之间的冲突埋下引线,再次注视时,冲突升级。
柳生与仙女两人最初以金钱关系展开,仙女称柳生为老大。与保润相比,仙女的存在满足了柳生的虚荣心,金钱的利用使柳生与仙女最初是和谐的氛围,但冲突并不会因此而消除,柳生与仙女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存在。对于柳生来说,仙女作为对象的存在并非是可以完全掌控的,一旦对象选择超越自身,虚荣就会幻灭,和谐将难以维持,冲突便由此升级。在经历了被强奸,举家迁移消失十年后,仙女以白小姐的身份归来,“他们的目光撞在一起,闪电不期而遇,伴随着一股隐秘的飓风”[2]130。此时的仙女已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自为与他人存在的不同,使冲突激化,这种激化是双向的,带来的结果是两个个体同时受到折磨,这种心灵上的折磨比肉体更令人煎熬,注视使由于对象的消失而暂且回归自由的个体重新受到限制,说明冲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亡,一旦对象间再次发生注视,冲突便伴随而来,自为与作为他人被注视的存在皆无从幸免。
保润与仙女初次注视就因被定义为截然相反的存在而产生冲突,自为存在的相互排斥以及柳生金钱利益的诱惑,使保润成为替罪羊并坐牢十年,身体自由受到限制,但这漫长的十年并未使冲突淡化,高墙四壁并未禁锢住保润自为的自由,反而成为了保润存在的动力。他的存活是为了与仙女、柳生的再次相遇,用注视来对两人进行灵魂上的折磨,也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道凛冽的刀锋般的光芒,刺过来,带着些许凉意。”[2]223在柳生面前,仙女可以是理直气壮的,但对于保润,仙女是一种有罪的存在,当仙女处于保润的注视之下时,超越性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像裸体一般地暴露于保润的注视之中,负罪感油然而生,无论仙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逃离超越自身,都无法洗去她的罪恶,她的努力最终把保润作为工具来对待,并把保润的自由作为被超越的超越性所显现出来。因此,仙女存在的本身是对保润有罪的,仙女如何为自己开脱都无法弥补,对象保润的出狱使仙女再次明确了冲突是无法逃避的,保润与柳生的存在是仙女实现自由的前提,也是对其自身自由构成限制的障碍,没有他人,仙女无法存在,面对两人的注视,仙女的自由再次受到限制。
二、羞耻——自为与他人的存在之存在关系
萨特认为羞耻的“结构是意向的,它是对某物的羞耻的领会,而且这某物就是我”[1]266。联系其对于我的解释,羞耻即是对我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通过对自身羞耻的感悟,我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一个方面,但这个发现的前提是他人的存在,只有在他人的注视下,自由被限制,无法避免地被他人定义,我才对自身感到羞耻,这是我在他人那里所显现的自为存在。这里的他人成为了我与自为存在的中介。保润、柳生与仙女三人通过相互注视产生联系,介入彼此,发生冲突,皆无法摆脱被束缚的宿命,这种宿命实际上就是一种羞耻的存在关系展现。
(一)跳小拉——保润的羞耻
保润的羞耻出现于第一部分保润的春天中,对于一个懵懂少年来说,春天是个充满爱意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保润与仙女相遇,两个独立自为的存在相互注视,却仅有保润一方产生了爱的情愫,保润作为恋爱者要求被爱者即仙女将其作为绝对的选择,但期望并未实现。因此在一开始两人就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机会。什么机会?什么机会都不存在了。他觉得羞耻。”[2]54作为保润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在爱情中期望与他人的限制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但保润所感受到的是自己在他的爱情和他的存在中贬值了,仙女并未把他当做恋爱者的存在。作为仙女注视的对象,保润意识到自身并由此作出对自身的判断,在算不上爱情的爱情中,面对仙女,保润自始至终都是羞耻的存在。
因为仙女的伪证使保润入狱十年,但出狱后的保润并未对她作出过激的行动,只要求仙女在水塔陪他跳小拉,从此恩怨一笔勾销。跳小拉对于保润有其特殊的含义:保润想要在仙女这里摆脱其羞耻存在的这个方面,以求对自身限制进行超越,突破限制回归自为的存在,回归自由,而回归的方式就是实现与仙女跳小拉的愿望。但仙女并未使其如愿,虽然内心对保润心存愧疚,但表面上仍趾高气昂,无论保润如何纠缠,在仙女面前,他必须承认自己就是仙女注视和判断着的对象,保润无法拒绝自由变成仙女所限制的对象存在,因此保润对其自由感到羞耻。在结局时,当保润误以为柳生在结婚前与仙女好上时,保润对自在已无法控制,这种羞耻的存在使保润最终杀死柳生,以此摆脱羞耻的束缚,以求解脱。
(二)镜子——柳生的羞耻
在保润面前,柳生本是作为骄傲的个体存在,他骄傲的资本之一是成为仙女的老大。但由于柳生选择的失误,强奸了仙女,使柳生存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品中部“柳生的秋天”中第一句就写到:“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2]119“夹着尾巴”的原因是柳生在父母的帮助下将强奸罪转嫁给了保润,面对保润与仙女,柳生的存在无疑由骄傲跌到了羞耻的境地。
保润被关押的十年中,柳生选择下海,混得不错,似乎羞耻已随着保润的入狱而逐渐消失,这符合萨特对于羞耻的统一领会:我在他人面前对我感到羞耻。那么这个他人目前不存在于我的面前,羞耻就不存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保润这个他人虽未出现,但他人的存在作为对象在我这里是完全不能变的,即保润这个对象存在的永久性,因此我的羞耻也总是持续着。对于柳生的羞耻,作者巧妙运用“镜子”的意向进行阐释。
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镜子”这个意象,在存在主义看来,镜子有其特殊内涵。“镜子的存在首先意味着他人的存在,镜子只是一个中介,通过它,人要过渡到面向他人的活动上来。”[3]219也就是说,镜子中的人是他人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人为什么要照镜子?就是将“我”向“他人”的方向转换,通过转换,镜子中的“我”不仅是我的存在,亦成为他人的存在。我与“他人”发生注视,即我与镜中之我对视,透过我的眼睛看到镜中之我和面对镜子的我两个我的存在,从而实现了对“我”内心的扫视,直面我的灵魂。理解了这一内容,就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的用心所在。
《空屋》一节中,柳生看到狱警的身影很像年轻时的保润,这时保润并未出现,只有狱警的背影,也无法对视,那么如何使他人存在来揭示柳生呢?苏童写道:“走廊尽头可见一扇铁门,迎面竖着一面大镜子。”[2]141这面镜子恰逢时机地出现在柳生面前,显然有其特殊用意。镜子里的映像,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下意识地向角落闪了一步,避开镜子的映照。柳生为何躲闪?是因为他看到了镜中作为“他人”存在的自己在注视自身,而自身由对保润的记忆逐渐清晰使羞耻感再次出现,说明柳生承认了羞耻感的存在,因此想要躲避镜中之我的注视,摆脱对保润羞耻的束缚,同时怕他人的出现洞察出隐藏在伪装之下的羞耻。
因此,羞耻是在他人面前对自身感到羞耻,他人可能存在于现实中,也可能永远存在于羞耻主体的灵魂中,正如柳生,通过镜子反观自身,这种羞耻具有永久性,柳生无法摆脱,除了羞耻与痛苦,他为这种永久性的存在感到自怜。
(三)绳子——仙女的羞耻
对于仙女,她的羞耻始终与“绳子”相连。为了让住在精神病院的祖父不再挖树,保润研究出了捆绑绝技,并在仙女拒绝同其跳下拉时,找到了类似绳子的“狗链子”将仙女捆住,这是第一次,保润从她眼里发现了羞耻、畏惧,还有绝望,保润用绳子证明了自己,也将绳子与仙女的羞耻存在紧紧捆在一起。保润也因此成为柳生强奸仙女的帮凶。
十年后,保润再度出现,从口袋中拿出尼龙绳,依然是他炫耀和示威的方式,拿着绳子的保润此时不是自身羞耻的存在,而是他人的存在,揭示仙女羞耻的存在。在仙女看来,绳子就是保润的象征,是十五岁时惨痛经历的象征,是羞耻的象征。仙女无法摆脱,其自为存在像被绳子绑住一样无法获得自由。
在结局中,仙女生下红脸婴儿,将他与一只大号蛇皮袋一并给了祖父,蛇皮袋里全是保润的绳子,绳子的再次出现说明仙女想要摆脱一切命运对她的束缚,尤其绳子是羞耻的象征。但她能否成功呢?作者留下空白,就存在主义理论来看,羞耻是对于自身“外表存在的原始体验”[1]361,当外表存在处于他人注视之下时,这个外表存在就介入到了他人存在之中而毫无遮掩,因此无从躲避,绳子对于仙女的羞耻性存在具有永久性。
三、他人即地狱
“他人即地狱”是萨特在《禁闭》中的经典台词,就“地狱”来看,是与“天堂”截然相反的存在,是一个没有自由,充满黑暗,会使人受尽折磨的存在。他人即地狱,“不是指他人会用残酷的手段虐待我的身体,而是指无法抗拒他人对我的自由限制,无法摆脱他人对我本质化的威胁,导致我的存在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中”[3]223。将“他人”比作“地狱”,即是将他人看作是限制“我”的自由、使“我”的人生受尽磨难、充满黑暗的存在。
保润、柳生与仙女始终是互为地狱的存在:对于保润,仙女使其陷入爱情的地狱,让保润经历了爱情的初体验,而柳生的嫁祸使其人生从此落入无尽的黑暗。保润为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与仙女、柳生产生冲突,自为存在被爱情束缚,受到柳生与仙女的双重限制,保润想要挣脱,但最后仍选择杀死柳生自身彻底陷入地狱之中。相比保润,柳生面对的是羞耻的永久性地狱,羞耻一方面来自于对强奸仙女的羞耻,另一方面是对转嫁保润的羞耻。这份羞耻并不会因保润坐牢、仙女离开而消失,镜子的存在印证了这点,保润与仙女是对柳生地狱般的存在。对仙女这个受害者,保润用绳子的威胁,柳生对她年仅十五岁时的强奸,两人无疑是地狱般的存在。仙女独特的个性吸引着保润与柳生,同时也延伸出无休止的矛盾与冲突,无论仙女多次发誓远离这片土地,最终仍敌不过香椿树街地狱般的强大引力。尽管结局中仙女再次离开,但地狱的追踪仍在继续,红脸婴儿的出生即是最好的证明,仙女逃不过“他人即地狱”的永久存在。
自为的存在在他人那里得到显现,我期望在他人那里达到形象的完美塑造,而他人亦期望在我这里得到满足,自为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性使相互之间皆无法实现满足,由此产生难以避免的冲突,冲突使自为与他人互相折磨,互相限制彼此的自由,从而无法超越,那么他人就成为了地狱的存在。苏童用《黄雀记》生动地阐释了他人即地狱的内涵。
[1]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2]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李克.存在与自由——萨特文学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Others are Hell: Existent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SuTong’s Huang Que Ji
LIU Wen-t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China)
In the new novel Huang que ji, Su Tong builds a complex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Baorun, Liusheng and Fairy, and uses Sartre's existentialist theories about the being-in-itself and being-for-itself as a basis for analysis of the novel. Starting from the existentialist theory of "Contemplate", the paper reveals the first signs of conflict and contact among the three characters. To further deepen the character conflict to the "shame" level, three images are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dancing, mirror and rope. Finally,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constructed by Su Tong is actually the perf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artre's "The others are Hell", Baorun, Liusheng and Fairy are mutual existence of hell, being-in-itself is shown in being-for-itself, being-for-itself in turn limits the freedom of itself, thus conflict appears and becomes unsurpassable as a symbol of hell.
being-in-itself; being-for-itself; being; contemplate; shame
I206.7
A
1004-4310(2015)02-0073-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2.017
2014-12-26
刘文婷(1991-),女,汉族,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