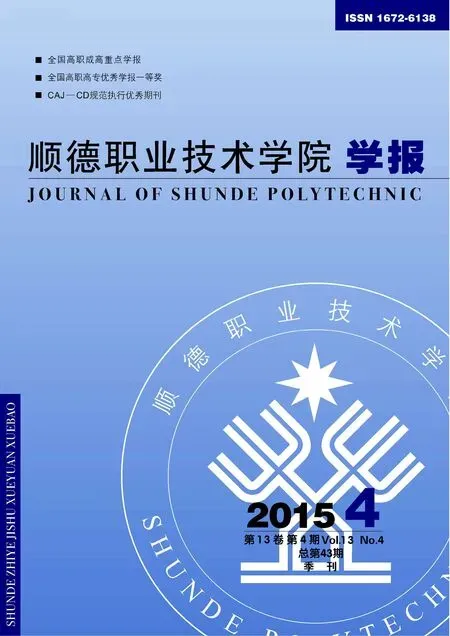影片《归来》中身份危机的后精神分析学解读
延永刚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张艺谋的新片《归来》上映后,赞赏和批评的声音兼而有之,赞赏者或为帝后级演员的精彩演技击节叫好,或为影片的忠贞爱情感动流泪;批评者或对影片改编效果表示不满,或对影片缺乏历史反思力度感到遗憾。赞赏也好,批评也罢,这些本来都是评论者的常态反应,但是如果对影片过早归类,可能会掩盖影片作为“这一个”的独特价值。毕竟,不能仅仅看到文革元素就将其和同类电影进行相互对比和评说优劣,也不能死死盯住原著小说来苛求影片的忠实性。笔者认为,影片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的寓言性,虽然影片里包含文革背景和商业元素,但是这些都没能抑制影片故事的独立伸展,故事本身随着情节展开不断明晰,然后逐渐超越这些元素,最后变成了一个关于身份危机的隐喻。
1 身份危机的症结:遭遇实在界
身份危机在影片中表现为双重维度:第一重危机发生在社会与个人之间,表现为特殊时代对陆焉识身份的拒绝,影片的前半部分就是这重身份危机的集中演绎。演绎的路线有显隐两条线索:显在的线索发生在陆焉识身上,一个被主流社会流放的右派分子,失去了正常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他不顾一切地想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来,但是却遭到主流社会强烈的排挤和拒斥;隐性的线索发生在陆焉识的女儿丹丹身上,她因父亲的右派身份导致了自己芭蕾舞“主角梦”的破碎,这体现着身份危机在下一代生活中的延伸。
发生在社会和个人身上的身份危机随着社会的变迁自行解决了,新的时代用一纸公函摘去陆焉识头上的帽子,抹去了身份隔离的印记,使陆焉识可以重新融入新的社会,开始正常的生活。然而,社会的变迁解决了第一重身份危机,却没能避免第二重身份危机的出现。这重危机发生在陆焉识和冯婉瑜之间,确切地说是发生在平反后的陆焉识和“患病”后的冯婉瑜之间,当陆焉识迎着灿烂的阳光开始新生活之旅时,他发现他和冯婉瑜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障碍,此时的他已经无法走进冯婉瑜的精神世界。影片后半部分集中表现的就是平反后的陆焉识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回到冯婉瑜精神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恢复自己身份的过程。最终,我们发现这重身份危机并没有像第一重身份危机那样得到了解决,而且影片的结尾似乎在暗示着第二重危机的不可解决性。如果说第一重身份危机的症结在于社会和时代,那么第二重身份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冯婉瑜的“病症”。关于冯婉瑜的“病症”,影片通过医生之口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描述,并给其定性为“心因性失忆”,同时,还给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精神疗法“似曾相识”,而影片的后半部分也是围绕着这个治疗方法来安排情节的。表面上看,影片就是围绕着这个病症展开故事的。病症源自于特殊时代对一个家庭的伤害,病症的治疗则围绕着时代转型后这个家庭的自我修复和疗伤。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影片,可能会遮蔽影片的寓言性维度。如果从后精神分析哲学角度来审视冯婉瑜的失忆,笔者认为,这种失忆是一种现实感危机的表征,而这种现实感危机源于实在界的溢出。
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将讨论的重点放到想象界和符号界,而以拉康和齐泽克为代表的后期精神分析理论则将实在界放到了理论核心位置,实在界的转向使精神分析理论的触角伸入到了人的隐秘幽微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日常现实和精神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不能和实在界相遇,甚至为了保证人们的现实感,必须将实在界排除在外。齐泽克曾以俄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马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画作为例来论述现实和实在界的关系。在马列维奇的著名画作《我们时代的赤裸、无框肖像》中,实在界和现实的关系以抽象的几何图形(一个简洁的黑方块,被置于白色的背景上)显现出来。在画中,现实即白色的背景平面,实在界即黑色的方块,现实要想获得自身的一致性,必须排除实在界,必须将实在界的身份转变为黑洞,即核心的匮乏,也就是说画家的全部用意就是力图拯救將实在界和现实隔离开来的屏障,即竭力阻止黑方框溢出边界,因为一旦黑方框溢出边界,向白色背景蔓延开来,现实就会解体,人们的现实感就会丧失。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在常态生活中,避免和实在界相遇是支撑人们现实感的方式。但是齐泽克认为,这样的现实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当发生创伤性事件的时候,人们就可能遭遇实在界,这时,人们的整个现实平衡都会被这一创伤事件打破,陷入现实感丧失的困境。在影片《归来》里,女主人公冯婉瑜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就陷入了现实感丧失的困境。在“车站创伤”发生之前,冯婉瑜的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这个现实世界虽然并不平静,但是基本上还在她的可理解范围之内,丈夫在十几年前就被划成右派分子而流放农场,虽然她对这一划分并不认同,但是在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里,这种惩罚带来的影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生活吸纳。事情的转折开始于丈夫陆焉识逃跑,她知道陆焉识的逃跑一定事出有因,这从她反问刘同志和邓指导员的话中可以看出,当邓指导员问她是否知道陆焉识逃跑的消息,她反问道:“你们把他怎么了?”她似乎隐隐约约感到丈夫可能是受到了无端的折磨和伤害,这种猜测使她原初的被压抑的愤怒和质疑开始释放,也就是说,在这时她已经对外在现实和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不信任,而“车站创伤”那一幕场景则使这种不信任发展到不能理解的程度。这也是影片的一个剧情高潮:她站在车站的行人天桥上,俯视着这一幕,这个视角足够高,高得让她足以看清发生在眼前的一切:一边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渴望回家的丈夫,一边是告密的女儿和抓捕丈夫的革委会成员,他们一起冲向自己,人性的美好和反人性的罪恶一起冲向她的世界,她不知道如何将自己融入到这一场景,那一声声歇斯底里式喊叫既是给丈夫的信息提示,同时也是她本人对于遭遇实在界的本能抵抗的表征;这个视角足够高,高得让她又看得如此模糊,当她的头重重地磕在地上那一瞬间,疼痛已经不能够再提醒她仍然处在现实中,现实在冯婉瑜的精神世界中逐渐走向解体。回过头来,再让我们讨论马列维奇的那幅画,最后作者以割腕自杀的方式诠释了实在界入侵的毁灭性后果,当然电影的女主人公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通过幻象空间的营构来屏蔽实在界的创伤,支撑自身现实感的一致,组织并诠释生活的意义。
2 身份危机的解决困境:幻象空间的悖谬逻辑
幻象是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并且有一个关于幻象的公式:$◇a,在这个公式中,$代表欲望主体,而公式中的菱形符号则有两层含义:首先它代表屏蔽——主体通过幻象屏蔽实在界,免受实在界的入侵带来意义的丧失;另外它还代表建构,主体通过幻象在空洞实在界中建构一个欲望客体,a就是这一欲望客体,也称小客体。齐泽克认为主体欲望与小客体的关系,不是小客体在先,主体欲望在后,恰恰相反,是主体欲望在先,小客体在后。只有主体欲望通过幻象建构一个框架和先验图示,小客体在这个框架里才具有意义。小客体成为主体欲望的目标,与其实证属性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小客体的属性是通过主体欲望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冯婉瑜精神创伤后的精神世界就是由幻象建构起来的,因此冯婉瑜的现实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幻象空间。在日常的现实中,它是失忆的,而在幻象空间中,她确实有记忆的,这些记忆就蕴含在照片、车站和信件当中。在她的幻象空间中,实在界创伤被屏蔽,经由幻象框架,她建构起来一个欲望客体,通过这个欲望客体,她想重新获得在创伤事件中失去的丈夫。因此,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着5号的到来。等到那一天到来后,她像经历初恋一样,整理好自己的妆容,兴奋地举起写着陆焉识名字的指示牌,来到火车站,期待丈夫的到来。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真正的陆焉识站到她身边时,她却视而不见。
这种矛盾深刻地诠释着幻象公式中主体与小客体之间的不可能关系、主体欲望与欲望客体成因的不可能关系。这种不可能是指主体永远不可能得到小客体,因为小客体并不能客观的存在,它只能在幻象框架下存在,只有被主体的欲望扭曲后才能存在。常人眼里,那个车站永远不会发生奇迹,因为陆焉识已经回来,就站在她身边,但在冯婉瑜眼里,那里却存在着小客体,一个空洞的存在,在那里有无限多的想象可以填补它的空白,这些想象是支撑她的世界具备一致性的唯一方式。从得知陆焉识平反的消息后,冯婉瑜就开始了追逐小客体之旅,每月5号这天,她都会做这个永无结果的重复的行为,但是这种追寻注定不会有结果,因为这种结果本身就是无限制的拖延,而不断拖延这种结果恰恰是幻象中的主体欲望本身,也就是说“欲望的实现不在于欲望的完成和充分满足,而在于欲望自身的繁殖,在于欲望的循环运动”[1]。冯婉瑜之所以实现了她的欲望,就是通过幻象,使自己进入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使她能够无限期的拖延,从而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换言之,通过幻象,冯婉瑜使自己进入不断匮乏的状态,而匮乏的状态恰恰是欲望之所以为欲望的根本。至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影片结尾出现了那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陆焉识举着陆焉识的名字和冯婉瑜一起等待陆焉识归来。那个被等待的陆焉识,必须在等待中才能在冯婉瑜的世界里具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在冯婉瑜的幻象框架中生存,在那里,冯婉瑜给被等待的陆焉识预留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后精神分析理论称之为“原质”的位置,当小客体占据了这个位置之后,就会变成崇高客体,“崇高客体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必须与主体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支撑主体幻象框架的保证,一旦这个距离消失,一旦主体过于接近崇高客体,崇高客体就会失去崇高的特征,变成普通的日常客体,由此主体的幻象空间就会坍塌,并陷入极度焦虑和恐慌的状态。”[2]在影片中,陆焉识回来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想回到冯婉瑜的世界,但是之所以屡次进入屡次都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现实中的陆焉识走进冯婉瑜的幻象空间,那么冯婉瑜幻象框架中的占据原质位置的崇高客体就会蜕变为日常客体,冯婉瑜的幻象空间就会毁坏,对其造成创伤的实在界就会再一次将她笼罩。
影片的结尾定格在了这样一个场景:过了若干年以后,一个某月的5号,在火车站,风雪交加,两位主人公已经进入暮年,冯婉瑜坐在轮椅上,眼中带着期盼,盼望那里出现她一直期待的人,而那个她期待的人——现实中的陆焉识,却陪伴在她身边,举着陆焉识的名字,在那里和冯婉瑜一起等待着陆焉识的归来。一个充满着悖论意味的结尾,我们看到了导演的一种妥协,一种对于治愈人物创伤的妥协。有人说影片的结尾是悲剧性的,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大团圆的结局,只看到了在风雪交加的车站,女主人公在等待着那个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人,也因为男主人公的一切归来的努力宣告失败,他只能在离女主人公最近的地方体验与她最远的距离。然而笔者觉得影片除了演绎爱情的悲情之外,还做出了一个伦理选择:“不要轻易侵犯他人的幻象空间。幻象空间是创伤主体的现实感的终极支撑,它是以特定方式组织她自己意义世界的方式,侵犯他人的幻象空间就是否定创伤主体的特定的绝对和神圣的细节,最终会造成主体性的贫困”。[3]其实影片《归来》的这种伦理选择——尽量不侵害创伤主体的幻象空间,从“读信”那一个场景就已经开始了,在经历几次直接进入冯婉瑜世界的失败以后,陆焉识逐渐改变了姿态,不去强制性地将自己置于冯婉瑜幻象空间中的崇高客体位置,而是选择以读信人的身份守候在冯婉瑜身边,当这些写在破纸片的文字通过陆焉识的口读出来的时候,信件巧妙地成为连接现实世界和幻象世界的纽带,成为连接作为日常客体的陆焉识和崇高客体的陆焉识的桥梁。而影片的结尾则是对这种伦理选择的延续,陆焉识继续守在冯婉瑜身边去重复那个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等待行为,在这种重复行为的背后去呵护冯婉瑜幻象空间的完整。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能够体会导演将影片命名为“归来”的良苦用心,它不仅指被时代放逐的陆焉识对恢复正常人身份的强烈渴望,更重要的是指陆焉识寻求自己在冯婉瑜精神世界合法身份的不懈努力。两种“归来”的不同结局传达给人们的不仅是历史变迁下的人物命运沉浮,更展示了社会大历史与心灵小世界的非一致性,如果非要和同类历史题材的影片做一个比较,《归来》更具备一种哲学气度,走得更深远。
[1]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0.
[2]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78.
[3]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69.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