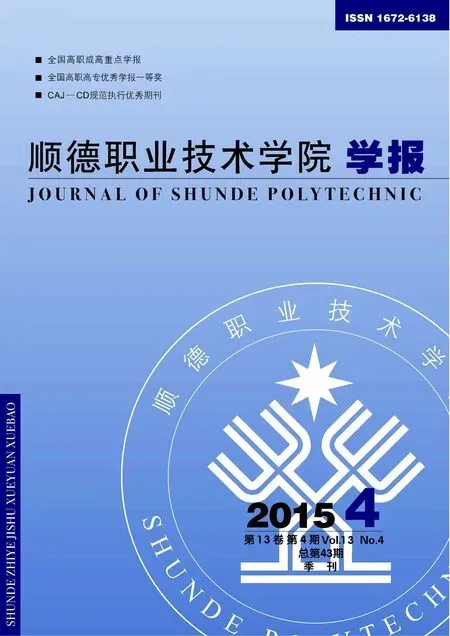自我存在的异化——《变形记》人物存在分析
雷 欢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如卡夫卡《变形记》的主题“变形”,这本书的人物其实都是扭曲而变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出自对自我存在和自由的追求,是在重重压迫下对自我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存在的厌弃与反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自我追求是不被允许的,更被整个人类社会所排斥。格里高尔除了以死亡的形式获得最后的真正的自由,他不会被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所接受。而格里高尔的妹妹葛蕾特与他的父亲则是另一种自我存在的异化。他们的变形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下,是对自我存在的放弃,转而去追求物质生活。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对冷漠的社会存在的认同,其结果,必然是排斥并抛弃追求自我的格里高尔。
1 格里高尔自我存在的困境
“存在的过程是每个个体生命自身体验的过程。”[1]133卡夫卡一生都在探讨“人”这一存在的问题,身为犹太人,卡夫卡一开始十分厌恶和鄙夷犹太文化,但是内心却又潜意识地赞同,并在他的生活与行文中体现出来。关于人自我存在的问题,没有人会比他更为贴切地了解到: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且又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的自我存在是矛盾重重的,也是困难重重的。
萨特认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2]8故而追求真实的自我,探究个体的自我存在是再正常不过的根本问题。社会是人的社会,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一员。故而当社会已经异化,在社会中生存的人必然会随之异化,而本真地追求自我存在的个人,便成了社会中真正的异类——百无一用的“甲虫”。
格里高尔的变形是注定的,因为他对自我的身份十分抗拒,对那个冷漠的社会也是十分厌恶。身为一个推销员,他只觉得那是一个累人的差事,不仅到处奔波,还要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低劣的饮食等等。从他的抱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的确是一个不公、冷漠且问题重重的社会。而格里高尔身边的人,且不说他早已经异化且变得自私自利的家人,就是社会上的朋友,也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3]39期待已久的爱情被人捷足先登,而那些同事,更是活得像贵妇人,至于他的老板,格里高尔最真实的想法是“也许开除了倒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3]39在上司面前,格里高尔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连病都不能生的工作机器。如果请病假,那么“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3]40仅仅是公司下面的一个推销员,请病假竟然会让老板亲自前来,这是难以想象的。社会在这里并非井然有序,而是显得极为荒诞。社会要求人完全抛弃应有的身体感觉,去做一个和机器无异的工具。故而格里高尔如果没有变形,那么等待他的就将是没日没夜的工作,是成为社会中的“非人”。
在重重的社会压迫下,格里高尔终于选择了真正的自我——变形。“变形意味着格里高尔·萨姆沙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脱落,恢复到原形。变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格里高尔无力承担社会角色之恐惧心理的展现;第二,则是争取自己真实自我的生存权,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4]94格里高尔的推销员生活是无望且奔波的,他的变形宣告着劳碌的终结,更是他所厌弃的社会生活的结束。特别是当秘书长被他吓跑后,那是格里高尔与社会生涯的正式告别,而之后呢?父亲将他赶回了房间。房间是个人自我生存的天地,是一个只属于自我的隐私空间。格里高尔被赶回房间,正预示着他回到了自我本真的状态。变形之后,格里高尔终于不再是挣钱养家的工具,他争取到了自我的生存权,亦即休息的权力,并且与家人建立起了他所期望的正常关系——得到亲人(葛蕾特)的照顾。
但需要明白的是,格里高尔虽然追求了真正的自我,但是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脱离了群体、脱离了社会的人便不再称之为“人”。“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正如萨特所说:“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2]1”“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2]5格里高尔身为家中的长子,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的责任便是供养家庭,是对父母和妹妹负责。故而格里高利追求自我的行为,在其家人看来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他背弃了应有的社会身份、逃避使命的行为。
身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在疲倦的同时,是骄傲和自豪的,因为他能让家人居住在一套挺好的房间里过着蛮不错的日子。在明确自己已经变形的那一刻,格里高尔在庆幸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了担忧。这种担忧体现为他赶火车的焦虑:在明知自己已经成了甲虫的时候,格里高尔仍旧想要起床去上班。当发现自己离不了床之时,格里高尔是焦虑的,他看着时间由五点、六点半、七点差一刻、七点一刻到八点,每一次时间的出现,都是他想要回归社会、回归工作的迫切渴望。时间的变化与格里高尔推销员的社会身份紧密相连,他明明已经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灵魂却仍是束缚于原本的社会身份之中。
格里高尔是否真的心甘情愿为家庭挣钱,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格里高尔看来,忙碌的工作之后,“直待他精疲力竭地转完一个圈子回到家里,这才亲身体验到连原因都无法找寻的恶果落到了自己身上。”家本是一个人休憩的港湾,但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有着恶果在等待他。所以“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一样。”[3]41这说明,他感受到了家庭中的压抑,感受到了生活其中的异化和痛苦。故而他并没有为能给家人挣钱感到快乐,而是希望将恶果排除掉,亦即从肉体上摆脱世俗的桎梏——变形。
格里高尔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为老板和上司打工上,但这不是出于他的自愿;他的另一个社会价值是为家庭迎来收入。价值的实现是令人满足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让格里高尔感到光荣,更让家人感到快乐。但随着生活的麻木,那种在格里高尔看来美好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家庭也的确是他在负担,大家都习惯了,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给的人也很乐意,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3]59没有了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本就失望的格里高尔自然难以为继,更何况这社会价值的实现还牺牲了他的自我存在。“有的时候,他没有心思为家庭担忧,心里只有高兴,却因为家人那样忽视自己而积了一肚子的火,”[3]78虽然责任依旧时时提醒着格里高尔,但是他自我意识的觉醒,早已使他远离了自我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身份。格里高尔真的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倒挂在天花板上摇来晃去,呼吸都变得轻松多了,舍弃了社会身份的真我是如此快乐,这样的追求让格里高尔难以抗拒。
卡夫卡认为:“现代人必须明确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清楚自己的追求与目标,不再依傍外在的东西(不管是神还是人)而活着。”[5]97格里高尔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脱离了繁重的社会劳动走向自由与自我。他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故而他抛弃了所负的责任,不再为家庭与社会所束缚。但可惜的是,格里高尔难以做到不再依傍家人而活,没有了妹妹的食物,他寸步难行,以至于最后被活活饿死了。
2 葛蕾特自我存在的矛盾
在格里高尔的变形之下,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他的妹妹葛蕾特。葛蕾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17岁少女,每天花着格里高尔给她的钱去买一点不太贵的东西,有时则和哥哥聊一下那个她认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上音乐学院。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前被父母说是不中用的女儿,却是主动担负起了照顾变形的格里高尔的责任。
葛蕾特在格里高尔变形前,她的自我存在和社会存在是统一的:受格里高尔细心照顾的妹妹、家中的幼女、爱拉小提琴的少女。但是格里高尔突然抛弃了他应负的责任,那么,家中有且仅有的年轻一辈葛蕾特,她的社会身份便不得不发生了变化:家中最年轻的劳动力,以及,照顾格里高尔的人。葛蕾特的自我存在异化了,由学院迈向社会,这是质的改变。既然“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那么身份已经发生变化的葛蕾特,便也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葛蕾特的自我存在是前后矛盾的。前期的她,性格软弱,会为了格里高尔拒绝开房门而啜泣,哪怕是开始照顾格里高尔,她同样是胆小的。“她一进房间就冲到窗前,连房门也顾不上关,她仿佛快要窒息了。”一次不小心看到了格里高尔,她也是“不仅退出去,而且是仿佛大吃一惊似地跳了回去,并且还呯的关上了门;陌生人还以为他是故意等在那儿要扑过去咬她呢。”[3]61格里高尔的变形一方面是无力承担社会角色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争取自己真实自我的生存权,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4]94,但这一行为显然是失败的,在葛蕾特看来,曾经关系密切的哥哥,这个时候全然是一个怪物了。葛蕾特对于格里高尔的变形行为是害怕和难以理解的,又何谈建立真正的关系。而等到确定格里高尔不能为她的职责分担一部分压力,反而加重了她的负担后,葛蕾特的态度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母亲因格里高尔而受到了惊吓,葛蕾特表现为“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葛蕾特明白那是从小到大悉心照顾她的兄长,但是面对不愿担负家庭责任的兄长,她唯一的态度就是厌恶和排斥。以至于到后来,父母对此还保持沉默的时候,葛蕾特首先提出了要把格里高尔送走的想法。“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3]78物欲泛滥的社会,葛蕾特不再是那个会给兄长写信报告家庭情况的贴心妹妹,而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审判者,对百无一用的格里高尔进行判决和清除。
葛蕾特的自我定位由一个家庭中的幼女变成了社会中的审判者,而且那个审判对象还是原本即将把她送入音乐学院的哥哥。这一变化是难以想象的,却也是有迹可循的。原本只需要衣来伸手的女孩,不得不干起了售货员的工作,并且还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学习速记和语法。对于一个原本只为音乐而苦恼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而究其根源,都来自于那个抛弃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所谓追求自我存在的哥哥格里高尔。所以如果想让自己的家庭摆脱困境,也只有排除那个毫无用处的“甲虫”。身处于那个压抑和排斥个人存在的社会,盲目地屈从于强权政治的葛蕾特,也就从一个绵软的妹妹转变为了刚硬的审判者。而事实上,在格里高尔死去后,葛蕾特一家的生活也的确重写了。
由软弱走向刚强,葛蕾特可以说是在进行着另一种自我构建,因为她的冷硬刚强只针对格里高尔,在父母的面前,她依旧是那个贴心温柔的女儿。格里高尔虽然变形了,但那是出自对自我存在的探寻,是对这个压抑的社会的反抗,妹妹葛蕾特显然不这么认同。故而,同样对待家人,葛蕾特面对父母时是温柔的,而面对同样爱她甚至是这个家里最爱她的哥哥,葛蕾特是冷酷的。这种矛盾的行为,其实一开始就存在的。
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格里高尔要为债务和生活忙到几近可怜仓皇的程度,但是身为格里高尔的家人,葛蕾特的表现是怎样的?哥哥只能去吃残羹冷炙,葛蕾特却能买点不太贵的东西,尤其是在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时候,葛蕾特不得不卖掉了她“每逢参加晚会和喜庆日子总要骄傲地戴上的那些首饰。”[3]71能为之感到骄傲的首饰,这说明葛蕾特平日里的生活还是奢侈的。她会不明白兄长格里高尔的辛苦吗?但是却能心安理得地去享受来自兄长的血汗钱。至于那个关于音乐学院的梦想,她与格里高尔反复交谈,虽说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梦想,但也并非不寄希望于爱她的哥哥。否则,如果真的毫无希望,并且真的为哥哥的辛劳考虑,她就不会去提这个问题。
在确定格里高尔死亡后,葛蕾特不像先前希望送走他时那样歇斯底里,反倒能开始冷静地观察对方的尸体,并发现他早已变得瘦弱不堪。这又是一次十分矛盾的行为,这说明葛蕾特并非不能接受甲虫,只是当格里高尔还在活着追求自我的时候,她是不能接受的,但当格里高尔追求的行为迎来终结,那么葛蕾特便又能以理性的目光来看待这个曾经爱她的哥哥,并且为之感到同情和怜悯。
葛蕾特的温和与强硬,照顾格里高尔的心甘情愿和焦躁不安,对兄长的敬爱与对他的怨恨,都是相互矛盾的。但这种种的矛盾,却又是相互调节,能在葛蕾特身上一一体现的。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只感受到了妹妹的温柔和贴心,而变形后的他,则更能理解个人存在的复杂矛盾性,更能“超于常人地洞察到生活存在的本身的可怕性”[1]304了。
3 父亲自我存在的变异
“卡夫卡的‘存在’概念来源于纠缠了他一生的父亲情节,来自于他对充满悖谬性的父子关系的体验。”[1]287众所周知,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从小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时刻想要反抗,但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父亲。《变形记》展现的便是具有卡夫卡特色的“父与子”:变异的父亲和惧父的儿子。
“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格里高尔承担的是长子的责任,而他的父亲,更应该承担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每个人自出生便离不开父亲,他的成长、意识的构建,都离不开父亲的指导。但是《变形记》中的父子关系是不正常的,格里高尔父亲的身份更是变异的。从种种的细节中可以看出,格里高尔的父亲,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父亲”。正如格里高尔变形的那个早上,他的父亲来叩门,声音很轻,但用的是拳头。将拳头朝向还没有见面的儿子,这并不是一个父亲该有的行为。而在看到格里高尔选择变形逃避了责任后,他的父亲更是直接站在了一个排斥者、压迫者的地位,“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3]52像野人一样的“父亲”自然不再是父亲,而只是一个敌对者,一个该去反抗的敌对者。但格里高尔眷恋着父亲也惧怕着父亲,他有足够的勇气用变形来反抗社会,却没有那个勇气反抗同样压迫着他的父亲,最终被他赶回了房间。
“父亲”的身份在格里高尔的父亲身上是缺失的,他不仅不为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追求自我的空间,反而是时刻“把脚顿得更响”以阻止格里高尔的反抗行为。身为家庭实际意义上的领导者,格里高尔的父亲并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反抗社会,亦即,反抗他这个父亲的权威。格里高尔是老板和上司手下的劳动工具,在他的父亲看来,则是挣钱的劳动工具。在父亲眼中,格里高尔首先是挣钱的工具,接下来才是儿子,而一旦儿子丧失了他的第一身份,第二身份也在同时被剥夺了。
“人的意义不是先在自明的,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意义上的人,只有在存在中才能体现出他的主体性和确定性。而现代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自主性的存在,才能算是活着,此外都只是行尸走肉。”[5]97格里高尔的父亲便是活生生的行尸走肉。在儿子的记忆中,“每逢格里高尔动身出差,他父亲总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格里高尔回来过夜总看见他穿着睡衣靠在一张长椅子上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把手举一举就算是欢迎……”用“行尸走肉”形容格里高尔的父亲是再适合不过的,他的儿子吃着糟糕透顶的食物,他却能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解决他极为丰盛的、摆满了一桌子的早餐。这不正是格里高尔极为羡慕但也极为痛恨的那些推销员的生活吗?用儿子的血汗钱来保证自己奢侈的生活,不顾儿子来回奔波辛苦不已,而只是将他当做一个“过夜”的客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样的父亲并不是我们所普遍认同的父亲角色,而只是个高高在上的暴君罢了。
“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父权制社会形态,本质上就是父子关系结构的拓展、延伸和放大。每个人生来就离不开父亲,需要依赖父亲的扶持,这是一种自发的存在;长大后的儿子必然要叛逆父亲的权威,需要脱离并超越父亲以求自身的发展,这是一种自觉的存在。”[1]289格里高尔的变形,一方面说明他“内心已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父亲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权威的难以撼动。”[1]289一如父亲的奢侈与格里高尔艰苦的对比,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父亲拿出了格里高尔每个月给的家用,且已经成了一笔小数目。这笔款子本来可以还给老板,让格里高尔少替对方卖命几天,但是他的父亲却把这笔钱存了下来。格里高尔的父亲将这笔钱存下的用意为何,我们并不清楚,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格里高尔的辛劳在父亲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多卖命几天是无所谓的,甚至连格里高尔也认为这是更为妥当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权威在格里高尔心目中难以撼动,即使它再不合理,都是难以动摇的。
对于格里高尔,他的父亲一直都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在格里高尔想要和家庭重新构建起交流的桥梁的时候,又或者格里高尔想要回到人类圈子的时候,他的父亲都没有接受他,更甚至一个苹果砸过去,让格里高尔认识到回归人类社会的无望。而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同社会的同类人时,格里高尔的父亲仍旧是一个变异的角色。他是家中的主心骨,权力的行使不容他人反抗,妻子女儿都要围着他团团转。但是在同时,他依旧是那个需要别人去服侍的长辈。比如妻子和女儿劝他去休息,他要摇头摇上一刻钟,等到她们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来劝他,他依旧不肯答应,直到那两个孱弱的女人搀扶着他站起来,他依旧不肯主动去休息,要她们搀着他一直走到门口,这才挥挥手让她们离开,自己回去休息,但结果呢?妻子还是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女儿也追了上来再搀了他一把。
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主心骨,要让妻子女儿如此耗费心力去扶持的人,难以成为一个好的家庭支柱。但格里高尔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扭曲的存在,他不仅紧握着家庭的主导地位,还要让疲惫不堪的妻子和女儿像从前那样,或者说要比从前更加尽心尽力地服侍他,这才能宽慰他失去了格里高尔这一经济来源的痛苦。格里高尔的父亲是物质社会下变异的产物,他享受权力但不履行义务;他身为父亲,并不教养他的子女而是掠夺子女;他身为丈夫,并不照顾妻子而是让妻子反过来照顾他。他处在家庭中绝对的领导地位,却浪费资源且又无所作为。格里高尔父亲身份的变异,加剧了格里高尔被社会与家庭的排斥。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变形与异化、罪罚与救赎,无论哪一个,都与存在主义息息相关。格里高尔是变形的典型,他的变形是对自我存在的追求,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抗。但也正是自我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内心的责任意识与自由的矛盾,让他的自我存在变得尤为困难,最后更是被人类社会排斥,不得不以死来寻得解脱。而格里高尔的父亲与妹妹,他们的自我存在同样是异化的,是不正常的,是社会生活下的一种变异。《变形记》中人物的自我存在,无不是身处在一种认识的困境之中。
[1]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2]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孙坤荣.卡夫卡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李军.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谢春平,黄莉,叔文.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6]叶廷芳.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让-保尔·萨特.自我的超越性:一种现象学描述初探[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高瑞刚.“他是人类的替罪羊”:论卡夫卡创作中的受难性[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9]吴晓玲.卡夫卡悖论式人格透视[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10]乐晓峰.论《变形记》中的生存意识:中学语文中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教学[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11]韩晓亚.论卡夫卡创作中的悖谬艺术[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