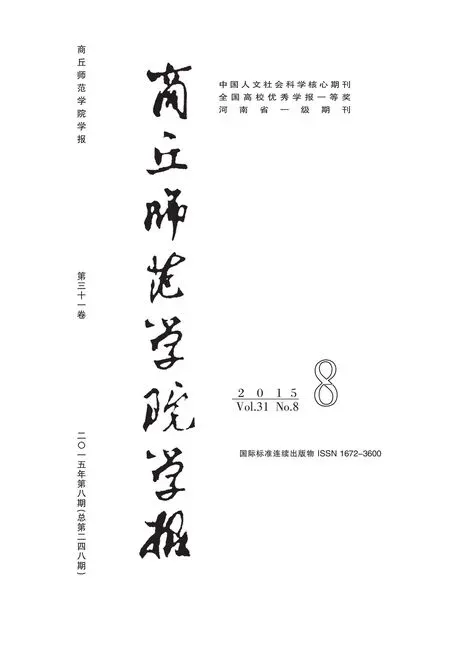正言若反·捐迹返本·章句歧解
——郭象解庄方法补苴
李 智 福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正言若反·捐迹返本·章句歧解
——郭象解庄方法补苴
李 智 福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郭象解庄的方法自汤用彤持“寄言出意”以来,学者不断补充,日益精微。在“寄言出意”这一大的范式之下,郭象的具体作法是非常复杂和精致的,正言若反、捐迹反本、章句歧解三条也是郭象解庄的具体方法。由于这三种方法的使用,他不仅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使得他的诠释与经典之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一致和圆融,自然与名教也由分裂走向合一。
庄子;郭象;《庄子注》;方法
郭象《庄子注》被奉为经典诠释中逆向创构[1]137的典范,对其诠释方法的检讨一直是学术界常议常新的话题。应该说,古人对郭象与庄子之间的顺逆关系已经有不少评骘,最经典的莫过于宋代普觉禅师“曾见郭象注庄子,却是庄子注郭象”一语。然而,对郭象解庄方法论的自觉检讨,首发其轫者当是汤用彤。汤用彤执“寄言出意”[2]第4卷,32,92为郭象解庄的基本方法,几成定谳。之后的学者承此根荄,继其余绪,不断检讨郭象解庄的新方法,又相继提出“辩名析理”(汤一介)、“忘言存意”(简光明)、“以意逆志”(韩国良)、“相因法”(康中乾) 等新论点,以至于刘笑敢更提出“跨文本性诠释”、“融贯性诠释”[1]199等新说,可谓是日益精深。本文将在继承前修和时彦研究的基础上,对郭象解庄的方法进行进一步检讨,补苴几个相对被忽略的论点,即正言若反、捐迹返本、章句歧解等三种解经方法。
一、“寄言出意”相关问题辨正
对郭象解庄方法的自觉探讨始于汤用彤。1940年,汤用彤以《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一文发表于《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第7卷,677。在这篇检讨郭象玄学的文章中,“寄言出意”一词作为郭象解庄的方法第一次①被提出来:
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方法之解答为何?寄言显意之义是也。[2]第4卷,92
《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至若书中毁圣贤之处,子玄力言均当善会其意,而不必滞于文。故曰:“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山木注——一身谓庄子》)案寄言之说郭注用以解书中不经处甚少,而用以解绝圣弃智处则其例甚多。[2]第4卷,93
约略同时或稍后,汤用彤完成《言意之辩》一文(该文具体写作年代待考,汤一介《汤用彤年谱简编》未录此文),重申其说:
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均不能不于此项困难之处,设法解决,其法为何,仍为寄言出意是也。(《言意之辩》)[2]第4卷,32
“寄言出意”又称为“寄言显意”,应该说这是发轫于先秦诸子、兴盛于魏晋名士的“言意之辩”在经典诠释学中的一次成功落实。《庄子》中的“言意之辩”本不是诠释方法的问题,其核心是为了化解“道不可言”与“道赖言明”的悖论,道体超言绝相,难落言筌,“道未始有封而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庄子看来,一切语言都是有限的,而道是无限的,无限的道体是不能用有限的语言来规训的。所以,在终极的意义上来说,必须忘言才能得道,庄子云: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显然,庄子的“言意之辩”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里毫不涉及诠释学与方法论问题。汉末魏晋以来,随着以“月旦评”为标志的人物品评兴起,“言意之辩”由存在论转而为审美论,再由审美论转而为哲学诠释的方法论。王弼的《老子注》开其端,郭象的《庄子注》殿其后。同时,庄子文章本身仪态万方,深宏恣肆,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天下》篇论庄子的文章风格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寓言》篇提到庄子的言说方式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刘熙载云:“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这种文章风格为后代的诠释者提供了能尽最大程度充分行其解释权利的机会。郭象认为,“庄子可谓知本矣,而未始藏其狂言”(《庄子注序》)。所以,他以“寄言出意”的方式解庄,在庄子的“狂言”之中构建起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因此,汤用彤以“寄言出意”为郭象解庄的“不二法门”,可谓是肯綮之论。当然,有的学者对汤用彤之说提出质疑,认为郭象解庄的方法与庄子本身的言说方式不应混为一谈,刘笑敢指出:
论者多谓郭象的注释方法、或诠释方法、或哲学方法是“寄言出意”,“辩名析理”等。此说或有不惬之处。“寄言出意”本来是郭象对《庄子》原文风格的一种定义或描述,是为了弥缝自己的“注释”与《庄子》原文明显不合的一种托辞。与其说“寄言出意”是郭象的方法,不如说是郭象自觉本人思想与庄子原文不一致时的托辞或辩解之方。[4]199
继刘笑敢之后,台湾学者简光明对汤用彤“寄言出意”说进行了进一步检讨,他指出:
若我们进一步思考有何不惬之处,就会发现:(一)若郭象以“寄言出意”为注解方式,亦即郭象藉由《庄子》之“言”来表达自己之“意”,然而“言”如果是《庄子》的文本,那么“寄言”的人是庄子,“出意”当然就是庄子的“意”,怎么会是郭象的“意”?(二)庄子以寓言为表意方式,可以说是“寄言出意”,郭象注解《庄子》时,直接说明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另外使用寓言来解释庄子的寓言,怎么可以说郭象是“寄言出意”?(三)魏晋时期注家虽然藉由注解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注文中,还是会表明那是作者的原意,郭象怎么可能公开表示他用“寄言出意”作为注解方法?由此可见,学者们所广泛接受的术语,未必就没有问题。[4]
简光明与刘笑敢一样,认为“寄言出意”是郭象看待庄子哲学的话语方式,“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山木注》),而非郭象本人的方法。简光明在此基础上提出郭象的解经方式是“忘言而存意”、“得意忘言”[4]268。这里,刘、简两位都严格厘定并区分了“庄子的表意方式”和“郭象注解《庄子》的方法”,无疑都极具说服力,也厘清了一些不必要的混淆。但这种严格区分亦不无商榷之处,其一,在《庄子注》中郭象认为,庄子在“寄言出意”,而这个“寄言出意”之“意”从根本上已经是郭象之“意”而非庄子之“意”。《庄子·天地注》谓:“庄子之言不可以一涂诘……故当遗其所寄而录其绝圣弃知意。”这里表面上是庄子所“寄”,实则是郭象所“寄”。其二,即使“寄言出意”本身是庄子的表意方式,但这无碍其作为一般的经典解释方式被使用。当这个词在魏晋时期被大量使用时,其题中之义已经超越了庄子,而成为一般的解经方式。汤用彤对此有全面而深刻的辨析[2]22。其三,正是庄子本身以所谓寓言、重言、卮言等三言的方式来“寄言出意”,才使得郭象的“寄言出意”成为可能。这样,郭象通过解庄来创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就不仅能得到庄子经典文献的证明,而且能得到庄子方法论的证明,从而使得他的创构极为圆融。其四,简光明所提的“忘言存意”、“得意忘言”与“寄言出意”只有名相之殊,而无必然之别。事实上,庄子不仅要“寄言出意”,而且也要“忘言存意”,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都是在隐喻“得意忘言”。如果认为“寄言出意”容易混淆庄子与郭象的区别,那么“忘言存意”、“得意忘言”等提法亦面临此危险。可见,汤用彤以“寄言出意”作为郭象解庄之方法,刘、简两位的非难并不能证成。
汤一介在汤用彤“寄言出意”的基础上又提出“辩名析理”、“否定的方法”两条[5]197-221。“辩名析理”是魏晋“名理之学”在经典诠释中的引用,“辩名析理”即通过对经典术语的重新诠释和辨正,在形式上既能和经典圆融,在内涵上又能表达出诠释者所追求的意义,强调的是诠释者对原著的名相诠释和逻辑重构。“否定肯定”是通过老庄道家特殊的思辨方式将经典中“有无之辩”落实为一种诠释方法,比如“无为而无所不为”、“相为于无相为”,这些老庄命题本身暗含着巨大的诠释空间。郭象巧妙地将名教的“有为”和自然“无为”结合起来,证成自己名教本于自然、自然不废名教的“内圣外王”之道。汤一介这两点无疑是对汤用彤“寄言出意”说之具体的补充。
另外,有论者将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与郭象的“寄言出意”说进行了比较[6] 334,两种方法有顺有逆,这种比较使得郭象的诠释有了更加丰富和深厚的理论背景,无疑极具启发性。总的来说,汤用彤“寄言出意”说的概括性极强,后人的不断补充实则都是对此方法具体的落实的研究,从某种意义可谓是纲与目的关系。本文将在前修和时彦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汤用彤之说再作几点具体而微的补苴。
二、补苴之一:正言若反
“正言若反”本出自《老子》第78章。释德清云:“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为反尔。”高延第认为,这句话“并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张岱年云:“若反之言,乃为正言。”[7]338可见,老子哲学言说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是“正言若反”。正言若反,即以否定的方式表达正面的意思,如大成若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都是这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为庄子所继承。《逍遥游》论接舆之言:“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齐物论》中瞿鹊子评论长梧子:“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这里所谓“不近人情”、“孟浪之言”,实在都是庄子的夫子自道。《天下》篇更清楚地评骘了庄子的言说方式: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庄子哲学的话语方式即是这些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也就是前文所引的“孟浪之言”,姑且称之为“谐语”。庄子之所以以此方式言说,乃是他意识到“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没有“庄语”,并不代表着他没有“庄意”,庄子以“谐语”代替“庄语”实则就是老子所说的“正言若反”。章太炎论庄子云:“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齐物论释序》)也正是这个意思。庄子继承老子之“正言若反”的话语方式,使得后来的解释者往往有“穷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林经德《庄子口意后序》)之感,但同时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8]188,有利于解释者更充分地发挥解释的权利。
日本镰仓时代高山寺所藏《庄子》残抄本,这是郭象《庄子注》的早期流传本,书后有段跋语,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郭象《庄子注后序》: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攻异端为贵也。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9]5
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有类似之语,似本此文而来。这里,郭象强调,庄子的话语方式之一是“正言若反”,即承认《庄子》中有很多话语看似是“反言”,实则是“正言”。如果执定其“反”而不明其“正”,就容易造成庄生弘旨不畅,奥义不明。郭象之所以删掉《阏亦》《意修》等庄子后学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庄学后学不解庄子“正言若反”之旨,就反论反,以致辞气鄙卑,妄窜奇说。庄子“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最终转化为郭象解庄的方式。郭象在解庄过程中,暗用“正言若反”的庄子话语逻辑,将庄子中合己意之言视之为“正言”,不合己意者视之为“反言”,这些“反言”实则都有“正意”,因此他对其中的“反言”作“正义”的诠释,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经典与诠释之间的扞格,修正了《庄子》原典中不合“名教”的“自然”之言,以使得“自然”合乎“名教”,证成“名教”即是“自然”。兹举例以证之。
《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章,重点在于许由视天下若敝履,言功名不过是身外之物,郭象却注云: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待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10](《逍遥游注》,本文只注篇名)
庄子原意是许由在“当涂”与“山林”之间选择山林而放弃当涂,郭象却无视庄子本旨之所在,在这段文字中演绎出一段“无为而治”的高论。唐人成玄英也意识到郭注与《庄子》原典之间的张力,云“(庄子)贬尧而推许由,寻郭注乃劣许而优尧”,并为之辩解云:“欲明放勋大圣,仲武大贤。贤圣而二涂,相去远矣。”(《逍遥游注疏》)这里,庄子重山林而轻天下、褒许由而贬帝尧,郭象却以“正言若反”的方式诠释为重天下而轻山林、褒帝尧而贬许由,完全走到了庄子的反面。
《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章,郭象注云: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者之不亏哉!(《逍遥游注》)
很明显,郭象把庄子看来是遗世独立、不落尘俗的世外高士看成是庙堂中“戴黄屋,佩玉玺”的朝廷达官显贵,最终得出“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大宗师注》),这就是郭象所谓的“游外弘内”之旨。
《大宗师》篇“彼游方之外者,而丘游方之内者”章,郭象注云: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冥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大宗师注》)
在《庄子》书中,孔子是“方内之士”,子桑户是“方外之士”,庄子看来是“内外不相及”,二者势如冰炭,高下之分甚显。而郭象却认为,庄子是“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庄子认为内外不相及,郭象认为内外可以相冥;庄子推重子桑户,郭象推重孔子;庄子重“游方之外”,郭象重“游方之内”,庄子的“高世之志”转变为郭象的“涉俗盖世之谈”,这实则都是郭象妙用“正言若反”解庄的效果。
《秋水》篇“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章,郭象注云: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秋水注》)
这里,庄子严格区分天人,牛马四足是牛马之天性,牛马被人乘骑是人为,庄子申天性而黜人为之意甚明。郭象却无视庄子此意,认为牛马天生即是用来被人骑乘的,人天生就需要乘马骑牛,这样,庄子看来是人为,郭象则解释为天性;庄子看来是天性,郭象则认为未必是。郭象用“正言若反”的方式得出“人事本乎天”的结论。
郭象以“正言若反”之方式解庄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列举。牟宗三曾论老子云:“‘正言若反’之方式,亦即‘辩证诡辞’方式。惟藉此诡辞之方式以保存圣智仁义,是一种作用之保存,并非自实体上肯定之。”[11]140但庄子之学至少在形式上要比老子彻底得多,庄子不仅在道的层面(本体层面)剥落圣智仁义,在用的层面似乎也没有给圣智仁义保留过多的位置。司马迁论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虽然贬意甚显,却也不期然地指出了庄学的特色。要之,庄学本身要解决的不是圣智仁义的问题,它也不是要解决“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它要解决的是人的自由问题。然而,郭象以“正言若反”的方式解庄,作为诠释来说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既然“正言若反”是庄子自我哲学言说的方式,其以“正言若反”的方式来解庄就有了来自庄子本身方法论的证明,而这个证据是诠释得以成功的基石之一。换言之,郭象解庄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有来自庄子的文献证明,更有其来自庄子方法论的证明。既然庄子承认自己是“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那么郭象以“正言若反”解之便是理所当然。
三、补苴之二:捐迹返本
“迹”之意,《说文》曰:“步处也,从辵亦声。”本意当是脚印、足迹。《庄子》有“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胠箧》)之语,后引申为遗迹、痕迹、形式、形象等可见之物。在庄子哲学中,“迹”有两义:其一,用来表示感官可把握的形相,庄子将形相称之为迹,道体是超言绝相的,“其来无迹,其往无崖”(《知北游》),所以一切有形迹可循者都不是“道”;要把握道就要断绝思虑,破除名相,只有“行而无迹,事而无传”者(《天地》),才是真正的“道”,只有“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其二,在庄子哲学中,“迹”除了表示形相之外,还用来隐喻语言、文字、经书等名相。庄子云:“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道体无迹,故不落言筌;至理不能言说,因此六经不过是先王之陈迹。迹因履出,而迹绝非履,所以,庄子要求遗弃其“迹”而追慕其“所以迹”。这种“迹”与“所以迹”的关系,实则是庄子言意之辩、道言之辩的另一种表达。庄子云: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天道》)
“书不过语,语有贵也”,在庄子看来,书不过是名相,而名相不能表意,所以经书不过是先王之陈迹。因此,庄子借轮扁之口云:“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道不是形器,理难落名相。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中云:“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定而咸适”,此一语秉本执要地直发庄学之玄旨。这也意味着,庄子最终是要摒弃“迹”而归本于“所以迹”,这个“所以迹”就是“道”。庄子哲学的这种话语方式又不期然地成为郭象解庄的方式之一。郭象大抵认为,《庄子》中一切剽剥儒墨、剖击仁义的言辞都是“迹”,人们不应该执著于“迹”而当知其“所以迹”,这个与“迹”相反的“所以迹”乃是庄子之“本”,所以读庄应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逍遥游注》),也就意味着郭象解庄的方法就要摒除其“迹”而明其“所以迹”,郭象称之为“捐迹反一”(《在宥注》),或者叫“返一以息迹”(《缮性》)。“迹”与“所以迹”(道)的辨正是郭象解庄的重要方法,笔者将这种诠释方法称之为“捐迹返本”②。(成玄英云:“一,本;二,迹。”见《南华真经注疏·逍遥游第一》)兹举数例以证之。
《逍遥游》篇“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章,郭象注云:
然遗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虽宗尧,而尧未尝有天下也,故窅然丧之,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四子者,盖寄言以明尧之不一于尧耳。夫尧实冥矣,其迹则尧也。自迹观冥,内外异域,未足怪也。世徒见尧之为尧,岂识其冥哉!(《逍遥游注》)
在庄子看来,尧受到汾阳四皓之感化,捐弃天下,结穴于《逍遥游》的“三无之境”。然而,如果诚如庄子所论,尧捐弃天下,就会导致因无人可治而天下大乱,这与郭象所崇尚的“内圣外王”之道迥然不同。因此,郭象认为,尧丧天下不是真正的抛弃天下,而是当其“游心于绝冥之境”时,其人依然“寄坐于万物之上”。郭象云:“尧实冥矣,其迹则尧”,这样,郭象通过“捐迹反本”的方式改造了庄子哲学,庄子哲学以“丧天下”为标志的对功名的抛弃转变为郭象的“游外冥内”之学。
《大宗师》篇颜回“忘仁义”章,郭象注云:
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物之功。爱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存夫仁义,不足以知爱,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大宗师注》)
庄子认为,颜回“忘仁义”是摆脱价值的束缚而实现了自由的第一步,但郭象看来颜回忘的是仁义之迹,而存夫仁义之本。最高的仁义是无心之爱,庄子对“仁义”等价值异化的批判,被郭象诠释为最高价值的仁义。
《应帝王》篇“有虞氏不及泰氏”章,郭象注云:
夫有虞氏之与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无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尝名,何胜负之有耶!然无迹者,乘群变,履万世,世有夷险,故迹有不及也。(《应帝王注》)
庄子原文云“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是帝舜,泰氏是太昊,即伏羲氏。虞舜是仁义之君的典范,帝尧时期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而太昊时代尚是原始淳朴的氏族社会,人们还近乎蒙昧。庄子认为,浑朴未分的“太昊”时代是比帝尧时代要理想的社会,因此云:“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郭象却认为“虞氏之与泰氏,皆世事之迹”,他以否定“迹”的方式否定了庄子对文明的批判精神,也否定了庄子心目中最完美的社会理想。郭象所崇尚的是“所以迹”与“无迹”的辩证统一,最终落实为“乘群变,履万世”的名教诉求。
《骈拇》篇,“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章,郭象注云:
兼爱之迹可尚,则天下之目乱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忧之,此为陷人于难而后拯之也。然今世正谓此为仁也。夫贵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无可尚之迹,则人安其分,将量力受任,岂有决己效彼以饕窃非望哉?(《骈拇注》)
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之本性所有,最终成为“不仁之人”谋取财富的手段。郭象则认为,“兼爱之迹”虽不可尚,但“无可尚之迹”的仁义却是应该提倡的,捐弃兼爱之迹,返回仁爱之本,这样,郭象由庄子“意仁义其非人情”之说得出“仁义自是人之情性”这一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宥》篇“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章,郭象注云: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祸。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复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谓无愧而不知耻之甚也。(《在宥注》)
庄子着眼于道德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异化,其目的是启发人对自由的觉悟。郭象则认为庄子批判的是腐儒之“迹”,并没有批判仁义的“所以迹”,这样,郭象同样以“捐迹反本”的方式不仅化解了诠释与经典之间的张力,而且最终保留了自己哲学的价值诉求。
要而言之,“捐迹返本”是郭象“寄言出意”的重要方式之一。郭象《山木注》云:“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将寄言以遗迹,故因陈蔡以托意。”郭象把庄子笔下一切不合“名教”的内容视为“昭昭之迹”,他认为庄子在批驳“迹”的同时而保留“冥冥”中的“所以迹”,“迹”是名相,“所以迹”才是本道,这样,郭象以“反一息迹”、“捐迹返本”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并改铸了庄子。“捐迹返本”意味着“迹”与“所以迹”的冥合与圆融,既避免了诠释与经典之间的扞格,又使得自己所弘扬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哲学体系得以创构。与前文所言“正言若反”一样,“迹”与“所以迹”也是庄学固有的哲学范畴。郭象自觉地选择这两个范畴来诠释庄子,这意味着自己的诠释同样来自庄子学的支持,因此说服力极强。郭象之注可谓是迹本圆融,息迹反一。其在《庄子序》中云:“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其以方枘圆凿的方式重构庄学,却近乎以假乱真,不露丝毫斧痕。
四、补苴之三:章句歧解
周秦子学一变而为两汉经学,以“离经辨志”为基础的章句之学本是两汉经学的基本范式,由于学术内容的复杂性,章句之学最终超越经学而变成一般的学术范式,使得“离章辨句,委曲枝派”(《后汉书·桓谭列传注》)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方式的主流。吕思勉《章句论》谓:“顾考诸古书,则古人所谓章句,似即后世之传注。”[12]5以此视郭象的《庄子注》,虽无章句之称,却有章句之实。郭象的《庄子注》以“离章辨句”的形式诠释庄子,有不重名物训诂而重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传统。这表现在郭象的《庄子注》中,乃有大量近乎歧解庄子的臆解。郭象在《逍遥游注》中明言解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实在是为自己歧解庄子寻找借口。因此,他在解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无视《庄子》原著句读、章句、字词的常识性规定,其《庄子注》随处即有文不案古、曲与生说、随意句读的解释。
当然,笔者所谓“歧解”,是指不合学术常规的解释,未必是误解,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曲解。当笔者说郭象“歧解”庄子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先人已经作古,因此何者是正解,何者是歧解,我们并无必然把握。然而,古人既然把文献留下来,一些常识性的语法、字词、句读还是可以基本判定的。在尽量尊重学术常识的情况下,检讨郭象的《庄子注》在哪些地方“歧解”庄子,这些“歧解”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歧解”是如何避免与经典之间之矛盾的,郭象是有意识地曲解还是无意识地误读,这些问题无疑都与郭象解庄的方法有关。下面将以一些例证对这些问题进行检讨。
《齐物论》:“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郭象注云:
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万物虽异,至于生不由知,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齐物论注》)
《释文》:“芒,芒昧也。”郭象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芒”字,本身并不错。然而,郭象却话锋一转,将“芒”的对象解释为“生”,“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人芒于生即人不知自我何所生,不知何所生就是自生。庄子原文所谓“芒”,本意是世俗之人昧于大道,不谙化理,“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心随境转,与物周旋,“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庄子本意甚明。郭象却无视庄子上下文情景,将庄子对世俗的忧患之言转而为宇宙生成论哲学,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歧解。郭象这种歧解最终论证出庄学本身即含自生论,从而为自己的宇宙论张本。
《应帝王》篇:“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郭象注云:
任人之自为。莽眇,群碎之谓耳。乘群碎,驰万物,故能出处常通,而无狭滞之地。言皆放之自得之场,则不治而自治也。(《应帝王注》)
《庄子》原文“与造物者为人”,本意是指人与造化为一体的境界,如《大宗师》篇“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天运》篇“丘不与化为人”都是此意。“与……为人”是一种固定的语法形式,主要是形容人的一种精神品质,郭象却将“为人”解之为“任人之自为”;庄子的“与造物者为人”是个人与造物者浃和的人生境界,而郭象却诠释为“任人之自为”的黄老之术。“莽眇之鸟”之“莽眇”,近乎今所言渺茫,庄子本意是在描写超越世俗的精神无限之游,而郭象却将“莽眇”训为“群碎”,“群碎”即世间群生万物,从而将庄子的超越无限之游诠释为世间在世自由。这里,郭象对“为人”和“莽眇”的诠释是明显不合常识的理解,其以歧解庄子的方式将庄子逍遥的绝对性消解掉,从而为自己的哲学立场提供支撑。
《天地》篇“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郭象注云:“夫用时之所用者,乃纯备也。斯人欲修纯备,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这里,庄子本是借汉阴丈人表达对文明智巧和机械主义进行批判,“纯白”本意是纯洁素朴之心境,与“机心”相对。郭象却将“纯白之备”化约为“纯备”,将“纯”训为“全”,“纯备”之意就是“用时之所用”。这样,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汉阴丈人在郭象这里便成为不能与时偕行、保守没落的愚人。之后,庄子借孔子之口云“彼假修混沌氏之术者”,郭象注云:“以其背今向古,羞为世事,故知其非真浑沌也。徒识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时任物之易也。”(《天地注》)庄子所谓“假修”之“假”,当训为“借”,为凭借之意,而郭象却训“假”为真假之“假”。如此训诂,孔子和颜回感叹“何足以识之”的“混沌氏之术”便被郭象彻底否定掉。这两则诠释无疑都是非常明显的歧解。
郭象以“章句歧解”的方式改造庄学的地方甚多,还比如《德充符》篇,庄惠辩“有情无情”,庄子云:“是非吾所谓情也”,此中“是”是代词,承前指代惠子之语,而郭象却以“是非”连读;“以是非为情”,庄子本是对是非之情进行否定,郭象却认为庄子是是非之情的肯定者,反差迥然。《天道》篇庄子云“退仁义,宾礼乐”,此处之“宾”为“摈”之借,是摈除之意,郭象却以本训解之,将“宾礼乐”解释为“以性情为主”,言外之意是以“礼乐为宾”,庄子要废除礼乐,而郭象则是要退而求其次;又《骈拇》篇庄子云“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庄子以反问表否定之意甚明,郭象却将这个反问句看成是一个肯定性的感叹句,得出“仁义自是人之情性”,这是与庄子截然相反的结论;接着,庄子感慨“彼仁人何其多忧也”,郭象解之为“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这可谓是典型的“加字解经”,庄子认为仁义非人之本性,郭象看来仁义就是人之本性,结果只能是去庄益远。郭象以“章句歧解”的方式误读庄子最严重的地方当是《人间世注》中对“楚狂悲歌”的误解。
《人间世》篇接舆狂歌:“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郄曲,无伤吾足。”郭象注云:
当顺时直前,尽乎会通之宜耳。世之盛衰,蔑然不足觉,故曰何如。趣当尽临时之宜耳。付之自尔,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岂为治乱易节哉!治者自求成,故遗成而不败;乱者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不瞻前顾后,而尽当今之会,冥然与时世为一,而后妙当可全,刑名可免……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谓全耳,非假物也,岂有寄鸿毛之重哉!率性而动,动不过分,天下之至易者也;举其自举,载其自载,天下之至轻者也。然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故乃释此无为之至易而行彼有为之至难,弃夫自举之至轻而取夫载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举其性内,则虽负万钧而不觉其重也;外物寄之,虽重不盈锱铢,有不胜任者矣。为内,福也,故福至轻;为外,祸也,故祸至重。祸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夫画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临物,与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临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弥贯万物而玄同彼我,泯然与天下为一而内外同福也。迷阳,犹亡阳也。亡阳任独,不荡于外,则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则凡称吾者莫不皆全也。曲成其行,自足矣。(《人间世注》)
庄子借接舆之口唱出对诸侯浇竞、天下无道的绝望悲歌,在郭象这里却变成超然生死、明哲保身、游外弘内、无为而治的处世说教。窃以为,这段注解是郭象歧解庄学最严重的部分,几乎句句都与庄子唱反调,庄学深刻的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和虚无主义哲学被他进行了彻底的消解,郭象“最终选择了与现实利益适应的一面,并用‘自然’把他包装了起来”[8]110。《晋书·郭象传》谓:“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郭象任职当权,熏灼内外,其自难体会庄子云“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吾行郄曲,无伤吾足”时的心境,所以其不惜矫厉庄学,粉饰太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元康之时,“竹林风流”已经堕落为“散发裸裎”的假风流,元康名士高蹈虚名,东施效颦,世风窳败,郭象以“名教”本合乎“自然”来改铸庄子,当是救世之弊,“他把庄学的逍遥和儒学的淑世结合起来”[13]220-221,应该说是把庄子的批判精神转化为一种“淑世之道”。
郭象对庄子进行“章句歧解”式的误读,在终极的意义上我们是无法判定他究竟是有意曲解还是无意误读,但若退而求其次言之,其有意歧解的成分显然要比无意歧解的成分大得多。然而,这种存心误读由于不能得到来自经典本身的反驳,所以这种误读被隐藏得天衣无缝,以致后世郭象《庄子注》的影响并不亚于《庄子》本身。向郭之义出,所谓“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至少在学术史上郭注与庄子本身保持了平分秋色的态势。
五、结 语
笔者在前贤和时彦研究的基础之上补苴三点郭象解庄的方法,严格来说,这三种方式甚至包括汤一介的研究都是在汤用彤“寄言出意”的大前提之下展开的,只是更细致地检讨郭象解庄的具体方式。正言若反、捐迹反本这两种方式本是庄子哲学的话语方式,郭象以此方法来解释庄子,无疑能得到庄子本身的支持,所以其说服力甚强。如果说诠释是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对话,那么这种对话可以是“以意逆志”、“心知其意”的同情了解,但也可以是“滥用”解释权利的“设对独构”。郭象用“章句歧解”的方式来解庄恰恰是抓住了经典诠释学中经典不能为自己辩解的弱点,尽最大能力发挥了自己诠释的权利。即使有不合文本原意的硬伤,但古人无法为自己辩解,学术同行的辩解按照《齐物论》的逻辑也终究是无效的。这样,他不仅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使得自己的诠释与经典之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一致和圆融。他在消解了庄学批判精神的同时,也将庄学高不可攀的逍遥落实为一种世俗的承诺,即逍遥非至人、神人、圣人之所独擅,亦为君臣皂隶、贩夫走卒之所有,逍遥无处不在,但要看此心安否。
注 释:
①简光明《当代学者以“寄言出意”为郭象注〈庄〉方法的检讨》(方勇编《诸子学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汤用彤先生首次提出“寄言出意”的文章是《言意之辩》,其说非是。考汤一介先生著《汤用彤年谱简编》,汤用彤先生1940年发表于《北大四十周年纪念册》的文章是《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而非《言意之辩》。汤先生后来发表的《言意之辩》中引注云“余已另有文论之(《北大四十周年纪念册》乙编上),兹不赘”,这篇文章当即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一文,可见《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在前,《言意之辩》在后。
②事实上,汤用彤先生将“圣人之迹之义”视为郭象解庄之“理论之解答”,这与“寄言出意”构成郭象解庄的两种方法,见《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一文。本文进而提出“捐迹返本”作为一种哲学诠释的方法。
[1]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汤用彤.汤用彤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简光明.当代学者以“寄言出意”为郭象注《庄》方法的检讨[C]//诸子学刊: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韩国良.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审美风尚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谢祥皓,李思乐.庄子序跋论评辑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南华真经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吕思勉.文字学四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3]李耀南.玄学与魏晋美学[D].武汉:武汉大学,2001.
【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5-03-25
李智福(1982—),男,河北井陉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与解释、道家与庄子学研究。
B223.5
A
1672-3600(2015)08-0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