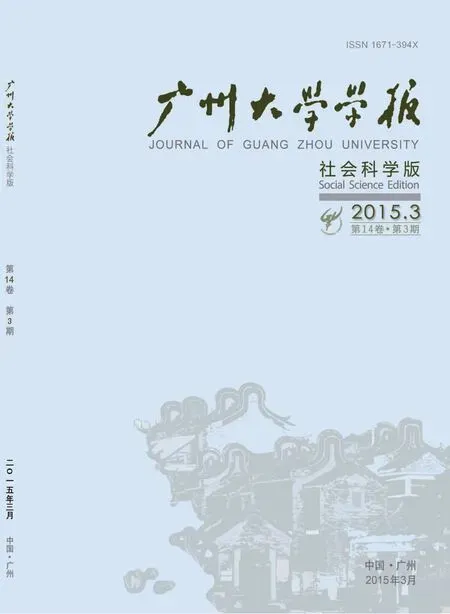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甘 宇
(重庆工商大学人事处,重庆 400067)
随着社会对教育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的提高,我国的教育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大体上遵循着“国家—社会—家庭”三方共同投入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差异化的扩大,强调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家庭的投入也不容忽视。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对教育成本分担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与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影响着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和范围。因此,剖析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教育投资的关系,对于优化家庭教育资源配置和国家教育相关政策安排大有裨益。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教育事业的产出的是以政府、社会以及家庭的投入为前提的,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教育投入的大幅度提高。2012年以前,我国对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长期为占GDP的4%以下,难以满足教育发展的要求。但正是近3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公共财政支出难以解释教育增长,正是家庭教育投资弥补了财政支出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以家庭负担更高的教育成本所换来的。[1]
在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诸多因素中,根据文献的研究方法不同,结论也不一致。根据对文献的归纳,父母的职业[2-3]和其受教育程度[4-5]、子女性别[6-7]、政府政策[8]以及价值观念[9]等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显然,在大部分文献分析的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各种因素中,收入变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Schultz发现,因为人对风险是厌恶的,同时市场存在着信贷约束,那么教育的收益率再高,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仍然难以获得提升。[6]倪永梅也通过分析认为,家庭经济条件是制约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10]但也有研究认为,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11]而龚继红和钟涨宝使用湖北随州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认为当家庭经济状况超过某一临界点(年人均收入3 000元)时,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才有明显提高;另外,他们还发现相对于中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更愿意为子女的教育进行高投资。[12]
“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充分反映了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生育数量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Becker及其合作者在效用最大化模型基础上,通过使用价格效应和质量效应进行假设: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子女作为家庭内部的产物,是一种正常的耐用消费品,其质量受父母的投入所制约,家庭对其购买的数量和质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质量增加的幅度比数量增加的幅度要大得多。因此他们认为,家庭收入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但这个增加的幅度很小,甚至是负的。[13-14]
在这一结论被提出之后,不同的学者进一步对控制变量进行修改和完善,或者使用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测算,获得类似的结果。Rosenzweig和Wolpin在修正Becker等人的理论的基础之上,使用了印度的数据获得了相同的结论。[15]而Hanushek等人则使用其他地区的数据和测算方法也证实了 Becker的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这一结论。[16]但是 Behrman 和 Taubman[17]、Qian 对 Becker的结论进行了质疑并相应地提出了与Becker不同的观点。[18-19]
Fan最早结合Becker的理论,使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孩子质量与数量的替代关系,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20]Rosenzweig 和 Zhang[21],Li、Zhang 和 Zhu[22]在我国存在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的大背景下,认为质量—数量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在中国确实存在着,而且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尤甚。但Qian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质量—数量的替代关系呈现的是倒U型特点,子女数量在两个以内增长时,其升学率会随之提高。但超过了两个,其升学率会下降。其认为之所以获得与其他研究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在其研究中并没有像其他研究一样将子女数量视为连续变量而非离散变量,降低了研究方法和结果错判的概率。
综合上述研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很多,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获得结论也各异。在参考其他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使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几个主要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分析。本研究将以901个家庭数据为样本,结合劳动经济学中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并对经典的“数量—质量替代”模型进行检验。
二、数据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CLDS)。CLDS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2012年CLDS是该项目的第一次调查。CLDS详细调查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的样本家庭成员个人信息、家庭财富、资产和教育等情况。“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家户是财产分配和继承单位。”[23]因此,使用该数据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城镇家庭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投资的差异问题。剔除掉农村家庭样本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使用的样本总量为901个城镇家庭。
(二)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1.主要解释变量
在本研究中,家庭年收入水平与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主要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支出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很大。而家庭收入水平是家庭经济条件的主要指标,收入越高的家庭,受到的经济约束越小,在进行教育投资时受到的限制越少。随着教育的收益率上升,家庭的教育投资将随之增加。在样本描述统计中,平均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年教育投资为0.343万元。根据“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子女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家庭对子女的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表1显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绝大部分样本城镇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为1个。

表1 变量定义及数据描述统计
2.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主要选取了家庭人力资本存量比、家庭劳动人口数量以及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等3个变量。家庭成员总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力资本存量比越高,其社会网络越广,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关系形成的个人资源”[24]使得其家庭收入来源比较稳定。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引进家庭劳动人口数量作为控制变量。一般认为,家庭劳动人口越多的家庭,其创造财富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越高。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从而对其投资持积极的态度。由表1可见,家庭主事者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处于高中水平。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数据进行估计。在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收入水平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回归方程为:

在上述方程中,Yi表示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Si表示家庭年收入水平,Wi表示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Xk
i,k=3…,N表示其他的控制变量,εi则表示随机扰动项。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考虑到模型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我们在进行回归时,对比了模型的稳健标准差和普通标准差,发现二者十分接近,由此获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根据表2中的回归结果得到回归方程:

表2显示,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对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存在显著影响,而且系数的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投资量越少。这与谷宏伟、杨秋平所得的结论相反,他们发现子女数量和家庭子女人均教育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我们的解释是,根据“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家庭在进行生育选择时,所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多,质量会出现下降,反之则质量会上升。在家庭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的弹性较小,这也就意味着,子女数量越多,每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教育投资量将会出现减少,也即是教育投资量被稀释了,因此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同时,在表2中我们也看到,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也对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家庭未成年子女获得的教育投资量越大。
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和其他控制变量并没有对家庭未成年子女年人均教育投资量产生显著影响。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样本选取中存在的不足所致。本研究中的样本为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由于国家已经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另外,高等教育投资部分未纳入本研究的范围。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家庭年收入水平和其他控制变量在解释家庭教育投资上没有产生显著差异影响。

表2 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
四、结 论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上升的家庭,对其子女人均教育投资水平将下降。也即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当然,这种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将来在样本更加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1] HANNUM E,BEHRMAN J.WANG M,LIU J.Education in the reform era[M]//BRANDT L,RAWSKI T G.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2] WYDICK B.The effect of micro enterprise lending on child schooling in Guatemal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
[3] 李红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消费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0(4):1-7.
[4] 孙彩虹.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差异分析[J].西部论坛,2003(1):37-40.
[5] 李旻,赵连阁,谭洪波.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承德市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6(5):73-78.
[6] SCHULTZ P.Investments in the schooling and health of woman and man:Quantities and returns[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3,28(4).
[7] 李通屏.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城乡差异分析[J].社会,2002(7):11-14.
[8] 张艳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6):54-58.
[9] 刘洁,陈宝峰.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中的价值观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7(6):27-36.
[10] 倪咏梅.论减轻贫困地区家庭义务教育费用负担[J].基础教育研究,2001(3):3-5.
[11] 孙志军.中国农村的教育成本、收益与家庭教育决策 :以甘肃省为基础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 龚继红,钟涨宝.农村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农村家庭的调查[J].统计与决策,2005(18):72-74.
[13] BECKER G,LEWIS G.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2).
[14] BECKER G,TOMES N.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4).
[15] ROSENZWEI G M ,WOLPIN K.Tes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fertility model: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J].Econometrica,1980,48(1).
[16] HANUSHEK E.The trade—off between child quantity and qua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1).
[17] BEHRMAN J,TAUBMAN P.Birth order,schooling,and earning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6,4(3).
[18] QIAN N.Quantity-quality: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school enrollment in China[R].Unpublished Manuscript,department of Economics,MIT,2005.
[19] QIAN N.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The only-child disadvantage in school enrollment in rural China[R].NBER Working Paper,No14973,2009.
[20] FAN S.Child lab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2004,71(1).
[21] ROSENZWEIG M,ZHANG J.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Twins,birthweight,and China’s‘One Child’Policy[R].IZA Discussion Papers,No2082,2006.
[22] LI H ,ZHANG J,ZHU Y.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of childre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Identification using Chinese twins[R].IZA Discussion Paper,No.3012,2007.
[23]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
[24] GUISOL,SAPIENZA,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526-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