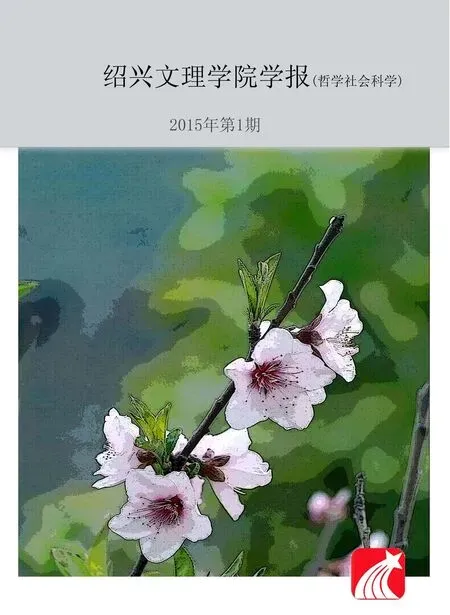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冯建荣
(绍兴市人民政府,浙江 绍兴312000)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冯建荣
(绍兴市人民政府,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佛教;越州;绍兴;传播;承祧;流变
佛教在绍兴的传播很早,从东汉末年至西晋,佛教在会稽(郡治在今绍兴)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献和考古发掘均印证了会稽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就已是不同凡响的了。到隋唐时期,佛教在绍兴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呈现了标志性的成果、地域性的特征和流变的新趋势。
一、隋唐五代时期越州佛教传播的盛况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越州(州治在今绍兴)佛教空前繁荣。经过东晋至南朝260余年的传播,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绍兴已是枝繁叶茂,五代作为吴越国的东府,越州成为中国佛教传播盛况空前的中心之一。其重要标志有三。
一是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僧和佛学著作。
这个时期越地佛教开宗立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宗派林立,著述成风的局面。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真正缔造者吉藏(549~623),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来越,先后在嘉祥寺住了12年,“嘉祥结肆,独檀浙东”。应召入京时,“禹穴成市,问道千余”[1]。他博学多才,法华、华严、般若诸学皆通,于三论尤精,一生讲述三论百余遍,著有《三论玄义》《三论略疏》等30余部,现存20余部,注引宏广,发明颇多,为三论宗带来了吉祥之光。他因此而成为唐初全国最高僧官“十大德”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嘉祥大师”。其弟子智凯(?~646)在嘉祥寺继讲三论时,“四方义学八百余人,上下僚庶,依时翔集”[2]。另有一系代表法敏(579~645),开讲时,“众集义学三门七十余州八百余人,当境僧千二百人,尼众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复记,时为法庆之嘉会也。”[3]三论宗由此而又称“嘉祥宗”,嘉祥寺由此而堪称三论宗的祖庭,越州也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三论宗的传播中心。唐武宗灭佛时,祖庭嘉祥寺毁,三论宗衰落并最终销声匿迹。
天台宗在越州亦盛行一时。先是有会稽籍僧普明(534~616)和山阴籍僧大志(568~609)皈依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后又有天台宗五祖灌顶(561~632)、会稽称心资德寺僧大义、诸暨焦山寺僧神邕、会稽大禹寺僧神迥、山阴大善寺僧湛然等大加弘扬。智顗学识广博,适应时宜,深得统治者敬崇。南朝陈宣帝曾为他特诏:“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宣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4]他还为隋炀帝杨广授菩萨戒,后者尊他为智者大师,在他灭度后还在天台山依其遗愿修建了国庆寺。他对佛学的论述主要分为止观、忏法、教判三大部分,有《法华经玄义》《摩可止观》《请观音忏法》等近40部著作,弟子灌顶整理了其中的大部分。灌顶不仅为天台宗在江南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也为该宗北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炀帝时,曾诏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5]。湛然是天台宗的九祖,除教授弟子外,还著有《法华文句记》《法华玄义释签》《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等50余部著作。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无情有性”说,使天台宗在创新中保持了兴盛。
禅宗在越州同样盛行。“南方禅法如寻根究底,可上溯到安世高和康僧会,以及《安般守意经》在江南的传播。”[6]154可见其历史源流之长。唐时,初传者为会稽妙喜寺的印宗(627~713),于广州遇禅宗六祖慧能而得禅玄。印宗颇受越州民众与刺史王胄尊重,除在妙喜寺外,还在越州天柱寺、报恩寺设置戒坛,度僧数千,著有《心要集》,纂集梁至唐高僧语录,《宋高僧传》有传。诸暨僧慧忠(?~776),创“义理禅”,受唐玄宗、肃宗、代宗三帝礼遇,被尊为“国师”。山阴大云寺僧慧海,所著《顿悟入道要门》引得四方僧众来越依附[7]。唐宪宗时,灵默禅师(748~818)到诸暨创立三学禅院(今五泄禅寺),其弟子良价(807~869),诸暨人,晚唐时与弟子本寂创立了禅宗曹洞宗。
律宗于东晋南朝时已在越地传播,至隋唐五代十国时,越州已是浙东的传播中心了。会稽籍僧文纲(636~627),先从道宣学律,后在长安讲律,为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唐玄宗四朝帝师。文纲高足道岸(654~717),常住越州龙兴寺,“江淮释子,辐辏乌合”[8],《四分律》由此盛行江淮。后应诏入朝,颇受唐中宗尊重。晚年回龙兴寺,并在此圆寂,时僧俗共哀,披麻戴孝,数以万计。他曾为高足玄俨受具足戒,为鉴真受菩萨戒,而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律学大师,足见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佛学泰斗。玄俨(675~742)本籍诸暨,俗姓徐,20岁受具足戒,住越州法华寺近30年,建置戒坛,招集律行,同宣般若;讲唐玄宗亲注之《金刚般若经》,颇合帝意,影响甚大;修剡县石城大佛像,七宝八珍,琳琅纷呈;著有《辅篇记》10卷、《羯磨述章》3篇、《金刚义疏》7卷,为“僧徒远近传写”;他还“受毗尼之密行”,为门人“觉引灌顶,皆不倾油钵,无漏浮囊”,史称三千门人、五百弟[9]。鉴真第三次东渡日本时,“天宝三载(744)岁次甲申,越州龙兴寺众僧请大和上讲律授戒”,“时越州僧等,知大和尚欲往日本国,告州官曰:‘日本国僧荣叡,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时山阴县尉遣人于王蒸宅搜得荣叡师,着枷递送京。”[10]可见越州僧众与官民对他的崇敬。当时浙东的主要律寺——越州开元寺(后称大善寺)住持昙一(692~771),一生讲《四分律》35遍,《删补钞》20余遍,著有《发正义记》,“从持僧律,盖度人十万计矣”[11],连湛然也成为他的弟子,华严宗四祖澄观亦从其学律。这一时期,在越州讲授传播律宗的还有昙休、丹甫、允文、元表、灵一、灵澈等。唐末五代,律宗在越州渐次衰落。
华严宗也在越州得到了传播,特别是走出了像澄观这样的大德高僧。澄观(738~839)本籍山阴,11岁依宝林寺洪霈禅师出家,20岁始四方求师,曾从昙一学律,从湛然学天台止观,从慧云、无名学禅,从玄璧学三论,从法诜学华严,可谓广涉佛学。后游五台山,住大华严寺,精研华严,著成《华严经疏》等400余卷,现存170余卷,有“华严疏主”之称,成华严宗四祖。曾奉诏参与翻译《四十华严》,并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10卷。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79),赐以“清凉法师”,礼为“教授和尚”;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诏入内殿讲华严法界宗旨,加号“僧统清凉国师”[12]。华严宗全盛时,法藏“因奏于两都及吴、越、清凉山五处起寺,均榜华严之号”[13],将越州也列为通过官方力量建立全国性象征、与两都并立的五个地区之一。智藏“及游会稽,于杭坞山(今诸暨境内)顶筑小室安禅。乃著《华严经妙义》,亹亹,学者归焉”[14]。
越地信仰净土,始于东晋慧虔、南朝宋道敬。至立宗后,弘传者为唐元英,在越州大禹寺结成九品往生社,有社员1250人。在净土教义里,观世音扮演着阿弥陀净土的指引菩萨的角色。“山阴比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清辉妙状,光映日月,幢幡华盖,皆以七宝庄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无常。……虔既自审必终,又睹瑞相。道俗闻见,咸生叹羡焉”[15]。俨然是一幅观世音接迎慧虔去净土的图像。与此同时,观世音对现世的“救苦救难”,又使其获得了广泛的民间基础,表现为专奉寺庙的大批涌现上。嵊县法性院,“晋天福七年(942),邑人于古大宁寺基上建。有大士像随潮而至,父老迎置于院,改观音院。”[16]
密宗在越州的传播者为寂照,住持龙兴寺;还有顺晓,为日僧最澄授过灌顶礼。他们都受业于该宗三大创始人之一的不空的弟子慧果。五代后,密宗渐融于诸宗。严耀中因其“没有自身独立的传授系统,但却在其它诸宗中流传不息”,而称之为“寓宗”[6]172。从这个角度而言,净土宗也是“寓宗”。不过越州密宗在融于诸宗、与民俗民风打成一片的同时,内容上还是保留了密宗寺院、密迹与会密传的僧人等相对的独立性。剡县惠安寺“有灌顶坛。张继剡县法台寺灌顶坛诗:‘九灯传像法,七夜会龙华;月静金殿广,幡摇银汉斜;香坛分地位,室印辨根芽’。”[17]这是一幅活灵活现的灌顶密法图。会稽开元寺的“戒坛四面,皆为天王及日月星宿之象”[18],实际上也是密坛。
唯识宗兴起于唐代,也在越州得到了传播。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以“慈恩”为名的寺院的出现。山阴县慈恩院,“后唐长兴二年(931)谢君彦舍地建。……大中祥符元年(1008)七月改赐今额。”[19]后唐会稽郡大善寺僧虚受,“《法华》《百法》《唯识》,各有别行《义章》。”[20]可以说是继承了唯识宗创始人玄奘一专多能的遗风。
这个时期越州佛教宗派林立,蔚然成风,奠定了越州在江南乃至整个中国佛学上的领先地位,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是寺院遍布州郡各地。
隋朝文帝时,全国有寺院3792座,炀帝时有3985座[21]。张国刚对唐代不同时期的寺院作了考证统计,648年为3716座,650~683年为4000座,713~755年为5358座,842~845年为4600座[22]。隋唐时期,越州“共创建佛寺208处、庵舍8处,其中尚不包括修建和会昌毁佛后重建的。如果按朝代分,隋代5处,唐代91处,五代120处”[23]6。根据李映辉的研究考证,唐时,以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有寺院834座,除长安、洛阳两都外,越州有23座,与治所在今山西代县的代州并列第4位,占南方总数364座的6%;此后有寺院664座,除长安与苏州外,越州有28座,与东都洛阳并列第1位,占南方总数365座的8%[24]。另据他统计,唐代寺院最密集地区为今浙、苏两省,包括越、扬等十州,该区域唐前期“总共有140所寺院,占全国点数的17%”,后期升至“169所寺院,占全国总数的25.5%”[25]。照此算来,越州寺院占该区域的比例,唐前期为16%,后期为17%。由此可见越州寺院在南方与全国的地位。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七月敕令毁佛,越州以浙东观察使治所而留大善一寺,“且延僧五人守之”[26],余均在毁撤之列。然而,实际毁撤的并不多,地方志有明确记载的才59处。这一方面,是由于佛教在会稽的强大势力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唐宣宗次年五月即位后即敕复佛寺。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州修建寺庙之风益盛。仅宣宗大中年间(847~860),就一下恢复了16处。在以后的40年间,除嘉祥寺外,其他都相继获得了恢复。
吴越国(907~978)的71年间,不仅修复前代废弃佛寺,还新建了120处。其中,钱镠除赐钱八千万恢复新昌宝相寺(今大佛寺)外,还创立了越州开元寺、会稽澄心寺、嵊州瑞像院;钱元瓘在位的9年中,建成了44处佛寺;而钱弘俶则称得上是佛教徒的领袖,他在大兴佛寺的同时,还铸造了约84000个封藏佛经的铜制宝箧印塔。
这一时期,寺院的组织管理也得到了加强。“寺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27]上座为首席长老,寺主主持日常寺务,都维那主诵经功课等业务。寺主有官方任命的,也有众僧推选的,如山阴县大庆尼寺“用十方规制选名行尼主焉”[28]。
三是越地禅诗融通,相得益彰。
隋唐时期的越州,是佛教僧侣的圣地,也是文人墨客的天堂。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僧人与诗人相友相兼、佛教与诗歌相交相会的禅林诗境,成为越州佛教与文化领域中的一大奇观。2200余位《全唐诗》的作者中,有400位左右来过越州,他们或壮游、或为官、或寓居,佛不离心,诗不离口,成就了有名的“唐诗之路”[29]。他们遍访越中名山古刹,表达山水禅林心境,丰富了诗歌创作的新题材,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意境。李白的《石城寺》、秦系的《云门寺》、宋之问的《游法华寺》、白居易的《题法华山天衣寺》、方干的《题宝林山禅院》、孟浩然的《题大禹寺义公禅房》等都是极佳的诗篇。
与此同时,许多越中僧侣,也崇尚课余咏诗,表达禅意禅趣,出现了一批著名诗僧。云门寺僧灵澈,曾从严维学诗,与诗人刘长卿、皇甫曾倾心相交,同诗僧皎然一见如故。悬溜寺僧灵一,“每禅诵之隙,辄赋诗歌事,思入无间,兴含飞动”;传法时,也是“示人文艺,以诱世智”[30]。诗僧们借助于诗歌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来观照世界、理解人生、阐发禅理、弘扬佛法,既是对佛教的一大贡献,同时更是对文学的一大推动。
二、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承祧与流变
宋元两朝的408年间,佛教的主要宗派继续在绍兴广泛传播。
弘扬华严宗的,在宋代,有慧定(1114~1181),山阴人,曾住戒珠寺、石佛妙相寺,著有《金刚经解》《法界观图》《会三归一章》等。有子猷(1121~1189),山阴人,住石佛妙相寺二十余年。在元代,有春谷弘华严于景德寺、宝林寺。其弟子大同终身弘扬华严,被视为华严正宗传人,信徒广众。
弘扬天台宗的,在宋代,有指堂,会稽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住持天台国清寺,时称“治山法师”;与朱熹等交游,有《指南集》行世。有仲休,被誉为“紫衣海慧”。在元代,有性澄(1265~1342),会稽人,曾应召入京,奉旨校正《大藏经》,赐号“佛海大师”,至元间(1264~1294),奏请收回为禅宗所占的国清寺,恢复台宗根本道场。有弘济(1271~1356),悉通台宗玄义,连性澄也延请其分座说法,曾与高昌国般若空利共译《小止观》。有允若(1280~1359),弘法于云门寺、圆通寺。有善继(1286~1357),弘法于灵秘寺。有元静(1312~1378),弘法于长庆寺、天衣万寿禅寺。
禅宗在唐末分出五家后,曹洞宗在绍兴的弘传者有天衣寺法聪禅师、超化藻禅师,临济宗有云门寺显庆禅师、姜山方禅师和石城宝相寺的显忠禅师,沩仰宗有清化禅院全怤,法眼宗有开创者文益弟子德昭的法嗣希辩、道圆等,云门宗主要有北宋天衣寺义怀及其弟子天章寺元善禅师、云门寺灵侃禅师等。
宋时,净土宗风行绍兴,禅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弘扬者多兼修净土。天衣寺禅师义怀倡导“禅净双修”,认为“若言无净土,则又违佛语”[31]。这种顺应众生通过简便途径往生净土心理的主张,不但为众生接受,也为寺僧接受,从而使禅宗得到了更好的弘扬,义怀本人也因此于宋徽宗崇宁(1102~1106)中,赐谥振宗禅师。影响广泛,并逐渐融会诸宗,成为实际上的绍兴共宗、天下共宗。
在全国佛教总体上已日见式微的情况下,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仍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表现出以下新的趋势。
一是朝廷赐额广泛,蔚然成风。
其实早在东晋南朝时,会稽佛寺就有了皇帝赐额的先例,这在全国来说,也是较早的。如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既成,启奏(晋)孝宗。诏曰:‘山阴旧宅为祗洹寺,永新新居为崇化寺。’”[32]
有宋一代,绍兴在原有寺庵的基础上,“在府城和山、会两县又新建了佛寺42处、庵舍41处。”对这些新建寺庵,朝廷多次敕赐匾额,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赐额今绍兴市境内寺院80处”;另一次是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共赐额58处。”[23]10赐额不仅是为了控制寺庙的数量与命名,而且也是显示朝廷对佛教事务享有的权威。不过,也有在地方官府许可或默许下,将废旧寺额移到新寺,以免赐额的麻烦与限制的。如绍兴的观音教院,是“乾道九年(1173)有沈安中舍所居,请于府,移会稽县界圆通妙智教院旧额建”[33]。与此同时,官府对寺主任命和僧侣人数的控制也较唐代有所放松。寺主除极少数敕差和一些十方寺(或称丛林)由地方官提名外,甲乙寺(或称子孙寺)等一般都自行产生,官府备案了事。如山阴灵秘院,“绍兴(1131~1162)中僧智性创。……(智性)请于府,移江北安昌乡灵秘废院额。智性年九十余,精神犹不衰,犹能领院事,淳熙十六年(1189)九月,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34]
在广泛赐额的同时,有的佛寺还得到了特殊的护持。建于晋义熙三年(407)的云门寺,宋太宗于淳化五年(994)诏改“淳化寺”,绍兴十八年(1148)宋高宗又赐御书“传忠广孝之寺”额。建于北宋至道二年(996)的天章寺,宋太宗当年即赐“天章寺”额,天圣四年(1026)宋仁宗又赐御书“天章之寺”额,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赐御书《兰亭集序》,淳熙十年(1183)宋孝宗诏重建御书阁以奉安仁宗皇帝。建于南朝宋元徽元年(473)的宝林寺,绍兴七年(1137)改名报恩广孝(又名光孝)禅寺,寺奉徽宗香火。
敕赐御书匾额给佛寺,始于晋代,南朝隋唐亦有,而如两宋之盛,则实在是前所未有,虽或有过滥之嫌,然亦说明宋时朝廷对佛教之护爱有加,绍兴佛寺与皇家宗室之关系十分密切。
二是功用广众,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
宋元时,始于六朝的城隍、土地和龙王崇拜在绍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批城隍庙、土地庙和龙王庙。它们与佛教寺院和平相处,互相影响,使佛、道、儒三家观念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结合点,从而壮大了稳定社会基层的信仰力量。
城隍崇拜的兴盛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表达了祈求城市安宁的愿望。土地神崇拜的兴盛与绍兴人多地少的矛盾相符合,旨在祈求一方平安与农业丰收。龙王崇拜与绍兴作为水乡泽国相关联,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因为越地先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35]。有的佛寺,还将与这些神祇有关的神迹作为特色来吸引信众。嵊县龙藏寺“旧号龙宫院,有巨井深浚,水色绀寒,疑有蛟龙居焉。又有老松如龙,数百年物也”[36]。不过,这些专门神庙的规模一般都较小,如会稽的显宁城隍庙仅有“一僧掌香火”[37]。
这时的寺院,社会化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用途日益繁多,反映了佛教的加速世俗化,这是与包括绍兴在内的江南经济的发达相关联的。有的寺院,作为读书讲习之处,寄厝棺柩之地,隐士避世之居,行人旅宿之舍。有的甚至成了生死二途的共同旅舍,如有个名叫唐信道的人,“宣和五年(1123)自会稽如钱塘,赴两浙漕试,馆于普济寺。寺后空室有旅梓,欲观之。”[38]由此看来,庄严的寺院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繁忙的联结点。
宋元时期佛教的流变,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绍兴佛教文化,大众化、社会化、世俗化进一步成为主流。
三是佛教寺产广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
宋元时期,绍兴佛教寺产规模空前扩大,寺院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成为经济实体,寺产多为房、田、地、山、荡,其来源或为朝廷所置,或为官绅所捐,或为百姓所资,不一而足。云门寺曾有田地300余亩。天章寺朝廷供田1000亩。宝林寺宋孝宗乾道间(1165~1173),置田5000亩,寺宇、佛像之藻绘尤盛。嵊县普安寺宋景祐二年(1035)赐额并置御田800亩、山60亩。宋淳熙十三年(1186),承节郎(宋代五十三阶武臣官阶中之第五十一阶)河北薛纯一“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岁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寺(建于晋时,在府城)”[39]。元代本立大师,“竭其心思,不惮劳勚”二十余年,建成绍兴路至大报恩接待寺,“买田千亩以充饥餐之需,买山五百余亩以供薪槱之用。”[40]
另外,始于东吴时的舍宅为寺,到宋时,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作为家庙延伸的坟寺。这是建造在家族茔地附近,并为其照料坟墓的寺庙,是“欲先世流泽常在子孙,使坟墓永有荫托”[41]。法云寺是陆游五世祖——光禄大夫、太子太保陆仁昭的功德院。雍熙院和宝山证慈寺均为陆游祖父——尚书左丞陆佃的功德院。天衣寺曾为宋孝宗子魏惠宪王的功德坟寺,南宋末僧福闻“乃魏宪靖王坟寺守僧也”[42]。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权贵指射民间寺庙为自家功德坟寺的现象。黄敏枝认为,“功德坟寺的发展结果,出人意表”,使“寺院已完全丧失其独立自主权,而俯首听命于权贵阶级,受他们摆布。权贵阶级在指射寺院为坟寺之后,无不视之为私产,有如新置一庄,一针一草皆为私物”[43]1。不过,将佛寺转为坟寺,对佛教来说,也非全然就是坏事。从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有利于佛寺处于权贵强有力的保护之下,甚至得到额外好处。如会稽报恩广孝禅寺(初名宝林寺),“绍兴初以濮安懿王园庙寓焉。郡守汪纲以钱十万令寺僧重加葺修,于是庭宇益整肃焉。”[44]
张弓认为,“舍宅为寺,移产入释,名为无上功德,实则含有借释荫产的明显动机。”[45]同时,由于拥有财产权,也很容易衍生出施主对主持的任命权。这种情形,对后来的绍兴影响也大。现在似乎又在重演了。历史真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三、绍兴佛教鼎盛的地域优势和历史渊源
应当说,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是与中国佛教产生发展这个大背景紧密相关的。绍兴作为江南佛教传播的一大重镇,也有其特殊的地域优势和历史渊源。
从地域上讲,绍兴处于东南沿海地区,东汉以来自然经济环境优越,海上陆路交通便捷,对于佛教的传播和交流都是十分有利的。据文献记载,早在东汉时期,高僧安世高(名清,字世高,出家前是安息国王太子)即入会稽,[46]标志着绍兴佛教传播的开始。三国时孙权(222~252)优礼来自月支国的支谦和来自天竺国的康僧会,支持他们译出了《微密持经》《阿弥陀经》等江南第一批佛经,“由是江左大法遂兴。”[47]西晋太康十年(289),西域僧幽闲在剡县澄潭(今属新昌县)卜筑新建寺[23]157,会稽佛教得到了直接真传。就目前发现有确切纪年的早期佛教造像,多在三国西晋时期,会稽越瓷青瓷堆塑罐上有形态多样的胡僧,说明当时在会稽地区有许多来自印度、西域各地的僧人。[48]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绍兴大量出土的三国、西晋时的青瓷谷仓、三足樽、双系罐、砖甓上出现的佛像以及相关的铭文表明,佛教已经广泛深入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丧葬习俗当中。[49][50][51][52]
到了唐代,越州更是江南地区的通都大邑,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为中国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密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高丽等,发挥了重要的源头活水与桥梁纽带作用。
最早“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的,是来自高丽(今朝鲜)的慧灌,他学成后赴日传授,成为日本三论宗的初祖[53]。日本的求法僧最澄、空海、圆珍和留学僧义真、圆载等,都到越州求过法。最澄在越州龙兴寺、法华寺习天台止观的同时,还在镜湖峰山道场受顺晓法师的密教灌顶,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归国时从越州带去了佛经102部115卷及大量佛具等。由于在越州的经历,他在日本创立天台宗时,主张台、密两教合一,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大特点。由于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的创始人的关系,日本曹洞宗法嗣经常到越州参禅。
从历史渊源上回溯,佛教在会稽的传播,是与会稽佛教的历史积淀和特殊的民风习俗相关。越俗“俗信鬼神,好淫祠”,[54]笔者在《秦〈会稽刻石〉考论》序言中指出:“最早祭禹的,可以追溯到夏王启派遣的使者及禹之后人”[55]22,“最早祭祀会稽山神的是越王勾践”,“最早亲祭大禹的帝王是秦始皇。”[55]23在官方祭祀活动的带动与影响下,越地先民敬畏祖宗神灵、祈求安康福祉的民俗心理、宗教氛围浓厚,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与“气候”。安世高、幽闲等异域高僧们来会稽,并不是偶然的。
“晋南渡后,释氏始盛”[56],会稽在120余年佛教初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与建康(今南京)齐名的佛教中心[57]。鉴湖筑成,会稽的生态环境明显改观,成为晋室南渡之际中原名门望族避乱的理想安居之所。东晋时期四方高僧亦纷至沓来,与本土高僧相融合,研究佛学理论。律宗、净土宗、成实宗、涅槃宗等学说纷纷创立。这些开宗立说的代表人物,有六家、六宗、六人生活或活动在会稽[58]。同时,佛经的大量翻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主要宗派在会稽的传播。上虞人慧皎(497~554),著成《高僧传》一书,录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南朝梁天监十八年(519),凡453年间的高僧257人,附见239人,创僧传体例。自东晋至南朝,“今绍兴市境内,相继创建寺庵达65处之多”[23]5。根据张伟然、顾晶霞的考证,南北朝时,会稽有寺院39座,数量居江南第三。
佛教加速传播与玄学扩大影响的需要,使僧侣与士大夫们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仅《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关双方交往的记录就有16条之多。他们由谈玄、谈佛而谈道,实现了历史性的合流,留下了18高僧与18名士交往等历史佳话[59]。这种合流,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促成了山水诗和山水画在江南的首先诞生;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僧人进入了当时的主流社会,推动了佛教在会稽境内的传播。帝王、士大夫崇佛,高僧们对政治及儒、道也是兴趣浓厚,积极参与,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南朝宋时的慧琳,“元嘉(424~453)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60]。会稽孔觊称其为“黑衣宰相”[61]。白道猷与竺道壹居若耶山,“纵心孔、释之书。”[62]竺法潜在越中“优游讲席三十余载……释《老》《庄》”。一生受到四位皇帝的敬重,为佛教赢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与社会地位,也为儒、释、道的交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更为会稽佛教中心的形成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切为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佛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支柱,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3]。作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放异彩的绍兴佛教,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唐]道宣.高僧传合集·吉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唐]道宣.高僧传合集·智凯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唐]道宣.高僧传合集·法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唐]道宣.高僧传合集·智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唐]道宣.高僧传合集·灌顶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严耀中.江南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宋]嘉泰会稽志(卷一一)高僧·大珠慧海传[M].
[8][宋]赞宁.宋高僧传·道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宋]赞宁.宋高僧传·玄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日]真人元开撰,梁明院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M].扬州:广陵书社2010.43.
[11][宋]赞宁.宋高僧传·昙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宋]赞宁.宋高僧传·澄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新罗,今韩国]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M].
[14][宋]赞宁.宋高僧传·智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唐]道宣.高僧传合集·慧虔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6][宋]嘉泰会稽志(卷八)“嵊县法性院”条[M].
[17][宋]高似孙编.剡录(卷八)“惠安寺”[M].
[18][宋]嘉泰会稽志(卷八)“开元寺昭庆戒坛”条[M].
[19][宋]嘉泰会稽志(卷七)“山阴县慈恩寺”条[M].
[20][宋]赞宁.宋高僧传·虚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1][唐]法琳.辩证论[M].
[22]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98.
[23]绍兴佛教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4]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25]李映辉.唐代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4).
[26]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嘉庆山阴县志·肇兴庙碑记[M].民国25年刊本.
[27]唐律疏议(卷七)“诸称‘道士’‘女官’者,僧、尼同”条[M].
[28][宋]嘉泰会稽志(卷七)“山阴县大庆尼寺”条[M].
[29]竺岳兵主编.唐诗之路综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0][宋]赞宁.宋高僧传·灵一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1][唐]道宣.高僧传合集·新续高僧传四集·义怀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2]建康实录·孝宗穆皇帝“永和三年(347)十二月”条[M].
[33][宋]嘉泰会稽志(卷七)“府城观音教院”条[M].
[34][宋]嘉泰会稽志(卷七)“山阴县灵秘院”条[M].
[35]应劭注.汉书·地理志(下)“越君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条[M].
[36][宋]宝庆续会稽志(卷三)“嵊县龙藏寺”条[M].
[37][宋]宝庆续会稽志(卷三)“城隍显宁庙”条[M].
[38][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〇)“余杭宗女”条[M].
[39][宋]陆游.渭南文集·能仁寺舍田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0]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绍兴路至大报恩接待寺记[M].民国25年刊本.
[41][宋]叶适.水心文集·郭氏种德庵记[M].。
[42][明]邵景詹.觅灯因话·唐义士传[M].。
[4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史论集[M].台北:学生书局1989.435.
[44][宋]宝庆续会稽志(卷三)“报恩广孝禅寺”条[M].
[45]汉唐佛寺文化史(卷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0.
[46][梁]慧皎.高僧传·安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7][梁]慧皎.高僧传·康僧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8]张恒.浙江嵊县发现的早期佛教艺术品及相关问题之研究[J].东南文化,1992(2).
[49]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江山三国吴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1989(2).
[50]阮春荣.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J].东南文化,1990(1)(2)(3).
[51]蒋明明.佛教与六朝越窑青瓷片论[J].东南文化,1992(1).
[52]周燕儿,蔡晓黎.绍兴县出土的六朝佛教题材青瓷器[J].东南文化,1992(2).
[53][日]元亨释书(卷一)[M].
[54]隋书·地理志(下)“扬州”条[M].
[55]平水新城管委会.秦《会稽刻石》考论[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5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沙门入艺术传始于晋书[M].
[57][日]钅兼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9](宋)高似孙编.剡录·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卷五)[M].
[60]宋书·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M].
[61]南史·夷貊传·天竺迦毗黎国[M].
[62][梁]慧皎.高僧传·竺道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J].求是,2012(22).
(责任编辑吕晓英)
The Spread, Inheritance and Gradual Change of Buddhism
in Shaoxing in the Sui,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eng Jianrong
(Shaox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In the Sui,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uddhism in Shaoxing reached its unprecedented peak with a variety of Buddhist schools springing up in succession; prestigious monks successively produced many influential Buddhist writings and translated works; and Buddhist temples were found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 offering a harmonious climate for the monks and scholars to be blended with the beauty of Chan and poetry by exhibiting themselves in Buddhism and poetry. It followed that though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China tended to declin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Buddhism in Shaoxing still benefited from the twilight of prosperit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from the advantage of Shaoxing as the wartime capita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us outshining alone and maintaining its bloo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t temples and the imperial clan stimulated the flourishing of the temples’ economy, embodying the rising trend of the Buddhist social secularization. Against the general backdrop of Buddhism spread all over China and Shaoxing’s special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prosperity, inheritance and gradual change of Buddhism in Shaoxing in the Sui,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legacy as well as the peculiar folk customs of the region, hence Shaoxing’s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pagation of major Chinese Buddhist sects.
Key words:Buddhism; Yue prefecture; Shaoxing; propagation; inheritance; gradual change
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5)01-0001-08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1.001
作者简介:冯建荣(1963-),男,浙江上虞人,绍兴市人民政府干部。
收稿日期:*2014-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