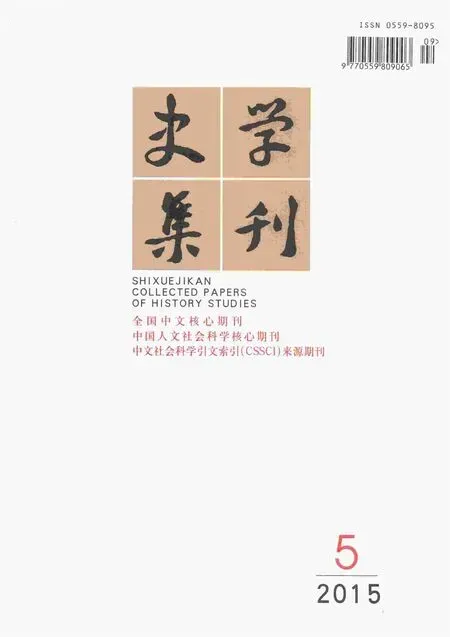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在由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组成的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这是因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无论是师从康有为而形成的在学术上与康有为的渊源关系还是并肩领导戊戌政变而形成的政治上的“康梁”集团,都决定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之深厚、复杂是谭嗣同、严复无可比拟的。与此同时,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关系亦非康有为、严复可比,无论是梁启超在谭嗣同生前与之共谋国事、切磋学术还是在谭嗣同死后为之刊发遗作、宣传思想,都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与康有为或谭嗣同和严复之间并无太多交集相比,梁启超与严复之间的关系可谓密切。严复 (1854—1921)与梁启超 (1873—1929)年龄差距最大,足足相差了19岁,两人的关系也最为微妙而复杂。一方面,在戊戌政变之前,严复、梁启超切磋学术,彼此有书信往来。另一方面,两人政见不合,尤其是对当时中国政局、时事的看法大不相同。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严复对梁启超极为不满,乃至在私人通信中不止一次地对梁启超大加谴责和攻击。严复与梁启超之间的相互评价天差地别:如果说梁启超对严复除了推崇以外绝无微词的话,那么,严复对梁启超则除了学问上的不屑一顾就是基于政治原因的不满甚至责骂。检视严复与梁启超之间的相互评价,既可以直观感受两人思想的异同,又可以进一步体悟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一
戊戌政变之前,严复与梁启超有过通信,大多是梁启超向严复请教学问或索要译稿、严复做答并探讨学问。这时候,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是平和的,既有礼节上的客气,亦有指教,饱含长辈对后辈的鼓励和期望。在写给梁启超的回信中,严复如是说:“载诵来书,撝抑之语,皆由至诚,尤征学养。如谓学不知本,则隔靴搔痒,不通文语,则凡所诵习,皆彼中粗迩吐弃之谭云云,此自盛德若虚,不自满假语耳。自仆观之,则足下虽未通其文,要已一往破的。无似因缘际会,得治彼学二十余年,顾自揣所有,其差有一日之长者,不过名物象数之末而已。至其宏纲大旨,则与足下争一旦之命,胜负之数,真未可知。况足下年力盛壮如此,聪明精锐如此,文章器识又如此,从此真积力久,以至不惑、知命之年,则其视无似辈岂止吹剑首者一吷已哉!”①严复:《与梁启超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由此可见,此时的严复在梁启超向自己请教学问时坦诚相待,既能指出梁启超的不足,又予以鼓励和点拨。不仅如此,面对梁启超对自己学问的折服,严复坦言自己的作文初衷与不足,两人之间俨然一对以文会友的老朋友:“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仆之命意如此,故篇以《原强》名也。能事既不足心副,而人事牵率,遂以中绝。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②严复:《与梁启超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514页。
戊戌政变之后,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急转直下,大加指责——这种态度越到后来越明显,以至于将中国政局的混乱归咎于梁启超的蛊惑,直接将梁启超说成是戊戌政变后中国乱象环生的罪魁祸首。出现这种情况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严复对梁启超的做法不满,焦点集中在梁启超的善变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上。在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回国之后,严复对其搅动政局的预测和担忧即缘于此。他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袒露了这种心声:“梁饮冰自执笔以还,宗旨不知几变,目下韬迹天津,云以著书为事,吾恐不能如前之 闻动众矣。时人看研究会之汤、梁,真是一钱不值也。南北国会皆已成立,后来执持国枋,即此两群猪仔,中国安得太平!”③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92页。
其实,早在戊戌维新前的通信中,作为长辈的严复已经直接指出了梁启超言论多变、无固定操守等问题,并加以劝诫。对此,梁启超在回信中一面对严复的批评表示认同,承认自己“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④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一面感谢严复对自己的指教,并且不无夸张和煽情地说:“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⑤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71页。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局面的风云变幻有关,更与梁启超本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善变是梁启超“与生俱来”的印记,并非想改就能改的。事实证明,这一特点确实终身伴随着梁启超。流质易变使梁启超被世人诟病,不仅是严复,作为梁启超老师的康有为也多次对梁启超的流质易变提出严正批评。以戊戌变法为开端,梁启超的思想变成了行动。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梁启超接触到大量西方学说,流质易变的特质被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宣传家,梁启超的言论对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清议报》甚至被誉为当时青年人的“函授讲义”(顾颉刚语),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随之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思想的一些消极面也随即暴露出来,理论上忽东忽西的善变在实践上造成致命后果。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和指责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有感而发的。这种不满甚至愤懑在严复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表露无遗:“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衂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迨万弩齐发,堤防尽隳,大风起而悔心萌,即在任公,岂不知悮由是。则曰:‘吾所极恶痛绝者政府,至于皇室,则向所保护者也。’嗟嗟任公!生为中国之人,读书破万卷,尚不知吾国之制,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于其体,诚欲保全;于其用,不得不稍留余地,则其误于新学,可谓深矣。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嗟乎!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且任公不亦曰‘共和则必亡国乎’?然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①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45-646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家之一,自称创立了“启超”体,笔端常带感情,故而含有魔力,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严复多次不无艳羡地说到这一点:
梁任公是绝妙议论家。②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15页。
言论界饮冰势力最巨,南海文笔沉闷,远不逮之,至如鄙人更当避舍。③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59页。
文辞优美,思想言论具有魅力原本是好事,乃至是一件大好事。问题的症结在于:梁启超不仅仅是学问家而且同时是宣传家,不仅仅是理论家而且同时是拥有亿万受众的政治家;他的思想言论是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故而影响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依据严复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笔下大有魔力”,梁启超能够以言论“左右社会”,煽动民众,搅乱社会,在思想界的影响力无人匹敌。就梁启超的影响所及,从“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到“自命时髦之旧官僚”,既可见其受众广泛,又可见其受众或者涉世未深,或者思想根基浅薄,总之极易被蛊惑。受众的广泛而无知为梁启超言论的危险性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喜欢出风头,梁启超爱发新奇之论,等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思改过之时,为时已晚。对于梁启超的所作所为,严复总结说:殊不知请神容易送神难。流质易变使梁启超的思想带有巨大的破坏性;由于笔端魅力足以煽动社会,尽管其主张忽东忽西前后相互矛盾,仍不乏追随者。致命的是,梁启超忽然主张暗杀、忽然鼓动破坏的反复无常不仅使追随者无所适从,而且给中国的救亡图存造成莫大损失。如此说来,梁启超的妙笔可谓他个人的幸运,亦可谓中国的不幸。对此,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有过详细的剖析、总结和概括:
嗟嗟!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南海高年,已成固性。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然此犹有良知进行之说,为之护符。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至于任公,则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其辞具在,吾岂诳哉!一夫作难,九庙遂堕,而天下汹汹,莫谁适主……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④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31-633页。
稍微留意不难看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表面上是针对其常带感情、可以呼风唤雨的魅力之笔,本质上或根本上则是不满意梁启超思想忽然东、忽然西的“前后易观”之宗旨。在严复看来,梁启超忽然暗杀、忽然破坏或忽然革命的前后矛盾言论归根结底是急功近利心理作祟,由于急于求成,故而易走极端,常常选择最危险的直线而非从长计议。众所周知,严复早在1895年就提出了“废君主”的主张,由此站在了戊戌启蒙的最前沿。与此同时,他强调,实行君主立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遵循自然进化(“天演”)的法则;如果贸然行事,必然引起混乱,造成巨大破坏。对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这用严复的话说便是:“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古圣贤所以严分义而威乱贼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发之初会孟津,而复散归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①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32-633页。基于这种思考,严复主张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应该从长计议,反对梁启超急功近利的做法,更反对梁启超不计后果的短视和快一时之意。在严复看来,梁启超的主张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于不能深谙中国现实,故而对中国的前途和政局不能从长计议。严复对后果十分慎重,由此不难想象他对梁启超随时更张的痛惜、担忧和愤慨。
严复进一步揭示、分析了梁启超之所以言论前后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出这并非性格使然,而是目的不纯、动机不正。按照严复的说法,梁启超发表言论的意图并非出于真心救国,故而在作文时往往是为了出风头而不计后果,出风头的目的又进一步决定了其作文好为极端之论,集中表现便是爱走极端。梁启超好走极端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救国,不如说是在祸国,正如抱薪救火一般贻害无穷。在此基础上,严复进而指出,梁启超好走极端与其煽动人情的妙笔相互造势,给中国带来了致命破坏。鉴于梁启超的言论已经多次给中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严复唯一的希望就是梁启超回国后如他自己所言远离政界,不再给中国造成新的危害。
上述分析表明,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主要针对梁启超的行为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客观后果,其中却隐藏着对梁启超的性格甚至是人格的不屑,对梁启超“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的揭露和剖析直接逼问梁启超的人格和道德底线,可谓不留情面。与此类似,在严复的视界中,梁启超迎合大众、随波逐流亦属人格问题。退而言之,即使承认梁启超是“好人”,没有人格方面的“缺陷”,严复还是止不住对梁启超在政治方面的幼稚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梁启超分不清言界与政界的界限,梁启超的所有言论和设想充其量都只限于纸上谈兵。这表明,梁启超对政界的认识是幼稚的,一旦入政界,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严复对梁启超回国后投身政界的担心正缘于此:“任公到京,虽备受各界欢迎,时有演说,然尚不闻生何效力。据言将于教育中寻些事业,不入政界,此言若诚,亦大佳事,何则?以任公而入政界,吾有以策其必毁也……学问分为两种: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平情而论,即任公本身即为其证,好为可喜新说,尝自诡可为内阁总理,然在前清时不论,其入民国,一长司法,再任币制,皆不能本坐言以为起行,至为凤凰草大政方针,种种皆成纸上谈兵,于时世毫无裨补,侘傺去位,此虽洹上在位,志不得行,然使出身谋国,上不知元首之非其人,下不知国民程度之不及,则其人之非实行家,而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不灼灼彰明较著也哉!虽然,任公自是当世贤者,吾徒惜其以口舌得名,所持言论,往往投鼠不知忌器,使捣乱者得借为资,己又无术能持其后,所为重可叹也!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黄陂、合肥皆好人也,即如今番之复约法,召集旧国会,非任公一言,安得有此,然而效可睹矣。悲夫!悲夫!”②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61页。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强烈不满之外,严复对梁启超的学问也含有微词。这不仅是因为两人的学术倾向和主张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因为严复认为梁启超的学术主张和兴趣恰恰助长了他的轻率、自负与狂妄。对此,严复剖析说:“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当上海《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 (疑为悔——引者注),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任公宋学主陆王,此极危险。)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①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48页。
在这里,严复的批评从剖析梁启超的思想构成入手,具体分为西学和中学两方面——既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严复与梁启超的学术分歧,又流露出对梁启超为学的不满乃至不屑。依据严复的分析,就西学而言,梁启超推崇洛克、卢梭等人的思想,而这些学说都属于十七、十八世纪之旧义,且以革命、独立为要义;这些学说是西方历史、社会的产物,不可在中国效仿。就中学而言,梁启超推崇陆王,而这是极“危险”的——正如自我辩解“凭随时之良知行之”一样,梁启超的主张和言论“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的西学与中学皆无根柢,无根柢则无所主;由于缺少固定操守,结果可想而知——不是随波逐流,即是左右奉迎。梁启超所奉为至宝的西方十七、十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皆是直线而决绝的。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难怪梁启超所提倡的“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严复的分析道出了梁启超所执前后矛盾的思想根源,因这一切皆与梁启超的中西学术渊源密不可分,故而“与生俱来”乃至不可更改。
上述内容显示,严复对梁启超的不满乃至攻击归根到底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考虑,焦点集中在对梁启超由于流质易变、所执言论前后矛盾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的批判击中要害,这一点也是梁启超生前身后备受争议乃至诟病的原因所在。对于自己平生的这一特性,梁启超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自省乃至自我解嘲。在这方面,除了在写给严复的信和《清代学术概论》中反复申辩之外,面对他人对自己政论多变的忍无可忍,梁启超再次做出了如下表白:“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②梁启超:《答和事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975-976页。梁启超的多次表白印证了严复评价梁启超的公允性,表明他对梁启超的批评既得到了梁启超的认同,又与其他人对梁启超的看法所见略同。
饶有趣味的是,梁启超对自己的辩解印证了严复对梁启超中学、西学皆无根底的指责:“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1-3102页。在这里,梁启超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剖析,承认自己对于近代(“晚清”)思想界的粗率浅薄负有责任,这与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相吻合。
二
大致说来,梁启超对严复的态度和评价前后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与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转变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充满尊重而无任何微词,这与严复对梁启超的不满甚至斥责更是相去霄壤。早年的梁启超更是将严复奉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即使是到了日本接触大量的西方学说、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之后,也没有改变对严复的态度。例如,与严复坚决反对康有为、梁启超从日本转译西学的态度截然不同,梁启超对通过日文翻译西学十分受用。尽管如此,梁启超并没有像严复对梁启超等人从日本转译西学表示不满甚至反感那样对待严复以西文译西学,而是将严复视为中国思想界的功臣,对严复所译西学的评价自然极高。在回顾、总结中国近代输入外学的情况时,一方面,梁启超坦言自己对西学的输入亦有功劳。对此,他不止一次地写道: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070页。
壬寅、癸卯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4-3105页。
另一方面,梁启超承认自己对于新思想的输入与严复相比自愧弗如。对此,梁启超如是说:“‘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5页。
与对严复翻译西学的赞叹有加相一致,梁启超对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极为推崇,在讲到相关学说或人物时,往往不失时机地提及严复。下仅举其一斑:
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盖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书侯官严氏译)出版于是年也。⑤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558页。
斯密氏之学说,披靡西土者已百余年,今且为前鱼矣,为积薪矣,而其书乃今始出现于我学界。(斯密《原富》严译本去年始印行)⑥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997页。
出于对严复西学素养和西学翻译的推崇,梁启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援引严复的观点加以佐证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例如:
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 (即天然界近于地文学范围者。)之状态,能使初民 (此名词从侯官严氏译,谓古代最初之民族也。)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⑦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563页。
呜呼!世运之说,岂不信哉!当春秋、战国之交,岂特中国民智,为全盛时代而已;盖征诸全球,莫不尔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百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试征诸印度:万教之狮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稣前九百六十八年,(此侯官严氏所考据也,见《天演论》下第三章案语。今从之。)凡住世者七十九岁。佛灭度后六百年而马鸣论师兴,七百年而龙树菩萨现。马鸣、龙树,殆与孟子、荀卿同时也。八百余年而无著、世亲、陈那、护法诸大德起,大乘宏旨,显扬殆罄,时则秦、汉之交也……由是观之,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578页。
更能展示梁启超对严复尊重有加的是,由于热衷于从日本转译西学,梁启超在一些概念、名词的使用上难免遵从日本学者的译法。梁启超在采用日本学者的译名时总是标出严复的译法,以示对严复的尊重。例如,梁启超遵从日本学者的译法,将逻辑学译为论理学,并不认同严复将逻辑学译为名学的做法——理由是,严复用以翻译逻辑学的名学一词滥觞于名家之名,旨在突出以战国时惠施、公孙龙为首的名家思想。这其实是对严复的误解。严复明确指出,所谓名学之名含义奥赜,深邃丰富;如果非要论其出处的话,则取孔子“必也正名乎”之名。正因为如此,严复认定孔子精通逻辑学,出于孔子之手的《春秋》和《周易》都是中国的逻辑学代表作。其中,《春秋》以归纳法为主,《周易》则以演绎法为主。除此之外,严复还谈到老子和朱熹等人的逻辑思想,却很少谈论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思想。这些情况共同证明,严复将逻辑学翻译为名学并非取名家之名,更不是为了以名家作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代表。尽管梁启超并不认同严复将逻辑学译为名学的做法,然而,他并没有由此排斥或漠视严复输入的逻辑学;恰好相反,梁启超在介绍、输入逻辑学时,日本译法和严复译法兼而采之。如上所述,严复、梁启超对日本学术的态度相去天壤:一边是严复对日本学术深恶痛绝,执意直接从西方以西文译西学;一边则是梁启超对学习日文和由东学译西学津津乐道。两人对日本学术的态度分歧直接表现在逻辑学上。一方面,正如排斥日本的哲学译名而采用形而上学一样,严复将Logic译为名学就是为了排斥日本学界对于逻辑学的译法,将Deductive译作“外籀之术”,将Inductive译为“内籀之术”亦是如此,因为“‘内籀’东译谓之‘归纳’……‘外籀’东译谓之‘演绎’”。与严复有别,梁启超的逻辑学术语很多采用日本学者的译名,这一点从其将逻辑学译为论理学,采取日本“归纳”、“演绎”等译名而不使用严复的“名学”、“内籀之术”、“外籀之术”等译名即可见其一斑。另一方面,与对严复西学的叹服相一致,梁启超对严复介绍、翻译的逻辑学持肯定态度;即使不认同严复将Logic译为名学,却十分认同严复对Logic兼具论与学两义的解说。综观梁启超的逻辑思想不难看出,其深受严复的影响——尤其与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穆勒名学》具有某种程度的渊源关系。严复介绍、输入的西方逻辑学对梁启超具有一定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一点,梁启超讲逻辑学时不时采用严复的观点便是明证。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是叱咤风云的启蒙思想家;在严复面前,他又是一位被启蒙者。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西学思想对逃亡日本之前的梁启超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谓是梁启超的精神导师;即便是在梁启超大量接触西学之后,严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梁启超对西学的基本看法和对具体人物的选择。就西学对梁启超的影响而言,严复的引介之功更是不容忽视。严复是系统输入进化论的第一人,梁启超则是进化论的追随者和鼓吹者。正是受惠于严复,梁启超对达尔文进化论推崇备至且受益匪浅,在输入西学时给予进化论重要一席。一方面,梁启超作《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和《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宣传进化论,并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等论文中多次介绍进化论及其影响。另一方面,进化论特别是生存竞争是梁启超宣传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重要武器,他将进化论运用到伦理、历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审视世界,探讨人生。毫无疑问,梁启超对进化论的系统了解最早、最直接地来自严复的引领和严译《天演论》的启蒙,这一点通过梁启超迫不及待地向严复讨要《天演论》译稿先睹为快和对严译《天演论》的至高评价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在讲到进化论或阐释自己的观点时,梁启超总是念念不忘地援引严复的观点为自己辩护。正是沿着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思路,梁启超推崇功利主义——专门作《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同时介绍了最先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功利主义大家——穆勒的观点,并力排众议推介日本功利主义者加藤弘之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所讲的功利主义与老师康有为“求乐免苦”的享乐主义相去甚远,力主通过利群利他来自利,而这一切均源于达尔文进化论基于生物生存竞争法则的思考和权衡。
鉴于严复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和自己对严复的崇拜,加之严复的西学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界至关重要的影响,梁启超对严复评价甚高,将之誉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①严群为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作序说,“梁任公谓几道先生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梁启超下此断言,依据是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和输入的西学对中国思想界的空前影响:“惟侯官严几道 (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619页。这段话出自著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屡次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因此,梁启超在此并非是专门表扬严复的,而是呼吁新一代输入西学、使国学“别添活气”的。为此,他鼓励青年说,由于时过境迁,新思想的输入将超迈严复。尽管如此,从梁启超对严复输入西学“大苏润思想界”“大有力”之表述中,犹可见其对严复引领近代思想界风尚的肯定和褒奖,特别是其中的“独一无二”之誉将梁启超对严复的推崇表达到了极致,与梁启超在其他场合对严复“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的界定相互印证。除此之外,梁启超多次从“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的角度突出严复在输入西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梁启超曾经说:“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此非特由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有未足者耶。”③梁启超:《东籍月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325页。就西学而言,梁启超对于严复“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的评价不仅是就严复对西学的介绍、翻译而言的,而且是就严复的西学素养和造诣而言的。不仅如此,在梁启超看来,输入西学远非易事,非同时精通中西学者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严复是“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的评价已经使严复学贯中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对严复的这个评价与严复评价梁启超中西学皆根柢浅薄相映成趣,也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对严复的服膺乃至膜拜。
三
严复与梁启超的相互评价不仅形象地展示了两人之间的思想和政见异同,而且透露出两人与康有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严复那里,对待康有为的态度与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恰成对立趋势:如果说严复对康有为是早期批判而后期趋同的话,那么,他对梁启超则由早期的切磋变成后期的决绝。姑且不论严复晚年认同康有为的孔教主张,自称“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④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661页。单就严复对戊戌政变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攻击来说,由始至终矛头主要指向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康有为年事已高,影响力减弱;二是梁启超风头正劲,成为海内外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三是梁启超流质易变、反复无常的主张带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梁启超那里,对于严复的折服便潜伏着对其老师——康有为学术的偏离或不满。这使严复、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始终越不过康有为,两人的关系最终演绎为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三人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的思想在逃亡日本之前,主要受康有为、严复两人的影响。这一点在梁启超本人不止一次地将康有为与严复相提并论中得到印证:
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①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73页。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子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②梁启超:《〈说群〉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93页。
对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思想建构来说,康有为、严复的影响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康有为的影响集中在中学方面,主要是奠基于“百家皆孔子之学”③康有为:《万木草堂囗说·学术源流》,美义华等主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之上的孔教思想;严复的影响则在西学,主要包括进化论、自由思想和社会有机体论等。正如早期的梁启超宣称“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④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86页。一样,对于梁启超早期思想的建构来说,中学与西学相得益彰,互为本用,这意味着康有为、严复对于梁启超的早期思想来说一个都不能少。
诚如梁启超所言,近代哲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4页。这用来说明梁启超的思想再合适不过了。既然其思想“不中不西即中即西”,那么,中西思想的不同比重也就从一个侧面意味着作为中学之师的康有为与作为西学之师的严复对于梁启超思想建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发现,康有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并不可以等量齐观。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和终身学术走向来看,严复的影响是更深远也更根本的。梁启超对于康有为对自己的影响有过集中阐述。他写道:“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⑥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958页。在此,梁启超提到了康有为所讲授的中学、西学和佛学,对于佛学,明确表示“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结合梁启超多次强调自己在佛学方面受谭嗣同影响可以想象,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在佛学。至于西学,梁启超并不认可康有为的西学素养,甚至在自己接触、了解西学之后以“三不”来概括康有为的西学水平。在著名的《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这样评价康有为的哲学及其与西学的关系:“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⑦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488页。由此反观,梁启超既承认康有为讲西学又不承认康有为精通西学,这是自称“‘学问欲’极炽”的梁启超崇拜严复的原因,也是他在日本接触大量的西方思想之后,便与康有为的思想渐行渐远,乃至“康、梁学派遂分”的根本原因。
大致说来,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集中在戊戌政变之前,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集中在“辛卯余年十九”(1891)一年时间,就内容来说则集中在中学方面。梁启超早期所做的《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读书分月课程》、《论支那宗教改革》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对为学途径的认识、对《春秋》、《孟子》的推崇和解读《春秋》、《孟子》的今文经学套路等均带有明显的康学烙印。如果说《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是对康有为思想的传承和发挥的话,那么,《论支那宗教改革》则直接声明“述康南海之言”,⑧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张品弓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263页。《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更是对康有为言学的转述和整理。为了突出这一点,梁启超特意指出:“略依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始教之言以相语也。”①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114页。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因为梁启超在听康有为讲学后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拜倒在康门之下。与对康有为学问的折服相联系,梁启超的思想深受康有为的影响。尽管如此,必须提及的是,就康有为与严复的比较而言,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更大。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是震撼于作“狮子吼”的康有为讲述“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作《新学伪经考》道出了千古秘密:古文经是伪经,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祖师。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难怪作为火山大爆发在思想界引起“大地震”。梁启超亦深受感染。这一时期的梁启超在保教问题上“述康南海之言”,以孔教为真教,坚信康有为提出的通过保教 (孔教)可以保国、保种的主张。在接触到严复宣传的西学如两人通信中提到的严复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原强》等论文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正是震慑于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梁启超在保教问题上与严复走到了一起,由此开始反思乃至反对康有为通过保教来保国、保种的做法。在写给严复的回信中,梁启超用他惯用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启超”体将自己闻听严复教诲时的醍醐灌顶、喜不自禁表达得淋漓尽致:“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②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72页。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对严复的折服直接冲击着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信从,因为“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的两义是梁启超自身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也是康有为无能为力的。在这种困惑下,梁启超请求严复指点迷津。这是对严复的信任,起因是对严复的学问——尤其是西学的折服。在此时,严复的教诲已经使梁启超认识到“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③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72页。这可与梁启超后来以宗教禁锢人之自由为理由反对康有为的孔教思想相印证。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进化论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单单是一种自然科学知识,而是一种观察宇宙、审视社会和处理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价值旨趣和行为规范一样,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绝非限于具体西学知识层面的某些观点或主张,而是致思方向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决定性影响。秉持进化论的思路,梁启超与严复一样认识到社会、国家是有机体,其强弱兴衰取决于构成这一有机体的细胞——国民素质的优劣,于是渴望凭借自由思想拯救中国于危难,于是开始大力宣传、推崇自由思想,并且开始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视康有为的思想。结果是,梁启超发现康有为的思想没有脱离古人“好依傍”之窠臼,这是标榜精神自由、高扬怀疑精神的梁启超所无法容忍的,于是与康有为思想的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本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明确论述:“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第3101页。
既然导致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是以自由为主体和宗旨的西学,那么,不难想象,严复对于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反过来证明了严复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作为其直接后果,梁启超的思想与严复更接近,而与康有为相距甚远,乃至直接对立——用梁启超本人的话说便是自己“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分歧除了集中表现为康有为推崇平等、梁启超推崇自由之外,还通过对宗教、大同和国家等等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来。
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始终夹杂着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只有在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更直观地看清楚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近五十年的思想进化所做的“概括总结”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绝佳材料。这个总结既表明了梁启超视界中的严复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又说明了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将康有为纳入其中,展示了梁启超视界中梁启超与康有为、严复之间的关系。现摘录如下:“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①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30-4031页。
秉持进化理念和乐观主义的梁启超认为,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学问是进步的,进步的标志是“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进步的过程也依照“感到不足”的具体内容依次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器物层面感到不足,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二是从制度层面感觉不足,“急先锋”是康有为、梁启超,其中最有价值的著作是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三是文化上“感觉不足”,也即1919年前后的五四运动。在这个审视和划分中,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耐人寻味:从大的方面说,梁启超将自己与康有为、严复同时归到了从制度层面感觉不足的第二期;从小的方面说,则对自己与康有为、严复的关系具有不同界定——将自己和康有为归在了同一派,均属“急先锋”之列,而将严复单独“另算”。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严复的西学渊源。在这个划分中,张力是十分明显的:第二期的代表人物是“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严复显然不在此列。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证明其是精通西学,至少是稍懂西学的——梁启超也是这样看的。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将严复誉为“输入欧化之第一人”。在这个前提下,梁启超之所以仍然义无反顾地将严复归在与康有为、梁启超同属一期的第二期,主要理由有二:第一,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严复对中学的眷恋和阐发与康有为、梁启超无异。梁启超将严复誉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是就严复介绍、输入西学的功劳、贡献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梁启超认为严复骨里子是西学家。依据梁启超的理解,这一时期 (大致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间较长,虽然政治界云诡波谲、变幻莫测,但是,“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同一个色彩”表明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底色或价值诉求是一样的,这也是梁启超将严复与康有为、梁启超归为同一期的原因所在。第二,三期之分是大分段,三期中时间跨度最长的第二期是与第一期、第三期相比较而言的,与一、二、三期之间的思想区别相比,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之间的思想差异是次要的,故而归到了同一期之中。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进行了三期的划分之后,梁启超紧接着做了一个“补充说明”,其具体内容是:“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①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第4031页。沿着梁启超的这一思路可以发现,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和严复作为第二期“新思想界的勇士”,与洋务派、新文化运动者区别开来,位列其中的尚有早期与梁启超共事、后来转向革命派的章炳麟,始终坚守维新阵营的严复归在其中可谓“唯一”正确的归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严复的历史定位可谓中肯,至于一面将严复与康有为和自己归为同一期,一面单独“另算”,如果从突出严复西学造诣的角度看是必需的,不可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梁启超有意与康有为的“亲近”或与严复的疏远。
综合考察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关系可以看到,一方面,学术传承的私人关系和戊戌政变的志同道合使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如影随形,两人合称康、梁的称谓本身已经胜于一切雄辩。另一方面,私人关系、志同道合与学术影响并不是一码事,更何况正如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样,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变数。正因为如此,无论对于梁启超与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都不可做固定或僵化解,康有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领域各有侧重,而且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