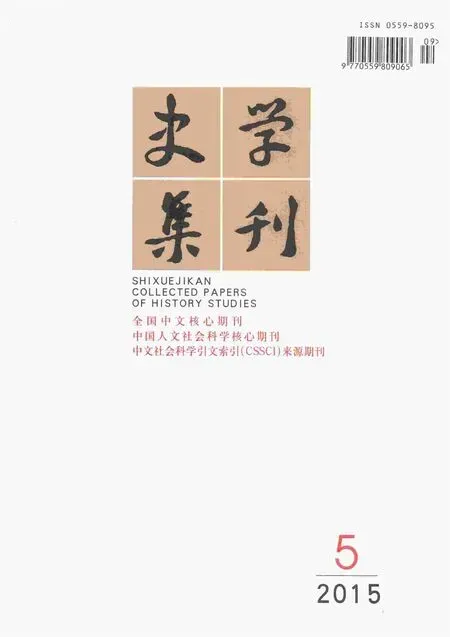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史学起源的社会条件
史海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吉林长春 130012)
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史学起源的社会条件
史海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吉林长春 130012)
文明的阶段性特征是定位历史现象的一种参照,而文明之间的联系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宏大的时空背景。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之间的交往、冲突、融合频繁而深入。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幸记录了一些文明间的互相评价,能够为某些文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提供证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曾经批驳了一些希腊人①希罗多德此处极有可能指责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把埃及人的灵魂不灭、转世轮回的学说纳入自己名下的做法。②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trans.By A.D.Godley,Cambridg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1,II.p.123.
历史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非常漫长,史学的产生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独立于其他文化因素。希腊和中国是史学的两大发源地,同时,埃及、两河流域、赫梯、波斯、犹太等文明遗留了大量的历史记录,这些历史记录却从来没有达到史学的高度。这样,即便没有直接联系的文明也可以为史学起源的问题提供或多或少的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古代文明的各种历史记录形式从而得出史学产生的一般脉络的思维并不严谨,不过,在一种长时段的文明比较语境当中可以更为精准地定位史学产生的初始环境,同时,也更容易对不同文明的“历史”评价其优劣得失。
埃及是古代世界神权政治的代表,随着国家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强化,以军事强权为支柱并辅之以宗教权威的王权符号体系逐渐产生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历史”表述模式,其中包括王权的象征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编年形式的历史记录等。以埃及叙事成就最高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为例,其中共记载对亚洲的战役17次,但是无一次涉及双方交战的具体细节。除了第一次战役 (米吉多战役)的背景介绍较为详尽之外,其他战役都很简略,而且对于法老所得战利品的记述比例远远超过记载战役本身。当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其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的进步,在第四次战役中提到:殿下命令将此次殿下之父所赐之胜利镌刻于神庙的石墙之上。③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2:The Eighteenth Dynasty,London:Histories & Mysteries of Man Ltd,1988,p.455.虽然这种历史记录的动机是出于王权和神意,但毕竟是一种对记录本身的自觉的强调。另外在第三次战役结尾的叙述中,殿下说道:“我发誓,如同拉神钟爱我,我父阿蒙青睐我一样,所有上述之事都是真实的……所有发生在朕身上的事情都是真的,我没有虚构”。④James 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2:The Eighteenth Dynasty,p.452.虽然这种强调真实的意图并非史学意义上的去伪存真,其目的只是在于证明:和其他可能伪造的记录相比,文中强调,法老代表诸神真实地履行了开疆扩土、维持秩序的职责,但是此处也在王权与神权的权威之下突出了“真实”的重要意义。埃及社会的政治模式是王权与神权的严密契合,法老秉承神的血统,拥有神的头衔,具备神的属性,凡战争、政务、建筑、外交、商业等等都冠以神圣的名义,如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科普托斯政令、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所签订的合约等,都充斥着浓厚的神意。古代埃及的历史记述证明了一个处于宗教的严格束缚的社会是不会有史学产生的。古代的犹太、印度以及一些较为原始的民族的情况与此类似,他们可以有各种记录,甚至不乏历史记录和历史反思,只是由于宗教的禁锢而没有产生史学。⑤关于犹太历史意识问题可参阅:Millar Burrows,“Ancient Israel,”in Roland H.Baintons,et al.,(eds.),The Idea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128.
两河流域的早期城邦体制与古代埃及的神权政治存在区别。两河流域的城邦也存在神化王权的情况,但是通常来讲,国王是以人类的身份统治国家的。而且城邦保留了原始的共和制传统,王权受到长老会和民众大会限制。苏美尔早期城邦的一些历史记述和埃及同时期的历史记录相较,显得更为周详。以能代表这一时期历史意识最高点的乌鲁卡基那改革的泥锥铭文为例,这篇文献非常重视乌鲁卡基那上台执政和前任国王卢伽尔安达政治劣迹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出了对事件原因的重视。①郭小凌:《说古代近东的历史记录》,《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整体来讲,两河流域一直处于战争频繁、历史剧变的时代,所以两河流域的政权都注重城邦的霸权和帝王的伟业。然而,也正是由于战争频仍,中期亚述之前的诸多历史记录所存甚少。亚述的王室年代记当中,不乏叙事精细者,但是其中所述诸王战事,全以炫耀武力和威望为特征。比如辛那赫里布八次战役铭文,第一次战役的开篇写道:(我是)辛那赫里布,伟大的王、威武之王、世界之王,睿智的牧羊人……。②吴宇虹、李海峰等编著:《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在第八次战役的叙述中,国王的英武和威力达到极致:我砍断他们的脖子如同 (砍)献祭的羔羊。我割断他们的脖子如同割断一条线,我让他们的血如同雨季的大洪水流淌在广阔的地面上……,③吴宇虹、李海峰等编著:《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第370页。亚述的年代记读之唯感血腥之气,还不如早期苏美尔城邦的个别铭文具有一定的历史判断力。整体来讲,两河流域的历史记录基本是一种政治工具。我们通常不知道历史记述的记载者为何人,也看不到他们对事实真假的区分,偶有对前朝兴衰的反思,却又走向神意。比如阿卡德王国的纳拉姆辛便是失败的国王的代表,但是按文献所载他葬送了邦国是因为违背了神意。④Jean - Jacques Glassner,Mesopotamian Chronicles,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4,p.22.两河流域文明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达到像埃及宗教那样禁锢民众心智的程度,但是政治权力对历史记述的控制,致使历史记述行为完全沦为政治动机的附庸。赫梯和波斯的历史记录与两河流域的情况比较接近。波斯具有良好的档案保存以及历史编写制度,但是编年记录被王权所控制的情况从《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当中所记载的故事可知一二:国王亚哈随鲁睡不着觉之时,就吩咐人去取编年记事来读。
即便是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更为成熟的社会,如果政治体制对于个体自由的禁锢过度,一样不会产生自由的学术,包括史学,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便是一例,这个城邦从来没有产生一位古希腊的出名学者。这样,中国史学和希腊史学起源的优越条件便显而易见了,那就是政治环境和宗教信仰对历史记述来讲没有形成绝对禁锢,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相对理性。不过,中国和希腊的史学初始化环境差别很大,包括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知识学科体系等。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研究的台湾学者杜维运先生,在“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一文中特别强调了中西史学起源的比较问题,其中认为古希腊重哲思轻历史,其史学地位低微,所以如果和中国史学起源相比,西方根本不会有令人兴奋的发现。⑤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张越编:《史学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页。关于中西古代史学的学术背景差异可参阅: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564页。因为此处杜先生已经提出了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尤其是史学和哲学的比较,所以本文也就此问题略作探讨。首先,应该承认从整体来讲,古希腊的哲学和历史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上的分歧,是历史和哲学一直面临的基本冲突的根源。其次,古典时代哲学和历史学体现在各类著作中的交织是有限的,而且这种有限的交织牵扯到很多层面的复杂问题。
不过纵观西方史学的发展,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对史学的推动力就是米利都学派奠定的哲学思维,这种思维开始对外部世界进行一种本原推究,而这种思维用之于对社会和人生问题认识的时候,便产生了对事件原因的追溯。很明显,希罗多德的“历史动力”概念就是沿袭了由爱奥尼亚哲学家发展出来的“宇宙动力”的概念。①Eric Voegelin,The World of the Polis,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410.哲学意味着理性和科学地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这对于史学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促使植根于趋于普遍理性和科学的社会土壤当中的自觉历史意识的产生。
希腊人在认知世界方面确实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向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学习先进知识。不过这种幸运更多地来源于希腊人自己的求知与创新,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埃及人确实有众多方面的实用知识,而他们的知识并没有达到一种抽象的层面,比如数学一直局限于土地测量和实物分配这些和政府管理相配合的实用层面。巴比伦人也有日食和月食的记录,但是这种记录多用于占卜,而他们关于行星的运动、二分二至之说常常和神话与传说联系起来,他们的历法也很难说是科学严密。真正对这些知识进行总结升华并创立学科体系的,是希腊人自己。虽然古希腊人欠下近东民族很多文化和精神的债务,但是在目的论和方法论上,古希腊人找到了与近东民族不同的答案。与古希腊哲学的求知爱智相适应,希腊历史学的重要目的便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不受任何权利的支配,希腊的史学也讲求经世致用,但是为官方和统治提供借鉴的意图和中国史学比较起来则非常薄弱。②乔治忠在《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对中国官方修史的缺陷做了系统而深入分析。另参见乔治忠:《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朱政惠,胡逢祥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8页;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0-195页。古希腊哲学是几乎所有知识学科的母体,从其中孕育出天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生物学等,而历史学和医学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但是从古典史家的作品中很容易判断,历史是和政治、军事、地理、修辞等等知识联系起来的,所以历史很难被完全排除到知识体系之外。古希腊很多历史学家都受过哲学的熏陶,色诺芬本身就是哲学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受到来自所谓哲学层面的“贬低”的影响。相反,在阐述政体问题的时候,波里比阿认为哲学对普通人来说太晦涩,他宁愿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具体简洁地阐述问题。③[古罗马]波里比阿著,翁嘉声译:《罗马帝国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而且,希腊的历史记载难以印证哲学思维下的循环史观之类的“历史观点”。从黑格尔到柯林伍德的关于古希腊“非历史”的哲学角度的判定,需要谨慎考察。诚如以研究古典史学闻名的意大利学者莫米格里亚诺所评论:非要说柏拉图比希罗多德更能代表希腊文明只是一种主观臆断。④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9.每一种文明在给予历史记录的自由空间和知识土壤方面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区别。古希腊和中国虽然都产生了史学,但是其社会背景和知识底蕴区别很大,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从文献中钩沉。不过,如果在没有对文献进行全面考察的情况下,非要说古代中国史学优于希腊史学也是一种猜想。同时,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应该明确史学处在怎样的环境下才能更为健康地发展,这种比较对于当今的史学的健康发展也具有基本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