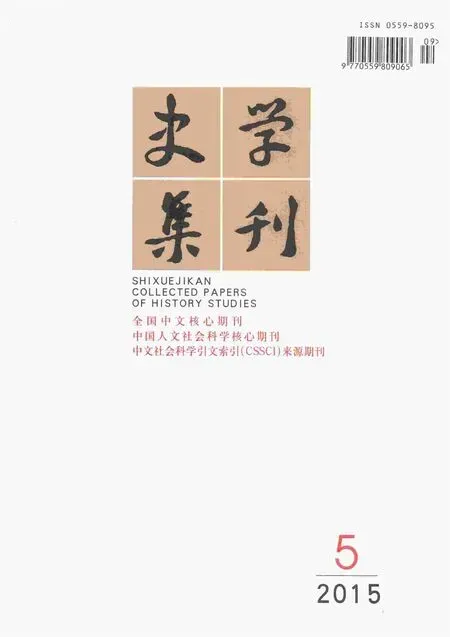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观
任东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阿诺德·J.汤因比 (1889—1975)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纵观其一生,几度沉浮、历经荣辱。汤因比自己也经历了类似于“文明兴衰”的过程。汤因比在1940年代中期声名鹊起,在1950年代中期却黯然失色,但在197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里又重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③William McNeill,“Toynbee Revisited,”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Vol.41,No.7(Apr.,1988):13.汤因比的两位同样大名鼎鼎的同胞——R.G.柯林伍德和E.H.卡尔分别对汤氏的历史观和国际观进行了批判。与其同一年出生的柯林伍德曾批评汤因比的“总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是自然主义的;他把一个社会生命看作是一种自然生命而不是一种精神生命,根本上是某种纯属生物学的东西并且最好是根据生物学的类比来加以理解。而这一点则与他从来没有达到过把历史知识看作是过去在历史学家心灵中的重演的概念这一事实有关”。④[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6页。对汤因比的历史方法和政治判断,比其晚出生三年的爱德华·卡尔一直持批判的立场。“事实上,汤因比很有可能是写作《二十年危机》的主要灵感。”⑤Cornelia Navari,“ Arnold Toynbee(1889—1975):Prophecy and Civi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6,No.2(Apr.,2000):296.卡尔曾嘲笑汤因比迷恋自由主义和“诸如集体安全这样的抽象概念”。⑥E.H.Carr,“Review of Toynbee,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6,No.2(1937):28.“汤因比教授坚持‘邪恶说’,认为这一失败 (指建立世界秩序失败)的原因是人的邪恶……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极端邪恶的时代,所以,汤因比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①[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 (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对汤因比最苛刻的批评来自于索罗金。他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知识到逻辑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并指出“这部著作两个根本性的缺点,这不是细节问题,而是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心脏和灵魂中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第一个是有关于汤因比把‘文明’当作历史研究中的单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作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基础的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的基本设想问题”。②索罗金:《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3页。尽管汤因比受到来自诸多研究领域专家的责难,但岁月并没有完全湮没他深邃的思想。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汤因比的许多结论已被质疑,但现代西方和整个世界依然需要正视他所捕捉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③Paul Costello,World Historians and Their Goals: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Illinois: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96.
汤因比漫长的学术生涯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研究主题的变化使汤因比的学术思想充满了争议性。汤因比曾自述: “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期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做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④[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汤因比曾作为公务人员为英国政府服务。汤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导致了他的研究主题不断地发生改变。“汤因比从民族到文明再到高级宗教的转移,虽然令人奇怪,但也可以理解,而且这种历史研究聚焦的转移深刻地改变了他的历史解释,也改变了他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⑤[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作为汤因比的朋友和学生,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马丁·怀特曾写道:“汤因比的职业生涯存在着一个悖论……汤因比发现他的合适职位是在大学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中间道路。”⑥Martin Wight,“Arnold Toynbee:An Appreci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2,No.1(Jan.,1976):10.因此,汤因比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学者,不同的学者在论述汤因比的历史学和国际关系方法时也持有相互抵牾的观点。戈登·马特尔将其界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⑦Gordon Marte,l“The Origins of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in Edward Ingram(ed.),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Essays in Honour of Elie Kedourie,London:Frank Cass,1986,pp.71-73.而肯尼斯·W.汤普森将其视为一个现实主义者,⑧Kenneth W.Thompson,“Toynbe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1,No.3(1956):365–386.默里·福赛斯和理查德·利特尔将其视为国际关系学英国学派的先驱。⑨Murray Forsyth,“The Class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Studies,Vol.26,No.3(1978):411-116;Richard Little,“The System Approach,”in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p.71 –91.查尔斯·E.琼斯认为,汤因比的态度已经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主义转向宗教乌托邦。随着宗教的路径压倒政治路径,《国际事务概览》对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准确分析,逐步让位给对国际动态不可能的预测。汤因比是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10]Charles E.Jones,“Christian Re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nglish School,”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3(2003):376.然而,汤因比学术思想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在令人困惑的同时,也拓展了其学术思想的弹性空间,更使其在全球化时代再次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
“全球化”是冷战终结以来最为流行的名词,“在学术界内部和外部的激烈讨论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取向,但关于‘全球化’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甚至没有一种近似的理解”。①Michael Lang,“Globalization and Its History,”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78,No.4(December,2006):899.围绕着全球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致形成了三个宽泛的流派: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以及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不和谐的、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极端全球主义者又分为两派,一方是欢呼个人自由和市场原则战胜国家权力的新自由主义者;另一方是主张当代全球化代表了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怀疑论者使用的是19世纪以来的世界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的统计数据,他们坚持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充其量只是表明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变革论者的核心论点是,确信在新的千年到来的时候,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塑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②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几乎与“全球化”这一词汇盛行的同时,“文明”这一概念在沉寂一段时间后,也重新获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众多学者的青睐。重申审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会对全球化理论的三大流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有助于修正极端主义者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有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的单位不是各个民族国家,而是各种文明形态;二是所有文明在哲学上是“同时代性”和具有同等价值。“对我来说,这种所有的文明在哲学上的同时代性的观点,由于被放到我们现代西方物理科学某些发现的背景中来加以看待而得到了加强。”③[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顾建光校:《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文明在哲学上的同时代性和具有同等价值,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诸种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和理解,这就否定了极端主义者中新自由主义乐观情绪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悲观看法。也正是这个原因,汤因比不太可能成为广泛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历史运动的创始人物。④Gordon Martel,“The Origins of World History:Arnold Toynbe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0,No.3(2004):343-356.针对文明是“不真实的”、国家是真实的观点,汤因比曾指出:“如果文明是不真实的,国家也一定是不真实的,因为国家和文明都是同一属性的现实或非现实。文明和国家都是人类关系的网络。”⑤Arnold Toynbee,“Review: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History and Theory,Vol.10,No.2(1971):251.然而,针对文明在新千年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崇拜偶像,有学者主张:“在我们已经进入的新时空中,文明不仅应该被‘消解’,而且应该挫其锐气。”⑥Bruce Mazlish,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0-161.尽管这种批评有其学术史的意义,但忽略了文明这一概念及文明史观能够提升各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经验,能够获得一种对历史综合、全面的解释,并对现实持有一种相对公允的认知和态度。
其次,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有助于消解怀疑论者的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中心论的影响。怀疑论者主要是以某一时段的经验且主要是欧洲经验来否定全球化,除了缺乏长时段的全球视野外,还忽视了对不同文明的比较,进而落入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汤因比指出,“形态学研究的方法必然是比较。形态学家必须对他所能收集的大量样本有一个宏观的眼光。”“无论是研究人类世界还是研究非人类的自然界,人们都要受制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是,在我们努力理解现实时,我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现实。”⑦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430,423页。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中心论就是歪曲历史与现实的根源所在。不可否认的是,汤因比的文明概念和文明史观未能将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这一重要的理念纳入进来。主体间性即人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在文明研究中,关于主体间性的强调表明,存在着对世界的不同视角、对世界本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现实”的不同认知。因此,“真实的世界”不是确定的和外在于思想的……不同的文明视角感知到不同的“现实”,这些不同的现实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①参见 Robert W.Cox,“Civilizations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in Mehdi Mozaffari(ed.),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2,p.5。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无疑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这种宏大叙事超越了人们容易陷入的历史狭隘主义——即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中心论。有学者认为,即使根植于 (文明)兴衰这一普遍法则基础上的普遍历史注定要失败,但人们在过去发现的模式也会成为我们头脑中的模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至少表明:这种尝试值得去做。②参见James Jol,l“Two Prophe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pengler and Toynbe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1,No.2(Apr.,1985):91-104。因而,汤因比文明史观所孕育的比较方法和全球视野,不仅消解了怀疑论者在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局限,也超越了怀疑论者的自我中心主义、狭隘的观念甚至是过度的专业化。
第三,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有助于提升变革论者解决全球化问题的认识能力。变革论者奉行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强调全球化的变革性和塑造能力。变革论者的观点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有诸多契合之处。“历史就是变化无常的事物……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不断地增添自身”。③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序言,第3页。汤因比还指出了人类文明存在的众多全球性问题,如污染问题、科技进步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④[英]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页。“现代人自满的根源是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科学成就虽然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是作为代价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在所谓发达国家中,物质虽然丰富了,但却引起了自然资源,引起了生产者的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抗争。”⑤[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97页。除了指出众多全球性问题外,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和文明视角还折射出当今世界的各个文明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之争。“无论是1920年代的斯宾格勒、1930年代的汤因比还是1990年代的亨廷顿,他们都凸显了根据文明和文化实体来观察全球秩序的异常强烈的规范性吁求。他们的语言、思想以及想象反映了与历史建构的密切关系,但也强烈感觉到文化信仰和集体想象。当然,他们也为争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套异常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⑥Andrew Hurrel,l“One World?Many Worlds?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3,No.1(Jan.,2007):138.文明史观和文明视角对于变革论者而言,是观测全球化未来趋势的一个有益的透镜。“变革可能内在于各种相互竞争的历史当中,也许这种自我赋予的诸种文明彼此碰撞或冲突是大规模变革的引擎。”⑦Barrie Axford,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Malden:Polity,2013,p.190.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将变革论者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远离了就事论事的困扰和束缚。
任何个体都是时代的“囚徒”,都无法彻底摆脱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89年曾指出,“汤因比对国际事务的分析而不是其历史著作,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根源。”⑧George Frost Kennan,“The History of Arnold Toynbe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36,No.9(1989):22.汤因比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我的历史观被染上了我个人生活经验的色彩。它一直受到我本人毕生的公共事务中所发生的各种好事和坏事的经验的刺激,而我则无法摆脱它。”⑨[英]阿诺德·汤因比、G.R.厄本著,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页。然而,伟大的历史学家却拥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智识和能力,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知识遗产。汤因比观照古今、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情怀所孕育的文明史观宛如一面透镜,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观测和认知全球化时代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来的“宇宙动力”的概念。①Eric Voegelin,The World of the Polis,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p.410.哲学意味着理性和科学地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这对于史学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促使植根于趋于普遍理性和科学的社会土壤当中的自觉历史意识的产生。
希腊人在认知世界方面确实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向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学习先进知识。不过这种幸运更多地来源于希腊人自己的求知与创新,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埃及人确实有众多方面的实用知识,而他们的知识并没有达到一种抽象的层面,比如数学一直局限于土地测量和实物分配这些和政府管理相配合的实用层面。巴比伦人也有日食和月食的记录,但是这种记录多用于占卜,而他们关于行星的运动、二分二至之说常常和神话与传说联系起来,他们的历法也很难说是科学严密。真正对这些知识进行总结升华并创立学科体系的,是希腊人自己。虽然古希腊人欠下近东民族很多文化和精神的债务,但是在目的论和方法论上,古希腊人找到了与近东民族不同的答案。与古希腊哲学的求知爱智相适应,希腊历史学的重要目的便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不受任何权利的支配,希腊的史学也讲求经世致用,但是为官方和统治提供借鉴的意图和中国史学比较起来则非常薄弱。②乔治忠在《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对中国官方修史的缺陷做了系统而深入分析。另参见乔治忠:《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朱政惠,胡逢祥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8页;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0-195页。古希腊哲学是几乎所有知识学科的母体,从其中孕育出天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生物学等,而历史学和医学被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但是从古典史家的作品中很容易判断,历史是和政治、军事、地理、修辞等等知识联系起来的,所以历史很难被完全排除到知识体系之外。古希腊很多历史学家都受过哲学的熏陶,色诺芬本身就是哲学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受到来自所谓哲学层面的“贬低”的影响。相反,在阐述政体问题的时候,波里比阿认为哲学对普通人来说太晦涩,他宁愿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具体简洁地阐述问题。③[古罗马]波里比阿著,翁嘉声译:《罗马帝国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而且,希腊的历史记载难以印证哲学思维下的循环史观之类的“历史观点”。从黑格尔到柯林伍德的关于古希腊“非历史”的哲学角度的判定,需要谨慎考察。诚如以研究古典史学闻名的意大利学者莫米格里亚诺所评论:非要说柏拉图比希罗多德更能代表希腊文明只是一种主观臆断。④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9.每一种文明在给予历史记录的自由空间和知识土壤方面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区别。古希腊和中国虽然都产生了史学,但是其社会背景和知识底蕴区别很大,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从文献中钩沉。不过,如果在没有对文献进行全面考察的情况下,非要说古代中国史学优于希腊史学也是一种猜想。同时,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应该明确史学处在怎样的环境下才能更为健康地发展,这种比较对于当今的史学的健康发展也具有基本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