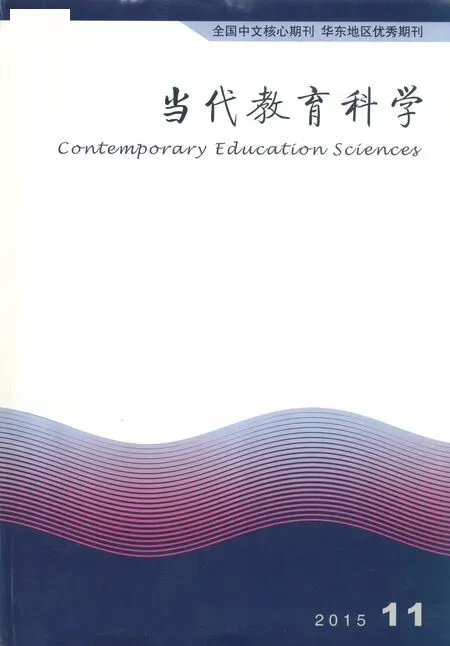现代“知识—权力”论的教育逻辑
●汤美娟
现代“知识—权力”论的教育逻辑
●汤美娟
知识社会学和福柯权力理论共同展示了现代知识体系的结构限制及其再生产机制。然而,在现代知识的“权力”运作机制中,学校教育所占据的枢纽地位及被规训者原有知识的能动作用被忽视。对学校教育独特作用及被规训者原有知识能动作用的发现和分析是对福柯权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知识分析体系。
学校教育;“知识—权力”运作;现代知识体系
知识社会学理论所揭示的现代知识的结构限制及意识形态性质给教育研究者带来了理论的启发,凸显了教育知识的生产机制。那么,具有结构限制和意识形态性质的现代知识如何被全社会所接受?这一知识体系又如何实现历时地延续?在此过程中,接受者的处境如何?这些便涉及现代知识的再生产问题。本文试图在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机制,并着重探讨学校教育在此机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接受者在其中的处境,以更好地理解教育知识的传递与再生产。
一、微观规训: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机制
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知识再生产,现代知识的再生产更顺利、更有效。这得益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新机制。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作用点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耻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1]也即现代权力运作试图形塑一种主体,该主体具有现代的思维方式,接受了现代知识的生产规则和程序。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现代人”的产生,与此相伴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被描绘为是对被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管的主体的定向生产”。[2]在此意义上,福柯说“主体问题”是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研究服务于主体问题的研究,它仅仅是为了“阐述主体如何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进入真理游戏之中”,[3]这也就同时解释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再生产机制。
尽管现代权力运作以人的灵魂为作用点,但这并非表示它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存在。相反,肉体在现代权力运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4]福柯称这些技术系统构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们扩散至整个社会,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部门。此外,由于这些权力技术的微观特征,它们的存在形式极为“隐蔽”。在福柯眼中,它们是“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的微妙安排”。[5]因此,要描述此权力运作模式,必须注意一些“细枝末节”,并将它们组织成一个“连贯性的策略体系”。
福柯凭借敏锐的理论眼光发现了隐秘于社会深处的规训技术,并将它们有机地连接为一个整体:现代权力规训模式。这一模式由以下几种技术构成:第一,对空间的分配。这一技术在“封闭”的基础上将空间进行“分格”,使其成为一个精细而严密的等级空间体系。这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基础。第二,对活动的控制。这一控制通过“活动和时间的吻合”、“身体各部分的联结”以及“身体和对象的啮合”三种方式实现。第三,时间的创生性筹划。这一技术将时间划分为连续的、平行的片断,并使它们按照“由简到繁”的原则形成序列。在这个时间序列的每一个阶段,每个人都会接受适合他自身特点的训练,并以考核作为结束。最后,技术通过精心计算的运作方式进行力量的编排,以实现充分利用每一个人。这种编排以“精确的命令系统”作为粘合剂,将不同年龄、力量的个人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组合。这样,这种技术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从单个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将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追求最高效率的机制。结合以上四种技术,现代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控制”,还是一种“训练”,具有生产和改造的功能。这是现代权力规训与以往规训机制的“断裂点”。然而,仅这四种技术并不具备这一功能,它们还需要一些微小的“规训手段”加以配合。福柯对其中最为关键的“规训手段”进行了描述,它们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这三者的组合赋予了现代权力规训以生产功能。层级监视将权力的目光分层,使权力作用对象的每一个举动都“彰明较著”,清晰而细致地控制成为可能。规范化裁决是规训权力系统的核心,它是一种“小型处罚机制”,主要对那些被遗漏于大型处罚之外的行为进行管制。这一裁决方式采取“奖—罚二元体制”,通过制定量化的计量方式,将所有行为纳入“好—坏”的等级序列之中。这样,它就可以“对人员本身及其种类、潜力、水准或价值……进行精确的评估”。[6]在此评估基础之上,规范化裁决采取“操练”惩罚的形式,也即“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这赋予该裁决方式以“缩小差距”和“矫正”功能。“它与其说是一种被践踏的法律的报复,不如说是对该法律的重申,而且是加倍地重申,以至于它可能产生的矫正效应不仅包括附带的赎罪和忏悔。这种矫正效果可以直接通过一种训练机制而获得。惩罚就是操练”。[7]最后,在现代权力规训系统中,检查将前两个规训手段结合起来,构成了权力运作的完整机制。检查通过“检阅”的形式将规训对象客体化,使之成为权力的凝视对象。以此,不可见的规训权力将可见原则强加给规训对象,将其固定于可见状态和被支配状态。与检查相伴随的是一套“书写机制”,它将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成为描述对象。这造就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做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8]这样,检查就将个体变成“个案”,成为权力运作的“轴心”。这三种规训手段的结合,确保了现代权力技术的运行,并保证了其生产和改造的功能,促使新的权力类型得以诞生。
现代微观权力体系的建立有效地将现代思维方式传递给规训对象,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现代观念的主体。这使得原本存在于某一群体的知识得以被其他群体接受,得以进入后代的思维,从而也实现了现代知识的再生产。
二、学校教育: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枢纽
在福柯所构建的“知识—权力”理论体系中,学校教育,和监狱、医院、军营、工厂一样仅仅是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众多领域之一。于是,他被称为“内敛教育家”。因为在其论著中,他虽然多次详细论述教育在“知识—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但却没有认识到学校教育的特殊地位,即现代知识再生产的“枢纽”。霍斯金意图对福柯的理论加以发展,他说道:“我的分析会将福柯的分析推进一步,因为当一个内敛教育学者已经不足够。我们必须正面去处理由教育实践方式的变化所产生的强大作用。”[9]这构成了霍斯金“知识—权力”理论的核心诉求。霍斯金将学校教育从福柯所列举的“知识—权力”运作的众多领域中拔起并置其于特殊的地位。他指出:“我们最终会走到一个景观奇特的交接点,发觉社会、制度和个人层面上的一切新现象,都可以在教育——这个看来是边缘的、无名分的领域找到自己的缘起。”[10]可见,霍斯金认为学校教育是现代规训制度与传统相断裂的节点,也是现代知识再生产的枢纽。也就是说,“知识—权力”在社会各领域中运作的推动力都来源于学校教育,它构成了现代知识再生产的动力源。
学校教育为何能够占据“枢纽”地位?霍斯金认为我们应依然追寻福柯的道路以求得问题的答案,即从微不足道的微型技术和实践方式中寻求答案。以此为研究原则,他发现学校教育中实践方式的细微变化带来了现代“知识—权力”运作机制的建立,使得现代知识的再生产成为可能。这些实践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定期举行严格考试;二、考试结果以分数评定等级;三、不断的书写工作,既有学生自己的书写习作,也有他人关于学生和组织上围绕学生的各种书写工作”。[11]这些变化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它们的相遇和结合却具有了所向披靡的力量:赋予现代“知识—权力”规训以内在的动力。霍斯金在文中论断道,“只有当书写、评分、考试这三种做法结合在一起,人类历史才发生重大变化,乃至出现断裂。……规训性知识的权力,直到这一刻才成为可想象的事。”[12]因为,它们的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权力类型,使得对人们的思维和精神进行塑造成为可能,从而也就使现代知识的再生产具有了可能性。在此权利类型的规训之下,第一批具有现代知识及思维的“主体”产生。当这些主体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其他领域时,他们将现代知识及思维移入其他领域,从而带来此领域中“知识—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他们是以上教育实践方式的规训产物,同时也是未来其他领域的规训者。因此可以说,学校教育是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枢纽。
三种教育实践方式的结合之所以具有如此效果,主要因为它们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结构。首先,这些实践方式在对学生进行规训的同时,将存于自身背后、支撑自身合理性的观念传递给了学生。以评分为例,“分数却不但用来互相比试,而且鼓吹竞争,为的是竞夺那些能显示自我有用之处的流通价值。分数给表现树立客观价值,用数量来设定十分是完美、零分是一败涂地的标准。”[13]对这一教育实践方式的接受便意味着对其中内涵的“竞争”观念的认可和接纳。与此同时,对该观念的认可和接纳反过来强化了评分这一教育实践方式的合法性。这样,评分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方式便被学生内化,成为一种“自动运行”的权力方式。“就这样,这些新型的学习者变成(懂得)自我规训、自我实现(的重要),是一群惧怕失败、永远追求奖赏的求真者”。[14]其次,这些教育实践方式所构成的精致的规训技术系统在塑造学生的思维和观念、使他们形成现代思维方式方面具有以往权力类型所没有的有效性。对此,霍斯金明确地论述道:“这些新的实践方式同时给学习者植进一种新而实在的知识力量。……给新学习者套上一大套新的建构知识的方法系统。作为新的自我,他们以新的语言提问、思考,并且书写。结果,他们出产了性质上崭新的知识形式。”[15]相较于以往的方法系统,这一方法系统更为强有力,主导着学习者对世界的认识,促使其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建构,当然也包括对教育的认识和建构。这样,以学校教育为枢纽,现代知识体系凭借新的权力类型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
三、表达—互动论: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内在张力
然而,现代知识体系凭借权力作用实现自身再生产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面临的是被规训对象原有观念和知识的能动作用。具体地说,现代“知识—权力”作用下的个体具有自主能动性,这一论断在许多研究的结论中已经得到验证。麦克.F.D.扬在研究学校课程中的意识形态作用时曾特别强调:学校教师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并非是被动地接受,而是经过了能动地理解。迈克尔.W.阿普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假定教育是被一小部分当权者有意识操纵的观念”[16]太机械了,被操纵者并非客观事物,他们有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因此,从个体来看,意识形态难以实现完全地再制,其内部总会发生极为隐秘的“变形”。古德森也曾以“在研究机构的改变的同时,应把重心放在机构中人的内部变化”[17]为原则,应用生活史方法展示了在英国重学术的学科传统作用之下,环境教育的创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与政府的斗争过程。于建嵘曾明确指出作为政治权力作用对象的底层并非是被动的,因此,他要求在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坚持“从底层社会内部的结构解读底层政治的运作逻辑”。[18]所有这些研究虽然存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它们共同展示了“知识—权力”作用下个体的自主能动性。
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现代“知识—权力”运作机制中也内含着个体能动性的作用。此能动性作用赋予了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知识—权力”运作以内在的张力。只是个体能动性在此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外在表现,个体所具有的传统知识体系及其思维逻辑是其能动性的来源。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体系并非是可以挥之即去的存在,它总是同现代知识体系相互斗争而存在。对此,金耀基所提出的“过渡人”概念有助于传统力量地发现。在使“传统—现代”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形成一个连续体的基础上,金耀基认为现代化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处于这一过程当中的人便是“过渡人”。在金耀基看来,“过渡人”在观念上具有“异质性”,这会给“过渡人”带来认知的冲突。“他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由于他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在心理上,积极地,他对‘新’的与‘旧’的有一种移情感;消极地,他对‘新’的与‘旧’的也都有一种迎拒之情。这种价值困窘与情感上的冲突造成了‘过渡人’内心的沮丧与抑郁,所以‘过渡人’是痛苦的人。”[19]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能动作用确实会体现为人们的“认知冲突”,但却并非必然,它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很多时候,“新”“旧”两种知识体系会在个体认知过程中发生“融合”,形成第三种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既不同于“旧”知识体系,也异于“新”知识体系。黄宗智在研究乡村文化变迁时所提出的“表达性结构—表达性主体”互动范式与此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这一范式之下,“主导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会由表达—表达转变为表达—互动。在表达—表达关系中,主导文化对于乡土社会来说,只能是凭其支配地位与话语权力而进行自身的霸权性再生产。在表达—互动关系中,主导文化走进乡土社会时,后者会对它所表达的结构根据自身的客观现实而进行解读和重构,在这种基础上,两者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则是一种互动性再生产。两种再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其结果的不同,霸权性再生产的结果只能是乡土社会对主导文化被动而无选择地接受。互动性再生产的结果将是复杂的,既可能是被动地接受,也可能是拒绝,还可能是主动接纳乃至内化。”[20]可以说,现代“知识—权力”运作机制建立过程中,传统知识体系的能动作用就表现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再解释”和“重构”。因此,现代“知识—权力”运作机制建立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与传统的张力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
可见,现代知识的再生产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直处于与被规训对象原有知识体系的相互斗争之中。这使得现代“知识—权力”运作的机制不再是简单的直线式存在,而是富有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构成了现代“知识—权力”运作机制的内在逻辑。
[1][4][5][6][7][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11,156,157,204,203,214.
[2]彼得·丢斯.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J].汪民安译.美术馆,2002,(1).
[3]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4.
[9][10][11][12][13][14][15][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0,52,46,47,47,47,48.
[16][美]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M].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
[17]Ivor.F.Goodson.Pat Sikes.Life histor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settings_learning from lives,Buckingham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75.
[18]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1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7.
[20]常君睿.教育主导的乡土艺术文化变迁——通渭书画热成因研究[A].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七辑)[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205.
(责任编辑:刘丙元)
汤美娟/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