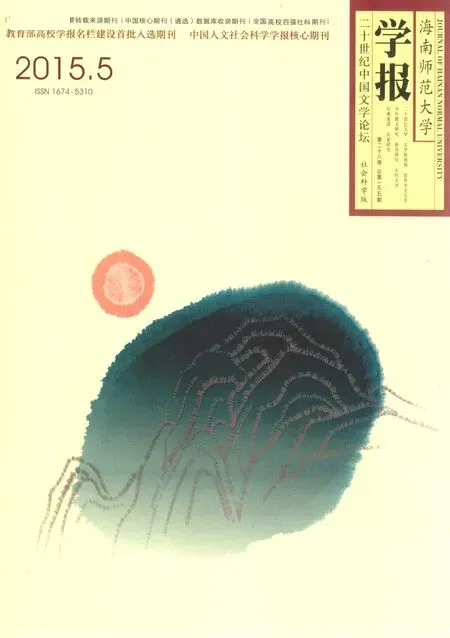现实主义:旧形式与新可能——论詹姆逊的现实主义观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350001)
划分文学史的段落时,现实主义肯定是无法绕过去的概念。如果需要采用这个习用的术语,那么,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是,除了用它来描述文学现象以外,还须有新的发现或突破而非完全陈陈相因。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詹姆逊给自己提出了两个问题:旧的概念形式还有必要注入新内容吗?怎样尽可能精确地定位这个充满矛盾的术语?就前者而言,詹姆逊给出的答案是,沿用旧术语可以跟传统保持联系。就后者来说,詹姆逊给出的策略是陌生化,也即是说,他试图在新的坐标系或关系网络中来考察现实主义。
一
众所周知,人们早已习惯了从内容方面来解释现实主义,而且,这也是讨论现实主义的强势思维方式。詹姆逊认为,不能止步于此。他建议,可以从形式方面来探讨现实主义,“不把现实主义看成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被动的、摄影似地反映和再现”,而是“把现实主义看成一个主动的过程,看成一种形式的创新,看成一种对现实具有某种创造力的过程”。詹姆逊坦言,他将使用的这种方法来自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它试图把现实主义的产生看作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的创造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的结果”。[1]278更具体、更准确地说,奥尔巴赫所谈的现实主义有两种,一是中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是现代现实主义。它们虽有很大差异,但在根本上,两者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文体有高低之分的古典规则,“顺应了我们不断变化和更加宽广的生活现实,拓展了越来越多的表现形式”。[2]换言之,在对真实进行诠释或摹仿时,现实主义应运而生,它不仅仅是创造了新的句法结构,更重要的是,实践了文体的突破与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新变的形式同时还是一种行动,“一种新的叙述形式需要取代老的、天真的、浪漫的叙事形式时,现实主义就产生了。‘幻想丧失’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的现实主义,或者社会暴露的现实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双重的行动,它在建立新的叙述形式和规范时,摧毁反映旧世界观的,已经失去意义的旧的叙述形式。只有以新的叙述取代传统的叙述,真正的现实主义才可能产生”。[1]298每一种文学形式都绝非一尘不染,而是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衰,往往表征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兴衰。在这里,詹姆逊强调的即是现实主义的一些叙述形式的新旧更替与新旧世界观更替之间的关联。因为有了这样的关联,现实主义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种行动。扩展开来说,詹姆逊还强调了任何新的叙述形式都是对时代直接的、积极的回应,都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品格。中规中矩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如此,求新求变、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如此,热衷于拼贴而少于创新的后现代主义亦如此。
另一种可以使我们对现实主义获得新认识的思考方式是,凸显金钱对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西美尔曾集中考察货币对生活风格带来的巨大影响,譬如,理智功能优于情感功能,生活风格趋于客观、算计、无特性等。[3]詹姆逊则认为,金钱不只是文学的新“主题”,更是其“来源”,“作为一切新的故事、新的关系和新的叙述形式的来源”。既然如此,文艺家就有责任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书写这些变化,而在描述这些变化、介入现实生活的同时,新的叙述形式自然也随之诞生。詹姆逊断言,“只有当金钱及其所表示的新的社会关系减弱时,现实主义才能逐渐减弱”,[1]299而货币给人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带来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这种影响不但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还滋生出另一些新的途径与范式。因此,现实主义必然也会产生新的形式,而不容易那么快就衰弱下去。
二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相互联系的形式阶段或文化阶段,詹姆逊着力找出它们在结构上的辩证关系,而且是可以用索绪尔式符号系统来加以说明的关系,同时,找出这些叙述形式跟特定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
索绪尔区分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前者是用来表意的物质形式,包括声音与形象两个部分,后者则是与上述物质形式对应的概念或意义。当然,这种对应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并非亘古不变,而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詹姆逊认为,除了能指与所指以外,还应该注意跟语言学关系不大的第三部分,即能指与所指标示的客观现实中的事物,它在任何语言行为中不可或缺。在詹姆逊看来,正是符号本身及其结构变化与世俗世界的化合,渐次产生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体而言,他把人类历史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四个阶段。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形态的结构古老而神圣,语言及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染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如果用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原始“规范形成”的时期。到了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去神圣化的世俗化。相应的,这个时代是“规范解体”时代。差别在于,詹姆逊认为,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说法未能展现出“物化”勇猛向前的解构力量。宗教衰退了,不再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扮演绝对主导的角色,而社会的超自然成分日益减少,整个社会不再有以往的种种神秘性。于是,一个真实的、外在的、不断扩展的世界摆在男男女女面前,崭新的经验与意义随之大量涌现。这是一个新时代,“符号中的三个部分形成的时代,参符产生的时代,语言参照系统中新的行为产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投射出一个存在于符号和语言之外的,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参照物的外在客观世界”。[1]284这个时代,文学语言对客体世界起着说明性作用,它被界定为现实主义。好景不长,催生现实主义及外在参照物的物化力量开始殃及现实主义模式自身,历史已经翻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页面。之前参符与能指、所指如胶似漆,而现今,能指与所指竟然弃客体的参符的经验于不顾,玩起了独角戏。尽管现实的世界仍然生生不息,但是,符号与符号组成的文化从中大规模撤离,愈来愈显示出一种“半自主性”。当文学倾力于符号内部的探索时,现代主义就已浮出水面。物化的巨能继续发力,辩证转化的下一站近在咫尺。后现代主义的阶段,能指抛开了所指,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沉迷于能指的嬉戏中,难以自拔。
沿着詹姆逊的理路,物化的力量驰骋不懈。在其理论演绎中,这一马克思主义遗产确有启人的洞见。问题是,物化概念在卢卡奇那里被发扬光大,曾经引发过激烈的论争。既然詹姆逊承继了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范畴,那么,此前的批评意见也就紧跟其后。“与卢卡奇一样,詹姆森集中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主观经验,此经验倾向于以意识问题和克服物化的需要来取代政治问题。此外,当詹姆森从破碎的心灵滑向全球总体性的时候,他倾向于逃避或削弱诸如团体特性、公共机构的实践以及民族国家之类本质中介的意义。”[4]换言之,文化的逻辑太过强大,以致于损害乃至湮没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詹姆逊笔下的物化还有过度总体化的苗头,资本主义物化的能力如此强大,抵抗是否可能?抵抗的能量又来自何处?至少,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概括中,人们很容易就感受到那种四处弥漫的悲观情绪。
三
现实主义内涵不稳,点燃过文艺界长期敌我相斗的战火,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两个同时并存又互不兼容的维度:美学与认识论。“对作品本身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技巧的任何强化意识,势必削弱对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真实内容的强调。同时,试图加强或支持作品认识论的使命的努力,一般都会压制现实主义‘文本’的形式特征,促成一种日益朴素、无媒介或反思性的美学建构与接受的概念。因此,只要认识论主张获胜,现实主义就落败;而且如果现实主义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或者是对世界的真实表现,它便因此不再是表现的审美模式,也就彻底脱离了艺术。”[5]跟美学领域里的其他概念相比,现实主义的这一内部矛盾或张力不免是一种缺陷——虽然詹姆逊又认为这种双重性具有独创性,因为如何在文艺作品里恰到好处地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了考验文艺家的一道棘手的难题。回顾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1928年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后,美学维度与认识论维度的论争从未消停过。其中,既有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之间的论争,又有左翼文学内部不同取向或派别之间的论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两者的关系确定下来:所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讲话》中不乏“辩证”的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但文学史的事实显示,政治标准第一更多时候无异于政治标准唯一。不过,认识论维度的一统天下并未能完全封闭美学维度的突围,或者说,作为一种美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其认识论维度也不可能彻底屏蔽美学维度。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界掀起的一次次大规模的整肃运动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到了“文革”十年,在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文艺界百花凋零之际,还有如野草般生长的不少“地下文学”、“秘密写作”延续了现实主义的血脉。
每当认识论维度占取上风时,对美学维度的辩护、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往往被斥责为“形式主义”,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之争也不例外。詹姆逊认为这场论争势均力敌,共同促进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然而,对卢卡奇的批判声音明显较强,他的一些观点与斯大林主义式的文学专制沆瀣一气甚至成了理论界的普遍印象。詹姆逊深为卢卡奇鸣不平,因为卢卡奇虽未公开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实际上对它十分厌恶,这从他当时用“自然主义”来称呼它可以看出来。要想公允地看待卢卡奇,就必须意识到,“卢卡奇的批评实践属于文类分析,它继承了文学话语中关于干预的各种理论,因此,如果把他简单地列入一种不成熟的模仿理论,说他鼓励我们像讨论‘真实’生活一样谈论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那无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的批评实践意味着对现实进行完全的‘真实展现’最终是可能的,就此而言,卢卡奇式的现实主义对社会纪实文学方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与最近那种将叙事文本视为符号游戏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对立”。[6]114不妨说,对卢卡奇而言,以文艺来干预现实至关重要,所以,文艺认识论维度的地位自然不可小视。从这个视角来看布莱希特,争论一触即发。不过,布莱希特眼里的现实主义既不是对现实的机械模仿,也不是单纯的形式类别。“‘现实主义’艺术品将‘现实的’和试验的态度同时进行,这不仅仅指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虚构的现实,而是指观众/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样重要的作家与素材以及技巧之间的关系。”[6]116
四
假如引入其它坐标系,那么,围绕现实主义发生的争论就会是另一番模样。“它在许多当代表现论批评中象征性的缺席,这弱化且过度简化了这里的一个濒于险境的理论问题。此即占有先机的叙事概念本身,它可以立马把艺术复制理论的种种诱惑永远消除,并使表现概念本身暗含的诸多假定变成面目全非的问题。”[7]165换句话说,在叙事理论的烛照下,先前讨论现实主义真实性问题的方式,乃至整套现实主义理论本身就成为问题,而现实主义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秘关系则浮现出来。在詹姆逊看来,意识形态时刻陪伴着我们,而且也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调适自我与社会的工具。因此,问题就转化为,作为一种叙事方式的现实主义,跟其它叙事形式相比,营造了怎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又对主体造成了怎样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可以借助与叙事相伴而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历史的与社会的详细说明。“通过指引(programming)读者,现实主义及其特殊的叙述形式为其建构出一个新世界。通过训练他们养成新习惯、开展新实践,培养他们在新型空间中新的主体位置。”[7]166毫无疑问,这个新世界生长的过程也是旧世界——无论是其经济基础还是其上层建筑——衰落的过程,是新旧势力相互博弈后重新组合的过程。现实主义是表述那些被压抑、被遮蔽经验的重要渠道,是命名、言说新世界中新经验的重要渠道。显然,现实主义打开了被封闭的现实,解放了被压制的主体,敞开了纷繁的经验,有着较强的去蔽性。从中也可看出,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一种直面现实的价值观。不言而喻的是,直面现实与作品的优秀与否从来就不能直接划等号。譬如,不能因为一个知名作家书写了计划生育这个敏感的话题,就头脑发热地把一大堆赞美的词汇统统加诸其身。在多数作家没有或不敢触及计划生育问题时,他率先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并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得失,应该说,这首先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敏感、良知与勇气。在这个基础或前提下,我们还有必要继续追问书写的好坏,譬如,语言、情节、结构、思想、意境等等各自处在怎样的水准。
按照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现实主义已经不太适合当代的文化形势了。但考虑到物化力量对社会阶级结构的隐匿以及它所带来的混乱与困惑,詹姆逊仍然把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现实主义之上。他期待这种现实主义能够“在消费社会里抵制物化的力量,重新发现被今天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社会组织中的存在碎片化系统地破坏了的总体性,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体系的情况下能够折射出其他国家里各个阶级之间的结构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概念将融合现代主义的辩证对立面中那些最具体的东西——在一个经验已经完全变成一大堆习惯和自动化的世界里,它强调对感知的恢复”[6]123-124。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深怀忧虑,这一历史阶段,物化危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下,男男女女的平常经验日趋碎片化、雷同化,他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或把握能力也日趋减弱。而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可以帮助男男女女们缝合众多经验的碎片,重新测绘被毁弃的总体性,重新定位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方位,重新审视这个结构中交错的阶级与阶层关系。问题是,当詹姆逊认为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拯救者时,有否把后现代主义给总体化?是否把后现代主义想得过于悲观了?有否忽视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积极一面?面对不可阻挡的强大物化势力,如果没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共同参与,就算要重测总体性,让人担忧的是,单单现实主义能够堪此重任吗?詹姆逊谈及总体性时,吸取了黑格尔、卢卡奇、阿尔都塞、阿多诺等人的相关思想。在后结构主义者把总体性与极权主义链接起来之后,总体性就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概念。因此,詹姆逊的总体性势必吸收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使其总体性包容足够多的差异。这也意味着总体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多种多样。关键在于,怎样的主体,测绘出了怎样的总体性,它是否有助于男男女女刷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宏大的总体性一朝垮塌,对总体性的测绘就成了一个西西弗斯式的行动。或许,这也就是大千世界中一部分男男女女的宿命。
[1]〔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20.
[3]〔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45-359.
[4]〔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5.
[5]〔美〕詹姆逊.可见的签名[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5.
[6]〔美〕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 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Fredric Jameson.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M].NY&London:Routledge,1992.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
——读《卢卡奇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