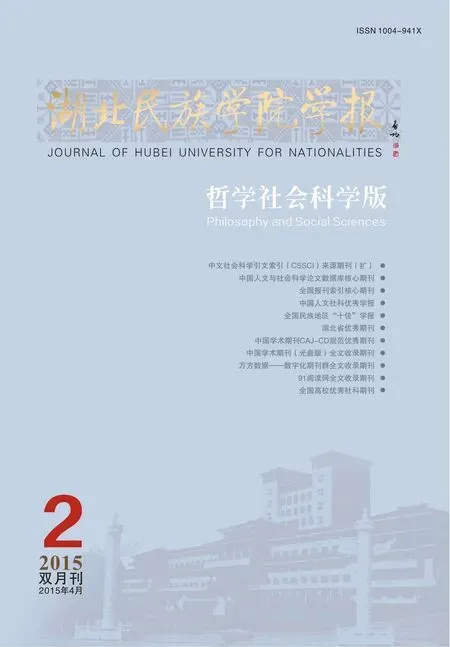论艺术形态中文字与图像的内在逻辑关系
彭 丽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论艺术形态中文字与图像的内在逻辑关系
彭 丽1,2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文字与图像是一种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二者既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在意指上都有实指性和虚指性。虽然文字与图像在历史演绎和艺术发展过程中是此消彼长的,但文字从没有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兴盛而彻底摒弃图像,图像没有也不会因为自身的兴盛而彻底摒弃文字。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文字与图像的发展是一个永远的实践。通过对文字与图像内在逻辑的深入分析,回答了当下文字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会消减、文学能否因视觉艺术的突起而走向终结的疑虑与困惑。
艺术形态;文字;图像;内在逻辑
日新月异的电子信息技术把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视觉时代、图像时代抑或电子时代。在此背景下,由新的科学与技术手段所催生的电影、电视、摄影等以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视觉艺术日益活跃在人类艺术的中心舞台,并似乎掌控了文化艺术的话语权;而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文学艺术则日益“失去轰动效应”,似乎被视觉艺术推向了边缘。有人曾由此预言:文学将在视觉时代走向终结。文字的价值和意义受到人们的质疑。
文字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会消减,文学能否因视觉艺术的突起而走向终结?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要探讨其关系,我们先区分下二者的概念。一般而言,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文明社会产生的标志。图像则有多种含义,其中最常见的定义是指各种图形和影像的总称,是由一系列排列有序的像素组成的。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当代西方学者对于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或侧重于文字,或侧重于图像,其研究成果难以客观而全面地揭示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如:巴拉兹·贝拉在其《电影美学》一书中预言,视觉文化的崛起,预示着印刷文化时代的到来,而语言将退居人类文化的边缘[1]28。即便着重探讨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也多是侧重于文字与图像的转化、配合、处理等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对于二者之间的相异与互渗及其内在逻辑生成关系关注不够。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传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其中金惠敏与赵宪章两位学者较具代表性。金惠敏注重图像与图像理论的研究,赵宪章则注重研究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其理论以“思想中心主义”为核心,“图像处于从属地位”的观点难免有失偏颇。总的看,以上理论都无法真正释解人们对文字价值和意义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归纳和考证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字与图像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解答当下人们对文字的质疑和困惑。
一、文字与图像的异质性
所谓异质性,即指语言与图像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每一种艺术形态都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如文学以文字符号为表现形式,影视以画面、声音及其动作等为表现形式,这种“特殊性”是由文字与图像的异质性所决定的。
倘若从存在与反映世界的方式来看,图像存在的方式是具象的,反映世界是直接的、直观的;而文字则与之不同,它以符号的方式存在,并以间接的、抽象的方式反映世界。如在“描写”一栋房子时,图像艺术呈现的是房子这一具象的存在,人们可以不通过任何中间环节便能感受到这一具象的特征和意义;而文字则以抽象的代码描绘房子的结构与特征,人们需要借助生活经验和想象力才能使文字具有具体意义,并结合具体语言环境感悟这一具象的象征意义。这是因为,作为意指符号,语言与图像从能指到所指,其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直线的”、“胶合的”,后者则是迂回的、并列的”[2]。正是由于语言的这一“直线的”、“胶合的”的结构特征,文字所呈现的事实与其自身意蕴是分离的,它只有通过所指才能与客观事物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同时需要接受者融入想象和理解;正是由于图像的这一迂回的、并列的结构特征,图像的所指也正是其能指的表征意义,接受者往往是在看到图像的同时理解其意蕴。
倘若从艺术表达效果和人们的思维活动看,文字与图像给予接受者的结果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感官所把握形式,另一种则是在人脑中最终的形式。对图像而言,这两种形式是完全一致的;而对文字而言,则并不一致。比如“梅花”,如果呈现的是一幅国画,人们在获得色彩、笔墨、线条等感官刺激的同时,能够感悟其美的内涵和意蕴,并将之传至大脑以记忆;如果呈现的是文字,不管是品读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足雪,为有暗香来”,还是吟诵陆游的“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人们对“梅花”的认知都是抽象的,从这些文字中对“梅花”的感知与其感性经验中的“梅花”是不可能一样的。再如,对“张三”的介绍,如果给出一幅摄影作品,人们便会很快记住其容貌特征;如果给出“张三”这两个文字,人们是无法感知“张三”的形象的,即使具体描绘出“张三”的容貌特征,人们记忆中的彼“张三”也非是此“张三”,只有与所介绍的“张三”相见或相识,人们才会把“张三”的形象记忆下来。由此可见,人们对图像形式的把握在感官和心灵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图像所反映的世界是直接的、直观的、具象的,相比文字更具形象表现力和审美震撼力;而人们对文字形式的把握在感官和心灵上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文字所反映的世界是间接的、抽象的,但这并不说明文字没有形象表现力和审美震撼力,这只是文字与图像相对的特征和意义。
事实上,文字有着自身独特的形象表现力和审美震撼力。就思想表达而言,文字比图像更为精准、更具优势。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3]158;赵宪章指出,“当文字与图像共处同一个文本时,文字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图像只是从属文字的‘辅号’”[2];赵炎秋也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图像对应的不是思想,而是世界的表象[4]。由此可见,文字与思想是同一的,文字的长处是表达思想。在文学艺术中,文字总以塑造形象为其基本任务,并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表达思想;当然,文字在塑造形象时有一个双重转换的问题,经过转换,文字的所指与能指都成为了形象的组成部分,这时,文字的思想表达功能暂居幕后,但仍在起着作用。而图像以具象的形式存在,其能指不能直接地表达思想,但图像有时又有直接表达思想的需要。图像通过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类型化与突出一定的语境等方法,使自己的能指直接与一定的思想联系起来,以达到直接表达思想的目的,如毕加索的绘画作品《鸽子》,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鸽子这一具象,更是对这一具象和平、友好思想表达的思考;再如,马格利特著名绘画作品《形象的判决》,如果在展览馆陈列或在客厅悬挂,其烟斗的形象会给人以无限的张力和哲学思考,但如果置放在公共场所,人们会不由自主将其联系到某种特定的概念,将之视为男厕或吸烟室的标志。在这些图像作品中,图像的具像在直接表达思想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只是这作用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服从着思想的表达。
二、文字与图像的双重性
所谓双重性,即指文字与图像意义指向既具有实指性又具有虚指性。文字与图像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有着自身的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二者的能指与所指。文字的能指是有规则的线条,所指是表征客观事物的概念,文字的建构性呈现的是一种“异构性”;而图像的能指是人们能够用感官把握的线条、色彩、体积等,所指是这些线条、色彩、体积所构成的具象所表征的意义,图像的建构呈现的是一种“同构性”。“异构性”决定了文字与其所反映的世界是不一致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字只有实指性抑或虚指性;“同构性”决定了图像与其所反映的世界是一致的,同样也不能证明图像只有实指性抑或虚指性。事实上,文字与图像在反映世界时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实指性又具有虚指性,这是因为人们的审美视角和判断依据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文字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只是一个或然的问题。
一般而言,文字是实指的,而图像是虚指的,这是由二者的意指功能所决定的。赵宪章指出,文字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这种生成机制使得文字获得充分自由,也使之准确的意指成为可能。正因如此,人们往往看到文字能指便能知道它的所指。但在文字艺术中,那种“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往往被打破,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意指关系。对此,我们可引用郭沫若《孔雀胆》一句台词来分析:“今天我们云南和大理联婚,但还缺少一位月下老人,所以请你在参知正事之前,还要参知婚事”,其中“参知正事”具有双重意义,就文字的符号意义而言,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官职,就其所指意义而言,它表明了故事中人物的身份;而由此变异而来的“参知婚事”,却丰富了文字的意指功能,充满了诙谐幽默而又让人浮想联翩的美学意蕴。在这里,如果从文字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看,“参知正事”与“参知婚事”是实指,人们很容易理解其能指和所指;但从文字与事物的关系来看,“参知正事”与“参知婚事”是虚指,存在着“意指落空”的问题,这是因为文字只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但却不是事物本身,文字并没有因为它的“约定俗成”而成为实指。正如黑格尔所说,字是从概念产生的,“诗人所给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名词,只是字,在字里个别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的东西”[5]。因此,文字的实指性只能从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来考量,如果从文字与事物的关系来考量,文字呈现的则是一种虚指。
赵宪章同时还指出,“相似性”是图像符号所遵循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图像必须以原型为参照,并被严格限定在视觉的维度,从而先验地决定了它的隐喻本质,符号的虚指性也就因此产生”[2]。在这里,赵宪章基于“思想中心主义”的视角,强调了图像的虚指性。由于图像是以具象的形式存在的,其能指与所指是多个向度的,也就是说,图像的能指不能明确地指向它的所指,比如,毕加索的绘画作品《鸽子》,图像的能指是鸽子这一具象,其所指则是多个维度的,或指向鸽子的概念,或指向对和平的呼唤,或指向友谊的传达,故而图像的能指功能与所指是不一致的,即图像是虚指的。但这种虚指性是从图像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来考量的,如果换一种视角去审视,即从图像与事物的关系来考量,图像是否存在实指呢?如果A人向B人呈示古代人的绘图肖像,介绍是某个历史人物时,B人是否会相信它就是某个历史人物的真像?B恐怕难以相信,即使是从历史文字记载中也难以真正感知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像,因此,判定绘图肖像究竟是何许人,既不取决于A人所介绍的语言,也不完全取决于A人的信誉度,而是取决于肖像绘图所表征的人的相似度。也就是说,图像能够根据其“相似性”原则如实或近似地表征事物,图像也因此具有实指性的意义。当然,图像的这种实指性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产生。赵炎秋曾为此列举了三种情况”[4]:一是图像应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如鼎由烹煮食物的器物演化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鼎的图像意指就从虚指变为了实指;二是图像应是类型化,如几个孩子出现在交通标志上,提示司机附近有学校、谨慎驾驶,标志上的孩子并非指代具体个体,而是一种类型,一种注意交通安全的思想,意指对象明确;三是应有图像的能指与所指产生了某种固定的联系的特定语境,如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判决》,如果置放在公共场所,便会与某种特定的概念构成联系,成为男厕或吸烟室的标志。由此可以看出,图像的实指需要一定的特定语境、文化传统等中介才能实现,它的意义指向依然没有文字那么固定和明确。
总之,文字与图像意义指向既具有实指性又具有虚指性。在图文共享中,究竟是文字占有主导性,还是图像占有主导性,既是由图文要素及其外部条件决定的,也是由人们的判断依据是文字还是图像来决定的,这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视角问题。
三、文字与图像的互渗性
文字与图像异质性、能指与所指内在的逻辑关系,决定了文字与图像是一种对立与统一的矛盾关系。说是对立,是因为文字是以所指表征事物,并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是思想形成的基础,这就使得文字在表征事物的概念与属性、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表达思想等抽象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图像则以能指表征事物,能指的要素主要是线条、色彩、体积等人的感官容易把握得到的,这就使得图像能够更加准确或近似地反映事物。说是统一,是因为文字与图像是对立的统一,二者是彼此渗透、相互支撑、密不可分的;是因为思想与表象是人类认知事物、把握世界、彼此交流与沟通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媒介。莱辛曾就诗歌与绘画进行比较,认为诗歌与绘画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和范畴,但却是相互渗透与包容的[6]156;陈平原也指出,图像可以把文字表达不清的东西变得一目了然,文字同样可以把抽象的哲理表述得准确而透彻[7]7。对此,我们也可以从人脑半球结构理论中获得支持。该理论指出,人的大脑分为左半脑和右半脑,左半脑主要司管抽象思维、象征性关系和细节逻辑分析,右半脑主要司管几何空间形象和特点,二者在功能上有分有合、互为补充,一同完成复杂的精神活动。该理论为文字与图像的互渗性提供了生理学的支持。
文字与图像的互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文字与图像相互支撑。相互支撑是指文字与图像在表现、交流以及效果上是互相依赖的。赵宪章指出,图像与文字的虚指性在一定意义是由其隐喻本质所引发的,当文字符号由实指走向由“语像”所图给的虚拟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整个语言艺术的世界”[2]。例如,“拖拉机像一只负重的乌龟攀爬一条蜿蜒的山路”,这里的“乌龟”不再是乌龟这一具象所表达的意思,而是“拖拉机”这一与其毫不相关的事物,于是“乌龟”由一种实指符号转化为一种虚指符号,并通过“相似性”与“拖拉机”发生联系。这句文字的优美及其所营造的意境,如果没有“乌龟”这一语象的支撑,其语言世界毫无疑问会大为逊色。当然,文字符号由实指走向由“语像”所图给的虚拟世界,并不仅仅在于“隐喻”,其主要原因应在于文字具有“构象性”,只是文字艺术将这一属性经过把文字意指转化为外在形象、再由外在形象转化为其内在意义,进而进入“图给的虚拟世界”。同样,具有虚指意义的图像也离不开具有实指意义的文字的支撑,如果欣赏一幅没有文字的绘图作品,人们肯定会不知所云。如动漫作品往往在综合文字、图像、绘制符号的基础上进行图像构思,虽然图像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没有文字的支撑,动漫便无法产生审美。
其二,文字与图像相互渗透。文字与图像的相互渗透性,如果从二者意指的逻辑关系看,是由其意指的双重性所决定的;如果从其符号意义看,是因为二者自身都各自包含了一些对方的因素,并且少不了对方的参与。一般而言,图像表征的是一种空间概念,而文字表征的是一种时间概念,但它们彼此都含有一些对方的因素,如“大与小”等文字符号意义是一种空间概念,图像的叙事功能表现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等。事实上,作为人类交流与沟通的媒介,文字不可能彻底离开图像而存在,图像也不可能完全摒弃文字而生存,正如赵炎秋所说,“没有纯粹不牵扯任何文字的图像,也没有纯粹不牵扯任何图像的文字”[8]。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原始人类正是通过图像进行表达和记忆的,目前考古发现的原始岩画、史前雕塑、人体装饰、陶器纹饰等,其内容和题材不仅涉及地理与天文、自然与社会,而且包括农事与狩猎、战争与礼仪等,这表明原始人类是“以图言说”的,也就是说,图像是其最主要的语言符号。文字产生之后,人类开始步入了“以字言说”的时代,但图像并没因此而消失,而是与文字走向了融合,从魏晋的“咏画诗”到宋元时期的“诗画一律”,从明代的“书法绘画”到清代的“诗画一局”,文字与图像形成了一种水乳相融的关系。
其三,文字与图像相互转化。从文字与图像的意指逻辑关系看,实指的文字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转化为虚指的图像。如看到“石榴”这两个字,人的大脑往往将之转化为石榴的图像,并随着对石榴大小、形状、色彩的文字描述,“石榴”的图像会更为清晰和丰富。再如,品读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诗句,“黄河”、“天际”、“奔流”、“高堂”、“明镜”、“青丝”、“白发”等图像会一一呈现在人脑中,这就是“看文生像”。在艺术形态中,由文字为工具来反映世界的文学,在影像技术条件的作用下,可以转化为以图像为工具来反映世界的文学的影视作品。从其“转化”效果和社会影响看,有的影视作品优于其改编的文学作品,如电影《集结号》的社会影响远远优于小说原作《官司》;有的影视作品却不如其改编的文学作品,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接受效果远不如同名小说。但这不能说明文字优于图像,也不能说图像优于文字,因为文字与图像是两种不同的媒介,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同样的道理,图像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条件转化为实指的文字。图像所反映的事物永远都是单义性的事物,它是具体的个别的,它的含义是特质和有限的。事实上,每一个图像都对应着词语,人们对任何一幅反映事物的图像,都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文字。
四、文字与图像的失衡性
所谓失衡性,是指文字与图像在历史演绎和艺术发展过程中不是同步前行,而是此消彼长的。从“以图言说”的“图像时代”,到“以字言说”的“文字时代”,再到当下的视觉时代、图像时代抑或电子时代,文字与图像在竞相“驱逐”,其结果是文字没能取代图像而存在,图像也没能将文字驱逐“像外”。从其“角逐”的诱因看,既是因为文字与图像具有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也是因为人类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科技的发展水平,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字与图像都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思想、进行交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媒介。
从符号形象的意义上来看,图像相对文字有着绝对的优势,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形象的本质是感性、直观的,图像能够瞬间抓住人的注意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而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和传媒技术,更是为影视、摄影、绘画、广告等图像艺术提供了无比优越的物质条件,图像艺术由此走上了超越文字艺术的“霸主地位”,成为人们理解和认识世界与事物的主要途径;同时,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物质性、符号性以及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等特点的消费文化,呈现了一种审美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展趋势,它一方面凸显了图像艺术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从图像艺术中获得了视觉快感和心理满足。但这能否说明文字功能的消弱和地位的降低?
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关于文字与图像关系的探讨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欧洲,图词之争源于公元前三世纪,在希腊艺术走向“视觉中心”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以得于视觉者为多”[9]47,并把图像作为知识的符号;而《圣经》则认为词是万物的本源和万物背后的本质。在我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一说,从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大象无形”,到王充的“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10]364,都强调文字的重要意义;而《周易·系辞》则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强调了图像的作用;从魏晋时期的“咏画诗”、宋元时期的“诗画一律”到明清时期的“诗画一局”、“诗画一法”,则突出了文字与图像的融合。从这些文字与图像的争辩中,我们无法作出究竟是图像优于文字还是文字优于图像的判断,事实上,对文字与图像关系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就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文字与图像符号类型之间形式或学术上的问题,它更超越了概念的日常考辩或维持艺术史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它似乎成了一种符号、审美和社会差异间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文字与图像的发展是一个永远的实践。
五、结语
马克思指出,当整体“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5]。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论揭示了人类是通过理论、实践和艺术三种形式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表象与本质的统一、形象与思想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文字与图像正是这种“统一”的手段和媒介。如果摒弃文字,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就会局限于表象、形象和感性;如果摒弃图像,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就会局限于本质、思想和理性,而本质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思想是以形象为载体的,理性也是以感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表象、形象和感性的本质、思想和理性是不存在的。表象与本质的统一、形象与思想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决定了文字与图像的统一,这种统一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据此,我们说,文字的价值和意义丝毫不会因为图像的兴盛而消减,文学也不会因视觉艺术的突起而走向终结,恰恰相反,文字以及由文字为主要表现工具的文学将会和图像以及由图像为主要表现工具的视觉艺术走向新的融合。
[1] 巴拉兹·贝拉. 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 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文学评论,2012(2).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
[4] 赵炎秋.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J].文学评论,2012(6).
[5]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6] 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陈平原.看图说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 赵炎秋.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研究[J].文艺研究,2012(1).
[9]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叶朗.历代美学文库·秦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5-01-0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艺术中的文字与图像研究”(项目编号:12YBA239);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当代视觉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反思”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00666)。
彭丽(1979- ),女,湖南株洲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
I022
A
1004-941(2015)02-01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