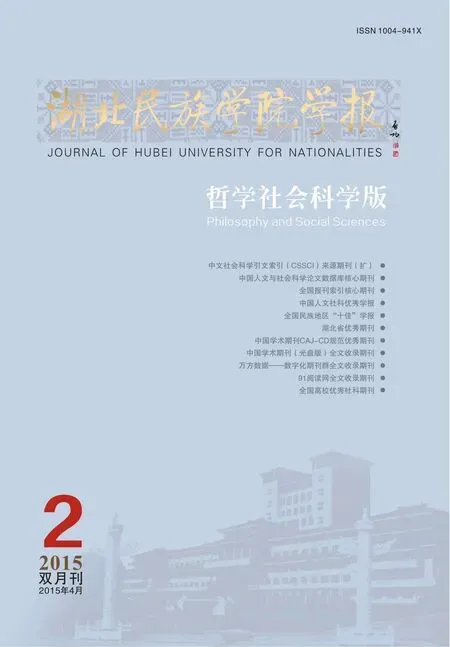清代乾隆时期新疆伊犁哈萨克贸易及其历史作用探微
张付新,张 云
(1.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2.塔里木大学 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清代乾隆时期新疆伊犁哈萨克贸易及其历史作用探微
张付新1,张 云2
(1.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2.塔里木大学 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清代新疆哈萨克贸易是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的重中之重,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贸易发展迅速,其贸易中心地点也从乌鲁木齐转向伊犁,客观上成为这一时期清朝政府治理边疆政策之哈萨克政策走向的重要考量。
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贸易中心地点;历史作用
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对哈萨克进行有效地统治和管理,针对哈萨克贸易制定灵活融通的民族贸易政策,并取得预期的统治效果。其中乌鲁木齐成为新疆哈萨克贸易最早的贸易地点,后来伊犁则成为清朝政府与哈萨克之间的贸易中心地点,学界对乾隆时期伊犁成为哈萨克贸易中心地点的研究极少,鉴于此,对伊犁成为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贸易的官办贸易中心地点的相关研究还有深入挖掘和探讨的空间,笔者不揣浅陋,比较系统地对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发生、发展到新疆哈萨克贸易中心地点的最终形成等历程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期对既往相关研究能够有所推进和深化。
一、政治交好:清朝政府与哈萨克开展贸易的来源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并统一西域之后,与哈萨克草原上的哈萨克三玉兹汗国有了广泛的接触,哈萨克三玉兹首领先后遣使赉表入觐行礼,主动归附清朝。乾隆二十二年六月(1757年),哈萨克中玉兹首领阿布赉悔过投诚,称臣入贡,并遣使者至热河行宫上表进贡,并在表文中表明“自臣祖额什木汗、扬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今袛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1]511,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哈萨克大玉兹首领阿比里斯之子吐里拜遣使入贡,在表文中表明“近闻左部输服,臣愿竭衰弩,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倍于左部”。[2]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哈萨克小玉兹首领努拉里(或努拉利)遣使入京朝觐,称臣归属清朝政府。“哈萨克三帐主动请求臣属于清政府,请求与清政府建立政治、经济交往关系,除了前述历史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无疑还有不堪沙俄压迫,希望得到清政府保护的愿望。”[3]由此,鉴于哈萨克三部首领“输诚内向”,清朝政府与哈萨克确立了正式的政治交往关系。此刻,“清廷对哈萨克汗国采取的策略总结为颇具时代特色的‘两优、三不’①所谓“两优”,即在政治上给以优待,经济上给以优惠。所谓“三不”,即不设官置守、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对哈萨克汗国与其它部落的纷争与冲突,不予介入;对沙皇俄国侵占哈萨克领土的行为,不予过问。转引郧军涛.中俄两国对外策略中的哈萨克因素[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20.策略。”[4]20双方经济交往也随之展开。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就提出通商贸易的愿望,“阿布赉请于乌陇古地方,将马匹易换货物,告以道远,商贩不便,约于明年七月,在额林哈毕尔噶、乌鲁木齐等处交易等语。”[1]549清朝政府则考虑“乌鲁木齐地方可以耕种,又与吐鲁番相近,若哈萨克往来交易,亦属甚便,今陕甘马匹仍须多备,请于明年哈萨克马匹到日,前往交易等语。”可见,清朝政府开始着手和哈萨克贸易准备工作,最初以民间贸易形式和哈萨克进行绢马贸易,“阿布赉请将马赴乌鲁木齐交易,臣等议以途远,商贩难集,请官为经理,选熟谙交易之人,照商人例,不必显露官办形迹。”[1]564因之前与哈萨克阿布赉有约在先,贸易地点定在乌鲁木齐,产生的额外浩繁运费由清朝政府承担,清朝政府也着手制定贸易章程,不可迁就,互惠互利,以示公平。“今既仍在乌鲁木齐交易,应否添派兵丁,亦听该督酌量办理,明岁系初次贸易,自当立定章程,不可迁就,而交易之际,又必示以公平”[1]565,由于哈萨克商队不能按照规定时间到达乌鲁木齐交易,清朝政府与哈萨克的贸易无功而返,还对此做好以防万一的前期工作,“今办理回部,业将竣事,无须多办马匹,伊等即逾期未到,不妨将货物存贮,俟其来时,再行交易,亦不可加以催督,于驾驭外藩之道,方为允协。”[5]362这一年秋季,哈萨克率商队前来进行首次贸易,清朝政府由此与哈萨克正式建立通商贸易关系,“今秋哈萨克前来贸易,顺德讷熟习哈萨克等情形,请令在乌鲁木齐驻扎,办理贸易事务等语。……谅秋季贸易之事,自不致迟误,可传谕兆惠、雅尔哈善、努三等知之。”[6]22同时,清朝政府“还派遣安泰到乌鲁木齐,总理屯田贸易事务。”[5]362此后,乌鲁木齐成为清朝政府与哈萨克贸易最早的官方贸易地点之一。由于哈萨克人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丝织品和锻匹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补充,清朝政府为了方便与哈萨克进行贸易,“还派专人在陕西等地采办各种锻匹,限期运往乌鲁木齐等贸易地点。”[2]这些措施推动了双方贸易的持续发展,贸易地点也随之不断增加,由最初的乌鲁木齐发展到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除日常进行定期贸易外,清朝政府还派军队驻扎贸易地点,开垦屯田,防范哈萨克“滋事抢掠”。“哈萨克抢掠乌梁海,系阿布赉属人,看来必非阿布赉本意,乃所属托名滋事,但哈萨克人等,素性喜于侥幸,一面在乌鲁木齐贸易,一面在他处抢掠,亦事之所有,……亦当预为防范,”[6]401清朝政府与哈萨克通商以来,哈萨克与清朝政府建立坦诚相待、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与哈萨克的贸易发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1760年),清朝政府开始在伊犁驻兵开垦屯田,把伊犁作为“新辟疆土”进行开发建设,“现在伊犁未通贸易,绿旗兵于开垦营造,亦属勤劳,请一体支给,俟秋收后,再照旧例等语。”[6]434为伊犁成为继乌鲁木齐之后的另一贸易地点奠定了前提条件。同时,清朝政府考虑到厄鲁特之地“现俱闲旷”,哈萨克迁移游牧,颇属宽广,准许哈萨克人到伊犁地区游牧,“将来准哈萨克人等,至伊犁游牧等语。”[6]458并在乌鲁木齐、阿克苏、叶尔羌、伊犁等处均设大臣驻扎,鉴于伊犁处于乌鲁木齐与哈萨克通商贸易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清朝政府已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开始采取“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统治政策,清朝政府派官兵对伊犁进行正式管理,开垦屯田,这使清军的耕畜数量需求量急剧增加,使伊犁日益具备清朝政府扩大与哈萨克贸易地点的现实条件,“现在乌鲁木齐与哈萨克贸易,彼处系通伊犁大道,若调辟展办事之副都统定长往乌鲁木齐,同安泰承办屯牧贸易等事,应有裨益,若辟展,则不过与冲繁台站相等,酌派官兵管理足矣。”[6]464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其游牧牧场大片闲置,这时“清朝政府准许哈萨克族进入放牧。从18世纪60年代起,哈萨克人的牧地就扩大到塔城、伊犁、阿尔泰地区。”[7]与乌鲁木齐相比,哈萨克在距离较近的伊犁放牧并进行贸易更为方便,减少了交易成本,符合哈萨克人的实际利益需求。所以,伊犁更能成为哈萨克商队进行商业贸易的理想地点,他们也愿意前往伊犁交易,“据阿桂等奏称,乌鲁木齐虽亦有屯田事务,但事已就绪,不比伊犁初次办理,且金梁素系兼管哈萨克贸易事,哈萨克现闻伊犁屯田,必驱牲只前往,可传谕安泰,明岁遣兵丁往伊犁时,即令金梁管领,并传谕阿桂知之。”[6]494由于伊犁驻兵屯田的发展,伊犁哈萨克贸易有所发展,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为将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处缎匹送至伊犁与哈萨克贸易事折提到“奏报哈萨克人来伊犁贸易,政府换获29匹马的情况,请求从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处调拨缎匹送至伊犁,以备今后贸易所需。”[8]55随后,伊犁哈萨克贸易继续进行,所需绸缎均从阿克苏、哈密等处和内地调拨并解送伊犁,阿克苏办事大臣舒赫德奏为将阿克苏缎匹送往伊犁以备与哈萨克贸易事折中提到“奏报哈萨克将到伊犁进行贸易,请求从阿克苏库贮缎匹中拨150匹黑色、红色及杂色缎匹,由驿站运送至伊犁。”[8]56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为调拨与哈萨克贸易所需绸缎事折中提到“与哈萨克陆续贸易,伊犁库贮绸缎用尽,请求从哈密库贮绸缎中调拨1000匹,由驿站分批解送伊犁。”[8]57据统计,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奏报与哈萨克贸易用过缎匹及换获马匹数目事折中提到“奏报十一至十二月间,哈萨克四次来伊犁贸易,共换获578匹马以及用过缎匹数目,”[8]57同年的十二月,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奏为购买前来贸易之布鲁特哈萨克羊只以供伊犁驻防官兵食用事折中提到“布鲁特尼沙、哈萨克拜萨里等牵1200只羊前来伊犁贸易,”[8]57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奏报与哈萨克贸易缎匹换获马匹数目事折中提到“奏报正月初四至正月十四日,威孙奥托克哈萨克塔买巴图鲁、亚克西拉克等三批人来伊犁贸易,政府共换获386匹马,其中一等骟马122匹、堪用骟马139匹、儿马125匹,还获牛7头,”[8]58同年二月,伊犁参赞大臣阿桂等奏报与哈萨克换获马匹数目事折中提到“奏报正月二十日至二月十五日间与哈萨克进行五次交易,共换获448匹马,其中一等骟马207匹,堪用骟马136匹,儿马、骒马105匹,”[8]58以上可见伊犁哈萨克贸易换获的马匹、羊只贸易成交额增长迅速,和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总体上已不相上下。
正如学者所认为,“清朝便把它和乌鲁木齐同样都当成长久的官办贸易地了。”[5]363由于伊犁屯田牧放规模的扩大,清朝政府对不断前往伊犁等地的哈萨克、布鲁特采取“已为大皇帝臣仆,事同一体,不便给回,亦不必向伊等稍为隐饰,”[6]496同时,这一地区的屯种粮饷事务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阿桂等奏,现在伊犁屯种等事,需员料理,恳就于乌鲁木齐所有满员,或同知,或知县,拣派一员,令往伊犁承办粮饷等语。”[6]498此时,随着西北边疆版图的扩大,清朝政府亟待调整统治政策,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因念陕甘总督,所辖既广,势难兼顾,是以准议将陕甘总督,改为甘肃总督,而陕西一省,归于川督管辖,”[6]504后来又考虑到甘肃总督“无鞭长莫及之处,莫若仍旧管辖,著将甘肃总督仍为陕甘总督,统辖二省,其四川总督,不必兼管陕西。”[6]504
二、互通有无:乌鲁木齐、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开展
由于清朝政府与哈萨克贸易的日益频繁,乌鲁木齐通过贸易交换的马匹牲畜数量大为增加,急需派兵丁进行专门管理,而“现在伊犁设立牧场,蒙古兵丁甚多,则乌鲁木齐马匹牲只,皆可解送伊犁,交与阿桂编群孽息。”[9]1及时缓解了乌鲁木齐马匹牲只容载量的压力。针对伊犁和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迅猛发展,清朝政府准许哈萨克商队在乌鲁木齐、伊犁和乌里雅苏台三地均可进献马匹和贸易,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朝政府对办理哈萨克贸易的谕旨是“据称,因道远多带马匹,并非专来贸易,若有愿售者,亦可变价等语。哈萨克全部为臣仆,其在西边游牧者,与伊犁、乌鲁木齐相近,自应在彼贸易。至阿布赉游牧,与古尔班察尔相近,在北路行走为便,伊等情愿来乌里雅苏台贸易,亦无不可。”[9]121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新疆生聚日繁,屯粮丰获,而乌鲁木齐等处,换获贸易日盈,应随时变通,以节繁费。”[9]202此外,哈萨克商队还在叶尔羌等地进行贸易,清朝政府要求管理此地的办事大臣满州官员要学习“清语”,“哈萨克前来叶尔羌贸易一折内,清语不通,素诚系满洲奴仆,又在回疆办事,理宜勤学清语,折内竟有不成话者,皆由素不熟习所致,著严加申饬。”[9]214除了与哈萨克进行的官方贸易之外,清朝政府准许内地商人来疆与哈萨克进行民间贸易,开放贸易地点仅限于乌鲁木齐、伊犁两地,“谕以内地商人俱在伊犁、乌鲁木齐,尔等若欲贸易,自可前往,”[9]222但后来被清朝政府定性为“是以将军等禁止贸易”[9]222,这种区别于官方贸易的私人贸易随之又被禁止。同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于清朝政府派兵驻扎塔尔巴哈台,哈萨克商队随之前往并通商贸易。而塔尔巴哈台与哈萨克“交界甚近”,它又与伊犁相接,由此致使乌鲁木齐的哈萨克通商贸易日益萎缩,“再塔尔巴哈台驻兵后,哈萨克不至乌鲁木齐贸易,”[9]224面对这种困境,时任伊犁将军明瑞提出有利于清朝政府的对策,“雅尔筑城以后,哈萨克商人必就近贸易,此例一开,则所用缎匹银两,既须从伊犁运送,而所换马匹牲只,又须送往伊犁,殊为繁琐,请饬谕哈萨克商人,俱向伊犁贸易,其有携带牲只数少者,如雅尔有须补额之处,亦仍令其交易,但伊等路费既省,其马匹等作价,应较伊犁少减。”[9]248此外,清朝政府还建章立制,以鼓励哈萨克商队前往伊犁进行贸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对前来雅尔进行贸易的哈萨克商队“量收牲只,以备屯田,其大队商贩,仍令前往伊犁,但恐哈萨克等贪图就近,不复前往伊犁,其价值应行酌减。再预备赏给之缎布茶叶,均请照伊犁之例。”[9]277这样,使乌鲁木齐和伊犁继续成为与哈萨克进行贸易的官方交易地点得以维护。对于驻扎清朝官兵私自与哈萨克贸易时常发生,清朝政府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若任官兵私与哈萨克贸易,恐滋盗窃之事,且私买价贱,官购价昂,亦为哈萨克所笑。……若有私相贸易者,查明从重治罪。”[9]355上述措施使哈萨克商队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开展的贸易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对于哈萨克霍集伯尔根内徙之事,清朝政府明确昭告,“雅尔、塔尔巴哈台等处,设卡驻兵,原以驱逐内徙之哈萨克,逐之不去,自应从重惩治,五岱所办,并不为过。……及哈萨克不应内徙,如违定行重惩之处,一一明白晓谕,并移咨阿布赉知之。”[9]366不久对哈萨克塔塔拜等人再次请求内附,清朝政府随即准许,将他们安置在地广人稀的伊犁等地,还编设佐领昂吉进行管理。“有哈萨克塔塔拜等恳请内附,朕谕令安插雅尔地方,或由厄鲁特,或由哈萨克内,派员管辖。”[9]367随着哈萨克的不断自愿内属,清朝政府欣然应允并参照哈萨克来投者的体例,对后来回归的厄鲁特部众一视同仁。“现在伊犁、雅尔,由哈萨克来投者甚多,其带来物件马匹,并未给回,哈萨克、布鲁特事属一体,岂可参差办理,殊属不晓事体。著申饬,嗣后有来投之厄鲁特,俱照哈萨克来投者,一体办理。”[9]373由于哈萨克性情豪放和随意性强,他们并不遵循清朝政府规定的官方贸易地点,在喀什噶尔、乌什等地随处进行私人贸易,把商业渠道由天山北路扩展至外蒙古等地。由此导致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绢马贸易减少,已影响了官方的哈萨克贸易的正常秩序,甚至无法保障驻扎官兵马匹牲畜需求。因为伊犁驻防官兵所需牲畜经哈萨克贸易所获,由此使清朝政府下令禁止哈萨克商队开展私人贸易,对违犯规定者严令治罪,“据阿桂奏称,伊犁贸易之哈萨克,近甚稀少,询据哈萨克贝克等禀称,伊等牲畜,均予游牧处,经喀什噶尔之回子易去,恐于伊犁等处需用牲畜有碍,且彼此来往贸易,日久必致滋生事端,已移咨绰克托严行禁止,并欲令哈萨克将伊货物扣留,其回子拿解伊犁治罪等语。”[9]388-389还禁止喀什噶尔回众前往哈萨克所在地贸易。
三、顺势赶超: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发展
由于清朝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较好的协调了各方利益,规定地点的官方贸易日渐繁荣,其中伊犁的哈萨克马匹贸易交易额增幅尤为明显,并从换获的哈萨克马匹中挑选膘肥马匹送往乌鲁木齐等处作为添补营马,“据阿桂奏称,现今伊犁换获哈萨克马匹稍多,……俟伊犁送到马匹时,即添补营台马匹,其如何交价,并较内地买马价值,节省若干之处,一并奏闻。”[9]407由于在伊犁交易的哈萨克马匹数量增加,加之伊犁设牧厂数处,滋生马匹,规模日益扩大,它已成为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马匹的主要运送来源地,甚至补缺与新疆临近的甘肃各标营缺额之马,一度还充补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马匹,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伊犁换获哈萨克马匹,近年为数渐多,经将军阿桂奏准,于牧厂内拣选二千匹,运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添补营台缺马,如尚有余剩,再转送内地甘肃各标营等因。……今伊犁既有此项余马,与其给价购买,不若通融拨补,请嗣后将伊犁贸易马匹,除将盈余解送甘省内地外,即由近及远,递次充补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缺额。”[9]413由于伊犁到内地路程遥远,官兵长途解面临解送人困马乏、途中难以赶牧等诸多困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朝政府对此谕令道:“查此项马匹,解往内地,既非一时急需,且自伊犁至内地,道路窎远,沿途若无停牧处所,马力亦不免疲乏,自应如该督所请。……将来自伊犁起解时,如沿途适逢冬令,即不妨暂留牧放,俟天气和暖后缓解,其由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解赴内地者,亦酌量时令,应于何处择水草休息喂养之处,均交与该将军及该督酌办。”[9]414同时对伊犁负责屯田事务任期三年的官员任命也做了调整,从内地调往官员前往伊犁接管,乾隆三十二年九月(1767年),“即照阿桂所奏,著肃州总兵俞金鳖,前往伊犁管理屯田事务,再留玛琥数月,协同办理,俟其谙习时遣回。”[9]414布鲁特哈萨克人不断前来投诚,清朝政府将他们设官妥善安置在伊犁,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据伊勒图奏称,伊犁地方,陆续由哈萨克布鲁特前来投诚之厄鲁特,日渐繁多,请于正蓝、镶蓝二旗各添设一佐领等语。”[10]18由于乌鲁木齐屯田所获粮食收成入不敷出,清朝政府把伊犁哈萨克贸易所换牛羊折变作为口粮接济乌鲁木齐,解决燃眉之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再伊犁现有与哈萨克易换牛羊之事,亦可以此作为口粮接济,著索诺木策凌与伊勒图相商,应如何运至乌鲁木齐,折变接济,一面酌办,一面奏闻。”[10]118除专门管理哈萨克贸易之外,清朝政府还在伊犁、乌鲁木齐两个官方贸易地点开设官铺,与商民贸易,以利养兵,乾隆四十年(1775年),“伊犁、乌鲁木齐等处驻防满兵,现俱开设官铺,分派贸易,殊失防守边疆之意,”[10]143对于前来归附的哈萨克和布鲁特人,则依具体成因妥善灵活应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署伊犁将军索诺木策凌奏称,哈萨克、布鲁特,来投之厄鲁特等,如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实有伊等亲属者,准其安插,若因地方丰饶来投者,概不准收等语。”[10]177同时,对伊犁哈萨克贸易具体交易细节又作如下规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既如伊犁与哈萨克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10]182因伊犁地区的贸易所需各色缎绢绫绸需求量日渐增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据佛德等奏,三处织造织解伊犁本年贸易所需缎绢绫绸,共一万一千匹,经陕甘总督勒尔谨转行解到哈密,逐一查验,内有霉默不堪应用之各色缎绢四十六匹,仍交原解官领回等语。”[10]197伊犁役用马匹除哈萨克贸易所换之外,马匹不敷之时仍需内地调往拨解添补,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寻勒尔谨奏,伊犁不敷马匹,请照旧于巴里坤镇标及附近之安西、靖逆、沙洲等营拨解,其巴里坤镇及各营缺额之数,请在司库照依营中过五马匹之例,领价买补。”[10]212各种外来人口的安插和移入,加之伊犁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长达数年的同步发展,使伊犁地区人丁兴旺,经济繁荣,促使清朝政府对伊犁地区的军政管理亟待调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伊犁十数年来,兵民商贾,较前数倍,兼以移驻绿营兵丁,其随带子弟,俱归民籍,户口益多,原设理事同知一员,管理难周,请添置抚民同知一员,分司地方事务。”[10]304期间,伊犁出现官兵私自与哈萨克交易牛马增价混乱等事件,清朝政府并未坚决取缔,而是按照官办贸易的规则选派官员监督贸易,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再哈萨克换易牛马,多有兵丁私用银两买用,及滥行增价等弊,嗣后伊犁各部落官兵,购买布匹等物,换易牛马,请拣派妥员,照官易例,监督换易。”[10]369这种顺势而为的经济政策有利于推动双方政治交往的密切,哈萨克汗及贵族从伊犁出发,主动向清朝政府朝觐,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据奎林奏,哈萨克汗之弟阿哈岱,并台吉扎达克之弟嘉拜,于十月十九等日,由伊犁起身来京入觐等语。”[10]466恰克图贸易关闭之后,对于俄罗斯和哈萨克大黄交易(鸦片)则是严令禁止。一旦伊犁哈萨克贸易所需官布不敷之时,清朝政府也会采取通融政策从疆内商民回子手中购买或交粮折布等措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据保宁奏,货买哈萨克牲畜官布,如有不敷,临时购买商民回子布匹应用,不无参差,请于正月借用库项五千两,预买布一万匹备用等语。……现在伊犁所需官布,皆由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办运,此项不敷布匹,即将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城回子应交粮石折布交纳。”[10]531次年,由各城折交布匹以供伊犁哈萨克贸易之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伊犁货买哈萨克牲畜,不敷布匹,请向商民回子等购买应用,奏到时,朕即以为买民布匹,不免从中多被沾润,莫若令喀什噶尔等城办运。”[10]534伊犁哈萨克贸易所换获的马匹解往内地时,通常要挑选膘壮的马匹作为首选标准,同时禁止途中私自偷卖马匹。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据勒保覆奏,伊犁等处所换哈萨克马匹,解送内地,近来好者甚少,著传谕保宁、永保,嗣后伊犁、塔尔巴哈台解送内地马匹时,务择肥壮者充数,仍严禁解员沿途抵换偷卖之弊。”[10]592如果伊犁哈萨克贸易所换马匹不敷解送内地之需时,则承担一半解送任务,“现在伊犁等处,因与哈萨克换马无多,不敷拨解,奏准停给一半,嗣后马匹从口外解到时,自当详加挑验,据实核办。”[10]592
由此可见,伊犁作为新疆总汇之地,生齿日繁,事务日盛,并且连通外藩部落,伊犁哈萨克贸易的迅速发展到了乾隆后期使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日渐衰落,其贸易中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当乌鲁木齐作为向伊犁进发的跳板地位建立起来以及清朝在伊、塔两地开辟了新的清哈贸易地点后,乌鲁木齐的清哈贸易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1]概言之,此时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贸易的官方贸易中心地点逐渐西移,由乌鲁木齐向伊犁转移,伊犁逐渐成为清朝政府与哈萨克进行贸易的主要贸易中心地点。
四、结语: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清代乾隆前期,新疆局势初步大定,基于政治和军事考量,清朝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西北边疆主要实施羁縻政策,对藩属哈萨克事务的管理正是这种治边思想的反映,这不仅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和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而且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随着清朝政府相继平定准噶尔贵族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此时的新疆边疆治理政策日趋完善和贯通,清朝政府对新疆事务的“信赏必罚、以昭劝惩”边疆治理政策,不仅是清代前期民族政策和边防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边疆政策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于“清王朝确立的对藩属哈萨克的宗藩关系制度和施行的羁縻服属的治理政策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12]它反映出这一时期清朝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政治意图和战略设计,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共同建造新疆地方秩序。具体到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层面的治理,尤其是对西北藩属部落事务的治理政策,其中主要体现在与哈萨克贸易的规则制定和贸易具体问题的处理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乾隆时期清朝政府与新疆周边少数民族积极互动和频繁交往的具体表现,尤其在处理与外藩部落的关系和矛盾纠纷时,清朝统治者往往谕令新疆各处办事大臣要做到秉公办理,不可有袒护内地人民之心,做到足以使哈萨克外藩心悦诚服。“清朝与哈萨克诸部的绢马贸易,既是一种贸易活动,又是清政府与哈萨克各部上层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与经济联系的纽带,亦是沟通内地与新疆政治、经济联系的桥梁。”[13]64对于与哈萨克进行的以货易货贸易,使双方各取所需、互利共赢,正如有学者指出,“哈萨克汗国和清帝国的边境贸易给双方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就其性质来说,已不是着眼于政治关系的朝贡贸易,而是建立在丝路贸易历史传统上的边境贸易。”[14]清朝政府一直是保持积极而慎之又慎的态度,无论是从专门负责管理哈萨克贸易的选派官员,还是事无巨细制定的贸易规则和章程、处理哈萨克部落卡界内迁游牧和人口安插上,都可以体现出来清朝政府宏观的边疆治理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制定哈萨克贸易的政策与清朝政府的边疆治理政策有重要的内在关联,这基于“清朝在前中期积极地向外拓展疆域,表现出对边疆地区的高度重视,其实正源于他们为中原内地构建安全屏藩的迫切之心。”[15]154当时清朝政府之所以将与哈萨克贸易的贸易地点选在乌鲁木齐,主要基于“清朝实行‘次第经理’的开发战略,乌鲁木齐成为清廷向伊犁进发的跳板,哈萨克提出用牲畜与清朝进行贸易,清朝便将贸易地点定在乌鲁木齐。换句话说,乌鲁木齐的清哈贸易是保障乌鲁木齐跳板战略正常实现的外部条件。”[11]正是由于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新疆开发战略的逐步推进,才使得哈萨克贸易进一步向西扩展,为伊犁哈萨克贸易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伊犁作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伊犁将军府所在地,又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和枢纽,加之哈萨克商队自愿请求在伊犁进行贸易,伊犁哈萨克贸易因清朝政府的重视而迅速发展,成为新疆哈萨克贸易的开辟西向贸易的中心市场,因为清朝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新疆西向贸易的开辟,又为清政府节省了大笔从陕甘、喀尔喀蒙古调解马匹和羊只供应军需的费用。”[12]同时,清朝政府对哈萨克人给予了优惠待遇,对其实行免税贸易。“哈萨克‘贡马’是哈萨克作为清朝徼外藩国进贡的马匹,其途径之一是哈萨克头目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与清朝贸易时进献‘伯勒克马’。”[16]清朝政府对边疆治理的经济政治体制,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模式,新疆也不例外。与哈萨克贸易的方式主要是以“抱布贸丝”为主,其中“因为伊犁贸易,是以以物易物为主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制定并实施较为合理的贸易政策与价格,在贸易开始进行时,就显得颇为重要。”[17]以由于伊犁、乌鲁木齐均系新疆地方,距离哈萨克、布鲁特边界较近,而伊犁更为接近哈萨克游牧之地。同时,塔尔巴哈台又与哈萨克接壤,地理位置上的天然接壤,使哈萨克人在心理层面上更愿意采取“就近贸易”原则与清朝政府开展贸易往来。正如日本学者佐口透先生所说,“清朝通过积极开放边境的市场,建立了游牧民和农耕社会的和平交易。先后以乌鲁木齐、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官办贸易地,开始了交易。哈萨克的统治阶级派遣商队到上述市场来通商。特别是伊犁成了双方通商中心地。”[5]371在乾隆后期,清朝政府根据由官布和民间购买的布匹所构成的哈萨克贸易的易换物,再根据交易马匹的肥瘦对哈萨克贸易又做了不同的贸易价格规则。通过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对新疆哈萨克贸易事务颁布的这些谕旨可以清楚地看出哈萨克贸易“这种官方贸易活动,绝非仅限于商贸与产品的成交,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政治与军事的意义和影响。具体而言,它是直接关系着清王朝西北边疆政策的实施,以及‘驾驭外藩之道’是否‘允协’的大事。”[18]可以说,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贸易活动的活跃,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这与清朝政府的边疆治理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清代边疆政策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19]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乾隆时期移居新疆雅尔、伊犁等地的哈萨克人迁徙现象,这与他们从事流动的绢马贸易和生活习性有着紧密的关联。当他们发现有更好的地方适合游牧和生活,就会举家迁居到这个地方,且定居下来,每一次迁徙,随着人口的增加,哈萨克聚落就会形成。所以说,伴随伊犁哈萨克贸易发生、开展和成为贸易中心地点的过程中不容忽略的是新疆哈萨克人大量的内徙和“输诚内向”,这就形成了历史上的跨界民族,“这是中国西北历史上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浪潮。”[20]503
客观地说,“清代伊犁地区的哈萨克贸易,不仅是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的自然延伸,而且是清朝与哈萨克的官方贸易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21]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制定的“外藩”民族贸易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清朝与哈萨克族建立和发展商业贸易的过程,也就是清朝贯彻与实施其对哈萨克民族政策的过程。”[21]这也为后来制定《筹办夷务始末》等较为系统的哈萨克贸易章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它同时也是清朝治理新疆民族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新疆经济的发展,交通的畅达,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使新疆与内地形成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大大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向往国家统一的凝聚力。”[22]118从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可以看出,在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新疆的社会经济形成了两个空间位置和性质均有所不同的经济圈。它们既相对独立发展,又互为市场,共生共荣。这两个经济圈又是与乾隆时期新疆城镇的城市化相伴生的。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抑或是横向的深层逻辑层面而言,乾隆时期新疆伊犁哈萨克贸易都无法割断与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对新疆开发和经营的战略意图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直接体现为清朝政府如何处理与卡外界内哈萨克的关系以及与哈萨克的绢马贸易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认真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都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23]13
[1]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二)[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2] 刘海燕.从清朝与哈萨克族的关系透视其边疆民族政策[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5(3).
[3] 王希隆.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J].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1).
[4] 郧军涛.中俄两国对外策略中的哈萨克因素[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5] (日)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M].凌颂纯,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6]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三)[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7] 洪涛.哈萨克族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3).
[8]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哈萨克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9]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四)[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10]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五)[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11] 陈海龙.乌鲁木齐何以成为清朝与哈萨克之间最早的贸易地点[J].史学月刊,2013(9).
[12] 厉声.清王朝对西北藩属哈萨克治理政策研究[J].西北民族论丛,2003(12).
[13] 赵海霞.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4] 李明伟.十九世纪以前的西北边贸传统[J].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Z1).
[15] 张荣.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6] 郑峰,张荣.清朝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问题再探讨——以“征收马匹”为中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4).
[17] 王熹.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马价、丝绸价与贸易比值问题[J].民族研究,1992(4).
[18] 王熹,林永匡.简论清代乌鲁木齐哈萨克贸易设立的原因与经过[J].民族研究,1990(5).
[19] 杜辉.清代边疆政策的宏观考察[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2).
[20]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1] 王熹.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几个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1).
[22] 王洁.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经济政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3] 马大正.略论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J].清史研究,1991(2).
责任编辑:胡 晓
2014-11-23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治理创新与‘平安新疆’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CSH006);2013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重点项目“非传统安全视域下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构”(项目编号:XJEDU090113B05);2013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一般项目“加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互动关系研究:以新疆为例”(项目编号:XJEDU090113C04)。
张付新(1978- ),男,甘肃陇南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民族贸易史、教育史和民族宗教文化史等;张云(1982- ),女,新疆阜康人,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区域文化史、民族学。
K294.5
A
1004-941(2015)02-003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