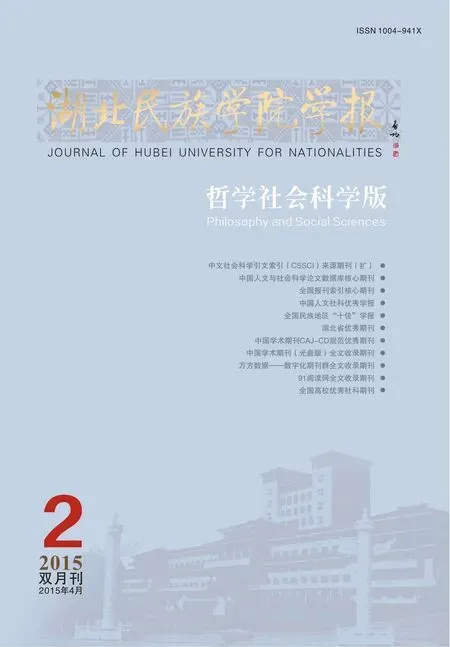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 锋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李 锋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目前,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文献整理、研究深度、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开拓空间,而且深化对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体系、丰富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领域,还在积累文献、拓展视野方面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可以考虑从整体性的角度,分纵、横两个向度,围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明、清边疆政策对文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各族别文士的交流对文论的影响,口头诗学等专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回顾;思考
当代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时至今日已历一个甲子。这期间,学界先贤筚路蓝缕,开启了对南方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梳理和继承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拓对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成为当下民族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既已形成一定的理论储备,尤其是文献搜集和整理方面贡献良多,另外在族别文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四种类型
总括式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论文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史》等。王佑夫的著作,可说开中国古代文论宏观研究之先河,特别是成书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从“本质论”、“功能论”、“创作论”、“语言论”、“诗歌论”、“起源论”、“发展论”等七个方面,首次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所涉及的理论主题,并较早提出了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的问题。除此之外,该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既强调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的联系和“共性”,也关注少数民族文论的“个性”,如针对文学功能论,该书就指出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强调文学的抒情表志功能,但不同之处在于“少数民族文论家们,在谈情感表现的时候,并不过分强调‘情’与‘理’的联系。他们并不认为文学所表现的‘情’必须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情感的原生性和自在性,认为文学应当是人的纯真性情的表现。”[1]56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的个别章节涉及到南方少数民族文论,如刘亚虎《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中用一节的篇幅,结合传统诗论简要梳理了赵辉璧、王崧、彭秋潭、师范等南方少数民族代表性批评家的诗论思想。
文献的整理和注释。此类研究分为三个方向,一是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如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主持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吴肃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以及云南、湖南、贵州等省主编的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等,另外还有一些包括少数民族古籍的丛书,如《云南丛书》、《丛书集成续编》等, 这些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使大量少数民族的珍贵文献重新走入研究者的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是各民族文论作品的编选和注释,如买买提·祖农等编《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王戈丁等编《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 <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续编》,《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汇编》(有关文论的作品选编)、彭书麟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等,这类“作品选”式的著作,将文献整理的焦点对准具体的少数民族文论作品,在文论内容的校勘和注释方面,有开创性贡献。三是个别民族文论作品的编译和注释,如举奢哲、阿买尼著,康健、王子尧译《彝族诗文论》,漏侯布哲等著,王子尧译《论彝族诗歌》,布麦阿纽等箸,王子尧译《论彝诗体例》,康健等编《彝族古代文论》,沙玛拉毅《彝族古代文论精译》,祜巴勐著、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陈湘锋《<田氏一家言>诗评注》(对序跋的整理和注释部分)等,针对个别民族具体文论家的文献,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注释,特别是有关彝族文论的研究,还涉及到翻译问题。这三个方向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文献的准备。
族别文论的研究。这一类文论的研究中,有关彝族文论的研究一枝独秀,如康健等编《彝族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何积全《彝族古代文论研究》,《民族文学探索》(论文集)中涉及对彝族古代文论的讨论部分。其中康健所编的论文集从历史背景、美学特征、学科价值、理论范畴、比较诗学等多个角度对彝族文论进行了研究,而巴莫曲布嫫与何积全的著作则都将纵向性的历史梳理和横向性的理论主题研究相结合,在较为全面概括了彝族古代文论的同时,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有深入的分析。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著作涉及到彝族文论,如刘亚虎等所著《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有一小节将彝族文论与汉族文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彝族文论研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彝族文论在文献方面已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彝文为原始载体的彝族文论体现了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与汉族古代文论的对比中,更能见出其理论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创新性。
各族别文学史中有关作家批评理论和思想的介绍。其中着墨稍多的有《壮族文学史》中对于郑献甫诗论的介绍和分析,指出郑氏诗论“颇有见地,与当时正统的宋诗派和桐城派颇异其趣,大体上接近袁枚的‘性灵’之说,而又不是故作依傍。”[2]974较好地说明了郑献甫诗论的特征。再如《白族文学史》中专辟一节介绍王崧的文学理论,将其文论思想与其学术思想相联系,指出其“道学”思想是其文论思想的基础,并将王崧的文学理论分成文论和诗论两部分,分别进行了评述。同时,该部著作还将白族文学史中包含文论内容的文献分成三类:诗话、诗文集和解经著作,并有简单地介绍。另外,该书中对于杨士云评论诗人、诗作,以及师范论诗诗和《荫椿书屋诗话》的介绍等也涉及到文论领域。《土家族文学史》中对于彭秋潭的诗论亦有介绍,着重点出其在竹枝词创作理论方面的突破。《纳西族文学史》中对于杨竹庐、杨昌、杨品硕等人的诗论亦有提及。
总体来看,既有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是开启了有关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先河;二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准备了资料、开启了思路。但这些研究也存在较大的不足。
(二)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不足
对文论文献的挖掘仍有遗漏。主要体现为,首先对有关作家批评文献的挖掘仍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对古代少数民族批评家诗文集、地方志(艺文志)中有关文学理论批评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还存在很多空白点需要填充。不可否认,有关民族古代文论的文献资料相对比较零碎、分散,而且多数民族的文论文献都是用汉语写成,夹杂在汉族文士的论著当中,不易辨识,搜集、整理起来也有一定困难,但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和准备性工作,对南方诸民族古代文论文献的全面整理事在必行。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其次对口头诗学文献的挖掘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所说的“口头诗学”与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所说的“口头诗学”(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有所不同,约翰·弗里所说的“口头诗学”指针对史诗创作和传承中口头传统的理论研究,而本文所说的“口头诗学”则指口头文学(神话、歌谣、传说、故事等)中有关文学理论的内容。,口头诗学包括口头文学中涉及文论的部分,以及探讨口头文学特征规律的理论,这些理论文献曾有少量被选入《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少数民族古代文论选释》、《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另外,一些口头文学的作品集中也收录有与文论相关的作品,如《中国歌谣集成》等,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有待整理、甚至是“抢救性的发掘”。
对已整理文献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首先对作家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如白族批评家赵蕃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自1981年出过一部研究专著以来,30多年其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赵蕃的“论诗诗”不仅在白族文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中亦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再如湖北土家族的《田氏一家言》中有序跋11篇,评点111条,如此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内容和思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篇专题的研究性文章。其次是对已整理出来的口头诗学理论和思想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如《中国歌谣集成》中所整理收录的大量歌谣,尤其是其中的“引歌”就有很多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对引歌的介绍是:“引歌,壮语称‘欢咯’、‘诗媒’,是关于唱歌的歌,内容包括歌谣的起源、承传、性质、作用、威力及传唱歌谣的意义等,具有民间诗论的性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但截止目前,有关这一领域研究还没有一部专著,论文也很有限。
对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汉族批评家对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评点、序跋),还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正如王佑夫所指出的,“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历程中,汉族学人作出了积极而不可或缺的贡献,他们的著述应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组成部分,纳入研究范围之内。”[3]这一点在南方少数民族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一部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发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汉族、乃至其他民族文士进行交流和酬唱的历史,可以说,没有汉族文士的参与,就不会有南方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学与文论。因此,对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能也无法仅仅因为族别之见,而故意忽视汉族批评家的理论贡献。
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整体性研究还是空白。上面所举的研究文献中,要么只是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作为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部分(往往是很小的一部分)加以论述,其研究深度和广度都难以保证,要么只是针对南方个别民族的文论进行研究,虽有一定深度,但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实际上只有对彝族文论称得上有专门的研究,其他民族的大量文论文献要么只是被初步整理和注释,要么根本还未得到整理,更遑论理论层面的研究和分析。而通过对南方诸民族古代文论发生发展的历史考察,更应认识到,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南方诸民族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即明代以降,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中央皇权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教育。明太祖认为“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反,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4]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明代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教育,包括遴选土官子弟入国子监学习、在民族地区广设府、州、县、卫和各司儒学,并诏令兴办社学,鼓励开办书院以吸引少数民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等等,这也是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到明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文学和文论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明代的汉文化推行政策实施的重点主要在南方民族地区,“南方和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儒学,广开学校,推行科举,开设书院;在北方也设立都司卫所儒学,但文化教育不被重视,学校教育数量不多”。[5]因此,汉文化的影响,以及与汉族文士的交流,是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文论发展的一个共同背景,也是区别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只有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从宏观上将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衍进的深层原因和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根本特征。
学界还没有正确认识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意义和价值。以文献的整理为例,一方面如上文所说,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南方诸民族的文献整理起来有难度,但根本原因在于学界对南方诸民族古代文论的价值和意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其在研究当中,缺乏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从而使相关的研究难以为继。有鉴于此,应从学科意识入手,加强学术舆论的引导,通过期刊和会议两大学术平台,多刊登、发布相关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使学界真正意识到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以及目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动力不足、发展乏力的问题。
二、拓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无论在文献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而进一步的研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 有利于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
考虑到现有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北方民族已有诸多成果,如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文字的古代文论专著先后问世,藏族、哈萨克族的古代文论研究已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但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除了彝族成果稍多外,其它民族还较有限,从整个少数民族文论的学科体系上看,处于明显的北重南轻的失衡状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南方诸民族古代文论,标志着南方民族文学由创作自觉走向理论自觉的新境界,在南方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南方诸民族文论,其形成和发展与汉族文论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与汉族古代文论有着相互参照的意义,这是北方民族文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进一步拓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不仅对完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学科体系有着直接而重大的意义,同时亦能为汉族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对丰富其学科的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
(二) 还原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丰富多彩的本来面貌
通过对各类文献中文论资料的钩沉、搜集和整理,让尘封已久的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理论和少数民族批评家、理论家进入研究视野,尽可能多地还原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拓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既有规模。以云南省为例,可供重新梳理的较集中包含文论内容的诗文总集就有《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滇诗丛录》等多种,这些文献虽有研究者进行过整理,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其中珍贵的文论思想和内容,包括序跋、作者小传,大量的眉批、夹批、旁批,这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包括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批评内容,如具体作品的分析、个别作家风格的评论、家族诗歌群体的介绍、地方诗歌风气的评论等多方面的内容。[6]另外,还应注意的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志(艺文志)中收录的作品,这些作品中也含有不少涉及文论的内容,如乾隆《丽江府志略》中有关木氏土司诗文的序跋和论诗诗。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的爬梳、抽绎和整理,将使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让很多从未引起过注意的理论和理论家进入学界视野,改变人们对于南方古代文论的“贫瘠”印象。
(三) 重新认识南方少数民族文论的价值
通过对代表性批评家和批评理论的深入考察,弥补之前相关研究的不足。如对土家族批评家田舜年,既有的研究多是肯定他在编辑容美土司作品集方面的贡献,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田舜年的一些批评言论,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端,如他主张兼顾“自然抒发”和“风雅兴寄”的批评主张,就和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有共鸣之处,他在《田氏一家言·跋》中提出“诗言志也,各言其所言而已……十五国风,大都井里士女信口赠贻之物。”[7]293反对刻意的模仿,“果若人言,绳趋尺步,诗必太历以上,则自有盛唐诸名家在,后起者又何必寻声逐响于千秋之上哉。”强调自然抒发的作品有天然之美,富于特色、自成佳作,“天机所动,将亦有自然之律吕焉。”但他同时也强调作品应“冲融大雅”(引吴国伦之语),这种见解已经彻底跳脱了在明末清初有重大影响、并造成极大流弊的复古和公安、竟陵三派的窠臼,展现出很高的批评水平和广阔的批评视野。另外,他提出“山鸡之羽文彩可观、泽雉之性耿介足垂。”(《田氏一家言·跋》)对“荒裔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具体而言,就是容美土司的文学作品)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表现出高度的自信,在当时而言,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口头诗学”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宝库”,包含着极丰富的文论思想,而且这一类文论从理论视角、具体内容到叙事风格,都与作家文论有极大的不同,表现出很强的理论特色。加强对“口头诗学”的研究,将极大地拓宽、丰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围,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中国古代文论的既有面貌。
(四) 创新民族文论的研究视角
从既有的微观、具体的惯性研究视角中跳出来,站在宏观角度,考察南方少数民族文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南方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南方各族别之间文论的关系,尤其是结合历史背景(宏观的大背景和各民族地区的小背景),分析和解读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形成、发展中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原因,如明代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及清代与“改土归流”相配套的文化政策等,对于民族地区文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使其具备了怎样的特征等问题,另外,还有明末清初大批汉族文士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该地区文论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利于从整体上描述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特征、准确定位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对不同民族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交往史的研究,还有利于我们了解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三、拓展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可能路径及内容
在开展研究之前,应首先认识到南方少数民族既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就地域而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在广义上涵盖了南方和西南两大区域,包括川、藏、云、贵、桂、湘、鄂、赣、粤、闽等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就文化而言,南方少数民族的整体性特征就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特别是明代以降,受“以夏变夷”文化政策影响,在南方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次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高潮,很多民族地区因此产生了第一批自己的作家文学,并进而有了第一批文论著述。因此,从文化这个角度看,南方少数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存在,这种“一体性”主要体现在它们与汉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一致性。可以说,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虽然包含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理论和思想,但因其“同源性”(即都受到汉族文论的影响),再加之各少数民族之间文化、文学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交流,使这些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其础上的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即纵向性的历史研究和横向性的专题研究。
(一) 纵向性的历史研究
目的在于梳理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本发展线索。考虑到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尤其是作家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是比较晚近之事,另外有些理论的产生时间也不易考证,因此在梳理过程中将以代表性人物、文献及其理论为主线,兼顾其时间上的先后,描述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历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会加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对新文献及其包括文学理论批评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二是加强对既有文献中文学理论批评理论和思想的研究;三是加强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结合,以求更为直观地显现南方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地位和价值。
(二)横向性的专题研究
明代的边疆文化政策对南方少数民族文论形成的影响研究。这种影响研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明代开始,中央皇权为加强对边裔地区的控制,通过强制土司子弟入国子监学习、在民族地区兴办学校、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学子参加科举等方式[8],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教育,大大提升了本地区的文化水平,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论的初步形成;其次,明代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土司及其族裔,并明文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9]7997将世袭爵位与学习汉文化直接挂钩,使得土司及其族裔开始潜心钻究汉文化,同时,由于对一般民众学习汉文化缺乏有力的政策举措,造成明代至清初,土司及其族裔成为南方民族地区接受汉文化的主体人群。与此相对应,南方民族文论的一大特征就是,批评的对象以土司及其族裔为主,而由于自身批评家从整体上尚未成长起来,此一时期批评的主体则以汉族文士为主*此就整体而言,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明代白族的杨士云、李元阳、赵炳龙等人,虽不是土司,但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也有文论存世。,如明代严首升、文安之对于土家族容美田氏土司的文学批评,杨慎、张含、贾体仁对于纳西族丽江木氏土司的文学批评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对此问题的研究,应以史实为基础,参考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既有成果,从文论的视角去考察边疆文化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早期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
“改土归流”对南方少数民族文论发展的影响研究。此问题的研究,应注意到“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地方文化最显著的影响,即平民的知识分子大量增加。在此之前,土司及其族裔在相当大程度上垄断了对汉文化的接受,土司一方面因为世袭制度和血统论意识的影响,在显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非常强调自身的贵族身份,另一方面为了方便统治、抵制外来文化对自身政权的可能威胁*如乾隆《贵州通志·艺文》载:“因土府陋习,恐土民向学,有所知识,即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靖道谟等:《贵州通志》,台北,京华书局1968年版,第711页)。光绪《普洱府志稿》亦云:“向来土官不容夷人应考,恐其为入学,与之抗衡。”(转引自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99页。)除了担心土民学习文化与其抗衡之外,土司还害怕土民因读书,走上科举之路,从而脱离他的统治,如赵翼《簷曝杂记》卷四载:“粤西田州土官岑宜栋,……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转引自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导致其在大力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却阻止治下的土民接触汉文化,实行“土民皆不受学”的愚民政策,而明代政府虽然大力在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但是对于土司子弟之外人群的汉文化教育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明代政府在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统治,因此在政策设计上,就特别强调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者——土司阶层的文化教育,却忽略了对一般平民接受教育的政策设定。这也为土司实行愚民统治提供了口实。,使得一般的少数民族子弟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清代在“改土归流”之前,就已经吸取了明代的教训,开始将汉文化教育向平民阶层推进,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令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10]135及至“改土归流”,加强对平民阶层的教育,不仅成为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推动“改土归流”深入发展的必须措施,因为参与“改土归流”的官员都感觉到,虽然土民在制度上摆脱了土司统治的模式,但是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依然对“流官”体制及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风俗的推行感到隔阂和不适,因此通过文化教育强化广大土民文化身份认同和对中央皇权的归属感,成为当务之急。[11]各地官员通过兴办“义学”、鼓励土民子弟等方式,吸纳大量平民学习,使得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大范围的传播。[12]因此,开始产生大量出身平民阶层的文学人才,如土家族的彭秋潭、彭淦,壮族的冯敏昌、刘定逌,白族的龚锡瑞、杨履宽、赵廷枢,纳西族桑映斗、杨竹庐等等,自然也相应地产生了一批文论著述。自“改土归流”之后,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变化就是批评客体从以土司及其族裔为主,转向以平民文士为主,批评主体以汉族为主,转向汉族、少数民族并重的局面。对此问题的研究,同样应以历史文献为基础,考察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特征的重大变化。可以考虑通过量化研究的方式,来辅助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南方各民族之间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研究。首先是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研究,包括汉族文学理论批评理论和思想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及其意义研究,汉族批评家参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文学理论批评的补充和启发研究。与汉族文士的文学交流、诗文酬唱,是文论生产的重要方式,也是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角度,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族与少数民族文论相互交流、影响的生动例证,还能据此勾勒出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其次是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各族别之间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的研究。这一类研究,目前来看,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虽然,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论文献并不很多,但是意义重大,因为这种交流必然基于一个事实,即南方诸民族对于同一文化身份(中华文化成员)的认同,惟有如此,他们才能用同一“文学话语”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化融合。
口头诗学研究。口头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歌谣、谚语、民间传说中的文论。如广西苗族歌谣《三月春雨》从歌者的角度,提出“人世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唯有山歌能够解除你心头的忧愁积怨;人世间充满争斗难有一汪清泉,唯有歌手能够倾吐真情替你说出心底的话语。”并热情洋溢地表示:“让我的歌是那火塘的红炭吧,时时刻刻温暖着你的心田”。[13]630从文学功能和作者职责的角度,赞扬了山歌和歌者。又如侗族《歌师传》,以较长的篇幅总结了侗歌的创作经验,提出了歌要以情动人,故事情节要完整、歌词要新颖、音乐要多样等理论。[13]953-955彝族戏剧艺人当中流行的谚语《编戏如金沙江里淘金》,其中说道:“编戏的人看透世上的事才能编出好看的戏……编戏如金沙江里淘金”。[14]488谈到了剧作者的生活阅历对创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创作的提炼问题。布依族民间传说《刷把舞的来历》,通过讲述刷把舞的来历,揭示了艺术来源于生活。[14]550口头诗学,以口头文学为载体进行传播,虽然不似作家文学的文论那样符合“学术规范”,但却具有民间叙事所特有的朴素、直率的风格,而且这些理论都经过若干代的口耳相传,是无数口头文学创作实践和表演实践的理论“结晶”,是至真至切的心得之言、甘苦之谈。
南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一个生动标本,籍由这个标本,我们可以看到南方诸民族虽然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但依靠中央政权的政策推动,由被动到主动地进入中华文化的主流场域,并在精英和民间两个阶层,都发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
[1] 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2] 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壮族文学史(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王佑夫.拓展民族文论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3(4).
[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卷239[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
[5] 刘淑红.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J].广西民族研究,2012(3).
[6] 张梦新,吴肇莉.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5).
[7] 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容美土司史料汇编[G].鹤峰县印刷厂,1984.
[8] 花文凤.科举体制下明朝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及其解决策略[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3).
[9] (清)张廷玉.明史·湖广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11] 赵旭峰.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2).
[12] 段超.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6).
[13]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4] 彭书麟.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飞霞
2014-12-18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南方少数民族文论研究”(项目编号:csw14046)。
李锋(1980- ),男,安徽桐城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论。
I059
A
1004-941(2015)02-00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