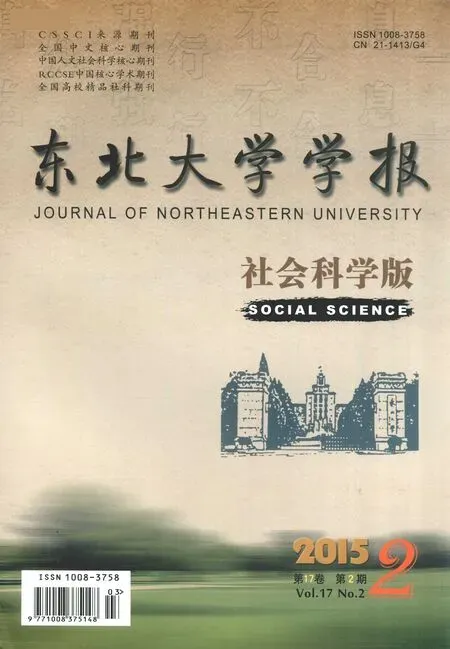读者接受理论关照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以《喜福会》的无根回译为例
——————————--
读者接受理论关照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翻译——以《喜福会》的无根回译为例
王晨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的汉译是一种特殊的回译,这种源语文本并非存在的回译被称为“无根回译”。如果从接受理论角度对华裔美国小说《喜福会》的无根回译进行研究,就可以通过译本对比,解析不同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而探讨译者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所进行的差异性关照。因此,将华裔美国文学的无根回译置于接受理论框架下,剖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主体、翻译对象等翻译要素对无根回译的影响,可以用来指导华裔美国文学的汉译实践。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 无根回译; 接受理论; 《喜福会》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18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0YJC740093)。
作者简介:王晨爽(197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华裔美国文学及文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2-0216-05
Abstract:Transl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genre of back-translation. Given that no source text exists in the process of back-translation, it is called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novel Joy Luck Clu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theory. Comparing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by Tian Qing and Cheng Naishan, it present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dopted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which proves that different translators may be concerned about different target readers and have different translation purpos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e put into the framework of reception theory and the effects of such translation factors as translation purpose,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method, translator and readers upon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be explored so as to guid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ased on Readers’ Recep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n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inJoyLuckClub
WANGChen-shu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Key words: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rootless back-translation; reception theory;JoyLuckClub
华裔美国文学具有文化翻译的职能,其作品的汉译属于回译。华裔美国文学的回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其回译的原文文本是隐形的,并非客观存在,故王宏印教授将此类回译定义为“无根回译”。本文运用接受理论对华裔美国小说《喜福会》的无根回译进行研究,通过对田青1992年的译本(下称田译本[1])和程乃珊等人2006年的重译本(下称程译本[2])进行比较分析,解析两位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而探讨两位译者在无根回译过程中,基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针对不同目标读者进行的差异性关照。
一、 无根回译
想要认识“无根回译”这个概念,首先应该将它和回译加以区分。Shuttleworth把回译定义为“将已译成特定语言的文本译回源语的过程”[3],它强调了源语的回归。方梦之等则认为回译是“把被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过程和表述”[4]97,即从A文本翻译成B文本后,再从B文本准确地返回到A文本,它注重的是对原文本的还原。在国内,回译最初是用来检验译文和考察误译的一种手段,但此评估方法在学界存在争议。2005年,刘芳以《喜福会》为个案从词汇和句子层面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汉译过程中文化专有项的回译问题,此类研究扩大了回译的研究领域,使回译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5]。此后,陈志杰考察了跨文化写作回译的特殊性。在他看来,回译的过程并非一定是个完整的循环式的翻译链,单向的翻译活动也能构成一种隐含式的回译活动,即从A文本到B文本的过程是隐形的,显现出来的仅仅是从 B文本回归到A文本的过程[6]。他对此种回译的认识比较透彻,但没有给予学术上的界定。此后,王宏印教授对这种特殊的翻译类型进行了理论概括,命名为“无根回译”。
中国题材的非汉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语的过程,即异语或异域写作的回译属于无根回译。它之所以被称为无根回译,是因为“这种翻译成汉语的返回只是文化上的返回,而不是语言的返回,即在语言上不存在以原文为根据的回译”[7]。显而易见,华裔美国小说《喜福会》的汉译也属于无根回译。目前,国内对无根回译的研究并不多,其中何子章和江慧敏的观点颇为醒目。何子章认为移民英文小说的汉译不该有翻译腔,应遵循“错觉理论”,即用流畅的语言翻译原作,使读者产生读原著的错觉,以为所读的就是用译语写成的原作[8]。江慧敏的观点与之相近,她主张无根回译须最大限度地向译语语言靠拢,并关注读者意识的转换,自觉地实现由源语读者向译文读者阅读视角的彻底转换[9]。
二、 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亦称“接受美学”,它强调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具有决定性意义。接受理论把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读者,并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个概念。任何读者在阅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之前,都会处在一种先在理解的状态。任何一部作品总要激发读者某种潜在的接受趋向,来唤醒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和期待。读者的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之间存在着审美距离,距离越小,读者就越容易接受[10]。因此,译者会尽其所能地去减小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与其译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20世纪80年代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并运用于翻译研究领域。接受理论为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它使翻译活动不再是译者与原作之间的单向交流,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并成为翻译质量的评价标准之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这种审美能动性,并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4]262。因此,译者为了使自己的译作能够被读者接受,不仅应密切关注原作,还必须考虑目标读者的潜在需求,并针对不同的读者进行全面的关照。
三、 译者对读者接受的关照
《喜福会》是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显而易见,它的汉译属于无根回译。译者田青和程乃珊的两种译本在中国国内读者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受读者喜爱。本文将以接受理论为基础,以《喜福会》的两个汉译本为例,拟从文学视野和文化视野两个方面来阐述两位译者在无根回译时,是如何对读者接受进行关照的。
1. 关照读者的文学视野
(1) 关于描写
外国文学注重心理描写,旨在刻画人物的内在情感和心理活动,以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而中国读者倾向于整体思维,把握故事情节的发展,往往忽略冗长的细节描写。在《喜福会》中,原文作者曾多处以浓重笔墨对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因此,在无根回译时,如何处理这些并不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细节描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请看《喜福会》最后一章,我们以“母亲”的一段心理独白为例来考察两位译者对其目标读者在语言层面上的不同关照。原文如下:
She began to talk as if she were trying to remember where she had misplaced something. “I went back to that house. I kept looking up to where the house used to be. And it wasn’t a house, just the sky. And below, underneath my feet, were four stories of burnt bricks and wood, all the life of our house. Then off to the side I saw things blown into the yard, nothing valuable. There was a bed someone used to sleep in, really just a metal frame twisted up at one corner…[11]273
田译本:她开始说话,好像在追忆被淡忘了的过去。“我回去看过那房子,寻找那房屋的旧址。那已经没有房屋了,只有天空。在我脚下,是四层楼房燃尽后剩下的瓦砾和朽木,这就是我家的全部生命。我看到院子里残余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值钱的,有一个平时睡觉的床,实际上只剩下了弯弯曲曲的铁架子挤在角落里……”[1]297
程译本:待我回到上海的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2]244
原文是“母亲”追忆自己与亲人失散多年后回大陆寻亲的一段坎坷经历。译者田青并没做任何删减,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直译,忠实地还原了原文,使读者进而了解外国文学的全貌。独白是“母亲”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倾诉,是对昔日故国生活的追忆,田青的译文超出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唤起了读者对原文的阅读兴趣。它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一种异域的阅读经验,充分地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从而使译文读者领略到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独特风采。而译者程乃珊出于对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关照,认为成段的心理描写过于详细,使故事情节拖沓,容易使读者生厌,于是在回译时毫不留情地将整段删掉。只译出了第一句话,向读者交待了故居已空无人烟,便用省略号结束本段。这使小说的情节更加紧凑,满足了读者想要看到美国女儿与大陆姐妹团聚的迫切心理。
(2) 关于四字格成语
汉语四字格成语是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沉积下形成的,易于被汉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在英译汉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英语原文中比较抽象、繁冗的表述,译者冥思苦想也难以下笔,但如能恰如其分地运用四字格成语给予应对,则往往豁然开朗。下面我们来欣赏《喜福会》第一章中的一个译例,原文讲述了“母亲”当年在中国逃难的悲惨遭遇,故事的开头是一段关于桂林的景物描写。原文如下:
I dreamed of jagged peaks lining a curving river, with magic moss greening the banks. At the tops of these peaks were white mists. And if you could float down this river and eat the moss for food, you w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climb the peak. If you slipped, you would only fall into a bed of soft moss and laugh. And once you reached the top, you would be able to see everything and feel such happiness it would be enough to never have worries in your life ever again.[11]21
田译本:我梦见怪峰突兀的群山,山里流出弯弯曲曲的河水,迷人的苔藓染绿了河岸,白露环绕山顶。要是你能顺流漂下,吃了苔藓,就一定会有力气爬到山顶。要是你滑倒了,准会躺在床一样的青苔上哈哈大笑。你一旦爬到顶峰,四周风光尽在眼中,那真幸福极了,保你一辈子不再烦恼。[1]7
程译本:中国有句俗话:桂林山水甲天下,我梦想中的桂林,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的山峦,白云缭翔,是个世外桃源。[2]7
田青几乎完全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和风格,没做变动,因此,我们在阅读田译文时,能明显地感觉到其语言上的直译痕迹,让人觉得确实是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符合潜在读者的语言审美期待。此处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衬托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与后面战争的残酷形成了对比,这种叙述手法无疑为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景物描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相比田青123字的译文,程乃珊的译文则显得格外简洁,只有53字。程乃珊连用五个四字格成语来应对原文中的排比句式,“青山绿水”“翠微烟波”“层层叠叠”“白云缭翔”和“世外桃源”,这一连串的四字结构使译文格外典雅,别有韵味。四字格短语节奏感强,简明精练,比较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身为作家,程乃珊具有良好的汉语基础和文化底蕴,对四字格的使用可谓驾轻就熟。在文学翻译中,若能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四字成语,可以使译文更为言简意丰、优美畅达。
2. 关照读者的文化视野
(1) 关照读者对文化专有项的接受能力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涉及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融入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它们构成了华裔美国文学的一大特色。传统美食、古代诗词、神话传说、传统节日和习俗、复古的着装等中国元素对于西方读者来说都是新奇而陌生的。因此,原文作者在写作时不可避免地要对诸如此类的文化专有项进行解释,以便于西方读者能够理解。译者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时,会根据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以便使自己的译文能够被读者所接受。《喜福会》下面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Three days before the lunar new year, she had eaten ywansyau, the sticky sweet dumpling that everybody eats to celebrate. She ate one after the other.[11]239
田译本:妈妈临死的前一天,吃了(元宵),人们通常是吃元宵来表示喜庆的。[1]259
程译本:她把毒药拌到元宵里吞下去了。[2]214
这是《喜福会》最后一章关于“吃元宵”的片段。显而易见,原文中“the sticky sweet dumpling that everybody eats to celebrate”是对文化专有项“ywansyau”的注释。为了让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元宵有基本的认识,原文作者用后置定语对其进行了说明。鉴于中国读者都明白元宵为何物,程乃珊便直接回译为“元宵”,省略了对文化负载词的解释。与此相反,田青没作改动,照原样翻译了原文,使目标读者能够更好地领悟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田青尊重原文的文体特点,使译文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相似,旨在尽量保留原文的异质成分和译文的陌生化,从而彰显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2) 关照读者的传统道德观
华裔文学作品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往往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既有对中国文化正确的继承,也有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因此,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叙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有悖于中国传统和伦理道德的现象,那么,面对被误读甚至被篡改的中国文化,在回译过程中,译者该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们不妨通过《喜福会》中的这个例子来分析一下两位译者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
Her arms and legs were moving back and forth as she lay on her back. She was like a soldier, marching to nowhere, her head looking right then left. And now her whole body become straight and stiff as if to stretch herself out of her body. Her jaw was pulled down and I saw her tongue was swollen and she was coughing to try to make it fall out.[11]238
田译本:我妈妈的房间里灯火通明。我一进屋就看到了妈妈,我跑到她的床前,蹬上脚凳。她仰面躺着,四肢前后挣扎,头左右晃动,大声咳嗽,想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她象一个士兵一样,正在跟看不见的敌人搏斗。过一会儿,她全身挺直,僵硬,她伸着下巴,肿大的舌头还伸在外面。[1]258
程译本:我睡意朦胧地跟着来到母亲房里,只见房内灯火通明,她躺在床上手脚抽搐,舌头麻木。[2]214
这是最后一章中原文作者以女儿的视角对母亲临终前进行的一段人物描写。母亲无疑是男权制度压迫下的牺牲品,懵懂的女性意识并没有改变她的悲剧命运。田青选择了直译,充分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让目标读者看到了一个身份卑微、垂死挣扎的姨太太形象。母亲走得不甚安详,弥留之际的母亲在女儿眼中并不慈爱,而是留存些许恐惧,这似乎并不符合中国的孝道文化,让读者难以接受。于是,程乃珊果断地进行了删减,仅用八个字来形容母亲当时的苦痛,即“手脚抽搐,舌头麻木”。在程译本中,译者大胆地删除某些不符合中国伦理道德的描写的现象无处不在,足见程乃珊多么注意迎合大众读者的文化传统和审美倾向。
四、 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和意图的交际行为,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即“目的决定方式”[12]。翻译目的会根据目标读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译者可以根据特定的读者对象,用最适当的翻译策略来达到目的语文本要达到的目的。”[13]
田青在译后记中阐述了自己翻译《喜福会》的缘由:“我之所以把这部作品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除了它巨大的艺术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沟通中美两国人民的情感,它象一条纽带,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我很庆幸,有这个机会为中美文化交流做些贡献。”[1]315可见,田译本是以原文作者的意图为翻译目的,其宗旨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英语学习,要求“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领向作者”[14]61。因此,田译本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力求不删减不增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特别是保留原文作者的主要语言风格和感情色彩。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况是以关照读者需求为翻译目的,即“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领向读者”[14]61。在译后感中程乃珊也交代了重译《喜福会》的目的,即为了使新版本“译文更流畅更忠于原著,此次对全书的译文逐字逐句对照原文重新撰写、反复推敲与斟酌,力图做到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2]260。可见,程乃珊优先考虑的是译文的流畅性,尽可能迁就和满足译文读者。因此,程译本势必会关照中国读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同时保留汉语的文化特质,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和适当的翻译方法如意译或编译等来达到译文的预期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程译本里经常出现任意删减或增补原文的现象,以至于使得译文和原文相去甚远。
五、 结语
回译的过程实际上是由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主体、翻译对象等翻译要素因信息的传播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在华裔美国文学的无根回译中,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 以翻译目的为导向,选择译文读者接受能力范围内的表达方式, 对译文读者实施文学视野和文化视野上的全面关照,从而顺利地实现其翻译目的,达到预期的翻译效果。《喜福会》的汉译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华裔美国文学汉译的过程, 更好地处理在无根回译过程中各个翻译要素之间的矛盾。
通过《喜福会》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无根回译时,都力求真实地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色彩,但基于不同的目标读者,两位译者在具体译法上又各有千秋。田青注重译文的充分性与学术性,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忠实地还原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原有风貌, 将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有利于引导对西方文化感兴趣的学者更好地去接近和探索华裔美国文学,并且满足了一部分有一定英文基础的读者对华裔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身为作家的程乃珊,在回译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归化策略,她把目标读者和译文的可接受性放在首位,充分考虑到潜在读者的接受倾向,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来再现原文的意境。程译本缩小了原文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文化距离, 让没有英文功底,对西方文化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尽管两个译本也存在不足,但它们为华裔美国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我们可以通过对此类无根回译作品的个案分析,探究如何兼顾译文的学术性与可读性的成功经验,形成理论结晶,以之指导华裔美国文学的翻译实践,服务于更广大的读者。
参考文献:
[1] 谭恩美. 喜福会[M]. 田青,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2]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 Shuttleworth M. 翻译研究词典[Z]. 谭载喜,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19.
[4]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Z].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5] 刘芳.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回译问题——《喜福会》及其中译本个案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 2006(5):7-10.
[6] 陈志杰,潘华凌. 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处[J]. 上海翻译, 2008(3):55-59.
[7] 王宏印,江慧敏.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2):65-69.
[8] 何子章. 差异及对立的终结——移民英文小说汉译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2009.
[9] 江慧敏.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论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的无根回译[D]. 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2.
[10] 金元浦. 接受反应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11-12.
[11] Tan A. The Joy Luck Club[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9.
[12] 许钧,穆雷. 翻译学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9:10.
[13] 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377.
[14] 张景华. 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