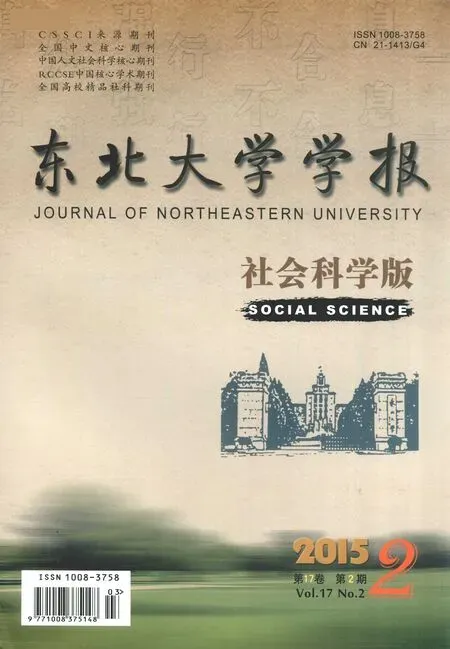论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基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的观点
——————————--
论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基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的观点
刘光斌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技术是如何应用到社会统治之中的?马克思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应用遵循资本逻辑,技术不仅取得资本形式,而且成为获取资本的手段统治活劳动;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遵循单向度逻辑,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它在生产、消费、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单向运用,造就了极权社会;福柯认为技术应用遵循微观权力逻辑,他把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规训权力技术和生命权力技术的应用造就了一个规训化社会。三位思想家关于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本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关键词:技术;社会统治; 马克思; 马尔库塞; 福柯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03
收稿日期:2014-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ZX028)。
作者简介:刘光斌(1978-),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2-0122-07
Abstract:As to how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social ruling, Marx thinks technology abides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echnology not only acquires the forms of capital, but also becomes the means of obtaining capital to rule the living labor. Marcuse holds that technology follows the one-dimensional logic in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Technology is a new form of control, whose one-way applications in such areas as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olitics and culture have created a totalitarian society. Foucault argues that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should follow the micro-power logic. By 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power, he concludes that the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to discipline power and life power have brought about a disciplinary society. The three thinkers’ viewpoint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social ruling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nature of technolog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to Social Ruling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Marx, Marcuse and Foucault
LIU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Key words:technology; social ruling; Karl Marx; Herbert Marcuse; Michel Foucault
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不必然导致统治,然而现实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技术统治、压制性的一面,那么,技术是如何被应用到社会统治之中的呢?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用各自的理论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为我们分析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资本逻辑,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不仅取得资本形式而且成为获取更多资本的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强化了对活劳动的统治。受马克思观点的启发,笔者注意到马尔库塞和福柯的相关论述也很有代表性。马尔库塞分析了技术的单向度维度,认为技术发挥了统治作用,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极权社会;而福柯主张技术遵循微观权力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权力技术的应用导致规训化社会的出现。
一、 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的技术应用
马克思明确指出技术本身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中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中的矛盾“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508。机器、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及在社会中的渗透使众多劳动者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受到控制,因为机器的应用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却增强了劳动强度;虽然活劳动制造了机器,却成为机器的附件,并受到机器的奴役;虽然减少了生产劳动力价值的时间,却延长了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日。总之,是技术及作为技术物化形式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应用,产生了社会统治的效果。在剩余价值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技术、机器取得资本形式并得到广泛运用,造成技术与活劳动的对立,强化了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关系。这种统治关系通过机器及体现在机器系统中的科学、工厂(社会的群体性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体系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工厂制度的完善,机器体系、科学,以及工厂制度一起作为“‘主人’的权力”[1]487统治了活劳动。
第一,机器体系支配活劳动。机器可以视做技术的物化形式,机器体系的应用引起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机器取得资本形式最终控制了活劳动。随着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的融入,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劳动资料的形式成为固定资本。在工厂手工劳动时期,以及工厂手工劳动向机器化大生产过渡时期,虽然存在机器的应用,却无法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机器体系,一直到自动机器体系在工厂中得到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才成为可能,机器也就取得资本形式。因为,机器体系形成后,机器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而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即固定资本,劳动资料转化为固定资本成为与资本相适合的存在,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在机器体系形成之前,机器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机器体系形成之后,机器虽然还是劳动资料,却以固定资本形式出现,不再发挥中介作用,而工人发挥了中介作用,一方面要维护机器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使机器作用于原材料。“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2]184,活劳动在机器体系中失去了自身的自主性,结果成为机器体系的肢体或零件,对象化劳动实现了对活劳动的占有。在生产过程中,机器体系支配了活劳动,“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人对立的独立的权力”[3]289,机器本身不剥削人,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家的贪婪,导致机器这种“铁人反对有血有肉的人”[3]354,实际上就是“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1]464,从而实现对活劳动的占有。
第二,科学发展控制活劳动。马克思认为科学发展为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手工业劳动阶段,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当社会生产进入到较高的大工业阶段,随着科学对自然力的掌握和应用,机器逐渐取代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机器取得关键的地位。其二,随着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机器体系自身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为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提供手段。在机器体系发展的条件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2]195,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目的在于将科学直接应用于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利润,科学服务于资本,取得资本形式,极大地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机器系统实现对活劳动的占有在现实性上是通过借助于科学的发展并影响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来实现的。科学为资本服务使机器完成以前工人完成同样的劳动成为可能,同时发明成为一种职业,推进了科学直接应用于生产领域。如此一来,生产过程中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自然科学获得资本形式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那些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学的人便利用科学来致富。科学的发展使“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2]188,或者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及作为其物化形式的机器体系的广泛应用,机器化大生产越来越依靠自动机进行生产,虽然人能够运用意识掌握科学,但科学一旦物化为机器之后,便会借助机器体系奴役人,作为与工人异化的力量存在。也就是说,科学被广泛应用于机器生产中,借助于其物化形式存在的机器实现对活劳动的统治,取得资本形式,“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1]487。工人的技能转移到机器上去了,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甚至不能奋起抵抗。科学被分离了,使它成了独立于劳动的一种生产能力,并强迫它开始为资本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本身不创造科学,只不过科学发展遵循了资本逻辑,取得资本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科学满足资本需要。与此相反,尽管劳动人民创造了科学,但是,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科学终究是为资本服务的,成为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手段,不可避免地成为作为与工人相异的力量,成为“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3]353。
第三,工厂制度统治活劳动。工厂手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协作需要特有的专业化、等级化、熟练化的工人,而在机器体系中,社会的群体性劳动是在工厂中进行的,机器化大生产中工人只需要完成简单的协作,工人只需要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整齐划一的连续的劳动,从而推动了劳动的平等化趋势。在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工厂取代家庭及小作坊成为重要的劳动协调机制。在工厂中只需要把工人分成小组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在机器体系中,工厂作为固定资本构成剩余价值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里完成劳动协作,组织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社会的群体性劳动,工人依据机器的需要被分成若干小组分配到不同的机器上去,目的是为了保证机器的运转,工厂的分工制度使活劳动服务死机器制度化、合理化。如此一来,工厂制度主要考虑机器的运转,工厂通过制度安排确保社会分工适应机器运转的需要,保证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工人只是被动适应机器运转的需要。工厂制度中形成的这种分工制度被资本当做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1]486,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1]488,也就是以立法形式确保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在工厂制度控制下的工人无能为力,只能屈从于整个工厂的分工制度,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统治。
总之,马克思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应用,体现在劳动力价值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技术作为资本形式统治活劳动,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条件使用工人”[1]487,结果便是工人与劳动条件的颠倒,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在工厂的分工制度下,活劳动成为死机构有意识的组成部分,即,“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486。机器、科学和工厂制度遵循了资本逻辑作为资本形式实现了对活劳动的统治,从活劳动与机器体系的关系看,机器体系统治了生产者,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造成工人的片面发展,促成死机器对活劳动的统治;从活劳动与科学的关系看,科学取得资本形式,应用于劳动过程进而统治活劳动,发展科学的人利用科学致富;从活劳动与工厂制度的关系看,工厂法典以立法形式确保社会分工实现对工人的专制。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提高生产力的方法是围绕资本运作而展开的,作为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机器、保证机器体系运转的工厂制度、取得资本形式的科学一起统治了活劳动,最终使工人不仅在劳动过程中服从于资本,而且在现实中服从于资本主义制度安排。
二、 马尔库塞:发达工业社会统治中的技术应用
和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注意到生产领域技术应用带来的自动化现象和统治问题,但马尔库塞更多地把技术合理性与统治合理性结合起来,把生产领域的技术应用扩展至消费、政治和文化领域,把整个社会视为技术应用的系统进行考察。因此,决不能把技术看做是中立性的单纯工具,而是受到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技术,是应用于特定社会现实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结果导致技术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的主要控制形式。作为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技术遵循单向度逻辑,发达工业社会借助于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变成为一个没有否定、没有对抗和没有批判的社会,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文化、政治和经济都被整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治框架,造就一个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导致劳动阶级的分化,产生对社会的认同。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在生产设施中得到了具体化(尽管对它的使用是不合理的)。”[4]22-23在工厂中,技术的应用主要实行机械化生产;技术被不断应用于改造和提高生产工具,并进行资源开发;劳动方式不断得到改善以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科学技术运用于企业管理,以科学经营方式安排生产劳动。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并对劳动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机器造成工人职业层次的分化,工人队伍中“蓝领”朝“白领”方向转化,但并没有摆脱被统治地位,机器反而“表现出更大的统治权”[4]27,因为随着机器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机器取代了工人劳动,工人必须掌握操作技术的知识和方法以适应机器运作的工作程序,工人职业层次的分化并没有提高职业自主权,工人及指导他们的那些知识性职业都受制于技术的统治,被迫适应技术的需要。另一方面,机械化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和态度,但并没有改变工人的处境,他们仍受到剥削。发达的自动化工厂中体力转变为技术和思维技巧,机器支配了生产者的身体,甚至控制了生产者的意识,实现对生产者的统治。在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使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缓和,比如,允许工人持有公司一定的股票,使工人越来越依赖企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允许工人参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甚至参与技术决策,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利益。在马尔库塞看来,这实质上是用技术控制的方式管理工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
第二,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满足了人们的虚假消费,造成了消费异化和奴役。劳动力的消费对维护社会的再生产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大量的消费,社会生产就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发达工业社会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消费,以不断刺激人们追求消费,达到更加有效地控制人们的目的。“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4]6现实社会中,诸如休息、娱乐等属于虚假需要,人们遵从广告及电视等各类媒体宣传进行的消费也不是人们的真实需要。因为,上述需要是技术社会从外部以隐蔽的方式强加给人们的,目的是使个人按照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方式生活,从而使个人失去了选择自己生活的自主性,甚至以为这就是他自己需要的生活。技术进步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实现“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4]10这一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对汽车、住宅及各种设施的需要等构成了人们生活的真实目的。马尔库塞认为事实上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技术这种新的控制形式在消费领域应用导致的结果,反而以为社会强制是为了个人自由,接受社会操纵是为了舒适的生活,压制性的社会需要可以与个人需要保持一致。这些消费只能是虚假的需要,在消费社会中,资产阶级不断利用技术制造虚假需要,实现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统治,工人可以同资本家一样消费同样的产品,人们在满足的消费中忘却了遭受剥削和统治的现实处境,而误以为通过消费平等方式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马尔库塞指出消费领域技术应用的统治本质,即“奴役的加强”[5]。
第三,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国家操控技术组织和生产程序,使统治转化为管理。马尔库塞指出政治权力通过控制机器生产程序,操纵国家机构技术组织发挥社会统治功能。政府控制机器生产程序,主要通过鼓励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科学发展;政府操纵国家机构技术组织主要通过相关政策和科学管理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是借助于对技术的管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机器在物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是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法取代的,“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4]5,因此,只要掌握了技术及其物化形式的机器,就掌握了统治权,管理好技术就能够实现对人的统治。由于生产技术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工人阶级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统治以管理机器的形式发挥作用,甚至“依赖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4]32。在技术世界中,统治者只要掌握技术组织和生产程序的管理权,就能够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由于技术受制于资产阶级尤其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技术以表面上满足了人们利益的形式出现,本质上掩盖了组织这些设施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马尔库塞指出“统治转化为管理”[4]31,这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反抗,维护统治利益,并且认为抑制性的社会管理越是合理、有效、全面地利用技术,受管理的个人越是很难打破遭受奴役的状态。
第四,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出现了单面文化,压制了文化的批判向度。文化的单向度主要表现为高层文化的世俗化。在马尔库塞看来,高层文化过去总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它的乐趣,高层文化是双向文化,它既是高于现实的文化,也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化,清除双向文化的办法,就是高层文化世俗化,排除高层文化与现实超越性、对立性的因素,结果便是高层文化合理性的丧失。高层文化世俗化得以实现主要借助于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文化产品大规模地复制得以实现,高层文化可以像商品一样进行买卖,从而使高层文化显示出来,并纳入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中。技术进步尤其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各种文化形式商品化的进程,导致各类文化的独创性、多样化及批判性精神丧失,而以同一性、齐一化的商品形式出现,如此一来,高层文化取得商品的物质形式使“它丧失了更大部分真理”[4]54。文化领域的单向度还表现为话语领域的封闭和全面管理的语言。马尔库塞指出社会宣传机构控制了话语权,为社会现实进行辩护,其单向度的表达方式必然限制思想交流,从而使批判性观念变得不可能。社会宣传机制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各种传播技术,向人们宣传各种观念,并且让人们相信,宣传的这些观念都是正确的,值得相信的,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要接受,甚至在行动上也要保持一致。通过灌输文化的单向度,实现人们对现有社会思想文化上的认同,“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4]12。
三、 福柯:规训化社会统治中的技术应用
福柯反对把权力看成是宏观的政治权力,而是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微观权力关系。他指出:我们从宏观层面分析权力,从国家机器、法律层面理解权力,过于把权力问题简单化,从微观层面理解的权力比国家机器、法律宏观层面理解的权力“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6]。因此福柯更多地从微观层面分析权力,把权力理解为一种微观权力关系,认为在整个现代社会,弥散性的权力已经浸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一定是靠国家机器来实现。这反映出一种新的政权运行方式的形成,“当我说到政权机器时,指的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7]。权力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网络是无处不在的,类似于毛细血管的形式,它渗透于人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网住出现在这个网中的所有东西,并且在微观权力关系中形成了一个规训化社会。知识与权力的联盟及其应用使现代社会成了一个规训社会。福柯探讨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的应用促进并丰富了知识,体现了权力的需要。其二,知识强化了权力。知识的进步,能更好地服务权力,增强权力的控制效果。其三,权力和知识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8]29知识强化了权力关系,权力制造了知识及其互动关系高度概括了知识/权力共生结构关系,即福柯所称的“知识/权力”概念。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及其应用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知识的进步,加强了对人们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规训、训练、操作和监督等;另一方面,伴随着权力关系的需要,知识得到发展。因此知识的进步和权力关系的细微化相互推进,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人们行为的各种控制和约束变得更加隐蔽、更加节约成本且更加有效果。在规训化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知识与权力的联盟,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统治作用,成为统治技术,这种统治技术以两种典型的方式在社会中得到应用。17世纪出现了规训权力技术,18世纪出现了生命权力技术,它们分别从个体化模式和大众化模式两个层面探讨了权力技术在现代社会统治中的应用。
第一,规训权力技术实现对个体的控制。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8]241-242,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技术,主要针对个体。具体来说,规训权力是通过惩戒或惩罚方式控制个体(肉体)的一种权力技术形式,它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姿势等,针对个体的肉体而采取类似于监狱的监视、目光注视、文字档案的记录,以及规范制裁等手段,通过对个体的惩罚,最终使个体成为一个服从规范又听话的顺从的肉体。福柯认为规训权力技术,是微观权力应用中的技术,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并且无处不在,把各种消极的抵抗控制在一个封闭的制度之中。在微观权力关系中,监视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以此为基础监视被广泛运用和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之中,最终社会“变成一种‘纪律社会’”[9]。与传统暴力、酷刑式的惩戒手段折磨人的肉体存在形式上的不同,规训权力技术通过采取渐进的步骤、细致入微的强制、持续不断的检查、规范化的训练,最终实现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重构,把个人变成顺从的肉体。规训权力技术对现代社会中个人被支配、控制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角度,规训权力技术的运作模式和程序已经不同于君权和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规训权力技术比后者更加节约成本,更加隐蔽,也更加有效。以现代制度形式出现的规范化管理及技术等都可以视为统治的力量,微观权力关系网络构成的权力社会就是一个规训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权力对人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细致地渗透到身体的方方面面。学校、监狱、医院、工厂和军队是规训权力技术应用到整个现代社会的典范。
第二,生命权力技术实现了对群体的控制。生命权力技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非惩罚的权力形式,通过国家发挥调节机制,将驯服的人作为整体的大众来管理。福柯指出生命权力技术针对类的人或群体,并与规训权力技术作了比较。规训权力技术通过惩戒方式力图控制群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人群分解为个体,针对个体采取诸如监视之类的规训权力技术;而生命权力技术同样针对群体,只不过是采用将个体整合为群体的方式,所采用的权力技术主要通过调控出生率、死亡率、再生产率、人口的繁殖率,来说明生命政治学。“针对总体现象,针对人口现象,通过大众的生物学或生命社会学的过程来实现”[10]235,导致了建立协调和集中化的复杂机构。18世纪便开始分析流行病引发的死亡现象,调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相应采取了一些控制人口出生的措施。人们在分析流行病引发死亡的基础上,促使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医学的确立,“包括协调医疗、集中信息、规范知识的机构”[10]230,为了让公众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还采取普及医疗事业,号召全民卫生学习这些措施。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工业化时期,福柯认为人们开始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那些偶然的群体,这些人因为自身的能力、事故、身体缺陷、残疾等因素成为社会生活中被忽视的少数人群。针对这些偶然的群体,生命政治学根据各类偶然群体的特点建立了相应的救济机构,甚至诸如个人和集团储蓄、保险等较为合理的机构,还包括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生命政治学还对人们的生活环境负责,比如对交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相关城市问题负责。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学通过获取出生率、发病率、死亡率及环境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从而确立了生命权力技术调节的领域,主要通过调控出生率、发病率、死亡率等来规范社会行为,它比传统权力更容易让人接受,更加有效。
福柯指出技术在现代社会统治中的应用,形成规训权力技术和生命权力技术这两种权力技术,前者依靠一定的机关采取惩罚机制来对个体进行规训,使个体成为温驯的肉体;后者依靠国家机制采用调节机制干预生物学过程,实现对群体的控制。福柯认为制度机构的整体就是制度的惩罚机关,生物和国家的整体就是国家进行的人口调节,分别实施对个体和群体的控制,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规训的整体机制和调节的整体机制不处于同一层面但可以“相互铰接在一起”[10]236。规训化社会就是这种双重机制作用的结果。“通过惩戒技术和调节技术两方面的双重游戏,它终于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口的全部。”[10]238规训化社会是权力技术应用的结果,权力技术不仅解释了个体惧怕惩戒而服从统治,而且表明权力通过调节机制从整体上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四、 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相关观点的评价
根据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的相关观点,我们对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作出四点评估。第一,技术扩宽了统治领域。在当代社会,技术统治早已从生产领域进入到政治、文化和消费等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技术改变了统治手段。从围绕资本生产,在工厂制度中实现对技术、机器和活劳动的管理,到技术成为新的控制形式,“统治成为管理”,以及微观权力统治技术中管理的广泛使用,说明技术取代传统的暴力酷刑等统治手段成为新的统治手段。比如,对消费的引导、对机器生产程序及技术组织管理,采用摄像头对人们行为的监控等等统治形式无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第三,技术增强了统治效果。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了死机器对活劳动的统治,或像福柯所说的那样,监狱、工厂、兵营、学校,甚至保险、个人和集团储蓄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无不发挥统治(管理)作用,都是权力技术应用的结果。第四,技术维护了统治利益。技术的统治功能从本质上说是对社会生活中的人的利益的反映,用芬伯格的话说,“技术是这些行动者的社会表达方式”[11]。在马克思那里,总是资产阶级为了资本利益利用技术和机器操纵和管理无产阶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处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操控下,掩盖着组织这些设施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反映了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
必须指出,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说明技术发挥了社会功能,但并不意味着技术的社会功能只是发挥统治功能,事实上,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技术之所以发挥统治功能说到底是为了管理和控制技术背后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在其应用过程中总会受到社会结构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仅仅揭示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有关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三人的技术观中只包含统治的观点。事实上,技术的统治功能只是技术发挥社会功能的一个方面,并且不必然像马尔库塞和福柯所说的那样,技术的社会功能完全是单向度的和无法改变的。马克思提出了改变技术统治功能的方案,即采用“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12],在他看来,只有进行制度的变革,才能最终实现劳动者对生产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掌握,进而可以改变技术、科学、机器及资本与活劳动的关系。如何避免技术的统治功能,在本文中不是论述重点,不再多述。总之,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作用,认清技术权力背后的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技术的社会统治功能及其运行逻辑,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技术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机器和大工业[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 马克思. 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 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反革命与造反(1971年)[M]∥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604.
[6] 包亚明.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61
[7] 杜小真. 福柯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269.
[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9] 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M]. 杨善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47.
[10]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1] 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4.
[12] 马克思. 资本的流通过程[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05.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