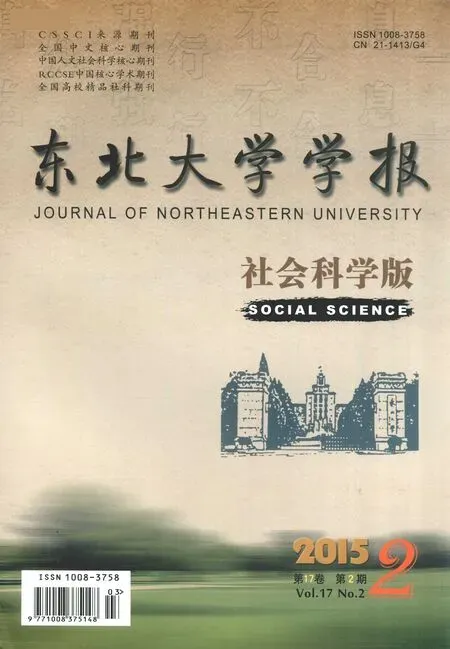网络空间的权力:技术与话语
——————————--
网络空间的权力:技术与话语
刘贵占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要:网络权力是社会行动者利用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对他人进行控制与支配的一种力量。依靠技术与话语作为双重支撑,互联网重塑了人类生产、生活场景,将世界连接为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相冲突的场域,权力在不同国家、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动。网络权力在信息技术定形作用下,呈现分权化与集权化相统一、生产性而非压抑性的运行特征。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利用新机遇发展信息技术、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的治理,还要建设本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抵御全球话语对于民族文化权力的侵蚀。
关键词:网络空间; 技术; 权力; 话语权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02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14C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HEUCF2014002)。
作者简介:刘贵占(1979-),男,山东郓城人,哈尔滨工程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1-0117-05
Abstract:The power of cyberspace is a tool with which the social actors tak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control and dominate others. Relying on technology and discourse as the dual support, the Internet has reshaped the settings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ving. It links the world as a field between the global and local conflicts, where power flow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or individuals. With the shap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ower of cyberspace has presented its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unity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being productive rather than repressiv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only use the new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Internet management, but also construct their own ideological system so as to fight against the erosion of global discourse into national culture power.
Power of Cyberspace: Technology and Discourse
LIUGui-zhan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Key words:cyberspace; technology; power; discourse power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信息技术与政治权力的融合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权力并非来自传统的政治过程,却和通信技术紧密相关。以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全球互联空间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基本力量,它重新塑造了人类生产、生活场景,重新分配了话语权力,对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生产提出了巨大挑战。从技术、话语与社会权力相关联的视角审视网络空间,有利于正确认识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范式。
一、 网络空间的技术迷思
网络空间的迷思(myth,本文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此词,指神话或虚假承诺)来源于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信息技术的力量首先表现为对人类生存时空的改造。
1. 建构全球互联时空
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根本物质性向度,也是支撑社会权力运行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空间一直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之中,从最初的原始洞穴,到农业文明中的部族村庄,再到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权力能量的释放正是通过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改造实现的,它再造了一个新的技术空间,突破了民族、地域限制,将人与人连接起来。网络空间的发展与资本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它会自动流向并控制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地域和人群,通过选择性地吸纳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而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
信息技术塑造的空间架构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了全球化的范围,社会行动者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失去了联系的必然性。依托于电子回路、节点和核心、技术协议三层物质结构,网络空间被高度压缩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全球零距离互联空间,连入的每个节点与核心具备完整的地方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功能。扩张后的网络空间还容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工作、购物、娱乐、教育、公共服务、政府事务等逐渐与地理空间临近性失去关联。大卫·哈维曾恰当地以“时空压缩”描述过网络时空,取消访问限制、管制,资本与信息可以在不同经济体、不同节点之间瞬时穿梭。互联网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不受民族、国家等地理空间限制的全球共时性平台。
2. 拓展公共话语领域
信息技术产生并推广以后,对人类生活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建构了一个民众可以自由接入、参与开放式对话、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拓展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形式。“公共领域”理论实际上反映了早期资本权力的扩张与建构,独立媒体的出现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高峰;而随着政府和垄断集团控制了大众媒体,大众传媒的作用从信息提供者演变成公共舆论的塑造者,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批判精神极度萎缩,公共领域岌岌可危。
网络技术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公共领域的颓势,基于P2P技术消除了中间环节,将人直接连接起来,改变了以Internet网站为中心的状态,重返非中心化并把权力交还给用户。麦克卢汉的学生莱文森乐观地对技术赋予网络媒介的无限权力及其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信息权力已经分散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脑之中,网络形成了一个新的非集中化的权力结构[1]。一方面,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对信息技术、信息传播的监管都降到了最低。另一方面,网络自媒体的出现降低了媒介使用的门槛,提升了民众的媒介近用权,出现了一批关注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批评性地验证报道内容,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政府控制。借助于新的传播方式,互联网的沟通威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共事件的透明成为普遍的诉求,网络空间成为社会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
3. 转变垂直权力关系
信息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政治功能,由于其强大的横向联系能力,社会组织结构由垂直纵向权力关系向横向水平权力关系转变,这种转变更加突出个体的自由选择。
信息技术不能被简单当做一种信息交流工具,技术性能本身是被带入社会语境并参与社会权力建构。技术的应用不局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要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社会组织或个体亦将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新机遇。互联网中人与人的联系不是面对面的社会关系,它以符号化的横向传播取代了人际传播,大大节约了信息流动成本,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接入到新信息技术中,社会成员拥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的接近政治信息资源的权力,并且进入到以超出传统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力网络之中[2]。近些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后果,表明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政治的载体,它改变了政治运作过程。以阶级纽带的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度逐渐让位于一种界限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横向网络关系。
二、 话语对技术的建构
抛开人类社会关系,单独理解信息技术带来的时空终结、传统政治权力终结,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技术通过工业资本生产而存在并体现其作用,对技术的理解需要放置于社会全景之中。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时代的巨大的、日常的技术哲学[3]。
1. 科技话语的兴起
在19世纪以前的哲学、文学艺术作品中,技术并不是一个受到人们重视的术语,许多人直接将其称之为机器、工具、工艺,技术并未受到重视。20世纪,语言习惯逐渐发生了转变,技术这一术语在外延和内涵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日常领域和理论领域。关于技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迷思性话语不断出现。
19世纪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们预言:电力将“照亮世界、消灭犯罪”。20世纪核能的支持者鼓吹:强大的原子很快就将能为世界供应几乎是无需计量的热能和电力。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深刻改变了日常生活,成了某种强大的政治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赛博空间逐渐成为技术和电子崇拜的新圣象,约翰·P.巴洛1996年发表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宣称赛博空间是不受工业权力干涉的完全自由领地。虽然很多历史预言已经证明了其错误性,但它同时印证了拉图尔的观点: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即科学技术,笔者注)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可能性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4]。
2. 全球化的语境
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显然受到了全球化的语境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需要资本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全球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的支持首先来自于股票交易商。互联网技术的“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唯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5]。
互联网成了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交汇冲突的场所,互联网上的每个节点都代表着地方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互联网技术征服全球的过程,也是美国政治价值理念的强势推销过程。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被许诺以美国语境下的“共同政治生活”,它承载了公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北非、中东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称将继续支持社交自由软件的开发,推进维护互联网自由的国家战略。西方价值观以“普世价值”自居,其互联网战略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剧烈的冲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是一个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世界文学”,越来越多的技术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全球化在本质上不能是美国化、西方化。
3. 新自由主义的语境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还受到了新自由主义语境的影响,它认为只有私人部门才能真正促进技术的创新,具有政府背景的网络技术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受到各种非难。新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经济政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其核心理念是政府在政策选择中的角色应当更多地被消除,代之以全球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互联网传播和服务技术的自由竞争,形成了具有行业领导力的跨国技术、传媒集团。伴随着跨国公司技术领军地位的确立,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技术全球主义主张打破民族保护壁垒,由全球市场力量自主领导技术创新,反对国家干预。然而实际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均受到了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共同重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私人部门承担着技术创新计划,政府正采取混合策略来消除法律障碍,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私人部门经济实力薄弱,技术发展获得国家的支持,从现实性上不难理解。
三、 网络空间权力的运行
网络空间技术权力运行表现为既定规则之内的自由竞争,话语权竞争表现为多国、多方的进攻与防御、参与与对话。
1. 技术定形下的自由竞争
网络空间打破了国家界限,网络权力运行在一个全球化与地方化既冲突又合作的复杂情境之中。网络治理权主体并不明晰,互联网是美国投资发明的技术,全球互联网主根服务器设置在美国,美国政府和国际企业实际控制着网络空间的主导权,他们是技术规则的制定者。
安德鲁·芬伯格通过“技术的定形”理论更加精细地研究了技术与权力的关系,他指出:“技术的战略创造了一个活动的框架、一个游戏的领域”[6]。如果把互联网空间的权力博弈比喻为游戏的话,游戏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一个框架起到了定形的作用,各国在网络技术所定的“形”里面来进行游戏和博弈,而技术本身就作为权力存在于游戏之中,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动和转换,各种力量都可以完善游戏规则、自由地利用规则、发展地方性的应用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代码就作为一种游戏规则起到了为参与各方“定形”的作用,游戏的结果却无法预料。
2. 意识形态进攻下的对话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以彻底压迫为基础的权力体系很难能延续下去,信息沙文主义同样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因此,约瑟夫·奈曾建议使用“文化帝国主义”[7]、“软实力”这些工具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美国已经成功运用“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动员其他国家参与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上来,成为经济利益上最大获得者,并且通过倡导“互联网的自由”打通对其他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通道。“冷战”时期,西方媒体曾经通过努力成功说服了一些国家的公众相信电影、电视、出版的审查行为与极权主义的纲领很难区分。一定意义上说,前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抵御意识形态信息侵袭的能力,政坛相继发生剧变。“冷战”结束之后,后冷战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终结,网络空间的维基解密、Twitter、Facebook等社交软件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政权合法性造成了巨大冲击。面对美国来势凶猛的政治意识形态进攻,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相继倒台或松动,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急需提升处理信息的技术及与发达国家对话能力。
3. 分散化与集权化并行
集权化与分散化看似是相互矛盾的不同趋势,而实际上这种矛盾的双向却能在网络空间权力运作中并行不悖。权力分散化是网络空间所透露的内容,包括对社会民主、自由的真诚的渴望;权力集权化是网络空间所掩盖的内容,包括被跨国集团所掌握的传播权力的日益集中。
分散化是从网络技术代码自身规则角度来说,互联网的P2P技术(实际上当前纯P2P技术应用较少)采用“去中心化”的设计,去中心化也就意味着“权力分散化”,技术被赋予“创造”“分享”等社会意义,是对话语垄断权力的一个巨大挑战。由于网络自媒体的兴起和话语权传播环境的碎片化,网络空间权力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的系统化能力。每个个体或组织都是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的一个节点,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支配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网络空间话语权力关系运作,呈现普遍性、协作性、分散化的特点。一些专家在网络空间发表“雷语”后遭到的网民“围剿”,便是权力分散化的一个微观例证。
集权化是从信息技术和资源的掌控者角度来说,网络通讯技术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筹划的一项未来计划,是美国决策精英们直接精心策划的野心勃勃的商业——政治目标。美国卫星通讯公司于1963年迅速成立,反映出美国领导层决心从其空间技术优势攫取最大利益,卫星通讯公司帮助美国在卫星通讯时代拥有并维持其技术领导地位。在当前的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副根服务器中,1个在英国,1个在瑞典,1个在日本,9个在美国。国际互联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掌控着全球互联网的域名解析系统,拥有使一个国家网络瘫痪的能力,而ICANN的管理权由美国商务部掌控。
四、 网络空间权力的控制
任何权力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运行机制作为监督。网络是一个全球化的空间,事关全球利益,民主控制符合全球利益。各国也需要制定一套符合技术经济学的制度,防止滥用惩罚技术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塑造来建构和维持地方性的共识。
1. 信息技术的民主控制
网络空间权力的全球化场域有了多个国家的参与,才有了存在的意义,才符合美国主导的“国际信息新秩序”,长期以来,美国把持了互联网的管理权力。2013年曝出的“棱镜门”事件表明,普遍的技术监控行为正在减弱全球互联网用户的信心,使各国对于互联网信任大为减弱,互联网面临分裂成独立国内网络的危险。
兰登·温纳认为采用民主的方式提高公众的参与,使用技术的民主控制可以应对技术失控的现象。他非常赞赏丹麦的“协商会议”、荷兰的“科学信息站”、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方法”管理技术的方式,无论普通民众的技能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有机会参与到技术更新的决策之中,协商结果还是相当民主、公平、合理的。技术的政治性决定了技术在开放性和限定性之间存在悖论,与技术相关的政治一旦在公共领域公开,必然导致不同立场和观念之间的冲突、争论。不论过程如何,民主化的程序会避免偏执的技术操作和运用。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入民主控制,不仅可以保证全球安全,还可以避免技术发展脱离人性与道德。
2. 技术经济学预防惩罚技术权力滥用
作为权力的技术本身亦有许多精细的制度支撑着权力的传递与执行,它主要通过政治力量对技术权力的惩罚或支持来实现。政治力量对技术的惩罚必须遵循权力经济学,一是要考虑惩罚权力的界限,以便控制惩罚权力;二是要对于技术权力的惩罚要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科学技术的运行需要技术化的制度予以支持或约束,如制定法典、确定违法行为和刑罚尺度、制定程序规则、确立司法官的职能等,程式化的法制民主是应对政治惩罚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对于从事恐怖主义、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技术,行政力量则有干涉、惩罚的合法基础。在经济领域,政治力量干预技术需要谨慎的法理基础,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相对独立,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一个原则,我国也已经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发展思路。互联网技术及其衍生品在“丛林法则”“市场逻辑”的自由扩张中,获得了巨大的成长空间,如果利用行政文件打败技术创新则难以服人。网络技术权力的监管与约束制度必须按照制度的效果与效率原则,符合权力经济学的要求,惩罚技术的发展必然由强硬形式转化为温和形式[8]。过于严厉的惩罚无疑会使新技术、资金流向环境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3. 意识形态话语塑造建构权力
工业社会控制依赖于一种强制力,网络空间的社会控制则主要依赖于一种认同性。网络空间里人们很难获得一致性的认知,但人们不缺乏寻找认同的努力。各国主流政治都试图在网络空间维持其权力地位,权力的维持不能靠技术暴力已经基本成为一个共识。
网络空间是一个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作用的场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内忧外患的场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防御、弱势地位是一个基本事实。发达国家强势的意识形态进攻给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自身的意识形态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公共话语创造、孕育、维持权力,权力通过话语来赢得公众,公共话语的创造与公共话语权的竞争成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重要议题。迎接信息社会全球舆论场的挑战,提升自身处理意识形态信息的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意识形态塑造依赖于知识体系的建构,通过知识化的话语传播,保持与国内民众的良好互动是维持政治权力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 何道宽,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 文森特·莫斯可. 数字化崇拜[M]. 黄典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兰登·温纳. 当代技术哲学与社会批判[J]. 安军,译.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09,26(5):1-5.
[4]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mb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9.
[5] Matterlart A.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étaire[M]. Paris: Ladecouverte & Syros, 2000:353.
[6] 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M]. 韩连庆,曹观法,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赫伯特·希勒.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 刘晓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8] 福柯. 规训与惩戒[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2.
(责任编辑: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