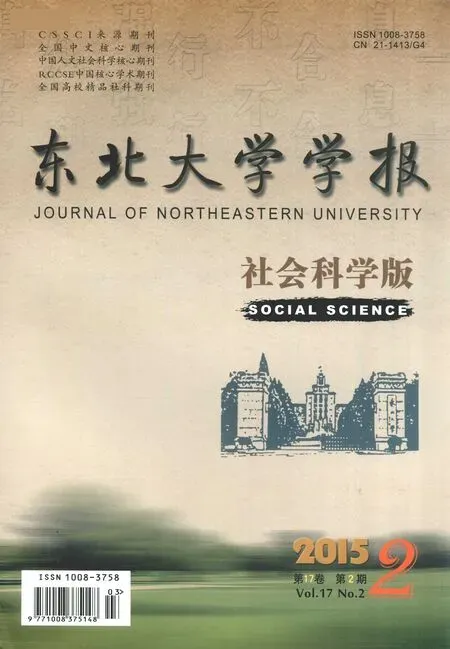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
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于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如何建立能包容更多社会需求和因素的法律范式,是法律体系乃至转型社会不断追问的话题。作为能动司法的学术回应,回应型法是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法之“应然”与“实然”结合的产物,并促使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契合了中国法律范式的发展要求。只是,中国仍处于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过渡的阶段。尽管存在人为导入回应型法因素和直接从压制型法过渡到回应型法的契机,但这却不利于整体法律建构。因此,中国欲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切实的法治秩序建构。
关键词:转型社会; 压制型法; 自治型法; 回应型法; 法治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5.02.014
收稿日期:2014-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4AFX004);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于浩(1988-),男,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治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5)02-0193-05
Abstract:How to establish a legal paradigm with more social needs and factors has been a heated issue for the legal system and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s an academic response to judicial activism, responsive laws are open, participative and flexible, which represent more social change needs. As a product of legal “ideal” and “factual” integration, they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nd universally accepted civil order, which fit the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China’s legal paradigm. However, China is still in transition from repressive laws to autonomous laws. Despite the possibility of man-made introduction of responsive laws and the direct transition from repressive laws to autonomous law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leg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China should rely on an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legal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responsive laws.
Towards Responsive Law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itional Societies and China
YUHao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transitional society; repressive law; autonomous law; responsive law; rule of law
一、 问题意识的引入:现象与文本
对于反映和调整社会关系定位的法律,无论是卢梭笔下的“关系着公共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还是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均处于因时而变和因地而变的动态过程中。因此,可以说法律在转变中的社会的角色是可塑可变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可塑,如何可变。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的一个主要基调,就是法治国家的建设。法律的本质属性与影响法律的诸多因素是什么,社会转变中的法律是处于何种动态过程中,这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两个问题。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属于法律本体论的范畴,牵涉到法律的本质属性、能够影响法律属性的社会因素或其他形而上的因素等子问题,它们关系到法律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其落实,以及在社会政策落实中形成的张力,之于法律及社会的转变而言,又有着实质影响。只有相对合理地理解这一层面的问题,才能在转型社会中为法律的制定提供正确的指引,并结合社会实际,从本土层面观察法律,最终实现法律的社会效应与其本身价值相统一的理想状态。
对转型社会法律的研究,很难绕过《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这一经典文本。该书写作背景是从罗斯福“新政”到美国民权运动等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事件的过程之中,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呼声日渐高涨,司法判决倒逼社会公共政策改变的情况逐渐明晰。作者立足于法律的社会性和形式逻辑的分析进路,通过确定法律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变量,并基于法律、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将法三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分别代表“作为压制性权力的工具的法律”“能够控制压制并维护自己的完整性的一种特别制度的法律”“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1]16。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从社会的横向层面展开对法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普遍的纵向法律发展分析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概念外延上的交叉关系。上述分类与其说是一种转型社会中的法的类型,毋宁说是社会反映之下所共同蕴含的一些法律要素,依据其强力大小所组合的不同法律模式模型,亦即季卫东教授所言的“按照理想型的方法建立的用以分析和判断同一社会的不同法律现象的工具框架”[1]4。这种从转型社会的实际出发,借助理想实验的技术手段构建法律框架,通过分析法律本质及其社会因素来考察法律在整体社会中的目的之方法,颇为值得赞赏,因而成为探讨转型社会法治建构与发展的有益进路和切入点。
二、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目的、概念与发展意识
要考察法律的本质属性及其影响法律表现的社会变量,应当从法律本体论的范畴出发,对法律的本质属性及相关的社会变量进行考察。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既着眼于法之“应然”,又从方法论上“将价值追求和经验实证结合起来”[1]2,采取了一种形而下的角度,指出法理学的权威性在被快速转变中的社会所动摇的情况,尤其是在关于“法律与秩序”的诸多危机中,社会的多元倾向导致固有的法律权威正统性受到质疑,以至于发生了维护现存秩序的行动体现法律体系僵化甚至异化的情况。这样的法律显然不能体现、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2]。为此,他们认为法学理论应当及时反映社会科学的新变化,将其更明确地从社会科学与哲学的交界领域转移到社会科学之下,提出通过经验材料的分析来感性地逐步逼近法律概念的“抽丝剥茧”式的方法,思考法律与强制、国家、规则、道德之间存在何种程度、何种条件的联系。他们甚至认为,法律的定义“应当是‘无力的’,而概念或理论则应当是‘强有力的’”[1]12,因之概念不仅可以识别相关属性,且可以提出在情势变更下的合理模型框架[3]。
正是由于变量强烈的语境性,才导致相应的法的模式具有了“混合性”特征,且上述三种法的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纵向演进的法律范型极为近似:“压制型”法大致对应“作为统治阶级暴力机器的”法律;“自治型法”大致对应“法治”模式,也就是当前的法律治理类型。那么,这是否说明“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之间不仅是横向上的法律诸因素组合,而且也是纵向上的法律发展模式呢?
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显然并不急于论证这一观点,而是转而确认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律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系的进化阶段”[1]21。他们坚持了黑格尔对发展的先验性质的理念,并强调发展是在横向上、在体制的价值和重要性上的体现,而不仅仅是时间维度中的“向前”。而且,这样的发展观念并不等同于对制度的价值评价,不对前后制度的优劣进行评判。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展不是激烈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改变,而是机制对于回应社会需求的及时性和力度上;社会形态不一定发生变化(至少不发生在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形态更替),但只要法律规范模式能够及时反映社会变革的因素,甚至是能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无论是社会秩序的跃进抑或跃退,这都是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发展”的合理内涵。
然而,由于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观察“压制型法”和“回应型法”,将程序的合理价值降低到实现实质正义的辅助角色之上,因而其法律结构是不稳定的,尤其是这样一种强调法律内在框架张力和弹性的法律模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社会变革、影响甚至主动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也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因此,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提出,只有重点发掘“自治型法”(法治模式)之中的合理内核,努力地从现有的制度设计出发,对自治型法中的程序和制度框架进行扬弃,从而迈向回应型法。这种“迈向回应型法”的呼声,可以说为司法制度的秩序建构和法律模式发展的前景开辟了一条新颖的路径。
三、 回应型法之目的:社会哲学的视角
迈向回应型法是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为可能的法律体系范式所作的一个积极描述和倡导。但从单纯的价值层面来描述或赞赏这样一个未来的法律体系范式,实际上并不利于实践的检验。但凡进行一种社会实验之前,都应当首先反思和论证,在整体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某一种社会实验“是否必要”;如果得出有利于该问题的结论,那么接下来才是追问“如何可能”的问题;如果论证的结果是拒绝这样的社会实验,那么这样的社会实验本身也就失却其合理性。因此,在中国语境当中进行迈向回应型法的实验之前,需要首先论述“中国是否需要迈向回应型法”这样一个显得更为关键而敏感的论题。
回应型法被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描述为一种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能动司法在社会领域倒逼制度设计的体现。但这样的一种描述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文本,从最基本的社会哲学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回应型法的目的论,从而回答回应型法的本土化是否必要的问题。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目的论层面的社会回应性之下,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法律目的的开放性和回应性能够增强通过法律解释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第二,法律对于社会变革的包容和支持弱化了法律的义务,并使建立一种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成为可能;第三,法律范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政治层面的话语权增强[1]87。
对上述三个论题的展开,事实上也就是论证在中国的语境下迈向回应型法是否必要的问题,因此这三个论证的结果将直接成为这一命题的条件。对于第一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就是空前地强调法律的目的解释论,强调法律解释应当首先探求规则和政策所内含的价值。这种规范性解释论的调子早在自治型法当中就已经被孕育了。法律一经诞生,就滞后于社会的特性,导致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成为必然;在解释的过程中,司法者结合生活经验,对法律的本意和立法者的意图进行合乎社会期望的解释,于是法律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即被引入法律当中,成为扩充法律内涵的一个必要手段。那么,如果按照理性实验的路径,在法律所固有的弹性系数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自由裁量权扩充法律框架内涵的行动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一旦超出相应的系数,就会产生突破被现有框架束缚的法力的合理解释,这样的社会性质上的修正是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显然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对第二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也是对在自治型法当中讨论极多的话题——对“法治”真谛的追问——的进一步延伸,只不过回应型法的目的不在于依靠程序调和利益博弈和冲突,而在于通过建设“以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一体化的”机制[1]103,不断在社会变革中进行解构—重构—再解构—再重构的这样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强调公共秩序的灵活性,肯定社会的多元性。这事实上可以在接下来的自治型法中加以进一步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最后对于第三个问题的讨论,同样也是基于自治型法的现有状况。在法治社会中强调“程序是法律的中心”和司法独立的结果[1]60,也就是在用实体服从换取程序自治[1]64,放弃对政治生活的干预来换取司法独立,导致政治层面的被动性成为法治社会中典型的法律制度特征。因此,在这三个存在逻辑上逐步递进关系的论题中,回应型法的性质是这样的:它的前提是基本的回应型法律范式合理地容纳了大量的社会诉求;基于社会变革所进行的法律解释,在维护法律规则权威的同时提升了法律的权利性质,从而削弱义务性和强力,因此调和利益冲突的程序也让位于更高程度的实体层面的社会公共秩序的追求;在这样一个解构和重构社会公共秩序的动态过程中,法律参与和政治层面的参与相互混同,通过能动司法的强化保障了社会的多元发展倾向。这样的制度有利于推动社会不同阶层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法律秩序的主张,社会自治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拔高,成为国家管治社会的崭新模式。这样一种法律治理模式,实际上是基于一国的高度发达的法治秩序而自生自发的;其组合因素在法治秩序内在动力的推动下逐步呈现出回应型法的基本框架。
那么,一个初步的结论呼之欲出:既然中国建设的是法治社会,且法治社会在经过高度发展之后将很有可能走向回应型法的模式,那么回应型法对于中国未来的法律模式建构而言,是合乎实际的,是必要的;但反观中国,不得不承认,当前中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距离回应型法的要求,依然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强调自治型法的建设,也就是当前中国法学所长期考察和追问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如何建设,又如何达致迈向回应型法的门槛?
四、 迈向回应型法:中国观点
在初步解决了“迈向回应型法是否必要”这一问题之后,紧接着的步骤则是将眼光投向中国现有的法律机制,而相关的论证也应当围绕着这套机制是否达到了回应型法所需求的准入门槛而展开。因此,对于迈向回应型法的整个论述,就需要从考察中国的法律体系入手。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工作是要论证一个更为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即“中国如何迈向回应型法”。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也是要从文本出发,具体考虑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对相关法律体系设置的描述,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的法律体系整体走向加以定位,从而确定中国的法律范式究竟处于哪一个位置;在这之后,结合实际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这不仅要从当前中国法律体系的表征入手,而且更需要从纵向的角度考察该种体制的发展经过,并紧密结合其时的社会发展的情况和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执政党在相关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立场,以便于更好地解读迈向回应型法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是一种糅杂着诸多压制型法因素的自治型法,或曰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由压制型法转向自治型法。追根溯源,主要是受苏俄式的法律制度影响。前苏联的法律制度是“压制型法最极端的表现形式”[1]38。“反革命”成为一种刑法意义上的典型政治治罪方式,因言获罪成为可能;由于法律成为推行政治政策的工具,因此法律机构也成为政治集团贯彻政治意志的附随。这些发生在苏俄大规模镇反运动中的情况,同样出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二十七年之间(1949—1976年)。在此期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都片面强调了法律作为阶级斗争“刀把子”的角色,导致法律与政治相混同,甚至出现了有法不依、违法执法的极端情况,压制型法的相关因素得以基本呈现出来。这样的压制型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制秩序,使新中国法治建设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于是在改革开放之际,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这也为中国的法律体系走向自治型法提供契机[1]3-16。
从1978年至今,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相当关键的一个阶段,也是摆脱压制型法,走入自治型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作“转型期”,实际上也就是描述中国法律体系从压制型法转向自治型法的过程。及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建设自治型法在中国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距离成为真正的自治型法(法治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独立审判观念仍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司法能动主义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饱受争议;司法审判受不同力量的干预比较突出;刑法中的压制性依然突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呼声从体制外延伸到体制内。这些都说明,从压制型法转向自治型法仍然是中国当前司法体系改革的基调,因此努力建设法治社会、建设自治型法仍是今后一段长时间内法律制度建构的主旋律。
五、 远未终结的结语:一个可能的跳跃?
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着眼的是转变社会中法律体系的范式及其可能演进的路径,认为发展的合理内核蕴含在各类型法阶段中诸要素的解构和重构这一动态的过程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当前所建设的法治社会,仅仅是作为自治型法的一种典型表现,并非法律发展秩序的终结和最高阶段。那么,如果建设回应型法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不妨作一个这样的假设:能否通过人为提速,在压制性转向自治性的途中直接导入明显的回应型法因素,使得自治型法作为从压制型法到回应型法中的过渡而非长期存在的形态,改变法律演进的自生自发秩序;换言之,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变中的社会,在自治型法尚未建设完成的时候能否人为地孕育回应型法因素,从而直接过渡到回应型法?
这样大胆的预设,基于压制型法与回应型法在关于法律的目的上的高度趋同,以及两者存在对程序的工具主义倾向。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尽管坚称,回应型法当中程序的“工具主义是为了较为客观的公共目的”[1]17,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法律的定位应该是回应社会需求的一种便利工具,是对工具主义的某种复兴[1]16。这样的观点就蕴含着压制型法与回应型法的某些性质上的诸多相近之处,主要体现在强调实质正义对社会的重要性,主张程序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工具,追求法律的目的,在超然的社会性下主张法律与政治的混同。事实上,当下中国的法律范式也存在着某些这样的类似因素。季卫东教授曾主张通过“新程序主义”来解决公众意见与职业主义司法之间的隔阂,即“通过商谈程序架构起公众与司法之间意见交流的通道;法官的裁量、当事人的自主交涉、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以及法官与公众意见的交互在审判过程中形成了主观与主观相交错、相碰撞的局面”[4]。在这样一种能动司法与社会需求相互的交流与博弈的过程中,容易呈现创造性混沌,但相互主观的判断在反复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规则和可预测性。此外,通过沟通、理解的媒介作用,其中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裁量权的行使方式等等也是可以预测的。这样一种社会利益交流机制,实质上是回应型法当中所主张的“协商参与”的萌芽模式。尽管没有涉及到回应型法的实质性主张,但这也为当前中国的法律范式建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然而,这样大胆的预设存在一个问题,即最终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国家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承认社会自治秩序进一步扩权,亦即自下而上地演变,而非自上而下地钦定。因此,如何避免过分强调回应型法对程序规则的形式主义解读,以及国家如何弱化干预和压制权能、允许社会自治的扩大,这是今后中国在迈向回应型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压制型法转变为自治型法的跋涉,还是迈向回应型法,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家如何正确理性看待法律的目的,如何应对社会不断产生的对法律合理性的询问[5]。
归根结底,合法性的认识是一个依靠规则和程序的论证过程,因此合法性源于程序的公正;这样的归纳使得迈向回应型法并不能基于压制型法而直接发生一个“惊险的跳跃”(马克思语),而是应当基于自治型法的程序需求。于是在当下中国,迈向回应型法的根基,是扎扎实实地做好法治社会的建构工作,坚定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6]。
参考文献:
[1] 诺内特,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 张志铭,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2] 于浩.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J]. 中州学刊, 2014(5):66-67.
[3] Selznick P.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Philippe Nonet and Howard Vollmer, Law, Society, and Industrial Justice[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4-8.
[4] 季卫东. 司法与政治改革互为依存[J]. 政府法制, 2010(8):11.
[5] 于浩. 共和国法治建构中的国家主义立场[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5):183.
[6] 张志铭,于浩. 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J]. 法学研究, 2013(3):3-10.
(责任编辑: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