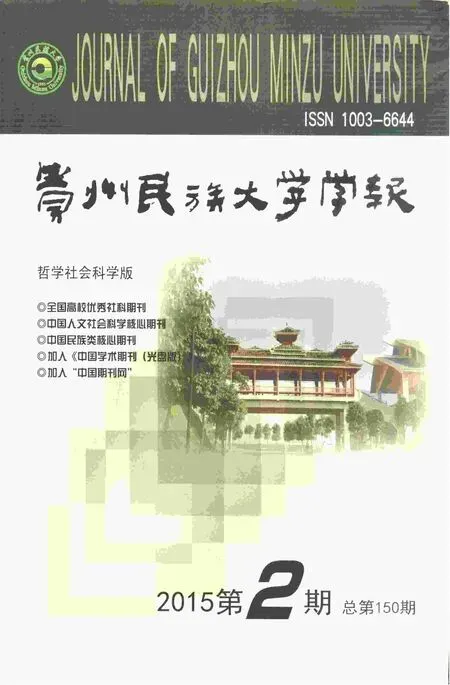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考述①
谭宝刚
(贵州民族大学 图书馆,贵州 贵阳 550025)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明清刻印古籍颇多,其中有清康熙六十年刻印古籍《庄子南华经解》一书,现就该书有关情况考述如下。
一、《庄子南华经解》撰作者、作序者和校对者
《南华经》本名《庄子》,是先秦道家经典著作之一,为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道教徒便尊之为《南华经》,且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而构思精妙,善用寓言和比喻,文笔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颇具浪漫主义风格,为先秦诸子文章之典范。鲁迅先生赞云:“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一书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庄子南华经解》就是研究《庄子》的专著,其撰作者为宣颖。
宣颖,字茂公,句曲人。宣颖在所撰《南华经解序》中自称句曲后学,则是句曲人也。句曲以山而名,句曲山在今江苏省句容市东南。①
宣颖的生活时代,应是在清顺治、康熙时。宣颖在《南华经解序》中云:“康熙六十年岁次中秋,句曲后学宣颖茂公自序。”宣颖完成《南华经解》,已经是七八十之年,根据其自序之言,则可知宣颖盖生于明末清初,而主要生活于康熙期间,或许还在乾隆时期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未可知。
宣颖的科举之途颇不顺利,终其一生,只得过贡生。关于宣颖得贡生时间,有两种说法,《乾隆句容县志卷九·人物志·文学》载:“宣颖字懋公,康熙甲午(1714年)选贡,文章与张鹿床相伯仲,所著有《南华经解》。”[1]P689而该志《选举制》中又载:“顺治十二年乙未,宣颖拔。”方勇先生以为“顺治十二年乙未,宣颖拔”为是。[2]P9其说可从。
关于宣颖生平,目前较为详细的记载见于清光绪年间《续纂句容县志》:
宣颖字懋公,一字茂公,崇德乡古逊邨人。性至孝,有逸才。少与诸昆季,及严用求、戴霖生辈,砥砺学问,有声庠序。既长,偕朱亮工,从溧阳马章民讲艺于三茅峰下,马公钦其德器。及亮工获解去,章民又大魁天下,颖仅以拔萃科贡入成。马章民寓书慰之曰:“大器晚成,行当以衣钵传生也。”已而终不遇。乃键户著述,网罗群籍,淹贯宏通,时人称为“学海”。晚年假馆邑之青元观,葛仙公炼丹处也,著《南华经解》,张芳菊人序而梓之,至今风行海内。颖不乐仕进,授读养亲。亲殁,庐墓三年。没世之日,遗书数十种,乱后尽佚。
由上可知,宣颖少时好学,曾与好友朱亮工一起师从马章民,深得其师马章民及时人称许。宣颖不乐仕进而勤于著述,他既甚赞庄子之才,亦喜读《庄子》一书,故在《南华经解序》中云:
向使以庄子之才而得亲炙孔子,其领悟当不在颜子下……不幸而圣人没微言绝,百家并噪无异禽鸟斗鸣。庄子于是不能自禁而发为高论绮言,以删叶寻本披枝见心,此又庄子之不得已也。后人读之,乃得徜徉其骀荡之姿、浩瀚之势、空灵幻化、殊诡清越之趣。此则庄子之不幸而后人之幸也。
呜呼,庄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时读《史记》,谓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及览《李太白集》,称之曰:“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予私心向往,取而读之,茫然不测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评注不下数十家,而未尝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胜名家,又未尝不茫然也。则意子长、太白所称,即此茫然无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窃疑其必不然也。吟讽之下渐有所解,屏去诸本,独与相对,则涣然释然,众妙毕出,寻之有故而泻之无垠,真自恣也,真仙才也,真一派天机也!乃知古今能读《庄子》者,惟子长、太白耳。诸家但摘其数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谓能读《庄子》,甚且字句之间大半强作解事,譬之主人觌面而旁猜张李,其支离可笑有不胜言者!噫,《庄子》之难读如是乎?予此本不敢于《庄子》有加,但循其窾会,细为标解,而不以我与焉?庶几《庄子》本来面目复见于天下,不致觌面旁猜而已。若其玄风妙旨,则鹿门茅氏尝曰:“太史公于庄子之学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赏其文尚未必知其学,况于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畅,神怡意适之际,跃如有见。则夫去圣既远,而为学人津筏有不可诬者。夫庄子既不避圣人罕言之戒,而于圣人之不欲剪者剪之,圣人之不轻示者示之,此庄子所以维末流之穷,而一出于忍俊不禁,一出于苦心致觉者也。后世分别九流,乃以异端目之。”予谓《庄子》之书,与《中庸》相表里,特其言用处少而又多过于取快之文。固所谓养之未至锋芒透露,惜不及亲炙乎圣人者。若具区冯氏谓为佛氏之先驱。呜呼,庄子岂佛氏之先驱哉?
宣颖研究《庄子》数十年,颇有心得,晚年所撰《南华经解》颇流行于世。
《庄子南华经解》前有两篇序文,一是其友人张芳之序,一是宣颖自序。张芳序末尾题“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长至日书于青元观,邑同学弟张芳菊人氏拜撰。”从文中“邑同学弟张芳菊人”可以看出,张芳字菊人,是宣颖同乡,年龄小于宣颖。张芳亦是句容名士,为当时所推许。《句容县志卷九·人物志·文学》载:“张芳,字菊人,顺治壬辰进士,授宜江令,旋罢。归,闭户不出,著作甚富,缘乏嗣,多所散佚,所传有《燕台联句》、《宜江唱和诗四集》。”[3]P689而《续纂句容县志·卷二十·拾补》所载更为详细:
张芳字菊人,一字鹿床,又字澹瓮,又号械庵拙叟。顺治辛卯举人,壬辰进士。历官长甫宜江知县,以宽简为治,旋引疾归。筑园亭于县治东南,竹树池塘,密迩城隅,有紫绵书屋、哲喜楼之胜。偕邑中耆宿,觞咏其中。精神矍铄,望之若仙。诗文古辞,直造古人堂奥。远近纂修邑志家乘,辄走书币,延聘求指义法。如《巢县志》、《古隍朱氏家乘》,皆其鉴定弅首。著述甚富,无子,多散佚。朱征君坦称其“风疏云上,一世逸才”,又称“笔墨谨严,齿牙非易”。借今于志乘谱牒中,得见吉光片羽,洋洋洒洒,沛若江河,真名手也。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张芳也是饱学之士,虽科举得意,但不迷恋宦途而怡情山水,喜藏书而乐著述。
《庄子南华经解》内篇、外篇和杂篇之首章,在“后学宣颖茂公著”文字后,内篇有“同学王晖吉季益较”八字,外篇和杂篇均有“同学王晖吉季孟较”八字。这是有关校对者的记录,“较”应作“校”,“益”应作“孟”,王晖吉字季孟,是宣颖的好友兼同学。关于王晖吉,典籍无载而不可详考。
关于宣颖及其好友朱亮工、张芳三人,《句容县志》有一段佳话:“三吴为文物之邦,句容、金陵附庸其风气为较近。前明之世,科第蝉联洎乎?国朝亮工发解于南国(朱献醇顺治甲午解元),菊人联句于燕台(张芳有《燕台联句集》),懋公著书于古观(宣颖成《南华经解》于青元观)。”则是三人在当时各有成就,应是相互砥砺的结果。
二、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保存状况、流传情况和入藏情况
《庄子南华经解》自问世以来,版本众多。台湾学者钱奕华考证指出康熙至民国有十六种版本,今引其考证出的清代版本如下:“《南华经解》是清康熙六十年版行于世,有宝旭斋刻本、积秀堂刊本、经国堂版本、经纶堂梓行本,嘉庆年间有王晖吉校海清楼刊本,同治年间有吴坤修刻本、半亩园刊本,光绪年间有怀义堂刊本。”[4]P490-503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庄子南华经解》则为康熙六十年经纶堂梓行、王晖吉季孟校本。该书刻印时间至今虽近三百年而显陈旧,但除开其前张芳序言第二页上部页面破损致使文字不明外,其余仍然保存完好。该书为小楷刻印,字体俊秀,亦一时之佳作。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一共六册,毛边纸封面,封面无字,封二右侧竖刻“句曲宣茂公先生手著”九字,中部竖刻“庄子南华经解”六个大字,左下角竖刻“经纶堂梓行”五字。附标签:书号,300075;书名,《庄子南华经解》;版本,清刻本;卷数,3;②册数:6。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在不同页码的天头,或不同页码的右下角或左下角钤有“武进孟晋斋珍藏”篆刻印,和“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藏”篆刻印。
“孟晋斋”是刘文介先生的书斋号。刘文介先生本字寿眉,又字眉叔,号眉盦、眉叟、眉道人,斋号“孟晋斋”,自谓“孟晋斋主人”。③刘文介先生是著名藏书家,一生嗜书如命,其不大的书房(孟晋斋)堆满了线装古籍,其藏书有不少来自其胞兄刘文俨。刘文介去世后,其藏书由女儿刘璥章和刘珩章商量后卖给原上海古籍书店。
贵州民族大学原名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创立于1951年,1959年因故撤销,所有图书及其他教学设备并入贵州大学。1974年贵州民族学院恢复办学,1977年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从零开始重建。2012年贵州民族学院升格为贵州民族大学。
从钤有“武进孟晋斋珍藏”和“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藏”藏书印来看,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应该是刘文介先生所收藏过的书籍。刘文介去世后,几经辗转,被贵州民族学院收藏,其入藏贵州民族学院的时间应该在1977年到2012年之间。
三、《庄子南华经解》版刻时间、版式、书之结构和刊刻之误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刊刻于何时?这我们可以从该书前面的两篇序言找到答案。
一是张芳所撰“序”,末尾题“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长至日书于青元观,邑同学弟张芳菊人氏拜撰。”“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即是1721年,“长至日”即是夏至日,此处是指康熙六十年(即辛丑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历是1721年6月21日。这就是说,张芳之序作于1721年6月21日。
一是宣颖自撰《南华经解序》,其末尾题“康熙六十年岁次中秋,句曲后学宣颖茂公氏自序”。康熙六十年,闰六月,当年中秋在公历1721年10月5日。则宣颖自序作于1721年10月5日。
查万年历,康熙六十年的除夕在公历1722年2月15日。
综上可知,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的刊刻时间,盖在1721年10月5日到1722年2月15日之间。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版框,四周皆单栏而粗线。白口,单鱼尾。版心鱼尾上部刻有书名“南华经解”字样,鱼尾之下则依次是篇名、页码和卷,如“逍遥游”、“八”、“一卷”分别表示该页是属于《逍遥游》篇,第八页,归第一卷。
其行格或行款,则因类项不同而有差异。
张芳所撰序,半叶六行,行十八字,乌丝栏。宣颖自撰序,半叶八行,行十九字,乌丝栏,但有的页面界栏不清晰以至于无。宣颖所撰《庄解小言》,半叶九行,行二十三字,无界栏。
正文行款,半叶九行,《庄子》经文顶格书写,行二十四字,宣颖解文低一格书写,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无界栏。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之结构:书前是两篇序言,一为宣颖同乡友人张芳所撰,一为宣颖自撰。其次是宣颖所撰《庄解小言》。再次,为《庄子》经文和宣颖解文。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虽刊刻良好,然亦难免有刊刻之误。如:《南华经解序》“圣人之体大而思深,为爱天下之至也,后有土智之才出焉”,“土智之才”当为“上智之才”之误。校对者之名为“王晖吉季孟”,在内篇之首叶则刻为“季益”,而其他各处仍刊刻正确为“季孟”;在各篇之首,有关校对者刻写为“同学王晖吉季孟较”,“较”应为“校”字之误。内篇总说“这一个物事漫天漫者地,是他庄子约略七个题目,大要不越乎此”,其中“漫天漫者地”应是“漫天漫地者”之误。《逍遥游》解篇题文字中,开篇刊刻“《庄子》明道之书,若开卷不也第一义示人,则为于道有所隐。”其中的“也”字应为“以”字之误。《天下》“以木为精,以物为粗”,“木”当为“本”字之误。又“建之以常无,主之以太一”,“常无”后夺一“有”字。
如此类失误,不一而足。
四、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撰作体例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庄子南华经解》有一定的体例。宣颖在撰《南华经解》时,先撰写解经总纲即《庄解小言》,然后是内篇、外篇和杂篇之经解。
《庄解小言》先叙述作经解之因,是此前注家或“全未得其结构之意”,或虽“字句之解,间有所长”然“至段落旨趣,则概未之及”,而郭子玄注“亦止可间摘其一句标玄耳,至于行文妙处,则犹未涉藩篱,便空负盛名也。”
次叙《庄子》结构,“内篇各立一题,各成结构;外篇虽不立题,亦各成结构。惟杂篇不立题不结构,仍可各段零碎读之。然《天下》一篇为全部总跋,洋洋大观。”
次叙《庄子》一书读法,“先细读其一节,又细读其大段,又总读其全篇,则窾会分明,首尾贯穿。盖必目无全牛者,然后能尽言全牛也。”
次略叙《庄子》内、外、杂篇之旨意及相互关系,“庄子真精神止作得内七篇文字,外篇为之羽翼,杂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随手存记之文。”
次叙《庄子》之表现手法或写作技巧,“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立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古今格物君子无过庄子,其侔色揣称,写景指情,真有化工之巧。”
末尾叙读经解之法,“读上文再读批辞,读批辞再读正文,反覆数过,胸中必有洞彻之乐。若不耐烦寻绎者,先不是读书人也。”
内篇先明分内外之因,“一编之书,何分内外?以其专明宗旨,故目之为内。”次叙内篇各篇题目即是主旨,“内七篇都是特立题目,后做文字。先要晓得他命题之意,然后看他文字玲珑贯穿,都照此发去,盖他每一个题目彻首彻尾是一篇文字,止写这一个意思,并无一句两句断续杂凑说话。今人零碎读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见他篇法好处。”
内篇之各篇,有先详细解题者,然后于全篇经文逐段逐节解释。其诠释精当者有如《逍遥游》云:
《庄子》明道之书,若开卷不以第一义示人,则为于道有所隐。第一义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即为道人之第一功夫也。内篇以《逍遥游》标首,乃庄子心手注猎,急欲与天下拔雾觌青,断不肯又落第二见者也,何也?天下人汩没于嗜欲之场,何事不钻研究竟?过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遥游其而不肯为者,亦只是逍遥游不知逍遥游三字?一念不留,无人而不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尘不染,无时而不自全,是第一功夫也。盖至逍遥游而累去矣,至于累空而道见矣。然且世人非惟不能到,抑亦不肯为者,其病根断可知矣。何也?从来嗜欲之累,识者遣而去之亦不为难。若夫等而上之,则有为名;又等而上之,则有为功。二者之累较难去焉。虽然,崇实则逃名,贵德则贱功,遣而去之,犹不为难。若夫累之最难遣者,惟有己焉。夫嗜欲功名尽去,而知能意见之,尚存彼此区畛之,犹隔阴阳,恭舒之,弗同与天地,皆已之未化者之为累也。而于道能吻合乎哉?故《逍遥游》凡一篇文字,只是“至人无己”一句,言尔“至人无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故窃谓孔子之绝四也,颜子之乐也,孟子之浩然也,庄子之逍遥游也,皆心学也。《逍遥游》主意,只在‘至人无己’,无己所以为逍遥游也。然说与天下人皆不信,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见识只到得这个地步。”
也有简论其题者。如,于《齐物论》云:“齐众物之论也。”然后细述该篇旨意,写作方法及段落结构。也有不论其题,直述旨意、分析结构和陈述大意者。
全篇之后,皆有总结语。
宣颖之解经,多在结构和文理,然也不乏精当之文字注释。如:《应帝王》“虎豹之文来田”,宣颖注:“二兽因有文彩,致人来猎。”《大宗师》“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明”,宣颖注:“与物同宜,而无私比。”“若不足而不承”,宣颖注:“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
五、《庄子南华经解》开注《庄》之新途径及时人之评价
《庄子》一书汪洋自恣,其哲理深邃,其想像奇妙,其说理透彻,后世文人多为之叹服。
历代注《庄子》者,或自哲学视角注解,或从文学角度评论。
自哲学视角注解《庄子》,阐发义理者如郭象、向秀《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标音注义者如李轨《庄子注音》、陆德明《庄子音义》、陈景元《南华章句音义》,校勘训诂者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皆注《庄》之佳作。
从文学角度评论《庄子》,宋有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刘辰翁《南华真经点校》,明有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林云铭《庄子因》,皆为世人所称道。
清初宣颖研究《庄子》数十年,晚年所撰《庄子南华经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庄子南华经解》用文理入义理的诠释方式,以文学兼哲学的解析手法,以文评庄,援儒解庄,为后世学人注解《庄子》开拓了一条新途径。
以文评庄者如宣颖在《逍遥游》总论云:
点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不及大年作一配衬。似乎又别说一件事者,令读者不能捉摸,真古今横绝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衬明小知大知,大势可以收束矣,却又生出“汤问”一段来。似乎有人谓“齐谐”殊不足据,而特以此证之者。试思鲲鹏蜩鸠都是影子,则“齐谐”真假有何紧要耶?偏欲作此诞谩不羁汪洋自恣,然后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锁住,真古今横绝之文也。
宣颖在这里分析庄子写作技巧方面,层层递进,令人折服。
而宣颖援儒解庄,以总论《逍遥游》为最。详见前引,此处不再赘述。在《逍遥游》解题中,宣颖将儒家“孔子之绝四”、“颜子之乐”、“孟子之浩然”与道家“庄子之逍遥游”并论,而谓之“皆心学也”,真是千古之绝论!
故时人张芳对《庄子南华经解》大为赞赏:
吾独惜夫庄与孟同时而不相知也。当是时,儒之嫡传有子思、子夏,周之传出于子夏之门人,轲之传出于子思之门人,孟犹之嫡传而庄其别传也。庄之书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辩杨墨未之及庄。毋乃子舆率其徒以游诸侯行类墨翟,而庄周未尝持其说以干列国守似杨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欤?
……
茂公宣子,好学深思,探颐是书有年,折衷诸家,为之笺解,划其萧砾,发其清越,是书哪复须注?既妙悟于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于言下。譬则画史磅礴,庖丁奏刀。又譬则帝青宝纲,光界重重,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穷,不能以智慧尽也。世之学者读《六经》、《语》、《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后从而读《庄子》之书。苟读《庄》深思而有得焉,然后从而读宣子之解。我知焕然冰释,怡然理顺,彼尧桀之诽誉,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书之行,其有功于孔孟甚大,曷可少哉?
注 释:
①据传西汉时茅盈与其弟固、衷修道于此,故又称茅山。上有蓬壶、玉柱、华阳三洞,道教徒以为十大洞天中的第八洞天。此说见于《梁书·陶弘景传》和《云笈七签》卷二七。
②但是馆藏索书卡则标4 卷,两者相差一卷,不知何故。
③刘文介,上元(今南京)人,汉族,专科学历。碑拓收藏家,藏品五千有余,有“上元刘氏金石文字印”章。金石学家,著有四十万字金石学著作《孟晋斋藏碑目》等。亦是藏书家,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书章。
[1][3]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㉞·乾隆句容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杨芳芳.宣颖南华经解之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4]钱奕华.《南华经解》以文评《庄》探微[A].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编. 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