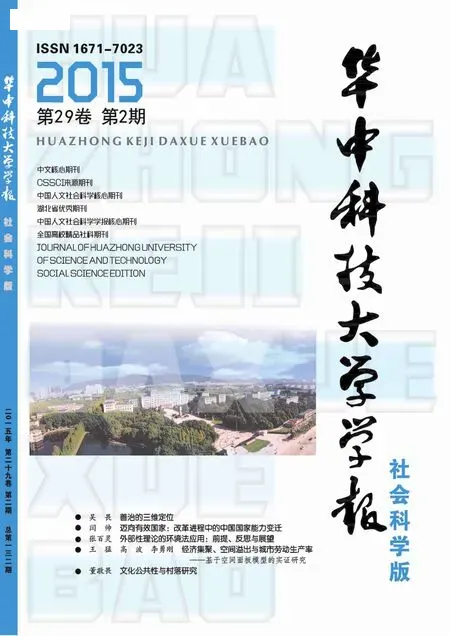从本源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产生史
陈飞,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400044
从本源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产生史
陈飞,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重庆400044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为了澄清市民社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回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详细考察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在这三种形式中,马克思认为,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蕴含着向市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其他两种共同体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不可能自动进入现代市民社会。在本源共同体瓦解和现代市民社会产生的过程中,货币和资本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主动轮”作用,离开货币和资本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
市民社会;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议问题,但鲜有关于市民社会如何产生问题的论著,在笔者看来,不了解市民社会的起因,将无法真正理解现代市民社会。其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各种形式》)中详细说明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向市民社会过渡的历史条件,并在阐释三种本源共同体的内涵、特征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向市民社会的过渡,其他两种共同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是,《各种形式》这一研究市民社会产生问题的经典文献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人们通常通过《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才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产生的理论主要集中于《各种形式》而不是《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仅以英国为例展开论证,缺乏普遍性且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未谈到,而在《各种形式》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考察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而且论证全面、深入、缜密,充满哲理。
一、亚细亚共同体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自由个性”阶段[1]107-108。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望月清司根据这三个阶段的特征把它们概括为“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它们分别代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了开出市民社会的出生证明,马克思回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并根据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人数的多少把本源共同体划分为三种空间上异质的文明圈:一个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亚细亚共同体”(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少数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古典古代共同体”(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世界)、多数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日耳曼共同体”(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世界)。马克思对本源共同体的划分沿用了黑格尔划分世界历史的方法。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的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合到一起统称为“古典古代”;此外,划分的根据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黑格尔是根据享有自由人数的多少来划分,马克思根据的是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人数的多少。马克思对本源共同体的划分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倒不如说是逻辑性的,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对本源共同体的分析看做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叙述,甚至看做历史事实。马克思的本意不是把本源共同体的真实情况忠实完整地再现出来,而是从所有-分工的视角论证市民社会的产生,他对本源共同体的分析就是在这一目的域中进行的,可以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对历史进行了一定的逻辑“重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认识的方法,即历史哲学的方法,当然二者在历史主体、历史动力以及世界观上存在着根本差异。
通过详细的论证,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可能独自地走向现代市民社会,亚细亚和古典古代共同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而单凭自身无法过渡到现代市民社会。因为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蕴含着现代市民社会产生的两个历史前提:“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1]465。在这两个前提中,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自由劳动,自由劳动就是自由的雇佣劳动,是指劳动者摆脱人格依赖关系而具有自由身份,能够自由地同货币相交换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要想使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自由身份,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也就是与土地相分离,因为只有不再束缚于所依赖的土地,他才能自由地劳动,自由地被雇佣。马克思认为,只有蕴含着这两个前提的共同体才是适合孕育市民社会的土壤,因为市民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个人摆脱本源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关系,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获得自由身份。
首先,我们跟随马克思来看共同体的第一种形式。在三种共同体中,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关系具有最复杂的层级结构,自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总合的统一体”、“单个的共同体”、“单个的人”。在1853年第一次印度通信时,马克思延续了斯密、穆勒、黑格尔等人的东方社会观,认为全土王有。在《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得出了君主只是法律上的所有者,共同体才是实际所有者的结论,把重心转移到了共同体上。“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惟一的所有者”[1]467,但这个惟一的所有者只是观念上或法律上的所有者。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是单个的共同体,单个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它是作为亚细亚共同体的基础而存在的,因此,在亚细亚,事实上的劳动所有与形式上的法律所有是分离的。相对于共同体,单个人并不是土地所有者,仅仅是占有者,因为土地是由专制君主以共同体为中介赐予他的。这种占有的实际过程越稳固,亚细亚共同体的所有制形式越持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无疑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来看,共同体才是实体,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1]468。个人与共同体牢牢地长在一起,不可能摆脱共同体的羁绊,与共同体处于一种自由的关系之中。可见,在亚细亚共同体中,个人不可能获得自由身份。
马克思认为,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使亚细亚共同体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在其内部包含着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条件,因此不可能发生劳动与土地的分离,它必然保持得最顽强、最持久。虽然亚细亚各国经常改朝换代,不断瓦解,不断重建,但亚洲的社会几千年来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它的历史似乎是一部自然史,只是一个个朝代不断征服的历史,像自然事件一样永恒往复。“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2]415,它不可能凭自身在内部过渡到更高形态的生产方式。在亚细亚共同体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无差别的统一,没有发生分离,城市只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只是专制君主或地方总督花费自己收入的地方,只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赘疣。在城市和乡村没有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在没有发生分工的地方,进入市民社会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市民社会正是伴随着商业、分工、交换等要素的产生才逐渐兴起的。
在亚细亚共同体中,劳动者不可能丧失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从而获得自由身份。“在东方的形式中,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1]487因而,在第一次印度通信时期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道义上谴责的同时,也从世界历史演进的立场赞扬了英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对印度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使命:一是凭借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破坏亚细亚稳固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社会;二是在破坏的同时把印度建成一个西方社会,即现代市民社会。可见,如果没有英国这个外力作用,印度不可能从本源共同体进入现代市民社会。因为与其他亚细亚共同体一样,在印度,劳动者被束缚于共同体自给自足的超稳定结构中,不可能自发地发生劳动者与其客观条件的分离,劳动者不可能获得自由身份,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
二、古典古代共同体
从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来看,古典古代共同体存在着共同体所有和从共同体所有中分离出来的个人所有两种形式。“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1]469以罗马为例,一部分公有地由共同体支配,其成员没有支配的权利;另一部分土地被共同体分割,由单个的罗马人所有,其产品也归他们自己支配。与亚细亚单一的共同体所有不同,古典古代共同体还存在着个人所有,亚细亚共同体中的超稳定性以及劳动的共同性被稀释了,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找到通向市民社会的道路。
对于个人所有与共同体所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在这里,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来维持的。”[1]470可见,共同体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单个的土地所有者是共同体的基本组成单位,共同体表现为由他们组成的对抗外界的联合体;另一方面,拥有小块土地的个人独立性、个人劳动所有是由共同体的存在来保障的。虽然二者相互依赖,但并不处于交互性的对等关系中。“共同体……表现为劳动主体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做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做中介的,是由国家的存在,因而也是由那被看做神授之类的前提做中介的。”[1]470可见,共同体所有占主导地位,它是个人所有的前提和保障,个人所有仅仅是共同体所有的派生物。相对于亚细亚的个人占有,古典古代的个人所有虽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还受到强大共同体的制约,不可能成为现代市民社会个人所有的源泉。正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望月清司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内心很失望。因为,在第二种形式中,他虽然发现了或许在谱系上与近代市民私人所有相连的‘劳动的所有者的私人所有’,但是一仔细分析,它们原来只不过是共同体所有内在矛盾的产物……它不可能被视为市民社会所有的源泉。”[3]365-366
由于存在着个人所有与共同体所有两种形式,劳动在古典古代被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现为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农业劳动,其产品归自己支配,体现的是私人性;剩余劳动表现为对共同体本身的维持,采取的是服兵役等形式,它“带有非经济的、政治性、宗教性的色彩,被认为是对给予自己土地的伟大国家的感谢之情的流露”[4]224,体现的是公共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并不是对等关系,个人必须服从共同体,并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军务)来捍卫自己的私有地不受其他共同体侵犯。剩余劳动总是处于上位的,对共同体成员具有压迫性,体现自己私人性的必要劳动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劳动。
相对于亚细亚个人作为最高统一体的奴隶而言,公有地和私有地二分的经济结构使古典古代的个人获得了有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主要表现为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政治自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个人不仅在安全上依附于强大的共同体,而且在心理上对共同体也具有极强的归属感,我们几乎看不到现代人所拥有的任何个人自由权利。在古典古代,个人的私人事务受到严密监视,个人的自由权利没有得到丝毫重视,个人的公共事务却被提升为必须效忠的使命。在公共事务中每个公民都被看做拥有实权的主权者,例如,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审判、参与决定战争与和平,等等。但在私人领域每个公民又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他的个人行为受到共同体法则的严格限制,他本人也可能被共同体武断地处死。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现代一项基本人权,在古代却被看做对神灵的亵渎。法律不仅干涉个人的信仰,而且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私人空间被共同体事无巨细的法则侵占得消失殆尽,以赛亚·伯林所罗列的自由清单被一项一项地撕扯下来。
因此,在古典古代,个人对共同体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虽然与亚细亚相比获得了有限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但并不具有自由身份,个人自由是不完全的,因此,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现代市民社会。其实,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权利,倒不如说是一种被共同体强加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正如贡斯当所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可以这样说,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同样的服从情形亦可见于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那里,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5]48
三、日耳曼共同体
与亚细亚、古典古代共同体相比,日耳曼共同体采取了较为松散的形式,尽管其成员在语言、历史、亲缘关系上存在着内在的共性,但共同性、稳定性大大减弱,蕴含着较强的个人主义因素,正是日耳曼共同体的这一典型特征使马克思从中发现了孕育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为了使公社具有现实的存在,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1]474可见,被森林分割开来的各个家庭采取散居的生活方式,他们独立地进行农业生产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亚细亚和古典古代相比,在日耳曼,共同体并不是先在的,共同体只是在为了个人共同利益的联合行为中才出现,个人及其行为是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基础,而不是相反。但是,共同体绝非可有可无,它是散居的个人及其家庭的保障,它把散居的家庭以集会的形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解决诉讼、举行宗教活动等。
从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来看,和古典古代一样,日耳曼共同体也存在着个人所有与共同体所有两种形式。但是,在古典古代,个人所有以共同体所有为中介和前提,个人所有是共同体所有的补充和派生;在日耳曼,二者的关系发生了扭转,共同体所有是个人所有的补充和派生,共同体所有以个人所有为中介。“个人土地财产既不表现为同公社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也不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而是相反,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1]475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不仅个人劳动及其产品归自己支配,而且劳动也基本上都是为自己支出的,这与亚细亚共同体中个人劳动形成强烈反差,在亚细亚大部分劳动都是被迫献给共同体的。在日耳曼,单个的家庭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表现为一个经济整体,即使没有共同体的援助在经济上也能自给自足。公有地(猎场、牧场、采樵地等)可以被每一个私有者以私有者身份使用,而不是像古典古代那样以国家代表的身份使用。个体的私人所有为日耳曼共同体成员获得自由身份奠定了物质基础,因为个体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自给自足,受共同体的约束较小。
当马克思看到在日耳曼个人所有已经几乎达到了从共同体的强制力量中解脱出来的程度时,他肯定一改在分析古典古代共同体时的失望情绪而变得欢欣鼓舞。因为个人所有构成本源共同体解体的原因,个人所有力量的增强逐渐削弱着共同体的稳固性。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对此有直接的说明:“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原始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6]478个人所有是从内部瓦解共同体的动因,它作为异质的因素引起了共同体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会逐渐破坏耕地、森林、牧场的公有制。但是,马克思在《各种形式》中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个人所有对日耳曼共同体的瓦解,而是在个人所有的基础上从商品生产、交换、分工等货币经济现象来探讨共同体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行文至此,我们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行文顺序考察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其核心是个人所有和共同体所有的力量对比关系。具体来看,从亚细亚、古典古代到日耳曼,共同体所有的力量越来越小,个人所有的力量越来越大,终于到日耳曼出现了真正的个人所有。马克思十分重视日耳曼共同体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如前所述,个人所有的出现改变了共同体的性质,预示着本源共同体的瓦解已为时不远。虽然三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但同属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三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劳动与土地的天然统一,劳动者对土地具有极大依赖性,劳动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在三种共同体中,劳动者都不可能具有自由身份,也就是不可能自由地被雇佣。
四、本源共同体(日耳曼)的瓦解与市民社会的兴起
在日耳曼共同体中所产生的个人所有为分工和交换提供了前提,马克思由此看到了市民社会产生的曙光。首先,个人所有是瓦解共同体的内部力量,它为摆脱共同体的约束获得自由身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其次,当个人劳动出现剩余的时候,个人拥有这些产品的所有权,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可能性。再次,家庭是日耳曼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整体,这有利于分工和交换的形成,因为单个家庭不可能生产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赖于分工和交换。最后,在日耳曼共同体中,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并不局限于共同体内部,当手工业出现之后,遭到了农业的排挤,这促使手工业逐渐在农业共同体之外建立一个不同的组织,后来这些组织逐渐演化为现代城市。日耳曼共同体的这种建立在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分工、生产与交换的方式为劳动和客观条件(土地)的分离提供了可能性,进而为劳动者获得完全的自由身份奠定基础[7]13。本源共同体的瓦解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最早发生在14世纪日耳曼世界的典型代表——英国,那时,英国发生了在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分工、交换等瓦解共同体的现象。为此,共同体成员留下了感伤的泪,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给自己以安全保障和精神慰藉的共同体,而被抛入到自由的、陌生的、无助的城市,他们不得不凭借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但是,共同体的解体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劳动者,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兴起。
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论证了货币、资本在本源共同体瓦解和现代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货币作为社会联系纽带和经济活动润滑剂,瓦解了本源共同体中的人格依赖关系,使这种关系逐渐演变为平等的自由交换关系,从而逐渐导致传统共同体的没落。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人的交往范围非常狭窄,只是局限在地缘关系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限交往。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促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摆脱了地缘或血缘的限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引用蒙塔纳里的话表达了货币的这种作用:“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8]338传统共同体在货币经济的瓦解下逐渐没落,市民社会逐渐产生和兴起。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由于具有购买其他一切东西的特性,谁拥有货币,谁就拥有支配世界的权力,拥有的货币越多,这种权力就越大。为了说明货币对共同体的瓦解作用,马克思区分了积累欲和货币欲。积累欲就是积累特殊使用价值的欲望,由于受产品的体积、性质、储藏条件等制约,所以仅仅是一种有限的欲望,而当货币被看做财富的一般代表之后,它使人们避免了这些麻烦。货币打开了真正的财富之门,成为历史发展的一大杠杆。人们从事劳动的目的是获得无限的货币,而非有限的使用价值,所以,人们的勤劳是无限的,货币成为发展一切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主动轮。以货币为目的的生产逐渐瓦解着本源共同体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生产的无限性代替了生产的有限性。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1]174-175
只有当货币转化为资本,超越作为货币的货币时,货币欲才必然“导致共同体的没落”,因为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具有强大的生产功能,从而超越第一阶段货币的流通功能。马克思说在人类社会第一阶段,货币仅仅是补充性、局部性的关系,在现代市民社会阶段,货币关系才成为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第一阶段的货币关系仅仅是交换关系,而在第二阶段,货币不仅仅是交换的中介,而且能够转化为自我增值的资本,从而转化为超越家庭制、奴隶制、农奴制的新型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390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具有巨大的创造力量和解放功能,它按自己的面貌开创了一个时代,赋予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结构和属性。
资本之所以作为开创和发展现代市民社会根本动力,其根源就在于资本强大的生产功能。“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9]927-928资本强大的生产功能是通过建立在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剥削实现的,剥削是榨取剩余劳动的一种形式,剥削对工人来说虽然意味着不正义,但却是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进行物质生产的根本动力。资本的本性就是通过剥削不断地实现自我增值,自我扩张,它表现为不断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欲望。在现代社会的生产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是生产的源泉,而且是生产的主体。这就打破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流行观点: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事实上,如果劳动者没有被资本生产所接纳,也就是说没有被资本雇佣,那么他只是一个可能的生产力,资本才是生产的主体。“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1]587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资本表现为融合一切、支配一切的权力。正是在资本的这种异常强大的助推下,现代市民社会才逐渐从本源共同体的母胎中挣脱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资本是现代社会产生的根本驱动力量,但并不排除还有其他动因,例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参与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过程。但是资本逻辑在整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二者都被融合进资本逻辑之中。
马克思为了开出市民社会的出生证明,回到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详细探讨了本源共同体三种形式的结构、特征,并以对土地的所有关系为视角,得出了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可能独自走向现代市民社会。货币、资本作为现代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量具有巨大的文明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表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有限性:资本的贪婪、反人性、潜在的违法性,等等,这些有限性使资本本身无法解决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给资本划界,把资本限制在经济领域,防止资本向道德和政治领域扩张。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韩立新:《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上),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9]《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
From Original Community to Modern Civil Society——On the History of Appearance about Civil Society
CHEN Fei
(Marxist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In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57-1858,Marx returned to the first stage of human histor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ppearance about civil society,studying Asian community,Ancient community,German community in detail.In this three kinds of forms,Marx thought,only the German community contained the possibility changing into civil society,the other two communities could not enter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without external force.Currency and capital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in history as“driving wheel”in the process of the original community breakdown and modern civil society breakthrough.
civil society;asian community;ancient community;german community
陈飞,哲学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政治哲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马克思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4QNMK05);中央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设项目“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由思想及其启示研究”
2014-11-20
B03
A
1671-7023(2015)02-00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