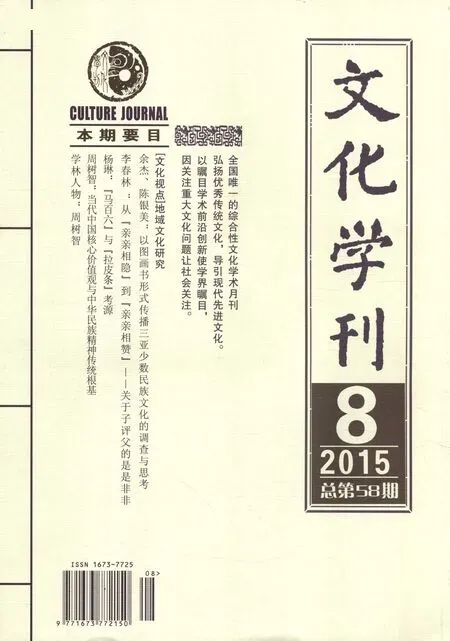从“亲亲相隐”到“亲亲相赞”
——关于子评父的是是非非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相赞”
——关于子评父的是是非非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亲亲相隐”乃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为了“避害”“生存”而“亲亲相隐”易得人们的理解与宽容;为了“趋利”“发达”而“亲亲相赞”恐怕就未必如此了,反倒是易得人们的不解与厌恶。某些人热衷于评赞乃父;乃父收自己的儿子为研究生,或推荐自己的儿子考研究生,进而举荐自己的儿子为领导者,都可谓“亲亲相赞”的生动样态,均属于刘知几《史通》中颇讥刺的“矜其乡贤,美其帮族”之典范。作家亲属提供作家的相关资料乃至作品的收集,其目的在于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方便,是可以的;但其对作家亲属的评赞却是自爱自重者所不屑为之。因为会误导研究者,使研究走弯路乃至歧路,所以是缺乏学术价值的,其为学术研究和道德建设提供的主要是负能量。
“亲亲相隐”;“亲亲相赞”;子评父;负能量
西方法学传统对于亲属之间举报和证明犯罪的原则与我们有所不同:不鼓励亲属大义灭亲,不强迫亲属之间做不利的陈述。亲属也有权拒绝做不利于亲人的陈述。西方法律如是为之乃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稳定。某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如果一个人背叛自己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去举证自己的亲人,那么反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它们认为,没有比这种背叛更伤害人类的尊严了,它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自明。”[1]这就意味着承认了“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和自然性,承认了“亲亲相隐”乃是人性的一种表现。
那么“亲亲相赞”呢?
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
首先,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通常人们都愿意给自己的亲属唱赞歌。给亲属唱赞歌,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唱赞歌,所谓年轻时子赞父,年老时父赞子,其实都是在赞美自己,赞美自己家族的基因。“在一个社会中,最基础也最为稳固的人与人关系,来自于家庭、血缘,两者也构成了相对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所谓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由此也必然会产生利益共同体。”[2]若是说“亲亲相隐”乃是为了“避害”,那么“亲亲相赞”则是为了“趋利”。前者是为了“生存”,后者是为了“发达”。为了“避害”“生存”而“亲亲相隐”易得人们的理解与宽容;为了“趋利”“发达”而“亲亲相赞”恐怕就未必如此了,反倒是易得人们的不解与厌恶了。
著名小说家、曾任《文学遗产》主编的陈翔鹤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1956年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主要编修人之一——林辰乃莫逆之交。陈先生之子开第,为在“文革”中冤死的父亲编选了一个集子,并请陈白尘写序,请林辰联系出版事宜。于是就有了陈白尘与林辰之间就此事的通信。陈白尘1984年8月31日致信林辰,林辰9月9日作复。林辰在信中说,他已见到开第送来的选目和编后记,“粗粗看了一遍,和您的意见一样,也觉得选得较宽,……像个专集,不像选本。而且在小说一门中又插入‘传奇、历史、小说、民间故事’的小栏目,不伦不类。……编后记除您所说‘水平不高,而且多有溢美之处’以外,文字也很差,……像现在这个样子,我看是不能用的。”[3]应当说以上林辰所言,还是仅就开第还不具备编选父亲选集的水平而言。看来,作家之子不一定天生就具备文学才能的基因(鲁迅在遗嘱中即反对儿子做空头文学家或艺术家,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物理学专业人才。可惜的是并非每一位作家都具有鲁迅此种清醒的认识)。下面林辰则说得更为严厉:“编后记两人署名,一人为作者之子,不便也不宜评论其父”[4]。显而易见,此处所言已经不单是对老友之子了,而是更具普遍性,同时也是将子评父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了——子评父所带来的溢美,有时并非学术水平问题,而是文德与史德问题。如是为之,往往会模糊乃至歪曲事物真相。即便儿子对父亲实行酷评,十分说成九分,乃至八分七分,仍会遭到众人的非议。因为为亲者赞与为亲者讳同样几乎是人之本能,中国尤其如此。
林辰有一篇杂文《严复小谈》专门谈这个问题。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贡献甚大,连鲁迅都蒙受其惠。但他有一个大污点:曾参加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其子严璩所作《严复先生年谱》却绝然不提此事。“子为父讳,自然是不足为异的。”[5]林辰承认了“亲亲相隐”的普遍性;但他对这份儿子给老子编定的《年谱》始终持存疑态度,“因为照中国的老例,子孙给祖先作的‘行述’‘年谱’之类,往往充满不合事实的溢美之辞,大都是不可靠的。”[6]他也承认了“亲亲相赞”的普遍性,然而给予的是否定性评价。
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陆平之女陆莹口述、陈洁整理的《父亲是知识分子》一文津津乐道于乃父在文革中的被整,而对其在反右中大肆整人,甚至超指标地定了722名右派(他之前的党委书记江隆基拟定146人)、使得更多的人家破人亡则不顾基本事实地进行辩解[7]。
郭庶英为父亲郭沫若所作的种种辩解(赞歌之一种变相)更具代表性。她从政治、文学、学术、道德等诸多方面为乃父大唱赞歌。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她说:“郭沫若与鲁迅都曾用笔墨相讥,但后来郭沫若识大局,对鲁迅是充分肯定的。”[8]倘若将两人的论战文字全部开列做些比较,那么谁高谁下,理在何方,昭然若揭,绝非“笔墨相讥”四字所能概括得了的,而“识大局”一语更是用春秋笔法贬低鲁迅。1966年“文革”爆发时,郭沫若表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来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句话曾在所谓“破四旧”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对此,郭庶英认为,如果说用“推陈出新”或“凤凰在涅槃中永生”来看这句话,那么它是彻底的。按此逻辑推演,“文革”岂不成了“彻底的”“凤凰涅槃”。1937年,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及子女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归国抗战,被很多人评为“抛妻弃子”。郭庶英反驳此说是“完全是不公平的”,她认为:“一个男人投身于革命事业,只要革命事业需要,也可以有新的选择。”[9]此说不独是为乃父强辩,而且为一切抛弃原配、大找“革命夫人”的“革命者”提供了“抛妻弃子”的理论根据。看来,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什么事都来得(倘若是真正地出于革命的需要,如地下工作者扮演假夫妻最后假戏真做,倒也可以理解,但郭沫若对于立群的追求可绝不是“革命”的安排,而是郭本人情色之需要,那在《洪波曲》中可写得清清楚楚)。此种辩护若是来自安娜之女,尚可显现宽容的心,可惜来自“革命夫人”之女,就彻头彻尾地成为为其本人的出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辩护了,变成令人厌恶的了。1971年,郭沫若暮年创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被学术界认为是迎合毛泽东之作。郭庶英说,“这种看法是狭隘的。”[10]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此处不拟详析,但只要看看郭沫若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分析,他居然认为“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表现的是地主阶级对贫农子弟的仇恨,就昭然若揭,他是否在迎合最高领袖,迎合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要之,郭庶英为乃父的辩解和歌赞确实体现出了父女亲情,其情可以理解,其理却大谬不然。这样的子评父,显然失却了客观性与公正性,难以服人,其实损害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形象,更对完整地研究郭沫若无益。
刘知几《史通》中颇讥刺“矜其乡贤,美其帮族”之现象,在郭庶英给老子唱赞歌这里可谓达到了极致,尤其是为父亲“抛妻弃子”及“烧自己的书”的辩解,可谓“空谷足音”“振聋发聩”了。诚然,父赞子者亦多有,如导师收自己的儿子为研究生,父亲推荐自己的儿子考研究生,进而举荐自己的儿子为领导者,都可谓父赞子的生动样态。
林辰先生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的。他的高尚人格不独在于其对友人之子的严要求,更体现在对子自己的儿子的文稿的态度上——他是属于父不赞子的“异类”的。
林辰1977年10月25日给自己的三子王山鹰及儿媳一信。信中说天津人民出版社请他审阅一部某人的《鲁迅论科学》书稿,同时提到:“你(按:王山鹰)的稿子,说不定也会来要我看看,那就很为难。如果真是这样,只好尽量推辞,请他们找别人看。”[11]在林辰看来,亲属之间审稿,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其实正直耿介的林辰倒不会因对子女的厚爱而网开一面,将“不行”说成“行”,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乃是不愿引起他人的非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亲亲避嫌”。这就不是普通的人性表现了,而是一种更高尚的人性。
当然有时由亲属为之的某些选本或集子的出版亦未必出于刻意拔高与美化之需要,如鲁迅《呐喊》最初的版本系周作人主编的《文艺丛书》之第三种,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于1923年8月印行。不料,成仿吾对此却颇有微词:“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其实弟弟将兄长的一本书选入自己主编的丛书中,也没有撰写溢美乃至大吹特吹的序跋评文,出于保存一个时期的创作文本、方便读者阅读之需要,似无大碍,成仿吾未免过于苛刻,但鲁迅还是于翌年将《呐喊》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与乃弟脱离干系。大作家、大学者总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我觉得,作家亲属提供作家的相关资料乃至作品的收集,其目的在于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方便,是可以的(如茅盾和老舍的子女大体上是如此做的),但其对作家的评论却是自爱自重者所不屑为之。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的编选者是罗银胜和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而《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顾准评传》的作者却只有罗银胜一人。陈敏之参与编选,恐怕是因为他作为胞弟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而他不参与评传的撰写,则是因为他是传主的胞弟,评得再客观、严谨,也只能被参考或不被参考,甚至被讥刺、质疑。这一点中外概莫能外:什克洛夫斯基在撰写托尔斯泰评传时,对托翁亲属的回忆录就一概持质疑态度。
更大的问题在于某些“亲亲相赞”乃是隐形的,赞与被赞者一方或双方所署之名乃为笔名或假名,读者不知赞与被赞者之血缘关系,会误以为是客观的科学的评判。读者若是被误导,可权充饭后谈资;若是研究者被误导,就会使研究走弯路乃至歧路。岂不哀哉!因而子评父一类的“科研成果”是缺乏学术价值的,其为学术研究乃至道德建设提供的主要是负能量。
其实,有出息的研究者是不会盯紧乃父进行研究的。亲情会成为变色幻镜,使你将绿叶看成红花,将平面看成立体。著名学者王晓明先生是作家王西彦之子,若是他研究乃父而不研究鲁迅,断然不会取得今日之骄人成绩。
并非所有的学人都有此种学术自觉与道德自觉。最近,笔者见到某位学者的文集,翻开目录一看,两篇评其父的大作赫然入目,不禁想起某省一部《新中国60年文学精品大系·文学评论卷》,亦曾见到一篇儿子评老子的论文。这些论述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笔者不拟置喙,只想指出:他在开列辽宁著名作家的名单时,其父居于肖军之前(其父确实是辽宁著名作家之一,笔者对其一部代表作的近于现代派的某些艺术风格曾予以评说,并得到作家本人的首肯,但他与肖军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相同),而在排列辽宁文学评论家的名字时又将自己排在高凯征(博导、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卫平(博导,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顶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高翔(《社会科学辑刊》主编、二级研究员)、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洪兆惠(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曹禺奖获得者)、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在辽宁工作)等二十余人之前,居于第四位。至于其本人的学术水平、学术见地如何,只要看看他的这本《文集》居然有从县级小报和《卫生与生活》上选来的文章(据我所知,那《文集》的编选是明确要求必须从省级以上报刊选录的),也就不必多说了罢!
我以为,选了一篇子评父,主编可能欲一星管二,同时表彰了父与子。殊不料,人们也可能这样想:原来研究其父的最优秀成果乃是出自其子之手(幸而不是如此);其子之最优秀成果(若非最优秀成果怎能入选仅含35篇的60年文学评论精选)乃是研究其父的。怎能不令人失笑?但也有人认为,该书主编很有学术水平,又颇有风骨与个性,焉知他不是用此种方式对子评父现象开了一个小玩笑?这大概亦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1]狄凯.亲属大义灭亲 被告可减刑[N].大家文摘报,2010-10-11.
[2]毕舸.“侄子举报叔叔”只可能是反腐个案[N].华商晨报,2014-08-14.
[3][4]林辰.致陈白尘[A].林辰文集:第4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9-10.10.
[5][6]林辰.严复小谈[A].林辰文集:第2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93.94.
[7]王金屏.陆平先生及“陆平现象”[J].文苑春秋,2010,(3).
[8][9][10]黄老道.郭沫若诞辰120周年郭庶英忆父亲.http://huanglaodao.blogchina.com/1247454.htm l,2012-02-23.
[11]林辰.致王山鹰、贺丽华[A].林辰文集:第4卷[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205-206.
【责任编辑:周 丹】
I206
A
1673-7725(2015)08-0033-04
2015-02-10
李春林(1942-),男,河北玉田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鲁迅学、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