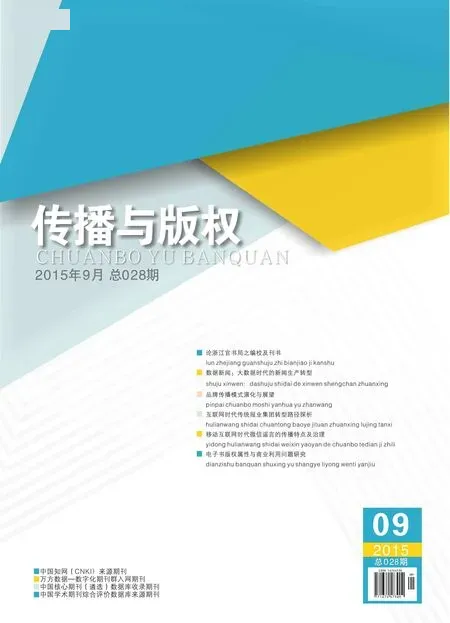2014年“玉林荔枝狗肉节”媒介事件的网络舆论走势研究
蔡雨容
2014年“玉林荔枝狗肉节”媒介事件的网络舆论走势研究
蔡雨容
2014年“玉林市荔枝狗肉节”媒介事件具有新的代表性。地方文化与自然生灵平等的冲突,随着社会变迁更加激烈。传统媒体对待此事相对保持冷静,而自媒体的多样化使得各方意见不同,与传统媒体比较,显得主动、激烈。在此研究该事件始末,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给类似事件做借鉴。
“玉林荔枝狗肉节”;媒介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学;沉默螺旋
[作 者]蔡雨容,贵州师范学院。
2014年引发全民大话题“玉林荔枝狗肉节”,在今年虽没有去年那么人声鼎沸,但始终离不开民众的视线。时间过了一年,现在以回顾的角度,重新讨论当年的舆论热潮,以传播学角度解释整件事原因始末。
一、引言
网络舆论具有将小事件变为“大话题”的魔力。尤其是新媒体时期,人们发表民意的渠道多样,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能让民众随时随意“脱口而出”,但也滋生了许多舆论乱象的弊端。网络的“草根性”,网民会条件反射同情弱者和底层,对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也会对名人有追随意识。每当网络热点爆发后,网民在事实并未完全发展或不了解事情发展经过时,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观点,从而激发固有的情绪,形成声讨或声援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助力”,舆论浪潮此起彼伏。玉林市夏至吃狗肉本是一个普通的民间习俗,为什么突然之间人尽皆知还蹿红外媒,究竟是什么推动民意的走向,我们应如何看待、应对、引导本次媒介事件的网络舆论走势,具有防范进一步事态扩散、防止当地居民避免遭受舆论带来的侵害和伤害的意义,对之后类似的事件发生具有借鉴价值。
二、“玉林荔枝狗肉节”舆论传播走势
玉林荔枝狗肉节,是中国广西玉林市民间自发形成的节日,是一种欢度夏至的民俗。在这一天,街边大大小小的大排档、饭店可以用人声鼎沸来形容。荔枝狗肉节的来历有俗语称:“冬止鱼生夏止狗。”由于狗肉温热,易上火,夏至是“阳气”最盛的一天,吃荔枝和狗肉这两种很“热气”的东西,正好与“阳气”呼应,可以“以阳制阳”;加上两广人经商居多,禁忌多讲究图意头,夏至来临意味换季,为图生意上好兆头,买来极易上火的荔枝、狗肉、老酒一起吃,有“红红火火、旺上加旺”的意思;如今逐渐演变成一个“吃”的节日,最初的意义已不再明显。就是这个普通的民俗在2014年却显得格外“刺眼”,有人还戏称“广西玉林夏至吃不吃狗肉成了这个夏天仅次于世界杯的第二件大事”。玉林夏至吃狗肉在近些年才兴盛,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逐渐被外地人知道。早在2010年,玉林荔枝狗肉节被国内一些动物保护的公益组织知晓,开始受到关注。2011年和2012年,若干公益组织自发组成了抵制者,开始到玉林狗肉档抵制。行为艺术家“片山空”2012年夏至日当天在堆满狗肉的桌子前下跪,“向狗谢罪”。英国《卫报》2013年6月18日发表文章,原题“中国城市因狗肉节挨批”: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居民们正准备举行一年一度的狗肉节,而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则极力批评这项不安全且残忍的活动。英媒的批论算是“玉林荔枝狗肉节”第一次在官媒上露脸,从那时起,各地小动物保护组织开始宣传抵制该活动。2014年5月2日,赵薇率先在微博写道“善待人类的朋友”并@尔冬升导演,从而拉开了明星呼吁抵制玉林狗肉节的序幕。明星的关注,引发广泛争议,爱狗人士得到明星的声援,反对玉林荔枝狗肉节的舆论占据有利地位,在与支持该节日人士的争论中出现极端的言行,双方矛盾白热化,支持狗肉节者以保护地方文化为由进行舆论反击。6月9日,为躲避爱狗人士狂热的救狗行为,玉林多家餐馆将招牌中的“狗”字遮挡。6月11日,网络红人罗玉凤“凤姐”发微博,力挺玉林荔枝狗肉节,引起新一轮舆论,随后持支持的力量逐渐强大。6月21日,在广西玉林市江滨新民路附近的狗肉馆,几名爱狗人士与当地食客发生冲突,导致一名食客嘴巴处流血,冲突双方被警方迅速带离。随着2014年夏至节的过去,网民对玉林夏至荔枝狗肉节的关注度逐渐减退。这段时间部分炒作者和商家借题发挥各取所需,对这场“想吃和不给吃”的博弈“添油加醋”。
三、玉林荔枝狗肉节引发网络争议的原因
(一)社会道德伦理冲突
爱狗人士和支持荔枝狗肉节人士的争执点,在于是否可以吃狗肉。爱狗人士认为狗不是畜生,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大肆屠杀是不对的。而支持该节日的人认为狗肉仅是普通的食用材料,与平时食用的猪肉、牛肉等无异。这样便产生了“想吃和不给吃”的争辩,从而上升到地方文化与自然生灵平等的冲突,即“吃”的权利。伊丽莎白.诺依曼认为“舆论是道德伦理的守护人”。(《沉默的螺旋》第七章让-雅克.卢梭传播了“公共意见”这个概念)舆论双方为守护自己所认同的“道德伦理”,使自己的观点成为公共意见而进行自我答辩。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最初反对吃狗肉者得到公共态度的支持形成相互联系的基础,也是保守谨慎的,从而它促使个体去适应当下通用的道德伦理和传统习惯,并且保护这样的道德伦理不会崩溃。爱狗人士的反对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道德伦理”,即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们食用狗肉是不道德的。
(二)名人效应也是造成本次事件受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由于每一年的玉林“荔枝狗肉节”都会屠杀掉大量的狗,遭到了众多动物保护等各界人士的声讨与反对。爱狗人士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发表个人意见,其中一些网络“大咖”看到后转载让更多关注他的人看到,一些不了解的网民受意见言辞影响,潜移默化接受观点。2014年接近狗肉节的那段时间,冯德伦、赵薇、刘晓庆、罗志祥等明星在微博上公开发帖,提出广西玉林市取消“荔枝狗肉节”,发出“取消荔枝狗肉节”的呼吁,粉丝的关注和点击量、转发量让“荔枝狗肉节”进入人们的视线。明星效应使得一些粉丝追随明星的步伐,带有凡伯伦的“上等人的效应”影响,其中也不乏一些社会名人阐述个人观点文章引人入胜,使读者产生共鸣。网络名人各抒己见,反对的和支持的在论坛、微博等网络平台“打口水战”相互博弈。
(三)动物保护人士言行失
在本次事件的调查中发现,不少民间参与动保的志愿者因“爱狗”而缺乏必要的理性,光凭热情办事,不注意方式方法,夸大事实,声称玉林满街杀狗,然而事实和网上说的内容存在很大的差别,围观的网民对爱狗人士的言论丧失信任,是造成舆论反扑的原因之一。
极端的言论同时引发本地一些本来反对吃狗的人士的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地域攻击不分人、泛滥式的抗议是一种恶心的行为,随后网络上也引来了一波民意反弹,结果导致民意分裂,原本可以争取的中立者,也因为部分极端的饲主不可理喻的言论而走向了对立面,当年(2014年)狗肉销量远好于往年。不仅如此,某些动物保护者以玉林市政府举办了狗肉节为借口,要求玉林市政府制止,没有理解“吃狗在民间”这个中心问题,反而采取了打算利用政府强权来实现制止吃狗肉的目的,引起网民不适。
(四)部分商贩的恶意炒作
玉林市政府早已申明玉林荔枝狗肉节是非官方举办,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玉林市举办药博会期间,商人宣传玉林当地饮食文化而使之有名。近年,荔枝狗肉节被网络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争议的同时,许多慕名的“吃货”纷纷来玉林尝鲜,带来了大量商机。一些商人便进行炒作营销,精心的策划包装,并结合网络进行病毒性传播推广,以达到营销的目的。
(五)地方政府的淡化处理
民众在网络环境中可以对他看不惯的任何人进行道德批判,恰恰官员是网民偏见深的群体,政府面对舆论压力通常采取淡化的方式消息,避开话题或者屈服于团体压力。玉林市政府对本次事件的做法也耐人寻味。有行为艺术家来到玉林市政府送上感谢信和锦旗,以感谢当地政府在狗肉节期间做的一系列工作,但政府方面并没有人收下锦旗。政府表示,玉林从政府到民间都从来没有举办过任何形式的所谓夏至荔枝狗肉节,只是本地一部分市民的饮食习惯。并在(2014年6月)6日向新华社记者传来《关于所谓“夏至荔枝狗肉节”的几点说明》,说明特意强调是为回应网络和社会的关注而公开做出的。除了公开报道的回应,玉林市政府还出台了内部文件,禁止公务员及家属近一个月内公开吃狗肉。玉林工商局通过商会向商户发布“口头通知”,严禁任何人当街宰杀狗类,禁止通过任何字号向公众招徕生意……一旦发现有商铺违规操作,将暂扣营业执照。不仅如此,玉林市的所有媒体对此事闭口不谈,地区电视新闻、报纸均无关于“荔枝狗肉节”的报道。于是在那段期间上演了玉林全城遮“狗”字的闹剧。玉林市政府采取规范商家经营、引导顾客改变饮食陋习等多种方式,让民众减少对狗肉的食用,企图以此削减舆论造成影响。在“荔枝狗肉节”过去半年后,12月12日广西官方公布了网民评选出的20道“桂菜名菜”,但这些菜肴均与狗肉无关。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何逸奎表示,尽管广西多地有吃狗肉习惯,且味道不错,但是“桂菜名菜”的评选,要结合本地特色、消费者需求、国际美誉度等因素,故不将狗肉列入“桂菜名菜”行列。相比广西退让舆论的做法,江苏沛县却大胆站出,在2014年6月28日(玉林“夏至荔枝狗肉节”后一周)提出今年将临时“加演”一届徐州沛县狗肉节(原本每两年才举办一届,逢单数年举办)为的就是关注、支持广西玉林狗肉节。动物保护人士言行失当,地方政府的淡化处理和部分商贩的恶意炒作导致事态一波三折。
(六)自媒体多样化,使得个体对“荔枝狗肉网”事件有多元化看法
舆论具有发散性,“意见的发散是舆论的基本特性,舆论主体对共同的社会问题同时发表意见,出现了分布与社会各处的意识传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诉说呈现出辐射形态”[1]。但凡舆论涉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等,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亲切感最强,参与话题讨论度也最强。首先,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不同于传统媒体,用户可以自主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及时了解各种更新信息和别人的观点,具有互动性,能提供给读者广泛参与发表意见和互动评论的平台。其次,网络传播速度快,比传统媒体的新闻发布省去了许多新闻评审环节,大大提高了时效性,荔枝狗肉事件能及时地、迅速地、不受空间限制地传播出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转发。再次,新媒体使用人群多为年轻人,新生一代对事件看法个性多样。但也是因为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互动性、时效性和自由度,用户可以发表言论前不用担心要为自己的言语承担后果,因此“不涉及事件本质、不符合事件本相的表层意见容易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意见倾向”[2]。
四、沉默螺旋下的“荔枝狗肉节”
沉默的螺旋是以一人的趋众心理为依据,认为人们总是害怕孤立位置,当自己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相符时就不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甚至更得势:看到这些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人越多,那么一派就显得更占优势,另一派则更是每况愈下。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3]。这次舆论事件从发展到白热化再到最后被新的热点事件取代,舆论的正反螺旋不断转换。
正螺旋形成之初,名人效应在其中起作用,即名人掌握的话语权更大,更有利于形成爱狗反对狗肉节的意见气候,是否应该食用狗肉的话题探讨被推动。随着事件关注范围越来越大,反对狗肉节的呼声越来越响,正螺旋旋转上升,反对的人范围扩大。受到舆论压力的“支持荔枝狗肉节”一方,在被动的情况下选择沉默,反螺旋螺旋下降。显现出来的反对“荔枝狗肉节”一方的势力开始强于实际情况,而支持“荔枝狗肉节”的一方的势力则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弱。这样的现象不断自我循环,反对荔枝狗肉节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即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应该保护他们而不是大肆宰杀食用,而另一方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且“缄口不言”,这也是为什么玉林举办多年荔枝狗肉节,在2014年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在正螺旋扩散时期,玉林不少市民怕夏至当天在饭店吃荔枝狗肉遭到动物保护人士骚扰,提前过上了“荔枝狗肉节”。
当舆论逐渐产生一边倒现象之后,正螺旋支持者,爱狗人士认为舆论支持己方,所以行事更加大胆,表达更加夸张,对玉林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造成损害继而引来了一波民意反弹。正螺旋支持者的言行有失,授人以柄,引起围观群众大不满,攻守之势逐渐转换。反“沉默的螺旋”现象出现,使舆论的形成更加多元化。中坚分子和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形成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舆论发生偏转的关键性因素。一直以“雷人”而著称的凤姐在众人反对抵制狗肉节的时候,大赞支持狗肉节,称人权大于狗权,单挑众明星,引发新一轮热议。网络上逐渐出现支持“荔枝狗肉节”的一方在新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意见,不少玉林当地的民俗学者纷纷站出回应玉林夏至吃荔枝狗肉的民俗,为“玉林夏至荔枝狗肉节”正名,“人权和狗权”“地方文化和自然生灵平等”等话题引起人们的思考。随着舆论逐渐支持反螺旋一方,一些爱狗人士恶意炒作,放大事实的事件也被网友曝光。以前有关玉林“荔枝狗肉节”的视频资料也被发掘,例如2013年6月29日CCTV-7中的《聚焦三农》,部分观众看了节目,了解了实际中的玉林“荔枝狗肉节”也表现出理解与支持。在央视的一项调查“你是否赞成官方参与狗肉节的主办?”中显示,支持者占大多数,拥有73%的支持率,而反对意见仅有27%。
五、结语
“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大众媒介具有的强大舆论权利。现实中,具有趋众心理的公众首先根据占强势的意见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而媒介意见常常作为社会的强势意见出现,因此,大众媒介的观点往往就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尽管决定一个群体中指导意见的因素很多,但大众媒介与社会主流以及主要控制力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也决定了什么样的观点占优势。这就形成一种螺旋,当大众媒介提出并支持某种观点时,持有与之相反意见的公众会保留自己的观点,并逐渐接受媒介的观点。但无论是正螺旋还是反螺旋,其中有很大部分的支持者的态度和观点具有不确定性,在受到特定事件影响或在反向意见的劝服下,存在跑票的可能性,通常那些感觉自己“被孤立”的人,他们最容易成为“最后一分钟的突然转向者”。其次,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为推动本次事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新媒体对大众言论更加理解和包容,使得反“沉默的螺旋”现象随着网络兴起和普及,也必将进一步发展,在舆论的形成与引导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也要肯定网络媒体作为意见交锋平台,为构建公民社会和搭建舆论交流平台所做的贡献。但网络媒体作为舆论交流平台,对舆论进行引导也是必要的。在新媒体中,舆论的形成非常迅速,一个热点事件的存在加上一种情绪化的意见,就可以成为一片舆论的导火索。网络管理者应及早发现不良的舆论势头,对具有极端言行和人身攻击的观点进行引导,倡导绿色舆论环境。[本文系贵州师范学院2014年大学生项目“‘玉林市荔枝狗肉节’媒介事件网络传播效果的传播学研究”(2014DXSD05)成果]
[1]刘建明.穿越舆论隧道——社会里学的若干定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2]胡钰.新闻与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