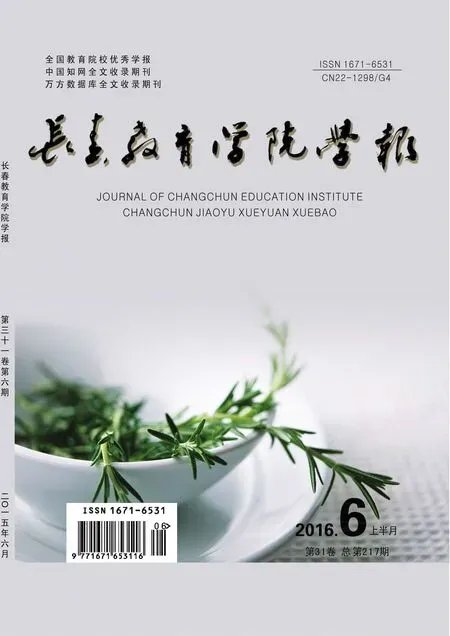从《呼兰河传》看萧红悲剧人生的性格
莫瑞芬
从《呼兰河传》看萧红悲剧人生的性格
莫瑞芬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呼兰河传》中所隐藏的对生命的追逐,正是萧红人生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萧红在以个体意识为中心的美学悲剧创作中,将自我与社会、自然环境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及因自主意识受到阻碍而迸发的情感抗争付诸笔端,寄托在凄婉悠长的文学里。本文从对《呼兰河传》文字片段的解析中,挖掘潜藏在萧红悲剧人生中的“达芬奇密码”,琢磨“性格即命运”的文学意蕴。
《呼兰河传》;萧红;自主意识;人生悲剧;性格迷失
在《呼兰河传》的开篇,我们可从对“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描述中,观照萧红的人生及真实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没有鲜花、没有诗篇、没有光和热,也没有音乐、艺术,更没有趣味。在所有该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1]似乎人生就是自然地长大,长大了就算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在这种与众不同的“稚拙”的人生感悟中,童年的孤寂及对自我、自尊的过于敏感,培育了萧红悲剧人生的萌芽。
一、失落的童年铸就任性的性格
在《呼兰河传》中,有一段关于《祖父的园子》的描述。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是萧红童年在祖父身边那个天真、无忧的生活情景的写照。祖父每天都要到后园去劳作,小女孩也跟着去,“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也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也栽花;祖父拔草,我也拔草”。[2]对后园子灿烂生命图景的描写,诠释了萧红儿时的纯真与对自然的热爱,并由此形成了萧红成年后情感寄托的闸口,清新的童年回忆,美丽的影像描述,是充满孩子气的心灵释语。然而,童年并非都是绚烂的,在缺失父母之爱的童年孤寂里,萧红有对现实的抗争冲动,她因为要戳破白净的窗户纸而受到祖母的针刺,在众多人的家庭里,饱尝了冰冷的人生际遇。20岁的萧红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漂泊的人生,之后情感的波澜、疾病的困扰,将近中年的她更加怀念童年的故乡,渴望回到她曾经留下快乐时光的祖父的园子。在那里,她能够与慈祥的祖父一起种菜;在那里,她能够获得老祖父的疼爱;在那里,她能够从深深的孤寂与落寞中找到无比的温暖和安慰。
在《祖父的园子》里,有萧红对童年的回忆,有情感的自然流露,读者从中可以解读出她的独特情感与自我愿望。“花开了,就像是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是鸟飞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是虫子在说话似的”。在无拘无束的文字间,萧红表达了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也为我们剖析萧红的性格特点创造了条件。在园子里浇水、种菜的情景是生动的,萧红的胡乱折腾并未受到祖父的责怪和限制,在这种为所欲为的情感流淌中,形成了萧红的自我意识与对生活的真实追求的对照。表达了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心灵自由。[3]在这份渴望里,她的心愿及理想就是在玩耍的时候能够恣意而行,假借自我表达对成人意识的厌倦。在人生的终点,强撑病体的萧红倾尽心力来描述祖父的园子,是在人生的落寞回忆中对童年梦幻的深切依恋,这也是生命委顿经历的率性使然。
二、萧红的悲剧体验是其悲情性格的最大诱因
呼兰河边的生活是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因年深月久而形成的“日常化”生活,与其说是痛苦的,不如说是应对灾难生活的生命战栗。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有对如跳大神、放河灯、唱秧歌、娘娘会……等节日活动的记述。跳大神是为了祭鬼,唱大戏是为了看龙王爷,为鬼而作的盛举,多是呼兰河人麻木的精神写照。虔诚的呼兰河人在生命的流逝里,对死亡庄严、神秘的恐怖感,完全变成了精神上的盛举,死了的人没有什么,活着的人似乎无所牵挂,在无价值的生与死上,面对生命的漠然,两个年轻的学徒为了争一个妇人而大打出手。与小团圆媳妇的死相比,在人们的视野里,小团圆媳妇就不应该长那么大,走路也不应该生风,而这些无中生有的所谓“病”,是其走向死亡的罪魁祸首,其中掺杂的真诚的愚昧与善良的残忍,令人心魂颤抖。萧红在《呼兰河传》里,用异乎寻常的语调来记述死亡,在荒凉的生命轨迹里笼罩着精神暗影,引导我们窥探生命悲剧的人性观,俨然是她个人生命孤寂的流露。在对“死”的叙述中,将内心的繁复性委婉而深切地表露出来,奠定了其生命悲剧的灰色。
生命的悲剧性不仅是对生命的持续挣扎,也是对生命渴望的永恒追逐。在《呼兰河传》中,缺乏灵性的尘世生活,使萧红失去了真切的情感体验,而生命中的矛盾与冲突,是萧红悲剧人生的根源。萧红的个人身世贯穿于社会、民族命运的漩涡中,尤其是在悲剧人生的精神体悟中,将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的生死理解融入自我的情感寄托中,也从切肤之痛中理解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困苦。萧红的苦难生命源自早熟的童年,背负着父母之爱的缺失,其主观情感充满了沉重与寂寞。“我家的园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4]这种苦难的人生悲剧情感打破了内心的安静,成为萧红悲剧人生性格的最大诱因。人性的建树与情感的融合是构建坚固生命的根本,而萧红的悲剧性人格,在面对死亡的恐怖与对生命执着的追求中,期许与荒寂终其一生的相伴。萧红不是哲学家,在理解生命及超越自我中难以从哲学视阈来梳理情感,不可能从童年的精神危机中感知生命的质朴。冯歪嘴子面对生命的挫折,看到一天比一天长大的孩子,能够从中获得生命的理解,从感情上拾起爱的希望与慰藉。然而,对于萧红的激荡人生来说,这种冷静而乐观的生活态度,无法从人性憧憬中获得满足,更难成为她笔下的坚强与执着。尽管萧红能够从自信中延续着对活着的执着,但却是悲凉的,无可奈何的。
三、情感纠葛与率性是萧红人生梦幻之殇的性格悲剧
现实中的萧红在对理想的追求中,跌入了梦幻的悲情世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现实与梦幻的纠葛繁复,一方面强化了萧红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一方面游走于现实与梦幻之间。萧红与汪恩甲的婚姻是包办的,而在萧红离家出走被抓回后,与未婚夫家解除婚约。其后的萧红再次离家与汪恩甲同居,最终两人因矛盾纠葛而未能走到一起。萧红的情感因其任性而得不到“童年梦幻”,以至于率性而为的性格成为破坏爱情誓言的尖刀。萧红的第二次婚姻是在真爱中度过的,萧军不仅不嫌弃萧红怀着别人的孩子,还鼓励萧红的文学创作,但后来又因情感不合而心生嫌隙,最终分手。萧红对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不解,而萧军对萧红的忍屈受辱最终成为两人情感破裂的导火线。得不到情感慰藉的萧红在抱怨中近乎苛求,而萧军的性格也难以像萧红的祖父那样满足萧红的“童年梦幻”。端木蕻良是萧红的第三段婚姻,也是萧红人生的最后一次离殇的爱情。萧红的率性未获得端木的理解,在萧红身患重病期间不辞而别。一路跌跌撞撞的萧红,难以从儿时的童年梦幻中获得释怀,而在其“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悲情呼声中,更多的是自我感伤。短暂的生命与纠葛的情感经历,使人生理想幻灭,在造就萧红悲剧生命的情感寄托中,也加剧了其作品的困顿与坎坷。祖父的宽容与宠爱不过是童年的自由生活,是不可复制和再现的,其偏执的性格,是悲情生命至死不醒悟的缘由。
萧红对悲剧人生的“冷处理”与朴实真挚的文字,向我们诉说了“忘却了难以忘却”的情感回忆,也增添了《呼兰河传》原始的、悲凉的审美意蕴。对于普通的生命与生命意识,在惊心动魄的消亡中恰恰体现了悲剧人生的审美深度,正是这种崇高而悲壮的情感体验,在淋漓痛快地宣泄后,为读者呈现了特殊的情感。正因为如此,在《呼兰河传》中,从萧红的悲剧人生的悲情意识阅读与理解中,她所选择的悲剧形式及悲剧内容,从根本上抓住了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实质,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1]钱理群.改革民族灵魂的文学[J].十月,1982,1.
[2]萧红.呼兰河传[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278.
[3]萧红.呼兰河传[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296.
[4]晓川,彭放主编.萧红研究七十年(下卷)[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319.
责任编辑:丁金荣
I106
A
167-6531(2015)12-0033-02
莫瑞芬/广东科技学院教师,硕士(广东东莞523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