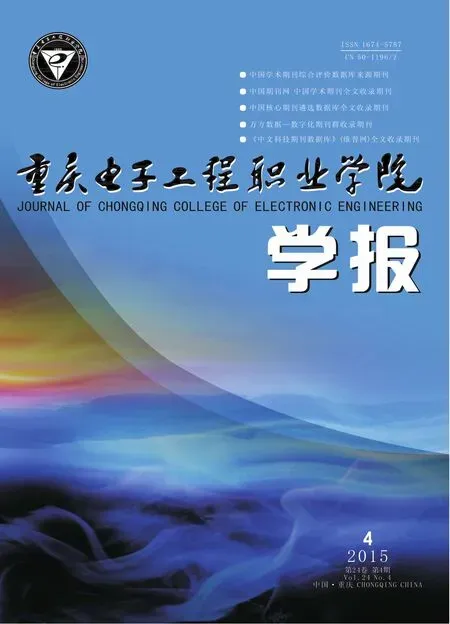从“东方学”角度解读《万里长城建造时》
黄轶劼,梅山瑛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从“东方学”角度解读《万里长城建造时》
黄轶劼,梅山瑛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是一部有着浓厚东方色彩的作品,小说中充满了西方关于东方的想象,无论是文本创造还是话语系统都有东方主义的特性。卡夫卡对中国的描述反映出中国长城被打上“他者”文化符号的烙印,同时这也是西方对中国进行东方化的结果。
《万里长城建造时》;萨义德;东方主义;他者
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是一部意义含混的作品,小说讲的不是中国长城建造结构等外在特点,而更多地侧重于把长城作为一种东方文化符号,用西方思维来想象中国传统。从题目上看,长城“建造时”,着重讲建造长城的经过,而并非长城建成的结果。小说通过叙述长城的建造过程来表达作者对中国传统的想象,事实上西方人对中国的东方化想象为卡夫卡的创作提供了写作素材,卡夫卡的东方想象也是建立在“西方意识”基础上的。
1 文本所创造的中国
《万里长城建造时》整篇小说离奇荒诞,读者熟悉的中国被作者披上了一件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是小说刻意创造出东方帝国的神秘感,不如说这是作者为读者创造出来的东方。
小说虽然通篇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甚至有意拉开“我”与作者本人的距离,但读者还是认为文章中的“我”是卡夫卡臆想出来的中国人形象,与作者卡夫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本的假设性使读者一开始就不可能将小说中的长城等同于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卡夫卡创作文本臆想的“万里长城”。
卡夫卡一生从未来过中国,中国长城“是根据布拉格的一处名胜,即劳伦茨山的‘饿墙'写成的。它离卡夫卡的住宅很近,是由囚犯建造的,墙本身毫无意义。”[1]实际上,这样一堵“围墙”与中国雄伟的万里长城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有着非凡想象力的卡夫卡却把这堵普通的墙刻画成具有悠久历史、载有光辉文明的万里长城。对于卡夫卡,万里长城在某种程度上和劳伦茨山的“饿墙”是一样的,并无实质差别。可以说,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塑造的东方形象并非来源于真实的经验和依据,小说中满是被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萨义德看来,东西方划分并非是单纯的地理划分,真实的东方与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差之千里。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中,萨义德清晰地定义了被西方人“东方化”的东方:“东方主义当然是指几个相互交叉的领域……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人为的产物,也就是我所谓的想象地理学。”这就说明,东方并非地理意义上的真实东方,它是个人主观意识作用的结果。通过想象,西方对东方做出各种猜测,并用一系列看似严谨的举措对这些主观想象进行合理论证,就如同卡夫卡根据家门口的饿墙创造出想象中的万里长城一样。卡夫卡虽然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文本中他对中国的再创造并不会让每个人都信服,因为他的这些“证明”依赖的是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经过西方思维模式的加工找出符合他们想象的论据,中国长城被打上“他者”的符号烙印。
2 对作为“他者”的中国长城的想象
萨义德在《想像的地理及其表述形式:东方化东方》一文中指出:“许多实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该做法特别适用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寻常的人和事:像外国人、某些突变、‘反常'行为等。”
阅读小说过程中,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与其说这是作者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卡夫卡为读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建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小说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看来,从古至今东方就是异于西方文化的“他者”,是位于边缘地带的客体,东方象征着神秘的巫术、奇异的探险、原始的部落、未经完全开发的族群。作为客体的东方理应是落后的、冲动的、无知的、蛮横的,等等。《万里长城建造时》所创造出的中国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
首先,从时间上看,小说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仅仅知道故事背景发生在高强度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读者看到一个和西方大相径庭的中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标榜自由民主,他们开始摒弃专制制度的封闭和停滞不前,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仍然被定义成东方专制的政治体制,长城象征着帝国的专制,城内的臣民必然是被奴役和服从的。小说通过参与建造长城的“我”的猜想和疑问,逐渐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组织结构高度集中的中国,长城采用分段而建的建造方法,以500米为一个单位,最后连接成一个整体。荒诞的建造方法和“我”对真相的质疑,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小说中的“我”为了寻求长城分段建筑的理由不断假设又很快推翻,不安于现状却又选择服从,相互矛盾的行为又让故事显得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小说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读者立马就能感受到卡夫卡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划等号。
其次,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对于修建长城的目的,百姓没有任何质疑,即没有语言上的表述,也没有思想上的斗争,无条件地屈从于上级的命令。即便是积极寻求真相的“我”也只有思想上的假设,推翻质疑后也选择服从。而处于庞大科层体系之上的官员也同样愚昧无知,他们不知道修建长城的意义,却有意消磨时间、复制长城。像螺丝钉一样机械服从、愚昧迷蒙的人物刻画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未经完全开化”的理解和想象。在这个体系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所做所想都不需要理由,读者的情绪也被融入这个荒诞的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感到陌生的世界。卡夫卡在进行文本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被“符号化”的中国。在经过提纯后,如同让人琢磨不透的故事寓意一样,西方读者了解到的是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原始、迷蒙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万里长城建造时》展现了作为“他者”的从属地位的中国。和西方的进步理性相比,处于东方的中国必然是愚昧的、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西方人用“他者”的落后野蛮来烘托“自我”的进步理性,“他者”的作用是为了凸显主体的出色。
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歪曲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大部分东方人自己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这些场景和《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描写相当吻合)……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此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接受上。如莫言早期的作品《红高粱》等,国内读者被小说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与其说是小说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封建落后的看法,这种迎合将会造成世人普遍接受西方审美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中国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著表现。
3 东方化的中国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尽管不包括中国,但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一套表述中国形象的话语,这些牵涉中国的文本为卡夫卡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也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产生了西方控制东方的权力,同时也很有可能影响了卡夫卡对中国的认识。卡夫卡从未来过中国,更谈不上与中国人交流过,那么他对东方的了解只可能来源于西方,所知的是一个被东方化的中国。
在西方,长城对于中国就好像金字塔是埃及的象征一样,关于中国的描述很早就和长城联系了起来。1833年,德国著名作家海涅曾这样描写中国:“你们可知道中国,那飞龙和瓷壶的国度?全国是座古董店,周围耸立着一道其长无比的城墙,墙上伫立着千万个鞑靼卫士。”[2]和海涅一样,同为说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很有可能受到海涅的启发。不仅如此,门多萨、利马窦都暗示过长城是分段建筑,而《万里长城建造时》最常提及的就是长城分段建筑的特殊性,甚至整篇文章就是从“我”质疑长城分段建筑的方式上展开的。正如残雪受到卡夫卡这样先驱的影响一样,卡夫卡所塑造的长城也是由他的先驱创造出来的。
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百姓服从观念严格、皇权至高无上,而这些都可以用长城作为载体来表达。由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里没有提及中国长城而被世人怀疑是否来过中国,长城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卡夫卡在《万里长城建造时》里一一呈现了这些特证,并且在上述特证基础上增添了一层关于人生困境的思考,而这些思索恰好又在时间上对应了西方关于长城象征意义的转变。独立成篇的《一道圣旨》是《万里长城建造时》的一个片段,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关于中国的想象。使者试图把弥留之际的皇帝的谕旨传达给遥远的臣民,然而他永远都走不出长城,完成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皇帝的旨意得以传达时,可能早已时过境迁,一切都荒诞得不可理喻,于是“我”对于这个问题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毫无疑问,长城象征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卡夫卡所描写的中国更加困顿、迷惘,更类似于一个站在十字路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形象。当使者走向大门,手里拿的已经是一个死人的旨意,即使送到接受人的手里也毫无意义。卡夫卡想象的长城是不可阐释的,把长城的具体象征意义虚化成不可言传的中国文化符号。而此时在西方,长城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门多萨与伏尔泰把长城作为中国强盛的象征,后来的福笛则将长城看成中国文明软弱的标志,卡夫卡有意将长城的意义进行模糊化处理,放弃了对长城确定意义的阐释。强盛的中国正站在变革的路口,作者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具体意义的探究,这与长城当时在西方的象征意义由强大转变为弱小的现象不谋而合。
4 结语
卡夫卡所创造的中国长城是文本性的,非真实的;是跨文化的,非单一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是带有浓厚东方主义色彩的。正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识给卡夫卡提供了丰富的东方学主题、乃至对中国的臆想,作者用矛盾的话语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模糊化、大众化,把历史阐述的不可能性拓展成诗学阐述的无限可能性。但在行文中,读者通过长城背后的历史隐喻仍能感受到作者西方的思维特征。
注释:
[1]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38.
[2]曹新民.话说陶瓷海上瓷路[J].陶瓷研究,2004.
[1]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周宁.万里长城建造时:卡夫卡的中国神话[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5]靳婷:萨义德及其《东方学》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论文.
责任编辑 闫桂萍
Reading“At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HUANG Yijie,MEI Shan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500,China)
Kafka's“At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is a novel which has a strong Orientalism flavor. In a way,it is full of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about oriental.Whether in the text creation or the discourse system exists the character of Orientalism.The description of China reveals that the Great Wall is branded the culture symbol of“heteronomy”.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West Orientalizing China.
“At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Wall”;Edward Said;Orientalism;heteronomy
I207.41
A
1674-5787(2015)04-0052-04
10.13887/j.cnki.jccee.2015(4).14
2015-04-12
黄轶劼(1989—),女,湖北武汉人,云南师范大学2014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梅山瑛(1989—),女,广西桂林人,云南师范大学2013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