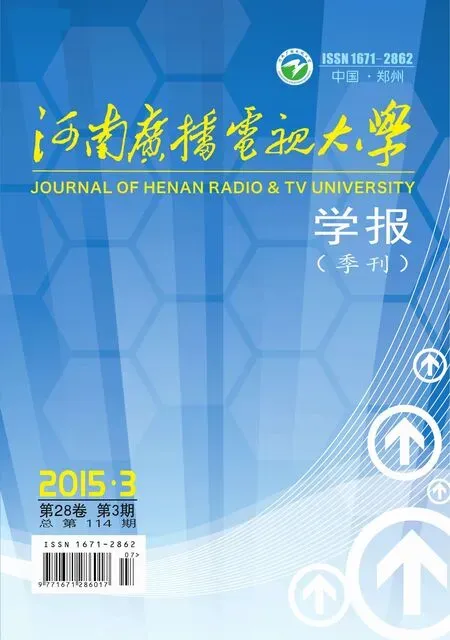刘勰与《弘明集》的编纂
刘玉叶(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刘勰与《弘明集》的编纂
刘玉叶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450001)
刘勰依止僧祐,信仰与学术思想均深受其影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重点探讨刘勰与僧祐《弘明集》编纂的关联,认为刘勰很有可能实际参与了《弘明集》的选文定篇之工作,在担任僧祐助手的过程中培养了坚定的佛教信仰和广博的学术基础,对《文心雕龙》的写作有极大影响。刘勰虽然参与《弘明集》的编纂,但僧祐著作为刘勰“捉刀”一说不确,本文亦尝试辨析。
刘勰;僧祐;《弘明集》
刘勰自弱冠始依止僧祐十余年,培养了坚定的佛教信仰和广博的学术基础,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深受僧祐影响,在其著作中必有所体现,在协助僧祐“抄撰要事”、“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学习过程中,也很有可能参与了《弘明集》的选文定篇之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弘明集》中的篇目思想价值经过了僧祐的审定,刘勰也根据文学性进行了择选,《弘明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定林寺弟子的一部在本土文化冲突交流中学习佛教义理的教科书。
一、刘勰依僧祐与佐僧祐著述
刘勰在定林寺依止僧祐,主要是依据《梁书》卷五十《刘勰传》的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集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高僧传》之僧祐传云:“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据范文澜、杨明照、陶礼天等先生考证,将刘勰来到定林寺的时间定于齐永明五年(487年)与写作超辩墓碑碑文的永明十年(492年)之间,《梁书》本传又记载他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天监三年(504年)为萧宏记室,此时刘勰已近不惑。故刘勰追随僧祐的时间最短11年,最长不超过16年。这长达十余年的时光中刘勰耳濡目染僧祐其人其学,自身人格与著作也必定深受感染,从二人学术之系联研讨二人著述之系联,依此亦为可行。若要深究《弘明集》与《文心雕龙》之系联,必须回归还原刘勰之依僧祐的原委以及在定林寺从事的事业。
刘勰追随僧祐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僧祐学识名望的崇拜。在《剡山石像序》中,刘勰就评价其师“德炽释门,名盖净众,虚心宏道,忘己济物,加以贞鉴特达,研虑精深”,对僧祐德行、名声、学识、智慧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刻画其建造石像的情景说:“律师应法若流,宣化如渴。扬船浙水,驰锡禹山。于是扪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仙腹之悬阁。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1]对僧祐不辞劳苦地宣扬教化的弘法决心真心敬佩,也对老师卓越的艺术设计才华所折服。同时,定林寺也是金陵相当有名的佛寺,自从昙摩密多于元嘉十二年开创以来,一直香火鼎盛,吸引了众多朝廷权贵名流,“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2],可以说是适合一位梦想“待时而动,发挥事业”的年轻人的好地方。刘勰也是这众多“息心之众”之一,怀揣“擒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抱负来到定林寺投靠名僧僧祐的。
而僧祐欣然应允刘勰一直追随在身边,也正是因为整理经藏与撰述的繁重工作需要一个这样得力的助手。刘勰也正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得到学习提高的,并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僧祐的夙愿。一是整理定林寺经藏工程,刘勰主要做“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整理文献工作,将定林寺的全部藏经校对编定,故称“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祐集经藏既成”,僧祐的下一个工作就是在全部整理过的藏经基础上编纂目录《出三藏记集》及写作汇编《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这个阶段刘勰从事的是“抄撰要事”的材料汇编工作。在僧祐的指导和多年的佛经整理编定实践中,刘勰“博通经论”“长于佛理”,成为有名的佛教学者。同时利用闲暇时间完成自己君子“树德建言”的理想,在青灯古佛下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同时,僧祐门下内外兼修、注重文史的学风也给予刘勰很大的思想熏陶和鼓励,据《续高僧传》卷六《明彻传》:“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又同传卷一《宝唱传》:“唱投僧祐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璧、续法轮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名僧传等。”僧祐门下弟子都不废儒家经史,并仿效老师,热衷著述。僧祐对写作的热情和责任感对于刘勰是影响极大的,从《法苑集》中所涉及的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也都能看出僧祐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也鼓励了弟子们不拘于佛经的学习,而广采众长,融于一体。
二、刘勰的佛教信仰
刘勰与佛教的关系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刘勰是否信仰佛教、为什么到定林寺依僧祐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王元化先生就认为刘勰主要是因为“避租役”而入定林寺的[3],张少康先生也认为“刘勰虽然身在佛寺,却心存魏阙”[4],认为刘勰把佛教当作躲避徭役、迈进仕途的手段,论据就是《文心雕龙》中甚少提到佛教内容,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仕进倾向。对于“家贫,不婚娶”的解释,杨明照先生的解释最有道理。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5]中云:“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其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即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
指出这种“贫”只是一种相对状态。况且若有此心,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刘勰已为官,还可婚娶,但刘勰坚持一生未婚,唯一合理的解释也正是因为他坚定的佛教信仰,若仅仅用“待时而动”就难以解释刘勰在定林寺十几年的耐心。
即使在刘勰“起家奉朝请”与僧祐告别之后,也仍继续从事整理佛经的工作,并为京城寺塔及名僧碑志撰写文章。刘勰此后又两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经,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说:“天监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浅识难寻,敕庄严僧旻于定林上寺缵《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同书《僧旻传》:“仍选才学道俗僧智、僧旻、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卷,皆旻取衷。”①
入仕后的刘勰于佛教戒律也时时关切。《梁书·刘勰传》记载:“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刘勰上表提议将二郊农社牺牲祭祀改同七庙,都使用蔬果祭祀。梁武帝非常赞赏,下《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此后,中国祭祀宗庙遂皆用蔬果。
祭祀用蔬果与儒家传统祭祀礼仪不符,而刘勰如此提议,也正是表明了当时融合之文化风气,僧祐也曾上奏梁武帝禁断渔猎。②儒佛之内心自然圆融,故《文心雕龙》中极少用到佛教词汇与理论,也并不能说明作者不信仰佛教。《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严肃、纯粹的文论著作,刘勰对其是保持着儒家式的“立言”而“不朽”期望的,故没必要写成《弘明集》一般的佛教论文。宗教信仰体现在行文中不会单纯地以词汇等来表露,而会在方法论、组织结构、思想体系等中表现出来。《文心雕龙》中这种浸染了佛教思维之处,学术界也有甚多研究成果,普遍认为《文心雕龙》受佛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断发掘出新的思想关联。
在《文心雕龙》的结构体式上,刘勰的设计就别具特色,设定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体大思精之义例。饶宗颐《文心与阿毗昙心》一文就认为,《文心雕龙》一书的体例安排直接受到《阿毗昙心论》的影响。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序志》篇注中亦云:“普遍认为言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宗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氏法式而为之,故能思理明晰若此。”慧远所著《阿毗昙心论序》云:“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文心雕龙》每篇之赞就类似偈,体例安排颇类似于慧远所著之《阿毗昙心论序》。另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体系也是吸取了佛学的因明学和成实论。[6]《成实论》所用的术语内涵明晰、解释清楚,和当时一般的佛学著作模棱两可的言说方式大异其趣,《文心雕龙》之所以语言上推理严密、结构系统体大虑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绝无仅有,也只能说明刘勰博采众长而为己用的学术思想。
三、《弘明集》为刘勰“捉刀”辨
确定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信仰之后,也是因为刘勰深得佛理,多作佛学相关文章,并且编定定林寺佛经,其功甚伟,学术界又有声音质疑僧祐的诸多著作刘勰不仅仅是“抄撰要事”、整理收集材料而已,而是全权代僧祐著述。这种声音在明代便已出现,明代曹学佺《文心雕龙序》云:“传称刘勰深于佛理,京师寺塔,名僧碑志,多其所作,予读《高僧传》往往及之。……窃恐祐《高僧传》乃勰手笔耳。”明徐渤《文心雕龙跋》曰:“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释迦谱序》《世界记序》等篇,全类勰作。”[7]严可均《全梁文》卷七十一释僧祐小传注也说:“案 《梁书·刘勰传》:‘……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如传此言,僧祐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8]今人范文澜先生说:“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9]杨明照说:“僧祐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此“舍人”也指刘勰无疑。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中以极大篇幅分析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之异同。认为“刘勰在僧祐处悉心钻研十余年,成了博闻广识的佛教学者。他作为佛教学者殚精竭思的最大业绩就是撰成佛典目录。……后再经考证,估计是以师僧祐之名传世的《出三藏记集》。”
依照这个思路,潘重规《刘彦和佐僧祐撰述考》[10]详证了僧祐著述为刘勰“捉刀”的假说,认为僧祐不能躬亲撰述有四个原因:“一曰祐劳搜集,二曰祐疲法事,三曰祐躬营造,四曰祐晚多疾。”定林寺的经藏整理需要“辨真疑伪,躬亲考验,访讯遐迩,费时尤多”;另外,僧祐的法事活动甚多。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略成实论》记载僧祐所参与的一期讲会说:“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召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11]可知一期讲会就要延续四个月之久,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杂务而委托德高望重的僧祐亲自处理,如天监九年,道人妙光伪造经典,便由僧祐奉敕审讯。另外,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中自叙“疾恙惛漠,辞管铨藻,傥有览者,略文取心”,在《弘明集》卷一序中也说:“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可看出僧祐身体状况。
僧祐在《萨婆多部记目录序》自言:“条序余部,则委之明胜”,在《出三藏记集·法集杂记铭目录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这成为明显的“捉刀”论依据;另外,作者还认为僧祐在《十诵义记目录序》中自道短于文辞:“昔少述私记,辞句未整,而好事传写,数本兼行,今删繁补略,以后撰为定。”作者还举出“文意辞气”方面的依据,如《文心雕龙》中的 “沿波讨源”“披瞽而骇聋”“暧乎若可觌”“原始以表末”“援古以证今”,在僧祐著作中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表达。
笔者认为,编定林寺经藏刘勰做的是“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整理文献工作,在《出三藏记集》、《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的写作中,刘勰则主要做“抄撰要事”的材料汇编,这点《梁书》的刘勰本传与《高僧传》的僧祐本传所记是记载非常清楚的。这几部著作至少主体是为僧祐自己亲力亲撰,而且即使是刘勰从事了一部分工作,也是忠实反映僧祐的思想。以僧祐事务繁忙就推断著作是别人捉刀,这是难以推论的。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也自述自己的生活:“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松清密;以讲习闲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飡,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可以看出,僧祐以一种忘我献身的宗教热情从事撰述事业,对于他看重的事业表达了亲力亲为之大愿。况且,不能因为僧祐的自谦之辞与专注于律学研究就断定僧祐短于文采,僧祐在他的《法苑集》中,搜集之博就可以说明他的兴趣广泛,文艺学养深厚。同样,僧祐在《弘明集》后序中的自谦之词“轻率鄙怀,继之于末,虽文匪圭璋,而事足鞶鉴。惟恺悌君子,自求多福焉”“学孤识寡,愧在褊局。博练君子,惠增广焉”,都表明是文为其亲手所制。再者,僧祐为人为学皆严谨求实,定林寺经藏中秉师承者都会指出,如《迦叶维律》注云:“昔先师献正,远适西域,誓寻斯文,胜心所感,多值灵瑞,而葱岭险绝,弗果兹典,故知此律于梁土众僧未有其缘也。”如刘勰为之代笔,又怎可能忽略不提?饶宗颐先生对此问题时隔半个世纪所作出的思考大有不同,也可以说明问题,1952年于《民主评论》五卷五期上的《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中云:“定林寺经藏目录,现尚存,书名《出三藏记集》凡分十五卷,题僧祐名,可能出勰之手。其中不少论文,可视为刘氏所作或至少可代表他的意见。”但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论僧祐》中,饶宗颐却认为“僧祐《出三藏记集》一书,有其独特之义例及行文习惯”,“措辞叮咛周至,出自肺腑,绝非刘勰所能代言”。饶老之见解甚是。学者指出的文意辞气相同者,正说明师徒思想之契合。“看到《文心雕龙》与署名僧祐的佛教文字颇有一致之处,此并不表示刘勰代为捉刀,而恰恰证明了刘勰受僧祐影响至深,可谓刻骨铭心。”[12]
注释:
①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梁武帝本人于四月受佛戒,崇佛正值高潮,而僧祐未竟之业,亦待及时完成,故敕刘勰、慧震二人,必在本年 (天监十八年即519年)。”(《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01页。)另杨明照认为是在萧统卒后的大中通三年(531年):“舍人为昭明旧人,既不得留,又未新除其他官职,中大通三年四月后,或即受敕于定林寺与慧震共事撰经乎?”(《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之《梁书刘勰传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页。)
②《广弘明集》卷二十六《叙梁武帝断杀绝宗庙牺牲事》:“梁高祖武皇帝临天下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修行佛戒,蔬食断欲。上定林寺沙门僧祐、龙华邑正柏超度等上启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鲜食之族,犹布筌网,并驱之客,尚驰鹰犬,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洽之旨。请丹阳、琅琊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敕付尚书详之。”
[1]刘勰.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M]∥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65:3309.
[2][梁]释慧皎,撰.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22.
[3]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张少康.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祐”?——读《梁书·刘勰传》札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2).
[5]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黄广华.《文学雕龙》与因明学[J].学术月刊,1984,(7).
[7]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49.
[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373.
[9][梁]刘勰,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30-731.
[10]新亚研究所.新亚学报(第十五卷)[M].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年份不详:27.
[11][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405.
[12]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417.
LiuXi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ongMingJi
Liu Yuye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1)
The faith and academic thoughts of Liu Xie were all deeply influenced by SengYou,which has been discussed in many papers.This paper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of LiuXi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HongMingJi of SengYou,and consider that Liu Xie wa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of HongMingJi,and developed his firm Buddhism belief and extensive academic foundation which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WenXinDiaoLong.Although Liu Xi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liation of HongMingJi,the statement that Liu Xie write the works on SengYou’s behalf is not exact,and this paper is also trying to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is statement.
LiuXie;SengYou;HongMingJi
I206
A
1671-2862(2015)03-0047-04
2015-03-12
刘玉叶,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