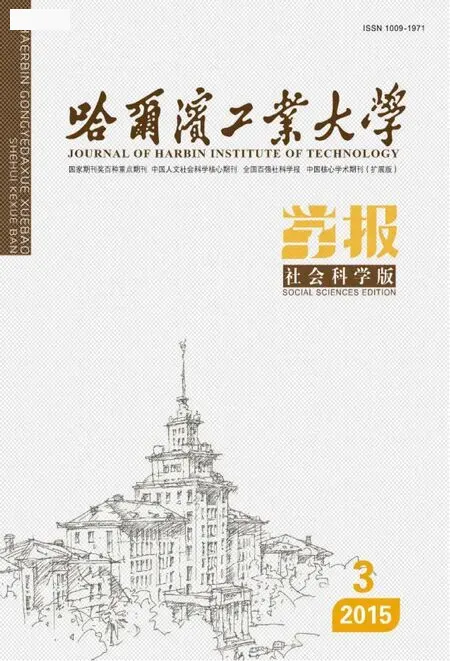发凡起例 别创一格——孙昌武、孙逊、王青的宗教文学研究
左丹丹,吴光正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20世纪的道教文学在一些个案研究上取得了方法论的突破和研究深度的开掘,其中王青、孙昌武、孙逊三人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宗教叙事学研究、道教神话研究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还涵盖了整个宗教文学史,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一、理论建构与文献阐释的神话学力作
笔者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百年来文学史论著中所维持的神话定义和中国神话历史化、中国神话零乱不系统等论断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指出理论的匮乏是中国神话研究的瓶颈,近日为撰写《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述评》重读王青先生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一书,再次为先生的理论建构和文献阐释所折服,因而决定将这本大陆学者不易看到的、可能会对神话理论和神话史研究带来冲击的神话学论著作一简单述评。
(一)为阐释汉代本土宗教和神话建构了科学的理论视野
作者为阐释汉代本土宗教和神话建构了科学的理论视野,并指出宗教与神话是一对孪生兄弟。作者把两汉时期的国家宗教界定为“普化宗教”,即“是一种自身并不独自存在的宗教,其仪式、教义、神职人员均已和其他的世俗制度(如国家、政治)混杂在一起,融合在其他世俗制度的概念仪式、结构里”[1]5;而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被界定为制度化宗教,即“具备了普化宗教所缺乏的独自存在”,“具备了特有的宇宙观、崇拜仪式以及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当时的黄老道、方仙道都可以从教团组织、政治倾向、信徒的社会地位和神学理论做出区分和界定。作者对神话的要素和功能作了重新阐释,指出神话应包含三大要素:第一,神话必须包含一件或一件以上的故事,故事中必须有主角,主角必须要有行动;第二,下述两个要求至少要满足一项:主角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或与非凡的世界有牵连,主角的行动是常人所无法完成的;第三,神话的创作者及与他在同一个文化社会的人坚信神话的真实性并以它作为日常生活、社会行动、仪式或行为的基础。神话功能主要表现为“神话乃是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宗教,都需要通过神话来神化教主、建立权威、培养及巩固信仰,宣传及解释教义,以及传授各种宗教技能”[1]49。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勾勒了汉代国家宗教的制度化过程,在彰显其政治功能的同时指出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宗教制度是在方士的参与、策划、操纵下建立起来的,郊祀、封禅、明堂祀典体现的是方仙道得道成仙、长生不死的精神,此后逐渐掌握朝政的儒生方士化使得儒学方术化、方士儒学化,最终导致了谶纬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的盛行。比如,作者指出郊祭主神太一神地位的提高得力于新垣平等方士和巫师的鼓吹,公孙卿的《宝鼎策书》指出,“宝鼎的出土,并非如有司所说的是象征着受命合德,而是象征着将要成仙,只要完全按照黄帝的做法:郊雍、封禅、游五山、学仙,就能像黄帝一样仙登于天”[1]106,于是至上神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进入郊祀并使郊祀成了候神求仙的方仙道仪式;而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神学理论使得汉代的郊祀、封禅仪式远比庙祭仪式隆重、受命之君比续位之君更重要;儒生们掌握权利后势必对汉武帝确立的仪式进行改革,因此,“太一的勃兴与衰落反映了方术和儒生两种不同的宗教观念在国家宗教领域内的斗争”[1]119。
(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属性作了重新界定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属性作了重新界定。作者认为“中国神话零碎不系统且较为缺乏”的论断是学术界用自然神话派理论套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不同民族的神话内容取决于神话产生时期的民族文化构成”,而中国文明的产生是靠政治秩序而非技术或商业的程序造成——以父系氏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确定的政治秩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神话在根本上是以氏族团体为中心的人文神话。作者利用考古学的成就证明中国的古史系统含有相当多的信史成分,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人文神话的主要形成途径并非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的神话化”,即“历史上的人物经过神化而有神话,其事迹经过夸张而变得非凡。”两汉时期的神话属于文明神话,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而创作的:“这些神话往往利用这一时期流行的某种信仰或观念来供给一种实际的解释,虽然它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客观知识,而是作为支持它行动的理由”;“它虽然不能分析实证,却被相信为事实或真理,并以此鼓舞某种行动达到某种目的”;“每一个时断每一个地方,一个事实的权威只能由授任一个流行的神话而合法化,只有神话能提供合法性”[1]70。
作者认为神话是古代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国家宗教和道教的主要神灵如太一神、黄帝、老子和西王母的神话史来揭示宗教神灵谱系与宗教神话的建构史。比如,作者认为黄老之学包括政治理论和方术之学并分别发展成为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下层的民间宗教,而黄帝和老子的神话在黄老之学演变为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宗教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指出:黄帝为实有的部族首领,黄帝传说在春秋时期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直接祭祀黄帝的姓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地位,其本身的宗教文化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流播,黄帝传说在战国中期以后的日益丰富取决于陈氏在齐国的崛起和代齐从而使得黄帝代替姜姓祖先而成为齐国的远祖;黄帝世系传说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功能,黄帝作为各氏族的共同祖先反映了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并得到几乎所有诸侯国的认同,成为全国统一的理论依据之一;黄帝成为制器和发明方技术数的文化英雄,成为五色天帝之一成为五德终始历史系统中的一环,成为《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并启发了后世道教的黄帝求取神话和各学派通过高人与黄帝对话来阐释理论主张的方式;黄帝神话在汉代及其以后分别出现长生神话、感生神话、异貌神话和受命神话,前者转化为求经与授经神话借此神化道教经籍,后三者是要强调黄帝的神性为君权提供合法性论证。在道家思想宗教神学化的同时,老子神话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渐渐从思想家而成为道教的教主。老子神话的发展是道教应对各种文化势力和自身教派发展的结果。汉代儒生为了集团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政治信念不断神化孔子,于是在野的方士集团也神化老子作为代表自己集团的先师与圣者,与君权和儒生集团抗衡,以便自己在汉朝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天师道尊崇老子并谓本派道术经籍亲受于老子,不同时代的天师道往往借助老子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威通过神话为他们的宗教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上清经和灵宝经都成了老君所授,于是老子成了各个教派的中心人物;老子神话在魏晋之后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即是确立道教的权威,对抗佛教的流播,这种文化使命反而促进了对于佛教神话的吸收。
作者尊重中国宗教神话的生成语境、文体特征和文化背景的同时融汇现代神话学和宗教学理论指出宗教仪式与神话密不可分并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彰显了宗教借助神话传播信仰建立权威的功能。作者认为,起源于《管子·封禅篇》的神话在稷下学派那里成为统一帝国各项制度的重要宗教大典,这一神话规定了宗教领袖的身份资格,成为受命于天的贤圣君主和统一国家的君权标志,因此,“秦始皇统一后便去封禅,但祭祀仪式由于没有神话存在而没有章法,儒生方士争论不休乃在于主神没法确定,结果以秦国的上帝代替了全国性的上帝,封禅时的大雨从宗教上否定了秦王朝的合法性”,只有当封禅神话彻底完成后相关的封禅仪式才得以确立。作者认为,赤松子神话和王子乔神话分别是焚巫祈雨仪式和乘蹻陟神仪式的神话再现。赤松子神话中的“雨师”、“入火自烧”与“随风雨上下”等现象与商周的祭祀传统密切相关,从侧面反映了炎黄之战基本上是一场巫术之战;宁封子、师门、啸父及陶安公神话都是赤松子神话的衍变,到了南北朝,这个故事变得不可理解,于是被时人合理化而使其发生了变异。作者引用卜辞文献和墓葬图画中的陟神仪式和道教文献中已经方技化的原始陟神仪式——虎蹻鹿蹻龙蹻仪式说明王子乔神话是乘蹻陟神仪式的神话再现。作者指出宗教通过神话宣扬其仪式、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和一整套传经仪式的操作程序,间接介绍了本派用以达到有价值的目标的的手段和技能。他将道教传经仪式和《汉武内传》相关情节作比较,指出《内传》的每一部分都与相应的仪式阶段有关,是典型的传经神话,由于所授的不仅是《五岳真形图》及灵飞六甲十二事这两种经符而且还同时传授了以教派服食为中心的不形诸文字的口诀,所以有些基本程序有所重复。
(三)神话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作者坚信神话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所以在研究汉代神话时在时间上向前后作了延伸,并采取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寻溯其历史依据,然后逐一考察它在后期的演变、分化及流播,以及它在现实政治宗教领域内的功能。”作者分析了钓鱼神话的形成及其在宗教中和政治上产生的长久而深刻的影响:指出涓子、吕尚、琴高、寇先、陵阳子明及子英神话中的五个神话实际上都是钓鱼得符神话的不同衍变,其原因在于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由于口头传承的变异和文本传抄的讹误,这一传说系统在谶纬中的变异是朝着把钓鱼得符这一情节视之为天命显现与祥瑞标志的方向发展,逐渐了失去其文本神话的原意。
作者还从宗教与神话互动的角度对相关作品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进行了透视,为文献考证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作者从宗教史的角度指出直至唐以后内容上仍有变化的《神仙传》产生于汉代结集于东汉:医药技术上的突破促进了方术的繁荣形成了南北两派,南派以饵食芝草等养生方术为主也吸收了中部的呼吸导引,北派以来源于西方的金丹为主,这一变革掀起了战国中晚期以来的求仙热潮;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把方士理论系统化并使其成为解释自然、社会、人事的一种哲学模式;秦始皇、汉武帝、淮南王身边的方士或在技术层面或在理论层面作出了贡献;东汉以后,在官方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方术在全国得到灌输,并形成以《列仙传》为中心的神话。作者用道教史考证神话史,指出《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下凡会汉武帝这一传说乃是在神女降真传说背景下产生的,产生这种传说的原因乃是灵媒技法的广泛应用;《内传》中的接神仪式、西王母服饰和服食很明显地接受了道教早期经籍的影响,其时间不会迟于宋齐年间,可以将它视为西晋末年或东晋的材料;他还钩稽上清派道士尤其是王褒等人的经历,并将《内传》和上清派的《茅君内传》、《真诰》记载作比较,指出西王母形象具体化、西王母侍女名称具体化等变化都说明《内传》人物均与教团教徒作原型,反映的是茅山教团南渡以前的宗教活动,即上清派的活动。关于《内传》的作者,小南一郎认为与上清派人士密切相关,李丰楙进一步推测为王灵期,詹石窗认为是灵宝派,作者从《内传》是一次传经仪式的实际记录这一观点出发,指出《内传》作者一定属于同时拥有《五岳真形图》、“灵飞六甲十二事”等经籍的教派,而且作者应该熟知《消魔服食经》及《四极明科经》等经籍,排除了作者为葛洪的可能性,指出《内传》原始作者为非茅山派嫡系的周义山之门徒,后来经过楼观道的加工和增饰。
二、历史描述和理论提纯
孙昌武先生的《道教与唐代文学》一书就唐代炼丹术、神仙术、宫观文化和三教调和思想与唐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唐代道教的政治化、学理化、世俗化和美学化倾向及其对唐代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再一次彰显了孙先生一贯提倡的历史描述和和理论提纯的内在理路。
这本书的成功得益于孙先生在佛教文学研究上所积累起来的学术经验,体现了方法和理论的高度自觉。它沿用了作者以往研究佛教文学的历史描述的方法,同时也试图对相关的文学现象做出理论上的提纯。作者指出:“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应从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入手,所以‘描述’工作是首先要做好的”[2]后记;这种工作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题目和资料,作些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一般道教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提供线索。”[2]36同时作者也坚信“宗教意识、宗教信仰等等全部宗教现象,关系到人的观念、意志、欲望、激情以及对于宇宙真理的追求、人生奥秘的终极关怀等等,是十分隐秘、复杂、难以索解的。……从这复杂、矛盾的现象里寻求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不仅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文学、认识文学与道教以及一般宗教的关系,而且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都会具有一定的意义。”[2]8因此又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纯,力图阐明唐代道教文化丰富的内涵,指出当时的文人主要是从观念、感情、知识、生活、文化内容等方面接受道教的当时的作者又善于把道教的某些观念转化为审美意识从而创作出具有更高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
(一)对唐代道教文化进行了准确描述并揭示了唐代道教文化的本质特征
作者对唐代道教文化进行了准确描述并揭示了唐代道教文化的本质特征。这种描述的成功是建立在作者对唐代道教文化的准确定位上,即抓住了唐代道教文化的四大中心内容并敏锐地透视出这四大中心内容的灵魂所在。一是炼丹术的公开化。作者指出《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在唐代文人群体中的广泛流传表明炼丹术已成为一种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实用技术,唐代丹经的的纂写、炼丹术的改进、丹药的医疗效果、黄白术的兴盛显示了唐代炼丹术的发达,推动了唐代炼丹术的广泛流传,同时统治阶层的热衷、炼丹术的效验和诱惑使炼丹术拥有了经久的魅力。二是神仙术的世俗化。作者指出唐代神仙思想的新发展主要体现为:对神仙的认识的新变,即神仙形貌接近现世人生、成仙途径更为简易;唐代道士的行为、学养和活动接近现实人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品格;朝廷的神仙观念和神仙追求的现实目的重于纯宗教的目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神仙转化为一种幻想、理想、人生境界,把隐居生活当成神仙生活,用谪仙来形容才能品行特异之人,用神仙来形容美女,甚至把神仙当作某种标格、境遇的美称。三是宫观文化的社会化。作者描述了唐代长安宫观的数量与名称、宫观人数和道观规模、长安宫观与国家祀祷、道观与道士的管理、宫观与教理的研究、道观文化性质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指出宫观不仅是修道的场所,而且是交游和游憩之所,也是都市中的重要的文化生活中心。四是三教调和思想的形成。作者认为儒道释三者的关系在唐代已经由相互冲突演变为相互摄取包容,在儒家学术和思想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对宗教的信仰心相当淡漠,这又使得他们更加自由主动地对待三教,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运用佛教和道教;形成三教调和思潮的因素包括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佛道二教的世俗化发展倾向,这一思潮的契合点则是三教对心性的体认。
(二)对唐代文人的复杂的宗教心态进行了准确描述
作者对唐代文人的复杂的宗教心态进行了准确描述,指出唐代绝大部分文人普遍缺乏虔诚的宗教信仰心。作者描述了文人出于不同观念而产生的对丹药的不同态度:有些人亲自尝试炼丹服药,有些人是出于虔诚的信仰,有些人则是为了求长生、除疾病,有些人则出于游戏的态度,有些人没有实践但由于接触到了相关的事实而会有所感受,有些人出于理性还会对炼丹服食进行批判,有些人对炼丹服食作了猛烈地批判但由于嗜欲的强烈转而倾心丹药甚至中丹药之毒而亡,而真正好道的文人则未必嗜好丹药。作者描述了唐代文人对待神仙术的态度,指出唐代文人入道学仙,或出于不满现实隐居以求志,或出于追求人生的适意和意志的自由,多数人已经没有宗教信仰的真挚与狂热,仅仅局限于羡慕而已,绝对没有了六朝文人的真挚的宗教意趣;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炼丹服药主要出于非宗教的目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隐居中和僧道的交流和宗教信仰也没有什么关系。作者还对文人游览宫观的心态进行了描述,指出宫观文化的发达以及符箓制度和斋醮科仪的完善定型只是为文人提供了接触道教的空间和激发创作的触媒,带着赏玩态度游历道观的文人除了表现道士和宫观的宗教含义外,更能利用这类题材抒写情志开拓出新的艺术空间:道士代表着特定的观念、人生方式和生活理想,宫观有着特定的宗教氛围和特殊的风景,因而分别成为神仙和仙界的象征。作者认为,我们如果“不了解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三教调和’潮流的发展趋势,是很难全面、正确地认识当时的文人接受道教的真实形态的。”[2]470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发现唐代的绝大多数文人都对三教同等看待同样接待,就是像杜甫、李白、王维这样分别倚重儒、道、佛的文人都同样具有三教交流的倾向;一些士大夫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或基于儒家伦理反对佛道二教但在观念和感情上却接受佛道二教的熏染;佛道深深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教养、生活、心理和习俗之中,成了个人的日常行为,不再拥有六朝的狂热和规模化集体性的宗教行为。这种信仰心的普遍缺乏表明那个时代的作家“倾心宗教往往是出于精神慰籍、‘安身立命’的需要,或只是以‘赏玩’的态度寻求精神寄托。”作者的描述为我们解读相关作品提供了标尺,解决了以往研究史上为某一作家是否信仰某种宗教、到底信仰何种宗教而产生的无休无止的纷争。
(三)揭示了唐代道教文学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和美学意蕴
作者通过对唐代“道教与文学”的四个专题的描述揭示了唐代道教文学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和美学意蕴。作者指出,唐代炼丹题材的作品除了展示人类肯定生命、追求生命长存等积极意识外,还有些作品是借这一题材来表现个人的意念、个人的主观情感,有的作家如李白甚至赋予炼丹服药以更加积极的意义,把它看成是不同于孔子甚至是超越孔子的另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宗教内容而具有了隐喻的色彩和审美的意味,有的作家如白居易等在表现炼丹不成的苦恼或抒写对丹药的失望和矛盾心情时往往反映了人类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精神苦闷从而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作者还指出,唐代“有关神仙的题材成为各类艺术常见的表现内容,被赋予了独立的审美意义,神仙从而成为一种美学思想。”[2]124在作者看来,神仙思想的深层意识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于无限延续生命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中土思维重人生重现实的品格,各种文艺形式对这种意识的表现,有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学,更多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宗教信仰或纯粹以神仙和神仙世界为象征来表达的喻意,即除了对宗教的真诚企慕和赞叹之外,作家们更注重借神仙题材来抒发个人情志、或表达喻意,体现了人们对超越现实人生的理想境界的希冀和向往、体现了人们鄙视和否定现实名利、对抗现存体制和传统甚至希望从中解脱出来的愿望,这样,神仙和神仙世界就成为与现实对立的理想境界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同时,神仙幻想为艺术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家笔下所涉及的关于神仙的意念、题材、形象、典故、语汇、表现手法也就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地位的美学传统。作者甚至认为,真正的宗教文学作品艺术水平一般不高价值有限,真正有价值的是作家受到道教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融入自己思想感情后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在作者看来,唐代文人描绘宫观风景的幽美胜异,刻画出另一种生活情境抒写自己的感受,或表达对道教信仰的理解和仰慕,或将道观视为解脱人生拘束安顿身心的场所,或用道观来衬托尘世生活的卑下和不足依靠,为士大夫提供了另一种生活出路和生活方式,其风格相应地以高逸空灵和神秘奇异为主。作者还指出,内丹道的兴起尤其是心性修炼理论的完善使得文人把锻炼心性、隐逸以求志、放心而外物当作理想的人生境界并把它们表现于作品之中。作者还论述了三教调和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佛道世界观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超越现实的表现空间,佛道二教的人生观为文人表达生活体验人生感慨提供了新的更为开阔的内容,佛道二教的思维方式为文学提供了恢弘的想象力,佛道二教的宗教生活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题材,宗教经验使得作家对心性的抒发和表现更加深刻造就了富于兴象、感兴和韵味的抒情文学,佛道二教在语言、事典、文体、体裁等方面也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出世的超世的宗教在唐代文人那里变成了人生的、伦理的和美学的宗教。
正由于作者在历史描述中准确把握住了唐代道教文化、唐代文人宗教心态以及道教影响唐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所以作者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能够用科学的尺度揭示出作品的深刻内涵。作者对神仙术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的分析就堪称道教文学研究的典范。这主要体现为对经典作家和主要文学类型的分析和研究。前者主要涉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白居易等人。作者认为李白的神仙题材的作品主要体现三方面的内容:对生命、对某种理想的生活境界对精神自由的讴歌;表达对于现世环境、体制和人情世态等不如意的一切的激愤和批判;抒写现世不可居、仙界不可求的矛盾和苦闷。这都表明神仙观念被李白诗情化、并向积极的方向发挥,李白的神仙幻想和追求是热烈地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强烈地追求个人理想和个性得以发挥的更自由更广阔的空间。关于李贺是否相信道教神仙、其神仙题材反映了何种创作心态,学界曾有激烈的争论。孙先生有鉴于此,从钩稽基本的史料出发,认为李贺接触并熟悉道教及其神仙思想和炼丹方术并进行服食炼养活动,但李贺绝不是道教徒更不是坚定的神仙信仰者,神仙世界的描写证明了他的深刻的心理矛盾和深刻的现实孤愤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利用神仙题材来表达自己对世事和人生的感受和想法、抒发多样的体验和感情,神仙幻想造成了作者意识中极具悲剧意味的情结,这一情结激发了他艺术才能和创造的想象力,心中的神仙世界成为艺术创造的材料,并使作品获得了隐喻色彩。白居易是三教调和思想的典型,“他的宗教行为主要是实现‘独善’之志的一种方式,或者是经世志愿不能实现的精神寄托。这样,在他的内心深处,宗教信仰也就不可能认真和虔诚地确立起来。”[2]235他对道教的理解体现了洪州禅的平常心,“即在观念中和实践上极力使平凡的人生转化为神仙生活,把自己当成人世间的神仙。所谓神仙观念的‘世俗化’,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2]236他把道家道教的体道追求和享受人生的现实态度等同起来,他不相信长生久视、神仙飞升而代之以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乐天安命的生活追求,他对待道教的矛盾态度和言行体现了他立足于人生实际的宗教取向,宗教成了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于李商隐来说,有关仙人和神仙世界的传说、典故、语汇等等则主要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材料。他在作品中写到有关神仙的内容,基本上已没有本来的宗教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比附、隐喻、象征。”“他借用这些材料来表现自我、抒写自己的心迹,当然这种表现是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的。”[2]248从作品中可以知道:他接受道教主要是赞赏其内丹心性观念和做法而不是信仰神仙和追求成仙,他接触道士、女道士是风气使然并不表明他在宣扬神仙信仰,他对宗教生活的一定程度的向往和对待宗教的理性态度都是真实的,利用道教的修养和思维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段写出的作品往往别有寄托而不是宣扬道教神仙。总之,“神仙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主要是作为隐喻、象征而存在,是抒发情志的手段和依托;他们往往是借助于描绘另外一个美好的、超然的世界来和现世相对照;或是创造一个幻想的境界来表达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看法和企望。这样,神仙观念和神仙术作为唐代诗人喜用的题材,其美学的成分就大大超过信仰的成分,其艺术的意义也远远超越宗教的意义了。”[2]263
后者主要体现为文学类型的分析。作者对游仙诗作了分析,指出真正虔诚的道教信徒是难以写出好的神仙题材作品的,只有超出狭义的游仙主题的限制表现出更深一层的含义或寄托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曹唐“既具有道教生活的亲切体验,又有人生坎坷的经历,所以他能把修道的精神感受和人世间的真情实感融汇无间地结合起来,又能使用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技巧,在游仙题材的写作中开拓出新生面。”[2]280“大小《游仙》二者在旨趣和表达上又有共同处:仙人生活、仙界情景在这两组诗里都体现了诗人的人生感受、思想情绪;它们都被诗人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而这种种内容又借助艺术想象加以演绎、提炼、创新,描绘出生动的神仙形象和境界,抒写出鲜明、生动的诗情。”[2]287作者通过对涉道诗的分析指出,唐代文人笔下的道士分为御用型道士、仙道型道士、仙隐型道士和文人型道士,道士们的超凡、脱俗、飘逸不群、不受拘束的风神引发了文人的羡慕和神往,因而这类人在作品中往往具有“现实和幻想”、“真实和虚玄”相结合的特色,艺术上显得空灵、简净,多用想象、联想、象征的手法,创造神秘、静谧的情境;道院则被描写成另外一个远离尘嚣的理想境界,是摆脱世俗束缚、性灵得以舒展的地方,是一种新型的“洞天福地”;宫观生活为女道士提供了发挥文学创作才能的条件,她们兼具仙凡的地位和面貌为她们赢得了活动空间,也使得她们的生活兼有神秘和低俗、超逸和平庸的色彩,文人带着欣赏、同情、依恋、羡慕等感情描写她们的空灵与华艳之美,在赞赏中流露出感伤。作者还分析了小说中所反映的新型神仙传说,指出唐代文人的道教信仰由于艺术创作自觉的强化而进一步蜕化了,小说中的神仙尤其是地仙、谪仙形象表明神仙已经成为单纯的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对象;一些神仙小说的辅教色彩已经淡薄而政治意义和讽喻意义则更加突出,神仙世界已经成为作家表达讽喻的载体;神仙下凡和考验失败等神仙故事类型则表明道教神仙思想和神仙追求已经被现实享受彻底地腐蚀和破坏掉了。
(四)指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道教自身的发展趋势,道教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在描述和分析唐代道教文化与文学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提纯,指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道教自身的发展趋势,道教在唐代体显示出政治化、学理化、世俗化和美学化的倾向并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政治化的结果是,道士们以帝王臣民以至仆从的身份活动在朝廷从而使得士大夫有机会和他们进行广泛的结交和交流;学理化的结果是,增强了宗教对文人的影响但也表现出逸脱宗教信仰的倾向,从而使得许多唐代文人对道教的兴趣更多表现在对其学理尤其是《道德经》的倾服并进而去赞赏宣扬道家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世俗化的结果是宗教固有的神圣性、超越性逐渐蜕化,宗教被充实以平凡的人生内容并以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给文人提供了更多接触参与的机会并形之于作品之中;美学化是指道教的蜕化培养了人们对它的欣赏态度,道教被当作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对象的成分得到增强,涉及道教的文学创作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越来越高,其纯宗教信仰的意义相对地越来越小了。
三、古代小说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和诗学建构
孙逊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3]一书在内容上着重探讨了古代小说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和诗学建构,在方法上既注重史料的充分占有又注重思辨的缜密细致,以专题的形式凸现了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历史变迁。
(一)探讨了宗教在小说形成史上的作用
该书探讨了宗教在小说形成史上的作用。作者认为,前期古小说的作者为古巫、方士及方士化的儒生,巫术思想、神仙思想和鬼神思想为古小说提供了思想资源、人物形象、环境意象和结构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探讨了佛教论议、俗讲和转变等佛教说唱艺术向白话小说演变的轨迹,指出佛教讲唱艺术使话本走向世俗化(即帝王贵族的教育娱乐方式演变为直接面向世俗百姓的表演技艺,从戏说即片段性笑话谑语转向讲说富有人物情节的佛教、历史和民间传说故事),俗讲、转变的体制和讲唱语言直接影响了话本的体制和说话套语,佛道论议直接孕育了敦煌俗文学作品《茶酒论》、《晏子赋》、《孔子项橐相问书》、《燕子赋》等,其表达方式和文体特征一直流传于民间最后成了邓志谟创作争奇小说的传统资源。其中最为精彩的是对佛教说唱文学与话本、争奇小说体制渊源的辨析。如认为押座文、散座文与说唱开场诗、散场诗、法师开题与说话头回、转变配图与“画本”及“全相平话”、讲经文变文篇尾与话本题目之间存在着演变传承关系。认为论议存在四大体裁特征:其一,除开题竖义时的论述外其主体部分短兵相接采用具有强烈角色分工色彩的对话体或问答体;其二,因其表演性质而有通俗化与口语化的风格;其三,常用“问曰”、“答曰”、“难曰”、“答曰”等提示语组成一个小循环,再由若干小循环连缀成篇,由于表演方式是两人的论难由帝王裁决,故往往以仲裁者的插话为循环的起结;其四,为“频解圣颐”,故注重剧谈谑论,即充分运用民间的嘲谑体裁,喜作漫画式的形象描写,杂用协韵宽泛的四六骈句,在语辞上讲求铺陈夸饰、广征博引。此外,作者详细分析了敦煌俗文学作品和争奇小说的体制特征,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承继关系。
(二)指出小说在宗教意识和世俗情感的张力结构中传达了古人的人生哲学
该书注重在历史的变化和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古代小说的文化价值作纵横考察,指出小说在宗教意识和世俗情感的张力结构中传达了古人的人生哲学。该书指出早期小说充满着宗教思想后期小说的宗教观念则成了表达俗世情感的载体。古小说传达了浓厚的巫术现象和巫术观念,早期神仙小说倡扬的是道教的内修和外养,六朝志怪小说反映了古代的鬼神崇拜。作者指出:频繁出现于明清小说中的胡僧具有浓厚的性色彩,这种性色彩和道士味与六朝隋唐的胡僧无涉而与元代以来密教文化的广泛内传及密道文化的紧密交融密切相关。作者认为,明清小说中的性描写与道教房中文化密切相关,道教房中文化确立了性描写的话语方式和言词面貌,铸成了艳情小说宣淫成仙的结局模式,构拟了艳情小说独特的女性主题,这一主题主要体现为对性的赤裸追求、择偶标准向性剧烈倾斜、贞节观念彻底崩溃、女性成了宣泄者却不是受害者。该书还注重从历史的演变中梳理宗教观念向世俗情感的演变。如,认为古代遇仙小说经历了由汉魏六朝宗教化到隋唐世俗化再到明清的艳情化的历史变迁,既反映了人性意识的觉醒历程也折射了道教的世俗化历程。再如,作者认为,唐人小说中的仙妓合流现象跟历史无涉而主要与唐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跟文人狎妓经历密切相关,这种合流塑造了超逸而多情的女性新形象,提升了婚恋悲剧的格调,产生了与事功不朽观相对立的情感不朽观。再如,作者认为古代小说中的情僧在空与情(友情与性欲)的对立结构中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最终集成地造就了《红楼梦》中“情不情”的贾宝玉——一个伟大的情人和佛门的智者。
(三)注重宗教对古代小说诗学建构的贡献
该书还注重宗教对古代小说诗学建构的贡献。该书在一些章节中谈到古代小说中的宗教观念逐渐由内容淡化为一种形式而成了小说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遇仙小说模式在后来的小说中主要起组织全书结构推动情节的发展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宋元讲史平话中的阴阳五行说和因果报应说在历史小说的结构方面形成了封闭式的总体框架和前后呼应的情节脉络,即命定的循环的历史观不仅使封闭式的叙事结构首尾衔接而且使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具有总括全局的功能,阴阳五行说涉及的关于自然征兆与事实应验对照以及因果报应说的作业与果报之呼应都使情节脉络贯通前后呼应,自然现象与人事变迁、人物异相与人物命运的对应原则还影响到作家对自然景物隐喻性和人物肖像的重视;作者勾勒了因果报应思想及其形式特征在古代小说发展历程并进而指出了因果报应思想形式化对古代小说诗学的贡献,即因与果成了连接作品的两个端点从而为作品的内容的充分展开提供了完整的艺术框架、果报成了人物性格的先天规定性并作为一种富有特征的个性而构成鲜明艺术形象的基础、果报框架甚至成了一种传达激进主题的保护伞;“转世”和“谪降”模式是古代小说常见的两种结构模式,为古代小说提供了时空自由从而增加了小说容量和表现力,为古代小说提供了宗教关怀使小说拥有了哲学意味,为小说提供了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结构特点从而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形式美感。
[1]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2]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