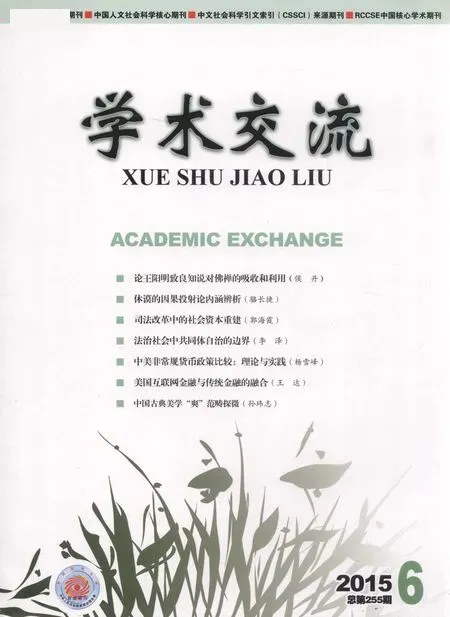中国古典美学“爽”范畴探微
孙玮志
(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1)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古典美学“爽”范畴探微
孙玮志
(广东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州 510631)
“爽”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范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种质素,发展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审美范畴。古代文人常常将“爽”作为文艺创作和人生追求的重要精神理念与审美准则来加以运用。而且“爽”范畴本身具有极大的粘合性和衍生力,又产生了许多与“爽”相关的子范畴。“爽”不仅被广泛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而且发展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精神理念和人生态度。研究“爽”范畴,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人在文艺创作中的审美准则,更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古人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的生命追求和价值选择。
爽;范畴;爽逸;生命追求
古代文人常常将“爽”作为文艺创作和人生追求的重要精神理念与审美准则之一,由之形成了“爽”这一审美范畴。而“爽”范畴本身具有极大的粘合性和衍生力,又产生了许多子范畴。在古典美学和文艺批评领域,除了单用“爽”字,还可以用爽逸、爽快、爽朗、豪爽、俊爽、清爽、爽利、明爽、爽直、舒爽、畅爽、爽健等合体范畴,或延用爽目、爽口、爽心、爽意、爽性、爽籁、爽曙以及爽然、爽爽、爽明、爽练、爽慧、爽异、爽悟等与之相关的名词和概念。这些范畴与概念共同构成了“爽”范畴的家族。“爽”范畴及其家族对于揭示古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爽”范畴的审美维度
爽是会意字,像人左右腋下有火,表示明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爽,明也”[1]70。《书·牧誓》曰:“时甲子昧爽”[2]204。《书·大诰》道:“爽邦由哲”[2]250。老子《道德经》有:“五味令人口爽”[3]118。《诗经》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4]84《左传·昭公元年》有:“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5]906《左传·昭公三年》曰:“二惠竞爽犹可。”[5]937《列子·黄帝》有:“昏然五情爽惑。”[6]33可见,在这些中华元典中,“爽”的几重意思都出现了。一方面,它作为形容词,有“明亮”“清爽”“豪放”等意思;另一方面,它作为动词,又有“差错”“违背、触犯”“伤害、破坏”“迷惑、迷惘”等意思。本文探讨作为古典美学范畴的“爽”,只探讨它作为形容词的那几重含义及其历史嬗变。“爽”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文艺创作和人生追求的诸多精神理念与审美准则之一,跟它同时具备多种审美质素密切相关。在我国古典美学中,不少范畴在独具特色的同时又形成了极大的张力,显现出开放性格局,不断衍生出多种审美质素。“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审美范畴,它兼具了“力度之美”“色调之美”“形态之美”等多种审美质素,形成枝繁叶茂的“爽”范畴家族,蔚为大观。
“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审美领域,展现在大量的诗评画论、人物品藻中。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评人物,就使用了“爽”及其后续范畴和合体范畴:“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7]99“济虽俊爽,自视缺然。”[7]192“瞻弟孚,爽朗多所遗。”[7]196“‘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7]243“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7]288“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7]290刘勰《文心雕龙》品评诗文及其作者,也使用了“爽”及其后续范畴和合体范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8]243“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8]1048“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8]1530“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8]1586可见,从一开始,“爽”范畴的使用就非常灵活,可单用,可延用,可以品评人物,也可以品评诗文,是一个衍生能力非常强,且贯通文艺批评和人物品藻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审美范畴。
到了唐代,“爽”范畴保持着郁勃旺盛的生命力,各种文艺理论中对它的使用更加频繁,也更加灵活多变。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风格爽举,不顾常流。”[9]110“神爽精诣,俯盼桃树。”[9]119“风力爽俊。”[9]135“笔迹超越,爽俊不凡。”[9]137“萧大连,字仁靖,简文帝第五子。少俊爽风流,有巧思。”[9]146“笔力爽利,风采不凡。”[9]174“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9]178“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9]191“杨公南,名炎,华阴人。孝著三代,门树六阙。风骨俊秀,神情爽迈。”[9]196既评论人物,也评论画作。“爽”的主语,往往是神、气、情、意等从人物身上或者从艺术作品中散溢而出的精神状态。古人相信作品所反映的精神风貌和人物的精神气质直接相关,因此,许多古典审美范畴具有了兼评人物和作品的功能,“爽”范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弘法大师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也使用了“爽”范畴:“兴发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皆须身在意中。”[10]1329“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10]1394“揽茕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10]1666一方面,“爽”范畴的家族不断扩大,被延用得越来越多,其各种审美质素不断被挖掘出来;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常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后续范畴和合体范畴,如“清爽”“爽朗”“爽俊”“豪爽”等。
到了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第一次以“诗话”命名,带动了这一特殊的文艺理论题材的繁荣发展。在他之后,出现了大批诗话,而“爽”范畴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这些诗话当中。如蔡启《蔡宽夫诗话》评价杜正献的草书“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气”[11]626,既评人也评书。严羽《沧浪诗话》有:“先生当于此时,耀神爽于云霄。”[11]2195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有:“虽造语粗浅,然亦豪爽也。”[11]1217蔡绦《西清诗话》有:“太白历见司马子微、谢自然、贺知章,或以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11]249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郭熙的《林泉高致》第一次提出了涉及“爽”范畴的审美特质及其重要作用的明确论述:“柳子厚善论为文,余以为不止于文。万事有诀,尽当如是,况于画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汨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挑之者,其形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出,然可与明者道。”[12]574在这段文字中,郭熙论述了作者的精神状态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作者必须有明朗专注的精神和勤快稳重的心气。“其状黯猥而不爽”,说明“爽”是与“昏暗卑下”对立的“明朗高迈”;“不爽则失潇洒法”,说明“爽”具有健捷流动、潇洒无拘的特点。而“不爽”,在郭熙看来,是“作者之大病”之一,说明他对于“爽”这一审美范畴的重视程度。郭熙对于“爽”范畴审美质素的挖掘和发现,对我们是极大的启发。
到了元明清时期,对于“爽”范畴的使用更加灵活多变,也更加频繁。“爽”范畴的审美质素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发现。谢榛《四溟诗话》中,评李太白诗“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和王摩诘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林啭黄鹂”为“爽健”[13]1325,评梁朝简文帝《纳凉》诗“游鱼吹水沫,神蔡上荷心”以“蔡”入诗欠“明爽”[13]1367。俞弁《逸老堂诗话》评唐子畏诗:“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初我做陶丞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语意新奇,如醉后啖一蛤蜊,颇觉爽口。”[13]1237杨慎《升庵诗话》评李嘉祐诗:“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楼。南风不用蒲葵扇,纱帽闲眠对水鸥。”“使人神爽。”[13]927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集中论述了“诗三义”中的“比兴”与“爽”的关系:“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13]482李东阳认为,使用比兴的手法托物寓情,能达到意蕴无穷的效果,然后“神爽飞动”,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自觉”。“神爽飞动”正如上文所说,“爽”范畴是对于神、气、情、思等精神气质的描述,而“爽”是超越了阻滞和穷尽,气息流动、神采飞扬的。李东阳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爽”范畴的审美质素提供了启发。
稍后于李东阳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亦多涉及“爽”范畴,他评桓灵宝的诗“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为爽俊[13]1907,评王翰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为“爽”[13]1928,评苏轼之文为“爽而俊”[13]1931,评王伯安文“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13]1943,评李兵之诗“通爽”[13]1950。此外,又有“高爽奇逸”[13]1960“雄爽流畅”[13]1967等语,可见在王世贞看来,“爽”具有“简约”“雄健”“通透”等质素,和俞弁《逸老堂诗话》评唐子畏诗“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初我做陶丞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语意新奇,如醉后啖一蛤蜊,颇觉爽口”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世贞评王伯安文“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都涉及了味觉,说明“爽”不仅调动情意、牵动视觉和听觉,还触动了味觉,产生了通感的效果,使得“爽”这一审美范畴更加活泼生动。李渔《闲情偶寄》在“贵浅显”一节中评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等语“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14]34,这说明在李渔看来,“爽”还具有“自然浑成”的审美质素。
可见,“爽”范畴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嬗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获得新的质素。其“力度之美”“色调之美”“形态之美”等多方面的审美质素,形成枝繁叶茂的“爽”范畴家族,蔚为大观。其审美内核始终坚守了超越阻滞和有限、追求自由和无限、追求郁勃生命力的精神向度。
二、“爽”范畴的审美质素
作为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爽”范畴的后续及合体范畴很多,与其内涵关系最近的主要有以下三种关系,分别反映了“爽”范畴的“力度之美”“色调之美”“形态之美”等多方面审美质素。
首先是“力度之美”——“豪爽”。古人进行艺术创作十分注重力度的美感,书法创作要求有“骨力”,颜真卿的书法就被公认为“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而在诗文创作领域,则历来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大审美风格,其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力度的强弱。“爽”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广泛使用,经常缘于其“力度之美”这方面的质素,典型代表是“豪爽”,其余类似的还有“劲爽”“爽健”“爽直”等被延用的范畴。它们的共同指向是“强劲刚健,超迈不群”这一审美质素。这种“力”当然不是死力、蛮力和暴力,而是神旺气足、自然散溢的生命力。白居易举刘禹锡为“诗豪”,就因为其诗歌具有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的特点,他称:“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文心雕龙》二十八谈“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8]1047认为诗文有风骨,才会“意气骏爽”“刚健”,否则“负声无力”。文章没有力度,就像鸟不会运用自己的翅膀难以飞翔一样。可见“爽”范畴的“力度之美”历来颇受重视。
其次是“色调之美”——“爽朗”。与此相关的还有“明爽”。“爽”的本义就是明亮。明亮的色调给人一种明快简洁、清晰无杂质的感觉,进而引发人产生积极明朗的情感联想。反之,具有积极明朗的情感基调,也能让人联想起明亮爽洁的色调。因此,“爽”在文艺批评领域,往往用来评价那些具有明快简洁、豪放有力的文学作品,如桓灵宝的诗“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被评为“爽俊”,王翰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被评为“爽”,苏轼之文被评为“爽而俊”。除了诗文领域,“爽朗”范畴也在人物品藻方面有广泛应用。中国历来有崇尚君子人格素养的传统。《论语》当中就有许多论及君子的言说,“君子坦荡荡”[15]81“君子和而不同”[15]157“君子喻于义”[15]36等,都说明君子具有坦荡清白的品质。这一点,跟“爽”的色调之美——“爽朗”是相通的。君子是爽朗清白的,既不消沉灰暗,也不繁乱复杂,而是像清晰无杂质的明朗色调一样,具有导人向上的精神力量。此外,在中国历史上,“和”“雅正”等风格的诗文一直占据正统地位,而“奇险”“哀靡”风格的则处于边缘地带。这与中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有关,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大都以团圆结束,崇尚月圆、完美、和谐,不平衡、不对称、奇异因为其不明朗、不清晰而受到排斥。这说明无论是“爽朗”之人,还是“爽朗”之作,都更加符合中国人普遍的审美理想。
最后是“形态之美”——“清爽”。与此相类似的范畴还有“舒爽”“畅爽”。这些范畴都具有“轻捷通透”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藻十分流行,除了对人物的精神状态进行品评,还经常对人物的外貌形态进行品评。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就评桓温为“高爽”,评嵇康为“爽朗”,评王武子为“俊爽”等。此外,魏晋人物为排解精神上的痛苦,往往吃药、喝酒,为了散热又穿着宽袍大袖,服饰也有飘逸通透的特点。可以说,“清爽”的形态之美,在魏晋时期广受推崇。此外,“清爽”的诗文风格也在此时得到极大发展。其中,以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尤为“清爽”。他们的诗歌都以自然山水和闲适生活为主要抒写对象,风格上具有自然清新、舒爽明畅的特点。如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都具有简洁清新、轻灵通透、自然天成的特点,读来令人忘俗。
可见,“爽”范畴的审美质素,是从不同方面一起发展起来的,这种情况造成了“爽”范畴内涵的极大丰富性,也给了它旺盛的生命力。
三、“爽”范畴的审美特征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爽”范畴具有多重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普遍性特征,即蕴涵的中国文学范畴的共性,如模糊性、多义性、家族群体性等;另一方面是它的个体特征,即它自身独有的、本质性的个性,如多维性、精神性、动态性特征等。
第一是“爽”的多义性特征。在我国古典美学中,具有多义性的范畴数量众多,相反,只有一个涵义的审美范畴几乎不存在。但是,像“爽”范畴这样具有歧义性、多维性特征的,就要少得多了。如前文所论述的,“爽”范畴同时涵括了“力度之美”“色调之美”“形态之美”至少三个方面的审美质素。这使得“爽”范畴历来活泼生动、富有生命力。因此,“爽”范畴的粘合性和兼通性非常强,具有很强的衍生能力,逐渐形成了爽快、爽朗、豪爽、俊爽、清爽、爽利、明爽、爽直、舒爽、畅爽、爽健等合体范畴以及爽目、爽口、爽心悦目、爽意、爽性、爽籁、爽曙、爽然、爽爽、爽明、爽练、爽慧、爽异、爽悟等相关的概念和名词。其使用领域不仅遍及神、气、情、意、心这些精神领域,也跨越到目、口等外在感官。这在我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中是比较少见的,一般的审美范畴只关涉内在的精神领域。直到现在,“爽”还经常被挂在嘴边脱口而出,既可以用来表示精神状态的明朗舒畅、运动过程的顺畅快捷,也可以用来表示某些食物的冰凉口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许多古典美学范畴如“古”“婉”“逸”“高”“拙”等只存活于古代文艺理论中而匿迹于现实生活了,而“爽”却散发出越来越强健的生命活力,活跃于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兼有传统积淀和现代活力的审美范畴。也许将来“爽”范畴还会产生新的含义,衍生新的用法。
第二是“爽”的精神性特征。“爽”的审美价值,不只是对一种文艺作品风格的追求,而且是对一种自然清新、舒畅通透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界的追求。中国文人和艺术家所崇尚的“爽”,最终指向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神气之爽、情意之爽。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当时政治混乱、社会黑暗,到处充满阴谋诡计和血腥暴力,人的生命脆弱不堪。生于如此乱世之中,清醒的文人士大夫们痛苦不已,常有“穷途末路”之感。阮籍经常驾车外出,毫无目的地赶路,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方,就放声大哭。阮籍的穷途之哭,代表了当时文人一种普遍的痛苦的精神状态。现实的阻滞和困苦让他们渴望寻求超越和解脱,达到精神上的自由畅通。“爽”范畴在此时进入审美领域,就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藻,多用“高爽”“俊爽”“爽朗”等范畴,如评嵇康为“爽朗”,评王武子为“俊爽”等。可见,当时“爽”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主动追求、自觉推崇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界。俗世的污浊和现实的阻滞,使清醒而痛苦的人寻求到“爽”这一审美范畴,并发掘其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种生命追求。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审美范畴,除了“爽”范畴,还有“远”“清”“通”“畅”“达”等。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这些审美范畴具有某些相同或者类似的审美质素,比如“自然清新”“舒畅通透”等。这不是偶然的,这正好体现了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局势和社会现实之下文人士大夫们的生命取向和价值选择——一种自由超脱、自然清新的生命状态。唐代李白的洒脱俊爽、宋代苏轼的豪迈爽朗以及历朝历代都有的崇尚自然清爽之风,无不体现“爽”审美范畴对于古代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重大影响。
第三是“爽”的动态性特征。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循环不已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僵化的实体。“道”“气”“象”“虚”“实”“大”等中国古典美学元范畴就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但是,“爽”范畴更加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其动态性特征。其“自然清新”和“舒畅通透”的审美质素,体现的就是一种流动的、散溢的生命过程。“爽”的本义是明亮,而明亮的色调给人一种膨胀、扩散的感觉,对比起黯淡色调给人的静寂感觉,明亮的色调是运动的,包孕着运动发展的无限可能。后来“爽”范畴又发展出“开朗”“清新”“豪放”等意思,同样着重发展其动态性特征,是对外开放、流通的,充满了舒畅自如的力度之美。这种动态性特征,根源于“爽”范畴对于天地自然状态的回归。现实的滞碍令文人士大夫们渴望效仿天道,达到自由超越、舒畅自如、气息流通、生生不息的生命境界。一方面,他们固然求静——远离俗世、隐居山林;另一方面,他们也尚动,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修养身心,都注重气息流动和回合变化,讲究虚实相生。他们所排斥的,不是动,而是毫无意义的骚动和损害身心的蛮力。所以,“爽”范畴的内涵,既有清澈通透的“清爽”之义、高蹈远举的“俊爽”之义、明亮清晰的“爽朗”之义,也有气息流通的“舒爽”之义。这些具体含义,虽然差异很大,但无不体现出超越现实的维度。这种维度使得古代文人士大夫具有了摆脱俗世纷扰的动力和方向。这也是“爽”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不断丰富、保持着郁勃生命力的原因。
总之,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爽”范畴在古代文艺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发挥,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的艺术和哲学中,自然天地无处不体现出流动畅通、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爽”范畴体现了这种效法天地自然的鲜活生命力。通过舒展生命、散溢精神、飞扬意气,中国的文人和艺术家们找到了突破现实中的滞碍和荡涤尘世中的污浊的动力和方向,在更加自由舒畅的精神境界中,实现了审美的人生。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王秀梅.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景中.列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南朝宋]刘义庆.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南朝梁]刘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10]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
[12][宋]郭熙.林泉高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13]周维德.全明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5.
[14][清]李渔.闲情偶寄[M].杜书瀛,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曹金钟〕
I227
A
1000-8284(2015)06-0186-05
2015-02-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逸’范畴的审美空间研究”(12BZW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发展研究”(GD13XZW 19)
孙玮志(1977-),男,河北徐水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