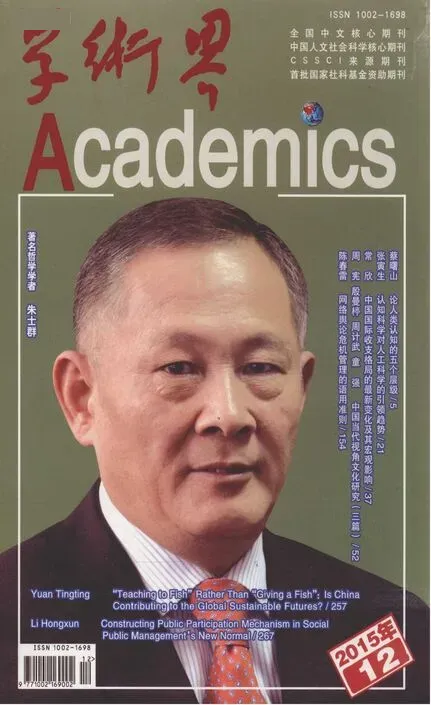20世纪30、40年代王献唐的史学生成论析
○李宝祥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一生治音韵、金石、文字、历史、考古、版本目录等领域,成就斐然,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目前学界对王献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并且不断深入。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对王献唐的学术进行探讨,对于王献唐重要学术组成的史学缺乏宏观的系统梳理和论证。随着王献唐往来书札的整理出版,王献唐日记的发掘,这位国学大师的史学成就更为明晰地显现于学界。学术的生成往往与学者的地理和生活环境密切关联,王献唐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从地理生活环境的变动及其对学术研究影响的视角来看,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段,即在济南执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和南下寓居四川时期。笔者无意对其史学成就作全面论评,现依据王献唐日记和往来书札等第一手资料,再结合王献唐的史著文本,对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生成理路作一剖析,尚祈方家正之。
一、王献唐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史学研究的起步和进展
1929年8月,在丁惟汾的举荐和何思源的招引下,王献唐入主山东省立图书馆,这成为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重大转折点。此后,在山东省立图书馆这一学术重镇里,他坐拥书城,搜集乡邦文献,广罗文博,在一个极为优越的学术环境里推进了自身在音韵学、版本目录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被学界瞩目和认可。就史学研究而言,王献唐的开端之作是写于1934年的《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两篇专文,撰文的缘起是他代表山东省立图书馆所收罗的14件春秋邾国彝器。1933年4月,王献唐接山东省政府通知,前往滕县洽谈新出土器物事宜。他在4月10日记:“寓滕七日,日跋涉于原隄阡陌之间,既获周代孟氏礼器十四事,目见耳闻,皆断石零金,偏于古器物为多,因别署此七日日记为《滕邑访古记》。”〔1〕在滕县,他前后驻留7日,经多方交涉,终使文物完整运抵济南。这些珍贵的邾国彝器收归山东省立图书馆,可谓理想的安置,也为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据王献唐日记可知,10月12、13日,他检阅《邹县志》《滕志》,画邾国疆域图,为撰写作相关的准备工作。14日,他开始撰写《邾国地名考》,同日《邾邑考》也起笔了。自15日至25日的时间段中,王献唐专注于《邾邑考》,对它进行了补充修订,并绘制《二邾疆域图》。26日,他查阅《尚书》《绎史》诸书,拟定写题《邾分三国考》。自27日始,他致力于《邾分三国考》的写作,11月20日写毕,交由屈万里清写。从22日开始王献唐即倾注精力写《三邾疆邑图考》篇,于1934年初完成了修订。3月,栾调甫主持编订了《国学汇编》,将《春秋邾分三国考》收录其中。
在《春秋邾分三国考》序中,王献唐述成文始末,“今岁滕县安上村,出土邾国彝器十四事:鼎二、敦四、盘匜罍壶各二,类有文字,归山东省立图书馆。余既亲与其事,拟撰专书问世。书中有文凡七篇:为彝器出土始末记、文字考释、器制考、邾分三国考、三邾史迹考、三邾疆邑图考。调甫主编国学汇编,索稿于余,旧作积置,一时未能爬梳,适草此篇,即以付之”〔2〕,王献唐对相关史籍稔熟于心,驾驭自如。将音韵学的学术功底应用于史实的考证是此文一特色。如他考证三邾中“滥”之得名,认为:“邾音后转若婁,因呼为婁。婁纽转滥,沿称为滥,此滥名之所由起也。单言为邾、为婁、为滥,连绵则为邾婁、为邾滥。”〔3〕王献唐对音韵学的推重和自觉运用也揭示出这一领域的成就在其学术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学者曾论及:“音韵学是王献唐小学研究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之开端与基础。”〔4〕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延伸应用到了他的史学研究领域,音韵学方法成为王献唐构建史学的重要理路。
王献唐历史考证的精深特质,藉此《春秋邾分三国考》初现端倪。他依据邾国彝器,结合传世文献,考证出邾国自周宣王之后陆续三分为邾国、小邾国和滥国,并将三邾三分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极为详尽,从而改变了先前典籍所记三邾史实断续、零碎的状况。他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中所展现的学术功力,有学者作了如此论评:“由《邾分》一文来看,其文献之谙熟、史实源流分析之精当,视史学名家亦不稍逊。”〔5〕此评可谓精辟入里。
《三邾疆邑图考》是《春秋邾分三国考》的姊妹篇,作者依据各种传世文献,运用音韵文字学理论,并参照金文陶文,系统地考证了漷水的数度变迁和邾邑可考者的古名今地。王献唐在文中论其考证之法,“要以当时之史事地势,后代之音理文字,参以金文陶文,略无乖舛,即可取测。”〔6〕由此窥知,音韵文字学是王献唐推崇并施用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他在文中多次采用音韵学的实例。如考查漷水流经过的相关地名,作了如是论述:“郭音近通用,郛从孚声,古读重唇,郭以通用,知古纽同郛字读如部。今水道经行之东傅庄、西傅庄,傅部同音,疑指漷言,谓东漷庄、西漷庄也。水之上流有固上村,因漷同音,疑即漷,上言漷之上游。水之下流入泗处有郭营,疑为漷营。”〔7〕又如,在举证“鞋”与“薛”的音近关系及“鞋城”的由来时,提到:“鞋古读如靴,与薛音近而讹。滕地别有薛城,邑人不疑为薛,相承不改,亦或恐与薛城重名,指称不便,以音近之鞋城当之,藉资为别。”〔8〕再如,王献唐认为古语发声分急声和漫声,方言有地域习俗的特点。“方土语言,随习而异。漫声连举为邾婁,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婁,訾婁亦为其一例,连绵字时或如此也。”〔9〕这就指出了“邹”“邾”“婁”“邾婁”“訾婁”不同音读的由来。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中,王献唐所用音韵学的案例较少,显得相对单薄。与此状不同的是,《三邾疆邑图考》则大量使用音韵学的实例,明显丰实了许多。
由《春秋邾分三国考》之序可知,王献唐最初计划对邾国彝器的相关研究拟定了七个专题,较为系统和完整。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邾国地名考》《邾邑考》的写作,但这两个题名与原先设想有异。由于各种原因,时至今日,《邾国地名考》《邾邑考》还没有形成印本公诸学界,致使其真实面貌,很难窥探了。
对于《春秋邾分三国考》,王献唐并不满意。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人的学术求精意识,二是因为他设计的相关专题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在1934年3月23日致柳诒徵书函中言:“外上鄙著《邾分三国考》一册,希交贵馆,不足存也。专上,并请道绥。弟王献唐顿首。三月二十三日。”〔10〕不过,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写成后,王献唐不辍笔墨,继续他未竟的专题探索。1934年初,在《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定稿后不久,王献唐即开始了《炎黄氏族文化考》的撰写,这样很快弥补了他的缺憾。
《炎黄氏族文化考》是一部考辨中国上古文明起源和史实的著作。在著述中,王献唐对当时所掌握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据此作了扩展和创新。1933年,蒙文通所著《古史甄微》一书出版,其中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王献唐的关注,因此他对《古史甄微》进行了认真研读。1934年10月22日记:“偶检近人蒙文通《古史甄微》,分炎黄二族,说与余合。又分伏羲为一族。余初本有此见,证据渺茫,未敢确定也。蒙书亦有启发处,稍嫌粗略,其方法与余完全不同,亦少系统,在近日出版界中究是有思想,有创作力之作品,其人为廖季弟子,经学家法,甚有根底,此其所长也。”〔11〕蒙文通认为上古民族应以地域划分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系,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对于伏羲为一族之说,王献唐以证据不足,不予确定。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力主东方为上古时代政治文化中心,其文云:“神农自陈徙鲁。鲁有大庭氏之库。是在昔为大庭之都。有巢氏治石楼山在琅琊。皆足见东方固政治战争之中心。为上世我先民之所聚处。河洛之繁荣乃在后。远不足与侔也。”〔12〕以东方为上古时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观点,为王献唐所认同。但是,蒙文通对东方地位的论述失之简略,没有详尽地展开,这是一大缺憾。《岭表纪蛮》是王献唐关注的另一部著作,由刘锡蕃所作的这部民族史著作在1934年印行问世。它记述了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的族源、风俗习惯、经济、文化发展等。特别阐述了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渊源关系。它设“汉蛮同族之十大证据”专章,从姓氏、干支、言语、祀典、契券等方面来论证汉蛮同族,这对王献唐不无启示,1934年10月22日记:“读《岭表纪蛮》毕。此书颇与余著《炎黄氏族考》有密切关系,于中获新证甚多。亦近来出版界中之一等书也。”〔13〕
作为一部未及杀青之作,《炎黄氏族文化考》在公示于学界之后,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它是对《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的拓展和深入,其第一篇就以“炎、黄二族之分野与三族氏族”专题,此下又设“三邾土著为东夷炎族”和“三邾氏族之分布”论题,这也足见对邾国彝器学术研究的延续性。王献唐在1936年所作《访碑图诗》中提到了这一点,“前年为图书馆收得滕邑三邾彝器,因考邾族,知三代华夷之界,即炎黄二族之别。更知震旦文教,占分炎黄二支。类聚群分,条理秩然。乃草《炎黄氏族文化考》,已得三十万言,期以三年成之。自谓凿破混茫,前所未有。偶为人言,辄哑然不信。”〔14〕王献唐在书中提出了大胆的创见,偶尔向别人提起时,鲜有认可者。事实上,他的一些论断,极具学术价值。如王献唐力主“民族”是解读上古文化的重要途径:“故欲研求古代文化,必以民族为骨干。民族不同,文化亦不同。年代愈晚,文化之界限愈溷;年代愈早,文化之界限愈清。”〔15〕此言堪称经典宏论,无可置疑。在此书中,王献唐提出,中国的文化虽属于炎黄二族,但主要是炎族,即夷族文化。欲求远古夷族文化,其中心就在山东。他主张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以泰山为中心,形成了东方的伏羲文化圈。文云:“证以礼制,明以习俗,征诸故书所载,泰山一带,为中国原始民族聚居之所,已无疑义。……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16〕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聚集于东方,主张东方是上古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由此而论,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所作出的论断,具有相当的学术预见性和前瞻性。
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他延续了音韵学的学术路数,在给齐鲁大学的演讲中明示了这一点。1934年11月,王献唐接受了齐鲁大学历史系的演讲约请,讲题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不久之后出版的《齐大旬刊》对相关内容做了如是报道:“历史系于十一月三日,敬请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来校演讲,讲题‘中国古代文化的新途径’。讲词大意,中国古代文化有空间性之不同,考其不同之原因,固与地方风土有关,然其根本原因,则在民族之不同。中国古代有二大民族,一曰炎族,二曰黄族。……概自周以后,吾人所知见之中国古代文化,皆二族之混合文化,二族文化自夏商二代,开始接触,至周乃产生此新文化。……研究民族之异同,有赖于民族谱系之书及地名之考究。尤须于小学与音韵学方面,先行着手也。王先生演讲引证精确,立论新颖,听众均甚称赞云赞云。”〔17〕诚如王献唐所主张的“尤须于小学与音韵学方面,先行着手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他大量地运用了音韵学的案例来梳理上古炎黄时代的历史,力图还原真实的情状。如王献唐辨析“夷”之音义时,指出:“夷隶脂部,古读若侧,为最初之本音。迟夷同音通用,迟读舌尖如侧,知夷亦然。”〔18〕他考证“舟”是炎族的发明,并指出“舟”“船”的音义关系,“舟读舌尖,与朱同纽,由侯转出者也。舟亦转船,船亦出朱,古言舟,今言船。其以船为循,谓船沿流而下者,皆后起义也。邾娄可单名邾,故船亦称俞,称舟,又可连名邾娄,故船亦称舳舻。此尤制出炎族之铁证。”〔19〕
在此著作中,王献唐将音韵学实例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音韵学例证的使用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音韵学的案例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在音韵学之外,王献唐还容纳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来构建史作。但是,音韵学在所有应用方法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可以想见的是,无音韵学之法,则《炎黄氏族文化考》不能行文,难以成书了。当然,此作是王献唐科学学术方法和博通史籍相融合的硕果。考辨史料,融会贯通的学术积淀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执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王献唐在史学研究领域起步。它由《春秋邾分三国考》篇肇始〔20〕,《三邾疆邑图考》篇继其后,至《炎黄氏族文化考》已成宏富巨著,蔚为大观了。在王献唐的学术体系中,史学领域的探索晚出于音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等学科研究。但是,研究伊始,并无稚拙之状,而是显现出了相当的成熟性、科学性。这种成就的取得,与他先前的学术积累有着莫大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学方法在王献唐20世纪3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它的应用,由点到面,愈加广泛和深入。另外,他本人博览群籍,会同融合的丰厚学术根底也是有力的促成因素。
二、王献唐居川时期的史学构建和创获
抗战军兴,政局骤变,打破了王献唐以山东省立图书馆为阵地整理乡邦文献、致力学术研究的状况。为了存护珍贵典籍文博,延续齐鲁文脉,1937年11月27日,他携馆中同仁屈万里、工友李义贵从曲阜出发,护书南下。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1938年2月抵达四川万县。此后,又经历了乐山、重庆等居所的变迁。1943年3月至抗日战争结束前,他借住于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
王献唐在四川的史学成就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为代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需要广博的资料,搜集购买资料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在他学术开展受到制约之时,傅斯年及时施以援手。其因由在于,王献唐就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时期,与傅斯年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形成了亲密和谐的学术关系。两学人间不乏书札论学、面晤畅谈之情状,相互引对方为学术知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山东省政府合组了山东古迹研究会,进行考古发掘,王献唐身任秘书,他的作为被傅斯年极度认可。在挚友处于经济困境的时候,傅斯年的支持是自然和合理的。1938年,傅斯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王献唐争取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助,依托武汉大学名义进行研究,得到了每月200元的最高资助额度。王献唐在10月18日记:“余隶人文科学科,月薪二百元,此项乃中英庚款会提出一部份款项,资助学术人员继续研究学术,意甚善也。当取简章一份,又交予请款书件、支款凭单,嘱由保证人签署再支款,共八、九两月四百元,即至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晤孟真,请其为保证人。至研究地点规定在嘉定,亦请孟真办理。”〔21〕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资助人员的发薪自8月份开始,傅斯年不但为王献唐受助一事融通,还做了他的保证人,这对于推动他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此,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撑。他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为学术方向,勤力研究,不断将相关成果提交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研究进度,接受考核。1940年6月25日记:“日前武汉大学转来庚款会函,嘱将本年研究结果作成总报告寄去,即起草,至午后四时毕。旋清缮,晚九时许竣事,即作函送武大,附还原件。”〔22〕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受赞助学人的学术成果进展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以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支持。无疑,王献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了认可,他持续不断地接受资助,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著,这成为王献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图书季刊》新第五卷第四期关于王献唐的报道中提到:“王献唐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之著作,……前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君献唐,十五年来即从事古代货币之研究;其着手撰述则始自民国二十九年。所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暂以金属货币为限,起自有周,断于西汉之末,计已成五十余万言。……王君现正在从事以上各篇增补改订之工作。预计一年后全书即可杀青。”〔23〕如是介绍,使学界对《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英庚款董事会在经济上的赞助是《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能够成形的外在条件。对“古代货币”这一专题的选定则根源于王献唐的金石学积淀。在撰写此作之前,王献唐已经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累计作成了金石学领域的单文百余篇和著作数部,奠定了他作为金石学名家的地位。他在主掌山东省立图书馆时期,多方搜集整理古代货币,积累了丰富的货币资料,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了《古代货币甄微》。对古代货币的研究称为古泉学,是金石学的一部分。金石学是文献史学的组成部分,它本身与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马衡在给金石学所下的定义指出了这一点,“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24〕金石学的研究可以裨益于史学,由金石学导向史学研究并无太大障碍。但是,金石学家未必能成为史学家,史学家或许罕涉金石,二者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和要求,金石学的研究偏于录著和考释,对历史的研究狭窄有限。史学家则要利用史籍文献、遗存实物等资料加以融会贯通,以解释前后过程,分析来龙去脉,作的是综合系统的研究。王献唐以金石学的学术基础和史学的视角考察古代货币源流、形制,揭橥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撰成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这一史学巨作。
1946年底,《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基本完成。不过,它的最早出版是在1979年,由齐鲁书社印行于世。全书约50万字,计分:周币、秦币、汉初货币、武帝货币及铸钱技工之演变五篇。在研究方法方面,此著运用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法,书中采用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币制的形制、源流和制作,展现了中国灿烂悠久的货币文化。王文耀先生在《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整理说明》中指出:“王献唐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典籍文献,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货币详加考订,把考古学与史料学、考据学与校勘学、文字学与音韵学紧密结合起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系统完整、内涵丰富、层次性强、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货币研究体系。本书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经济史、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评论可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范例。
20世纪40年代,王献唐著述的《国史金石志稿》〔25〕是他史学研究的又一扛鼎力作。1945年8月,王献唐在《金石志稿金文部门编讫总报告》提及:“金石志稿,为中华民国史一部分,故其取材,以民国出土金石,及清人或以前各家未节录者为限。”〔26〕《国史金石志稿》是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是从考察民国金石学成就的视角来撰写的,金石器物的搜集以及金石学的学术收获是王献唐撰写的前提。这一史著的由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学术活动的参与。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内迁,文化学术事业受到重大冲击。其中,档案整理工作需要重建。1939年1月,张继、吴敬恒、邹鲁等向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建立档案总库国史馆案”,获得了通过。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将党史编纂委员会改名为国史编纂委员会,并设立国史馆筹备处。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始告完成。当时的王献唐正埋首于《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撰写,还身负保护齐鲁文博的重任,本无意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但在时任主任委员的故交张继多次的诚意邀请下,他难以推脱,才应允助力。1940年3月,王献唐成为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出任了副总干事和第一组主任,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职责。在此期间,他出席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一些重要会议,同张继和但焘、朱希祖等协商组织办法,筹划解决会务事宜,还多渠道购买搜集民国史料,为自身的职责躬行而为,不遗余力。
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期间,王献唐与学术文化界的名流但焘、朱希祖、金毓黻、蒋逸雪等有着频繁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互动。这样一个活跃有力的学术环境,大大激发了他的学术研究欲望,他以《国史金石志稿》的编纂献力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学术进展,同时也推助了自身的史学研究。此时《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尚未完成,《国史金石志稿》又予以着笔。这样,王献唐有时同日中兼做两部著作,如他在1944年6月15日记:“写《国史金石志》第三期稿,从盘匜起。……午饭后,检阅各书,增补《钱考》二条。至贞一处查书,回写《志稿》。”〔27〕又如他在8月23日记:“八时起。致庚款会一函。拟取回已送去之《钱考》八册,通盘整理,并托次箫代取。近闻该会奉令将结束矣。……点校《钱考》。……午饭后,小睡。仍点校《志稿》。……晚饭后,至彦堂处,与萧君闲谈。回校《钱考》。”〔28〕
学术自觉性和使命意识使王献唐在撰著《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的同时,勤力专注于《国史金石志稿》的著述。他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所获薪俸有力地支撑着学术研究。他就职期间得到过加薪,1944年7月27日记:“又接菊田函,自四月份起每石米代金为三千七百元,自五月份起薪俸加两倍,补助费加七百元;因自四月份补发各费,截至六月止,共一万五百余元,已交交行汇出。”〔29〕12月13日记:“又接菊田函。汇来万七千八百余元。自十一月份起,薪俸补助费等连前共加至十六倍,是月即增发六千三百元,合十月份代金,共如上数。”〔30〕这种加薪固然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幅度的加薪也证明王献唐的工作和研究得到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的认可。王献唐还不定期地撰写《国史金石志稿》进展报告书,提交学术成果。他在1944年12月28日记:“撰第四期志稿报告书,以年度终了矣。”〔31〕1945年1月25日又记到:“再整理《志稿》,连同清校第三期本共五册,包裹由邮寄荩忱。并发荩忱、菊田两函,第四期《志稿》至是告一段落。至第三组送还所借各书。”〔32〕当年8月5日,王献唐再次向张继致函说明他撰写《国史金石志稿》的进展情况,“荩忱先生左右:前笺计达,承汇七月份米代金已收到,希释念。第五期金石志稿已完成,共五卷四册,另具总报告一册,与志稿挂号寄上,至希核转主任委员鉴阅为荷。”〔33〕
王献唐在撰写《国史金石志稿》时,遭遇着身体病痛的困扰,1945年8月5日致张继函中提到了这一状况,“弟目疾经打针服药之后迄今不愈,此病牵及神经,长此以往,将成痼疾,拟迟一、二日再赴宜宾诊治,或长期住院亦未可定。第四期志稿抄本俟稍迟再校寄。专此。敬请崇绥弟献唐顿首,八月五日。弟病大抵出于风湿,由川中气候所致,能回北方或能痊愈。现只早盼敌人无条件投降矣。”〔34〕由于王献唐健康状况和时间等原因,《国史金石志稿》最终没有完成。原本拟定金、石、骨玉、木陶四类,原计划加上总叙和小叙,也没有实现。1945年8月,他完成了“金文部”二十卷。石、骨玉、木陶三类未作。这部《国史金石志稿·金文部》在王献唐生前并未印行。直到21世纪初,王文耀先生主持整理书稿后,2004年由青岛出版社发行,共七册。尽管《国史金石志稿》属于未竟之作,但是它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国史金石志稿》所录各器,以民国出土及清代同类著作没有收录的器物为限,收录的器物有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它杂器包括铜镜、古鉨、佛像、古币等,为一般著录类书籍所罕见。
对于撰著的史作《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王献唐极为看重,他在1943年12月21日致函秦汉史名家陈直时,提到了自己相关的学术进展,“现为史馆撰《国史金石志》,又为庚款会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史志》杀青尚早,《通考》大体完成,约五十万言,五年心力,尽于是矣。”〔35〕在撰著期间,王献唐经受了爱子王裕华病逝的巨大打击,他本人也数度遭遇着身体病痛的折磨,面对这些精神和肉体的磨难,他以极大的毅力来克服,不断推进着研究。《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确实是“心力”之作。
王献唐在客居四川时期的学术作为延续着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确立的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先前金石学的成就成为了他构建《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这两部史著的学术理路。以两部史著奉献于民国学术界之外,王献唐还有《殷周礼制甄微》〔36〕之作,亦是关乎史学。这种学术志趣昭示出,在居川时期,史学研究成为他学术方向的主流。尽管其它的学术领域仍然涉猎不弃,但是就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已经难以与史学创获相匹敌了。
三、结 语
王献唐学术体系的构建中,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研究突显。史学研究的开端和早期成果是关于邾国彝器的考证之篇——《春秋邾分三国考》和《三邾疆邑图考》,这种考证关涉的是齐鲁地方历史的专题,相对狭小。在两文基础上,王献唐深入研究而作成了《炎黄氏族文化考》,其研究视域则延展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秉持着宏观思维与具体论证相结合的学术路径,他对音韵学的应用较之先前更为充分和丰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会通揭示了王献唐科学性、实证性的史学治学理念和实践。护书南下后,身居异乡,王献唐的史学创获,以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学术资助和参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为契机,倾力撰著而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和《国史金石志稿》两部巨著,此前他丰厚的金石学积淀成为着笔的基石,学术自觉性和使命意识是他不辍学术研究的逻辑支柱。
王献唐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史学构建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特色。什么是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何以可能?恐怕这个问题对于当代许多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它既简单又难以作答。王献唐的史学实践明示了这样的道理,跨学科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也不是对历史学之外学科浅尝辄止的作态,而是以学术的高度自觉性和学术的崇高使命感,长期累积,不辍研究,自然而然实现的结果。
注释:
〔1〕〔11〕〔13〕王献唐:《太平十全之室日记》,未刊稿。
〔2〕〔3〕〔6〕〔7〕〔8〕〔9〕王献唐遗书:《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16、3、11-12、21、41页。
〔4〕李勇慧:《王献唐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19页。
〔5〕宁镇疆:《由考古发现说王献唐先生〈春秋邾分三国考〉之贡献兼及小邾国史的相关问题》,《王献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10〕《王献唐先生来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七年刊,1934年,第10页。
〔12〕蒙文通:《古史甄微》,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55页。
〔14〕王国华:《王献唐传略》,文教资料简报,1983年第1期,第20页。
〔15〕〔16〕〔18〕〔19〕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39、363-364、18、93页。
〔17〕王献唐先生莅校演讲,《齐大旬刊》第5卷第8期,1934年,第56-57页。
〔20〕按王献唐日记所载,对邾国彝器的研究是以《邾国地名考》篇开始,接着又写《邾邑考》篇,两文都在《春秋邾分三国考》之前。不过,在当时《邾国地名考》和《邾邑考》是否为成熟文章,或者它们的研究成果已经由王献唐分解融合到《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之中。目前由于资料的缺失,难以把握真相了。鉴于此状,暂以《春秋邾分三国考》为王献唐史学的开山之作。
〔21〕王献唐:《双行精舍日记》,未刊稿。
〔22〕〔27〕〔28〕〔29〕〔30〕〔31〕〔32〕王献唐:《平乐印庐日记》,未刊稿。
〔23〕《王献唐氏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之著作》,《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1944年,第110-111页。
〔24〕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页。
〔25〕关于《国史金石志稿》一书的学科归属,有不同的认定。其中李勇慧师在其博士论文《王献唐研究》中把它界定为王献唐的金石学著作,杨现昌的博士论文《<国史金石志稿>校订》则将其定位于金石学、文字学的著作。从具体的内容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按照王献唐本人的出发点,是将《国史金石志稿》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此作也冠以“国史”两字。这样,从它的构建逻辑看,应当归属到史学中。由此也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对一部著作的定位不能采取是此非彼的认识。
〔26〕〔33〕〔34〕《王献唐编纂金石志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四109。
〔35〕周天游:《黄宾虹、王献唐、郭沫若诸家致陈直论学书九通》,《文献》1991年第3期,第20页。
〔36〕《殷周名制甄微》是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末撰写的一部重要史著。他在相关日记中有载,如1938年10月1日记:“续考稷祭,至晚饭后八时,得九页。社稷两祭至是完全考毕,共成百余页,约三万言。大似汉人说《尧典》,殊觉支蔓,需大加删改也。”栾调甫对此表示了极大关切。1939年2月26日,他在书函中言:“前书云,近作《殷周名制甄微》,案类释名,因名求制,已成二十万言,何其伟也。”不过,王献唐的《殷周礼制甄微》至今尚未出版,致使学界难知其详。